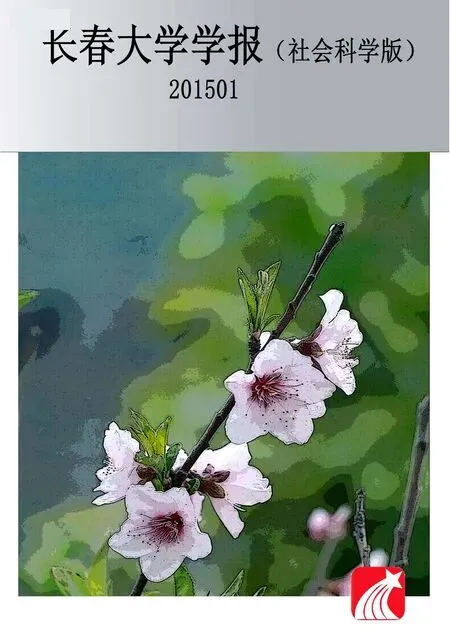泰戈爾與蘇軾詩歌宗教思想比較分析
泰戈爾與蘇軾詩歌宗教思想比較分析
盧迪
(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泰戈爾與蘇軾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極具影響力,兩人出生于不同國度、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生體驗造就了詩歌主題與宗教思想的不同。泰戈爾詩歌宗教思想崇尚“宗教是通向上帝與自由之路”的理念;蘇軾將“仁、善”看作人生最高的追求。通過對兩人詩歌宗教思想比較分析,揭示其宗教思想內在的沖突與統一,為未來詩歌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思想基礎。
關鍵詞:泰戈爾;蘇軾;宗教思想;比較分析
收稿日期:2014-06-12
基金項目:2012年度安徽省高等學校省級優秀青年人才
作者簡介:盧迪(1981-),女,安徽淮北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2文獻標志碼:A
泰戈爾和蘇軾不僅是詩人,在文學的平臺上更代表了兩個國家的文化潮流和宗教思想。中國和印度有著同樣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兩國的文學和詩歌作品都豐富了世界藝術的百花園。兩者差異也非常明顯,都擁有其獨特的文化魅力。泰戈爾詩歌中的宗教思想側重于“個體平等”和“梵我合一”;蘇軾詩歌中的宗教思想則強調“仁德慈悲”和“豁達自由”。兩種宗教思想的對比也是文化的對比,詩歌中宗教思想生長的土地最終要歸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化內涵。
1泰戈爾與蘇軾詩歌宗教思想解讀
泰戈爾是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詩人,以及社會活動家和民族主義者,也是亞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泰戈爾將畢生的心血和智慧都奉獻給了世界文學,在教育、藝術、宗教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圣雄”甘地稱贊泰戈爾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其詩歌作品最吸引人的魅力在于其宗教思想所傳達出的哲學精神,詩歌中宗教思想價值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作品本身[1]。印度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哲學與宗教的天堂,印度人民普遍信仰宗教。印度的宗教思想有伊斯蘭教、佛教、錫克教、婆羅門教、印度教等,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眾多印度宗教文化,養育了善良真誠的印度人民。泰戈爾在宗教思想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成長,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思想觀念。泰戈爾出生的年代正是印度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其言行、思想、詩歌都被打上了宗教思想的烙印。其宗教思想具有整體性、連續性和連貫性的特點,在他的詩歌中可以明顯地體會到其宗教思想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格論”,強調“自我”和“靈魂”。泰戈爾倡導“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擁有同等權利”的理念,詩人在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改善農民生活的運動中,用詩歌嚴厲地抨擊社會的舊習俗和野蠻行為;他在宗教觀上堅持“人與自然合一”“梵我合一”[2]。泰戈爾看來,自然與生命是無限循環的,而要在無限循環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就要遵守和諧統一的原則。詩人最著名的詩歌《吉檀迦利》就是獻給神的禮物,充分表現了詩人渴望“人神結合”的人生態度和追求。
蘇軾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和詩人,他才華橫溢、不拘泥形式,創作手法灑脫大氣,人生觀念瀟灑曠達。史書記載:“蘇軾生性放達,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3]在蘇軾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共留下了2700多首詩,其詩歌和文學作品所表達的思想無不與禪、佛相關聯,儒家思想是蘇軾創作的基礎。任何詩歌和思想的形成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和個人經歷都是分不開的。蘇軾的詩歌根植于北宋的社會土壤之中,建立在北宋文化環境和個人的生活歷程之上。他將內心的情感融入詩歌,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魅力。宋代掀起了一場“儒學復興”的浪潮,儒家思想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蘇軾在“儒學復興”的運動中,將儒家、道家、佛家三種思想進行了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宗教思想,為儒學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和視角。正是這場文化運動,使得蘇軾的宗教思想逐漸開始走向成熟。蘇軾的一生,與宗教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首先,其思想以“仁”為核心。他一生為官,造福一方百姓,是儒家思想“勤政為民”和佛家思想“慈悲為懷”的體現。面對起伏坎坷的人生經歷,能夠做到灑脫曠達,與宗教思想密不可分。其次,其宗教思想集三家之大成而融會貫通。蘇軾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充分吸收了佛、道兩家的思想精華,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宗教思想修養,他是真正的宗教思想的實踐者。
2泰戈爾與蘇軾詩歌宗教思想比較
2.1 情感表達
“愛”是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也是宗教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人詩歌都離不開情感與愛的表達,情愛、母愛與泛愛構成了情感的整個世界。通過對這三種情感的比較,體會兩種宗教思想的不同。
2.1.1 情愛表達
在印度宗教經典里有提及情愛的詩歌,基督教《圣經》里的《雅歌》,便是將男女的愛情比作人對于“神”的向往,耶穌也將自己比作生活中的新郎。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說:“泰戈爾是一個愛的詩人,愛情從他的心里、靈魂里泛溢出來,幻化了種種的式樣。”泰戈爾的《愛者之貽》第15首說“她村里的鄰居都說她黑,然而她在我的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雖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4],可謂情人眼里出西施,這便是愛情,泰戈爾以其直白簡練的語言訴說著內心的愛情。泰戈爾的愛情詩寫給女人,也寫給宗教里的“上帝”,是寫給“上帝”的贊美詩。
蘇軾與泰戈爾所表達的情愛觀有很大區別:泰戈爾將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戀”與弗洛伊德的“性愛理論”進行了完美統一,蘇軾通常在詩歌中為愛情營造一個純美的虛幻的意境。《江城子·鳳凰山下雨初晴》中的“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通過美好意境來營造氛圍。蘇軾的愛情詩風格也是多變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為紀念去世十年的妻子而寫,“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情感樸素真摯,備感沉痛。蘇軾的詩歌在男女情欲的表達上更為含蓄內斂,詩詞《雙荷葉·雙溪月》“紅心未偶,綠衣偷結。背風迎雨流珠滑。輕舟短棹先秋折”,他“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影響下,將宗教意識和情欲觀念融為一體,詩歌中情欲的表達也沾染了宗教色彩。
2.1.2 親情表達
在泰戈爾的作品中,母愛是最容易與讀者產生共鳴的,也是泰戈爾宗教思想與哲學思想的起點,擁有戰勝一切的力量。詩人以飽滿的激情贊美母愛、歌頌母愛,情感直接而熱烈。在《金色花》中,詩人寫道:“當你沐浴后,濕發披在兩肩,穿過金色花的林蔭,走到做禱告的小庭院時,你會嗅到這花的香氣,卻不知道這香氣是從我身上來的。”[5]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和諧生動的畫面,孩子化身為花香,時刻追隨著母親的腳步,只有在母親身邊才是最幸福的,用細膩的文字刻畫了一個溫婉善良的母親形象。“當母親看書時,我便要將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書頁上,正投在你所讀的地方,但是你會猜得出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影子么?”[6]泰戈爾以一個調皮的孩童的身份寫這首詩,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母親的依賴之情,這也是宗教思想中最干凈、最純凈的感情,孩子是上帝派來人間的天使,母親是孩子的守護神。
蘇軾詩歌中的親情主要體現在對兄弟的感情上,這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手足之情”,并開創了“夜雨對眠”的文化意象。蘇軾兄弟從小在一起讀書學習,其興趣愛好相似,擁有很多共同的話題。蘇軾的“夜雨對眠”詩將親情作為了人生的最終歸宿,不僅包含了情感對人生的慰藉,反映了詩人對時光逝去的焦慮感,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了儒家文化觀念中對血親人倫的重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中,全詩以“悲”為基調,營造了一種憂郁感傷的氛圍。“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這兩句詩充滿了與弟弟分別的痛苦,同時對弟弟厚重的牽掛之情也躍然紙上。最后四句“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在提醒弟弟也包括自己,不能忘記最初的志向。“夜雨”意象的運用也來源于我國傳統文化中“悲秋”的意識,這種悲秋的意識和儒家的“中和”思想是有所背離的,但是也體現了蘇軾獨立思考與人格的成熟。
2.1.3 泛愛表達
泰戈爾曾說過:“愛是我們周圍一切事物的最終目的。愛不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根植于萬物中的喜,是從梵中放射出來的純潔意識的白光。”[7]泰戈爾的泛愛論,包含了印度傳統宗教思想中的“泛神論”的思想,同時也吸收了西方國家的平等、自由、博愛的觀念。詩人的泛愛與祖國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詩選》:“我能生在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運氣去愛她,我是有福的。即使她不曾擁有王室的珍寶,但是她的愛的活財富對我就夠寶貴的了。”詩人對祖國的情感毫不掩飾地表現在詩歌里,這是一種大愛。泰戈爾的泛愛與宗教是緊密相連的:“你把你的愛給了我,充滿著世界因你的禮物。你的禮物聚于我身上,而我卻不認識,因為我的心中正睡著夜,可是我雖然沉埋在睡之谷里,我早就快活的渾身打顫,而且我知道因為你的大宇宙的寶貴的報告,你將從我這里接受一朵小小的愛的花,在早上我心醒來的時間。”其中對宗教和神的愛與贊美也是泰戈爾情感的一種表達,這是一種崇拜和感激之情。
在蘇軾當時生活的社會,泛愛主要體現在對人民和對國家兩方面。當時社會正處于恢復儒家傳統的道德倫理中,社會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和法規。蘇軾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將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之德”作為自身形式的準則,“圣人之德”是指儒家的“仁義孝悌忠信禮樂”,這是一種大愛,以“仁”為核心的思想追求在蘇軾的詩歌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蜂戀花·密州上元》:“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更無一點塵隨馬。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卻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8]。在正月十五燈月交相輝映的時候,滿城的仕女在游玩,忽然聽到吹簫的聲音,原來是農民在祈求來年的豐收,蘇軾心系百姓,直到深夜才離去。這首詩里體現出蘇軾對儒家思想的踐行,同時也體現著對祖國深沉的愛。蘇軾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儒學同樣推崇的是“國破家何在”。
2.2 生命訴求
生命是宗教永恒的主題,包含死亡、美學、人格等內容。由于受宗教思想影響,兩人詩歌中都滲透了宗教元素,他們在詩歌中都提到了生命意象。
印度的宗教思想強調生命與宇宙之間和諧統一的關系。泰戈爾說,“人的靈魂意識和宇宙根本就是統一的”,是生命和神的統一。其詩歌是對宗教思想中“梵我合一”思想的繼承[9]。在詩人看來,生命是宇宙的整體,是由“梵”主宰的。“梵”是宇宙中最高境界的自我,是人生命的最終追求。詩人懷著無限的敬意贊美“梵”,“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讓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腳下,接觸這個世界。像七月的濕云,帶著未落的雨點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讓我的全副心靈在你的門前俯伏”。詩中“神”在作者心中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抽象關系,而是成為了肉體的化身,無處不在,永恒地存在著,將無限的循環和有限的生命統一成了衍生萬物的本源。其次,詩人認為生命是有靈魂的。他在《什么是藝術》中講道:“在我身上還有另外一個人,不是肉體的,而是人格的人,人格的人有自己的好惡,并且想要找到某種東西以滿足自己愛的需求。”由此可見,詩人將所謂的人格看成了生命本質的一種體現,是人生命存在的本體。人格具有雙面性,一方面是自我的人生觀,另一方面是超我的價值觀。自我的人生觀是要受到社會規律的限制,也是這個世界上一切不平等、侵略、欺詐的根源。而超我的價值觀則是生命最高的境界,宗教中的“神”或者“梵”是可以超越自然和現實的力量,是人格的最高的追求。
蘇軾在看待生命和人生的問題上是以儒家思想為本的,他認為“天”的力量是無窮的,掌控著人間的一切,而皇權就是“天”的象征,因此自己的生命是歸于皇帝的。“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思想也是蘇軾所尊崇的。蘇軾認為君主的權利是“上天”給予的,正所謂“天命可畏”。蘇軾說:“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眾,必法祖宗。”他一直以儒家的“君權”思想作為束縛自己道德修養的準則,這種理論將皇權推向了合法性和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是兩人思想最大的不同。同時,蘇軾對生命本質的感受也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響。人生來是罪惡的,要在人世間洗凈身上的罪惡,以求得來生的幸福。《安國寺浴》:“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發臨修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床足。豈惟忘凈穢,兼以洗榮辱。默歸毋多談,此理觀要熟。”詩人企圖掃除塵世間的污染,同時擺脫身上功名利祿的束縛,以求得內心的安寧和清凈,這也是這首詩的主題。這種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佛學“大乘般若性空”思想境界的影響,是蘇軾在安國寺里“默坐”之后對生命本質的一種感悟。
在泰戈爾的詩歌中,有著對生命歸宿與生命本體之間關系的深深思考,泰戈爾將自己定義為“詩人的哲學家”,他在用詩歌展現獨特的“生命”美學。這種展現方式和東方所提倡的神韻美學是不盡相同的。他認為宇宙之間是和諧統一的,對立和矛盾會使世界的本質發生變化,生與死在本質上就是統一的,表面上的對立只是暫時的,生命的結束就是重生,這是一種輪回的生命美。這一理論和儒家的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都是對死亡的肯定,體現了生命的美。美學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一種升華的生命,宗教中的美學繼承了對平靜和諧的追求。泰戈爾的美學思想來源于宗教,對其既是一種繼承,又是一種發展和超越。他的詩歌“蓮花開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覺地在心魂飄蕩,我的花籃空著,花兒我也沒有去理睬。不時的,有一段的幽愁來襲擊我,我從夢中驚起,覺得南風里有一陣奇香的芳蹤”,借助美學意象表達了對生命美的喜悅。同時,詩人認為所有的情感都是可以轉化的,所有的罪惡都能夠在朝著善良和美的方向發展。泰戈爾渴望見到上帝,在詩歌中表達“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憐,但你永遠用堅決的拒絕來拯救我,這剛強的慈悲已經緊密地交織在我的生命里。有時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時候我急忙警覺尋找我的路向;但是你卻忍心地躲藏起來”,后期詩人明白這種欲望即是罪惡。尼采曾經說:“只有作為一種審美現象,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把人生看作一件藝術品,這就是哲學思想上的審美意識。
蘇軾的美學意識起源于儒家的宗教思想,經過道家和佛家的融合,實現了本質上的超越,其詩歌中美學意識的體現尤為明顯。他在《定風波》中寫道“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當再次回望人生時,無論幸福還是痛苦貌似都不見了。此時審美意象的最終歸宿為順其自然和人合于天,克服了生命中的局限性,將磨難、富貴、榮辱都當作了人生的一種經歷,這是對“人生如夢”思想的一種突破。悲劇只是人生中片面的一個體現,蘇軾在后期的詩歌中構建并完善了美學體系,將樂觀冷靜的生活態度與激情抗爭的悲劇精神進行了完美的結合。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所說“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正是對蘇軾后期思想的高度概括。
3結語
在近百年的時間長河里,泰戈爾和蘇軾的詩歌作品以其獨特的意蘊、優美的意境和深刻的思想內涵,熏陶了一批又一批熱愛文學的人。兩人的詩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中形成,卻擁有同樣的價值和力量。泰戈爾和蘇軾詩歌中所體現出的宗教思想都帶有時代和國家的烙印,是世界文學史上寶貴的財富,也是生命饋贈的禮物。
參考文獻:
[1]李金云.泰戈爾文學作品中的宗教體驗[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05.
[2]楊樺菱.泰戈爾愛的哲學和宗教思想在2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沖突與融合[D].重慶:重慶師范大學,2013.
[3]李明華. 蘇軾詩歌與佛禪關系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1.
[4]李金云.論泰戈爾思想和文學創作中的宗教元素[D].上海:復旦大學,2009.
[5]李騫.泰戈爾與冰心詩歌宗教精神的比較分析[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100-103.
[6]蘇蔓.泰戈爾《吉檀迦利》的宗教內涵[J].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4):30-32,36.
[7]張德福. 熔詩情與哲理于一爐:泰戈爾宗教詩歌評述[J]. 南亞研究季刊,1998(4):59-61.
[8]龍晦.從《前赤壁賦》談蘇軾的宗教思想[J].中華文化論壇,1998(1):72-79.
[9]武澄宇.淺議泰戈爾的宗教觀[J].青年文學家,2010(16):222.
責任編輯:柳克
AComparativeAnalysisonReligiousThoughtofthePoetrybyTagoreandSuShi
LUD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bei235000,China)
Abstract:TagoreandSuShihavegreatinfluenceintheworldhistoryofliterature.Theywerebornindifferentcountriesanddifferenttimes,andtheirdifferentlifeexperiencescreatedthedifferencesofthethemeandreligiousthought.ThereligiousthoughtofpoetrybyTagoreadvocatedthephilosophythat“religionisthetrailtowardsGodandfreedom”;SuShitook“benevolenceandkindness”asthehighestpursuitoflife.Throughacomparativeanalysisofpoemsbythetwoonreligiousthought,thispaperrevealstheconflictandunityofinherentreligiousideas,whichprovidesatheorysupportandideologicalfoundationforthefuturedevelopmentofpoetry.
Keywords:Tagore;SuShi;religiousthought;comparative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