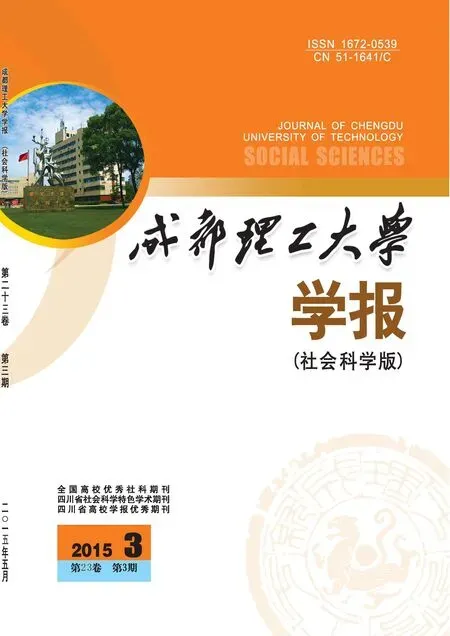人物性格與歷史真實——萊辛與伏爾泰關于此問題的論爭
徐 超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

人物性格與歷史真實——萊辛與伏爾泰關于此問題的論爭
徐超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伏爾泰認為真實是美的第一要素,戲劇情節要符合歷史的實際;萊辛則認為性格才是戲劇表現的重心,作品為了表現性格可以改編歷史。萊辛對人物性格的強調與他試圖要建立市民悲劇的主張聯系起來。伏爾泰的戲劇觀以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為基礎;萊辛對戲劇的認識則以古希臘特別是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理論為根基。在啟蒙大潮中,萊辛思想的古典色彩與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關鍵詞:萊辛;歷史真實;人物性格;教育意義;古典個性
18世紀中葉,德國戲劇在戈特舍德的帶領下師法法國。致力于建立民族戲劇的萊辛挺身而出,批判德國戲劇的法國化潮流,力圖建立起德國的市民悲劇。在《漢堡劇評》中,萊辛對德國戲劇的法國老師們——高乃依、達希埃、拉辛、伏爾泰等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甚至對比較欣賞的狄德羅也不無微詞(1)。在這些批判對象中,伏爾泰在萊辛筆下出現的頻率最高,也最為萊辛關注。伏爾泰是啟蒙時代法國戲劇的代表人物,他的戲劇美學被戈特舍德等人介紹到德國,給正在成長的德國戲劇以很大的影響。萊辛不贊同伏爾泰對歷史真實性的強調,也不贊成他對莎士比亞的評價,更不同意伏爾泰關于法國戲劇優越于古希臘戲劇的“進步”觀點。在萊辛與伏爾泰的分歧中,兩人關于人物性格是否要符合歷史真實的論爭尤為值得注意。
一、駁“歷史教科書的愛好者”(2)
伏爾泰畢生從事戲劇創作,先后寫下了50多部劇本,并有大量的戲劇評論問世。伏爾泰的戲劇觀念上承古典主義,重視情節的真實性。伏爾泰把真實性看作是美的基礎,認為:“真實是美的第一要素,其他種種不過是為真實錦上添花。真實是對一切語言和寫作體裁的試金石。”[1]283對伏爾泰來說,戲劇創作尤其應該重視真實性的要求,“戲劇藝術總是要求可信”,所以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所寫的一切都應該是真實的”。伏爾泰所謂的真實,不僅是“作家所表現的事物同人物的年齡、性格、處境吻合”,更應該與史實相吻合。不僅戲劇創作要如此,伏爾泰要求戲劇評判也應該堅持這個標準。所以,他要求評論者“首要的一條便是弄清作家的言論總的說來是否真實,按當時的具體場合是否真實,以及放在作家假托的人物口中是否真實”[1]283。
因此,真實與否便成為了伏爾泰戲劇創作和戲劇評論的首要準則,凡不符合這一原則的便都需要拿到歷史的審判臺前審視一番。所以,伏爾泰批評布瓦洛,說他的諷喻詩《曖昧》“有違此律”,“寫得很糟”;批評高乃依,說他“把西那寫成一個優柔寡斷的叛臣是違背史實的”,并總結說“高乃依在許多細節中違背了真實的規則”;批評托馬·高乃依(3),說他的劇本《艾塞克思》犯了許多歷史性錯誤;贊揚拉辛和莫里哀,因為“拉辛的作品中充滿真實感”,“莫里哀所寫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更有甚者,伏爾泰對莎士比亞也頗有微詞。在他看來,莎士比亞在歷史真實的問題上,也犯了許多錯誤,因為他的作品不夠真實,充塞著亞洲式的夸大[2]。
伏爾泰的戲劇觀念影響了正在成長的德國戲劇界。然而,萊辛對德國戲劇師法法國頗為不滿,尤其是對伏爾泰,處處語帶譏諷,目之為“歷史教科書的愛好者”。在萊辛看來,伏爾泰對高乃依兄弟的指責是有問題的:把歷史真實作為衡量戲劇作品高下的標準,是對一個劇作家的刁難,是對戲劇藝術的誤解,是在“詩學當中扮演歷史學家的角色”。萊辛認為二者有各自不同的本質規定性,有各自不同的評價標準;但伏爾泰卻混淆了二者,他試圖用歷史來研究、檢驗劇作家的作品,把戲劇作品置于歷史的審判臺前,來證明他所引用的每個日期、每個偶然提及的事件、每個值得懷疑的人物的真偽。萊辛以其才氣縱橫的幽默諷刺說:“伏爾泰先生想做一個深湛的歷史學家,這恰好是他的弱點。在《艾塞克思》這塊場地上,他搖搖擺擺地騎著自己這匹戰馬,猛烈地反復周旋。遺憾的是,他的這些活動只是毫無意義地揚起一片塵埃。”[3]119
與伏爾泰把歷史真實看作戲劇的美學基礎不同,萊辛反對用歷史真實性的要求來衡量戲劇作品。在他看來:“戲劇家畢竟不是歷史家;他不是講述人們相信從前發生過的事情,而是使之再現在我們的眼前;不拘泥于歷史的真實,而是以一種截然相反的、更高的意圖把它再現出來;歷史真實不是他的目的,只是達到他的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們,并通過迷惑來感動我們。”[3]60
概而言之,在詩與歷史真實的問題上,萊辛與伏爾泰存在著三點不同。其一,題材選擇的不同。伏爾泰主張詩的題材要符合歷史的真實;萊辛則認為,詩,尤其是天才之詩,不必拘泥于歷史真實。事實上,天才作家的作品經常而又嚴重地違背歷史事實,有時出于胸有成竹,有時出于驕傲自滿,有時則出于無意。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指責天才作家對歷史的無知,我們就是可笑的。因為至高無上的天才是出于特定的目的來組織“另外一個世界”的。其二,詩的目的不同。萊辛認為,題材的選擇應該服從詩的特定目的;伏爾泰忽視了詩的特定目的,一味地要求詩要符合歷史真實。而歷史事件是支離破碎的、充滿了偶然性。詩若不加選擇地原樣照搬歷史事件,就不能再現生活的本質與整全。所以,詩人,尤其是天才為了表達他自己的意圖,就需要把歷史世界的各部分加以改變、替換、縮小、擴大,由此造出一個自己的整體。只有在詩人編織的此一“整全”之中,我們才能看到生活的本質,才能更好地認識人、認識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的感情。其三,評判詩的標準不同。伏爾泰用歷史學家的標準來要求劇作家,用歷史的標準來檢驗文學作品;而萊辛則試圖把詩從伏爾泰的歷史束縛中解脫出來,讓詩獲得自己的獨立性。
所以,萊辛認為詩有其自身的規定性,即便是在處理歷史題材時也要照顧到詩和歷史本質上的不同。戲劇不是編成對話的歷史,它不是紀念大人物的一項使命,也不是知名人物的頌詞。戲劇情節可以選擇歷史事件,也可以根據需要改編這些歷史事件。戲劇要以自己獨立的美學標準來評論,而不能以歷史學家的要求來進行。
二、萊辛對人物性格的強調
盡管萊辛否認歷史真實是戲劇評判的標準,但他并不排斥劇作家從歷史中選擇題材。萊辛也認為,劇作家可以從歷史中選擇人物。但萊辛從歷史中選擇某一個人物的標準,不是這個人物做出了什么樣的事件,而是這個人物具有什么樣的性格。在萊辛看來,事件是偶然的,而性格則是本質的;作家之所以選擇一個事件,不是因為這個事件的“事實、時間和地點的環境”是真實的,而是因為“使事實付諸實踐的人物性格”是可取的。對于萊辛來說,性格遠比事件更為神圣,因為“事件只是性格的一種延續”。不僅如此,性格之所以比事件更重要,還在于戲劇作品的教育意義并非寓于單純的事件,而是寓于性格之中(4)。
萊辛判斷戲劇好壞的標準與伏爾泰明顯不同。伏爾泰以真實性為標準之一,而萊辛則摒棄真實性而以性格是否可取為標準。以萊辛的標準來衡量,性格是否可取主要在于性格是否富有教育意義。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也許并不具備感染他人的人格魅力。所以,萊辛主張戲劇創作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超越歷史真實,歷史無非是姓名匯編;作家可以任意處理事件,只要它們不與性格相矛盾,而性格則需要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當面臨沖突時,劇作家要選擇符合在作品中所要表現的道德目的的形式而不選擇歷史的形式;戲劇家根據教育性目的而選擇的性格與實際不符是一個可以諒解的缺點。人物的性格要比他們做過什么更重要:“一切與性格無關的東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顧。對于作家來說性格是神圣的,加強性格,鮮明地表現性格,是作家在表現人物特征的過程中最當著力用筆之處。”[3]122
萊辛認為,人物性格可以超越歷史真實。這一看法馬上就遭到了“伏爾泰們”的質疑:“盡管人們給予一個詩人或一個小說家以這么多的自由,難道也允許他運用這種自由來描寫最為眾所周知的性格嗎?如果說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事件,那么,能允許他把盧克萊齊婭描寫成淫蕩女人,把蘇格拉底描寫成好色之徒嗎?”[3]172其實,如果仔細考察萊辛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我們會發現萊辛并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雖然強調性格比歷史真實更重要,但他并不會贊同把盧克萊齊婭描寫成淫蕩女人,把蘇格拉底描寫成好色之徒。在萊辛看來,“如果對性格進行了仔細的觀察,那么事件,只要它們是性格的一種延續,便不可能有多少走樣”,“這種性格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引起這樣的事件,而且必然引起這樣的事件”,“性格決定了這個事件變成現實的形式和方式”[3]172-173。所以,萊辛并不認為人物性格可以無限制地偏離歷史真實。他認定的性格可以改編歷史,是在一個框架內進行的。這個框架就是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格。戲劇事件的改編也是在人物真實性格基礎上的改編。
萊辛不僅在理論論辯中強調性格的重要性,在他的戲劇作品中也可以見出這種傾向。讀過萊辛劇本的讀者一定會對萊辛筆下的“猶太人”的真誠與慷慨、“智者納坦”的寬容與智慧印象深刻[4]。與伏爾泰重視歷史形成鮮明對比,萊辛尤為重視人物性格的刻畫。那么,對萊辛而言,人物性格的刻畫到底有什么意義呢?
萊辛認為,性格是作家在作品中表現道德目的的最重要因素,而歷史真實也許會不符合這個目的。所以,作家的創作有時會面臨這樣一個沖突,是選擇符合歷史真實但不符合教育目的的事件還是選擇符合教育目的但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事件呢?萊辛主張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在他看來,根據內在可能性或者教育性自由而選擇的性格與歷史事實不相符,是可以諒解的。萊辛要求作家塑造的一切性格要具有目的性:“有目的的行動,使人類超過低級創造物;有目的的寫作,有目的的模仿,使天才區別于渺小的藝術家。后者只是為寫作而寫作,為模仿而模仿。”[3]177有目的的模仿是天才的、詩的,為模仿而模仿是渺小藝術家的,是歷史的。因為“他(天才)的主要人物的氣質和素養,包含著遠大的目的,即教導我們應該做什么或者允許做什么的目的;教導我們認識善和惡,文明和可笑的特殊標志的目的;向我們指出前者在其聯系和結局中是美的,是厄運中之幸運;后者則相反,是丑的,是幸運中之厄運的目的。”[3]178萊辛把莎士比亞視為這方面幾乎獨一無二的偉大天才。伏爾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在萊辛看來,恰恰暴露他缺乏戲劇表現的天賦。
為了達到教育的目的,對性格要有所選擇。不是所有的人物性格都有教育意義。在《漢堡劇評》的開篇,萊辛開宗明義談到:“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不管他選擇哪種形式,只要不單單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機智、學識而寫作,他總是著眼于他的時代,著眼于他國家的最光輝、最優秀的人,并且著力描寫為他們所喜歡,為他們所感動的事物。尤其是劇作家,倘若他著眼于貧民,也必須是為了照亮他們和改善他們,而絕不可加深他們的偏見和鄙俗思想。”[3]9所以,戲劇要摹仿最光輝、最優秀的人,描寫為他們所喜歡、感動的事物。這樣的性格和行動才是有教育意義的。萊辛批評馬蒙泰爾,因為他塑造了蘇萊曼二世的形象。在萊辛看來,這種人物不應該成為藝術摹仿的對象。因為他可憐而又可鄙,缺乏教育性。相反,我們觀察萊辛筆下的人物,猶太旅客、薩拉小姐、明娜小姐、智者納坦等則大多是道德的楷模。
早在青年時代,萊辛就已經表現出對戲劇的目的性的重視。1756年,20多歲的萊辛與友人尼克萊就戲劇的功能問題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尼克萊反對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凈化說,并把當下德國悲劇水平的低劣歸罪于亞氏,認為悲劇的目的不是教化道德而是激起情感。萊辛則認為尼克萊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亞里士多德。萊辛認可尼克萊的悲劇應激起情感的主張,但并不認為這是悲劇的最終目的。他認為悲劇的最終目的是使觀眾能夠更加善良、更有道德,而激起情感只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而已(5)。不過,此時還年輕的萊辛把悲劇應該激起的情感僅限定于憐憫。11年后,萊辛在《漢堡劇評》中修正了當初的看法。他在悲劇應激起的情感里增加了恐懼,但仍堅持認為戲劇應通過激發情感而教人向善。
萊辛試圖通過模仿最優秀的人來照亮和改善德國的市民,并以此來建立屬于德國的市民悲劇。事實上,他的這一嘗試并不成功。他所在的劇團很快就倒閉了,而且他的戲劇主張后世也頗多爭論。朱光潛認為,市民悲劇的主張消解了崇高感,而沒有崇高感的悲劇就不可能成其為悲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指責說:“狄德羅和萊辛雖然大力主張所謂‘市民悲劇’,但這種悲劇卻很少取得高度成功。這是從鄧南遮輕蔑地稱為‘民主的灰色濁流’中冒出來的氣泡之一。隨著‘市民悲劇’的興起,真正的悲劇就從舞臺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只是小說、問題劇和電影。”[5]88朱光潛對市民悲劇的認識雖切中肯綮,卻也不夠準確。事實上,真正的悲劇并未從舞臺消失,萊辛的劇作尤其是《智者納坦》在戲劇舞臺上常演常新。萊辛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其戲劇主張和成就上,更體現在他的觀念和個性上。
三、萊辛的“古典個性”(6)
伏爾泰秉持理性主義精神,認為文學創作應該以真實為基礎。萊辛年輕時追慕伏爾泰,后來卻與他漸行漸遠,以至在《漢堡劇評》中把他作為主要的批駁對象。萊辛反對伏爾泰的最有力武器是亞里士多德詩學。對萊辛而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衡量戲劇高下的準繩,是判斷戲劇理論是否偏離正道的依據。
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因為詩表現的是帶有普遍性的事情,而歷史描寫的是具體事件。詩人之所以描寫了過去發生的事情,不是因為它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而是因為這些事情是可能會發生的。這種內在的可能性才是戲劇情節選擇的根據(7)。萊辛繼承了亞氏對詩更富哲學性的認識,并以之作為反駁伏爾泰這位“歷史教科書的愛好者”的依據。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通過引起憐憫和恐懼之情而使這種情感得到“卡塔西斯”(katharsis,宣泄、凈化)。萊辛在《漢堡劇評》中對亞氏的悲劇觀念作了詳細的解釋。他“用恐懼的對象來說明憐憫的對象,用憐憫的對象來說明恐懼的對象”,認為恐懼是憐憫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悲劇正是通過激起恐懼和憐憫之情而使這些情感得到凈化。萊辛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德性的適度觀念來解釋凈化,認為凈化就是“既要凈化根本不懼怕任何厄運的人的心靈,也要凈化對任何厄運都感到恐懼的人的心靈”,“既要凈化過多地感覺到憐憫的人的心靈,也要凈化極少感覺到憐憫的人的心靈”(8)。萊辛認為亞氏的規則,全都立足于產生最高的悲劇效果,即使人向善。萊辛在亞氏詩學基礎上,明確地提出戲劇的目的在于教化作用。在這一點上,萊辛在《關于悲劇的通信》時期和《漢堡劇評》時期的看法是一致的。青年萊辛就已經認定“悲劇激起我們的同情心,目的就是使我們能夠變得更加善良、更有道德”,“同情卻直接教人向善,無須我們自己參與其事;它既教化有頭腦的人,也教化傻瓜”[6]20,38;在漢堡國家劇院擔任顧問時,萊辛再次重申當年的觀點,認為戲劇是為了“照亮他們(平民)和改善他們”、“教導我們認識善和惡”[3]9,178。所以,在與其他戲劇理論家出現分歧時,萊辛所做的經常是“求教于古人”,用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等古典詩人來為自己及時代引路。伏爾泰顯然不會贊同萊辛的這一主張,因為他是一個“持進步見解的新的劇作家”[3]59。伏爾泰認為他的民族的悲劇作家在許多作品中遠遠超過了古代希臘人,“希臘人可以向法國人學習熟練的表演,學習場次安排的偉大藝術”,“學習情敵們相互之間怎樣進行機智的對話,作家怎樣使大量崇高的、光輝的思想放射出光芒,學習……”[3]56-57但在萊辛看來,伏爾泰自詡的這些進步戲劇的美妙之處恰恰是為古人的樸素特點所不齒的。伏爾泰主張進步的戲劇觀,萊辛則師法古人;伏爾泰張揚理性,萊辛則注重德性。萊辛至此已走向了他當年的老師的對立面。
在對莎士比亞戲劇的看法上,兩人再次表現出了這種差異。伏爾泰批評莎士比亞的戲劇不真實,也不能理解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鬼魂的意義。伏爾泰用“冷靜的理性”在《塞密拉米斯》中創作了一個鬼魂形象。但在萊辛看來,伏爾泰的“鬼魂”只是一部藝術機器,莎士比亞的“鬼魂”則是一個真正行動的人物。兩相比較,優劣立判。兩者相差這么大的原因就在于:伏爾泰這個“文明開化”的理性主義者并不是真的相信鬼魂,而莎士比亞是把鬼魂當做自然的存在的。所以,在萊辛看來,莎士比亞才是古希臘悲劇的真正繼承者。
萊辛對戲劇規則的認識不僅不同于伏爾泰,也不同于他的朋友尼克萊和門德爾松,甚至亦不同于同樣標榜以亞里士多德為師的高乃依、拉辛等法國的古典主義作家們。盡管法國的古典主義作家們也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為指導,但在萊辛看來,他們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卻是成問題的,原因在于他們把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縮減成了幾條死板的教條,并把這些教條當成戲劇完美性的唯一源泉。而正確理解亞里士多德需要“以亞里士多德的方式來理解亞里士多德”,需要把他的詩學理論結合他的修辭學說和倫理學說來理解。
不僅萊辛的詩學理論以亞里士多德為基礎,甚至他的表達方式也取法于亞里士多德。萊辛認為,“亞里士多德慣于在他的書中挑起爭論。他這樣做絕不是輕率的,無目標的,而是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思想深邃的亞里士多德幾乎一直是采用這個方法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首先尋找到一位能夠與之辯論的人,才能逐步達到問題的實質”(9)。在萊辛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把這一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關于悲劇的通信》與尼克萊和門德爾松展開論爭,《拉奧孔》與溫克爾曼和斯彭斯等人論戰,《漢堡劇評》以伏爾泰、高乃依、拉辛等人為論戰對象。在與這些論敵們的論戰中,萊辛無一不是以亞里士多德為理論根基。所以在此意義上,托馬斯·曼把萊辛視為一個“古典作家”,一個“神話類型的人物”。這樣的人在民族文化崛起和繁榮的背景下,負有“收拾、清理自己精神的居室,規定秩序,加強理論和法則,建立概念的基礎,確定差別之清晰分野”的職責。因此,這種類型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有一個特點:愛論戰的傾向(10)。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漢娜·阿倫特把萊辛視為“黑暗時代的人性”,褒獎他主動地向世界言說,與不同的觀念爭論,“把他人當做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兄弟”[7]。
伏爾泰是啟蒙思想的領軍人物,他對歷史真實的強調是啟蒙思想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反映。萊辛主張以古人為師,與伏爾泰的進步的文學觀形成鮮明對照。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萊辛與伏爾泰所代表的啟蒙精神拉開了距離。所以有論者認為,萊辛“審慎地與啟蒙運動保持著蘇格拉底式的距離”(11);更有論者認為,萊辛是“第一個要求對啟蒙進行啟蒙的人”(12)。在啟蒙現代性語境下,萊辛與啟蒙的距離提醒讀者反思啟蒙理性的自大。萊辛對啟蒙進行啟蒙的方式是強調古代的觀念,強調文學的表達與人類情感及德性之間的密切聯系。
注釋:
(1)值得注意的是,萊辛在《漢堡劇評》中幾乎沒有涉及到對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理論的奠基人布瓦洛及其《詩的藝術》的評論;也沒有涉及到盧梭,盡管他關注盧梭的戲劇理論。
(2)在第十五篇劇評里,萊辛在討論伏爾泰的劇作《扎伊爾》時給他的封號。參見[德]萊辛:《漢堡劇評》,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3)托馬·高乃依為比埃爾·高乃依的弟弟,也是一位戲劇作家。
(4)參見《漢堡劇評》第33篇。
(5)參見《關于悲劇的通信》,1756年8月31日尼克萊來信和11月13日萊辛復信。
(6)這一提法出自[德]托馬斯·曼:《論萊辛——在普魯士藝術科學院萊辛紀念會上的講話》。見[德]托馬斯·曼:《歌德與托爾斯泰》,朱雁冰,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7)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第9章,見《羅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8)《漢堡劇評》第79篇,第396頁。
(9)參見《漢堡劇評》第70篇。
(10)參見托馬斯·曼:《論萊辛——在普魯士藝術科學院萊辛紀念會上的講話》。見[德]托馬斯·曼:《歌德與托爾斯泰》,朱雁冰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11)劉小楓:“萊辛注疏集”出版說明。見[德]萊辛:《歷史與啟示》,朱雁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
(12)[德]漢斯·昆:《啟蒙進程中的宗教》。見[德]漢斯·昆、[德]瓦爾特延斯:《詩與宗教》,李永平,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93頁。
參考文獻:
[1][法]伏爾泰.伏爾泰論文藝[M].丁世中,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伏爾泰.哲學通信[M].高達觀,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德]萊辛.漢堡劇評[M].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4][德]萊辛.萊辛劇作七種[M].李健鳴,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5]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張隆溪,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88.
[6][德]萊辛.關于悲劇的通信[M].朱雁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7][美]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M].王凌云,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編輯:黃航

The Argument on Character and Historical
Reality betuteen Lessing and Voltaire
XU Cha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Voltaire regarded the truthfulness to history as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a drama, and the plot of the drama must conform with historical reality, while Lessing regarded the character as the core of a drama, and the history could be adapted for revealing the character. Lessing’s stress on the character connected with his advocation for the civil tragedy. Voltaire’s conception of the drama was based on the rationalism in the Enlightenment era, whereas Lessing’ conception of the drama was based on the poetics of ancient Greek, especially on Aristotle’s poetics. Lessing maintained the classic elements in his thought and kept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in his reflection upon it.
Key words:Lessing; historical reality; character; educational meaning; classical personality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5)03-0047-05
作者簡介:徐超(1981- ),男,河南淮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詩學研究。E-mail:xuchao66888@163.com
收稿日期:2014-11-15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5.03.010 10.3969/j.issn.1672-0539.2015.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