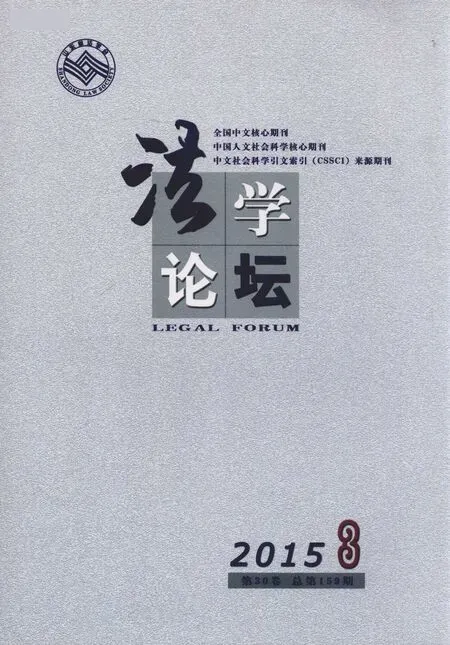減輕處罰的功能定位與立法模式探析
劉 軍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北京100088)
我國《刑法》中的減輕處罰①由于我國《刑法》沒有加重處罰量刑情節,因此本文主要探討減輕處罰相關問題,但其實二者內在的法理是一致的,而且如果將來考慮加重處罰的立法模式,則可以有效改變我國法定刑偏重的印象。量刑情節存在功能不清、定位不準、角色尷尬等先天缺陷,是直接導致我國量刑過程思維混亂、層次缺乏、難以規范的幕后真兇。如果要進行卓有成效的量刑規范化改革,必須正確界定減輕處罰量刑情節的功能,厘清與其他量刑情節尤其是從輕、從重量刑情節的關系,對減輕處罰量刑原則的規定進行修正,徹底變革當前量刑情節的立法模式,從源頭處思所以、在頂層上做設計,如此才能有效化解司法實踐的操作難題。
一、減輕處罰量刑情節的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刑法》除了第63條(減輕處罰原則)之外共有20個條文規定了減輕處罰,其中,總則條文15個,分則條文5個。《刑法》總則條文中,除了第10條“對外國刑事判決的消極承認”可以認為是刑罰的適用條件之外,其余的均為法定的量刑情節。其中:(1)減輕與免除處罰連用的情形有4個條文,包括防衛過當(第20條)、避險過當(第21條)、脅從犯(第28條)、重大立功(第68條)②《刑法修正案》(八)第9條新近作了修正,“刪去《刑法》第68條第二款”,即“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被刪除。的相關規定,前三個條文為“應當型”的二功能量刑情節,最后一個為“可以型”的二功能量刑情節;(2)減輕與從輕處罰連用的情形有7個條文,包括未成年人(第17條)、已滿75周歲老年人(第17條之一)、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第18條)、犯罪未遂(第23條)、教唆犯(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第29條)、自首(第67條)、立功(第68條)。除了未成年人和已滿75周歲的人過失犯罪的情形為“應當型”的量刑情節之外,其余的均為“可以型”的量刑情節;(3)從輕、減輕、免除處罰連用的三功能量刑情節共有3個,包括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第19條)、犯罪預備(第22條)、從犯(第27條)。前兩者為“可以型”的量刑情節,從犯為“應當型”的量刑情節;(4)單獨規定減輕處罰的條文僅有2個,即第24條犯罪中止“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和第67條第3款關于坦白的規定,即“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相比較《刑法》總則關于減輕處罰規定的復雜情形,分則的規定模式相對較為簡單,除了第276條之一“惡意拖欠勞動報酬罪”之外,其余四個條文均為貪污賄賂型犯罪,包括第164條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383條關于貪污賄賂罪的處罰規定、第390條關于行賄罪的處罰規定、第392條的“介紹賄賂罪”,而且均為“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從以上的列舉中可以看出,我國減輕處罰立法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與我國《刑法》中的從寬量刑情節類似,減輕處罰大多數為多功能量刑情節,①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加重量刑情節,從重量刑情節均為單功能量刑情節,從寬量刑情節大多數為多功能情節。單功能的從輕量刑情節只有《刑法》第67條第3款關于坦白的相關規定,即“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單功能的免除處罰情節有3個,包括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第24條第2款),自首“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第67條第1款),“非法種植罌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獲前自動鏟除的,可以免除處罰”(第351條第3款);再加上減輕處罰量刑情節2個,單功能的從寬量刑情節共計5個。易言之,我國的從寬量刑情節大多數為多功能情節,屬于功能選擇性情節,僅僅認定與量刑情節有關的事實還遠遠不足,還不能就此確定對量刑輕重的作用大小,還需要法官依據《刑法》的規定在數個功能情節中進行選擇才能最終確定究竟是減輕或是免除,或者僅僅是從輕處罰;(2)量刑情節又分為“應當型”(命令型)與“可以型”(授權型),因為從重量刑情節都是單功能情節,所以問題不大,但是,從寬量刑情節大多數為多功能量刑情節,再加上“應當”與“可以”的模糊指示,更讓人難以確切地把握,而且法官是如何思維的并無法從外部進行觀察,也談不上監督;(3)競合的處理方法不明,不但是同類的量刑情節競合的處理方法不明(如多個從輕量刑情節或者多個減輕量刑情節如何適用刑罰的問題),不同種類的量刑情節的競合更是存在很大的問題(如減輕處罰與從輕、從重處罰的競合,在適用了減輕處罰之后,是否還允許考慮其他的從輕、從重情節)。易言之,除了首先需要在多功能情節中進行甄別以決定是否適用減輕處罰之外,還需要厘清與其他從輕、從重量刑情節的關系,如果仍然需要考慮其他的從輕量刑情節,則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大量刑不均衡的程度;對于從重量刑情節更是尷尬,“從重”已經沒有意義,因為已經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了;如果不允許考慮其他的從輕、從重量刑情節,則會導致量刑情節閑置,量刑結果難以反映案件的全貌,更容易引起當事人以及社會上一般人對于量刑公正與否的疑忌;如此,惟一可選擇的解決辦法就是,在事實甄別并依法確定了所有的量刑情節(包括減輕、從輕、從重量刑情節)之后,再全面地進行權衡,最后決定是否適用減輕處罰。但是如此以來,減輕處罰因受制于其他的量刑情節也就失去了其功能與作用,并與立法原意嚴重不符。
與其他國家的刑法相比較,我國《刑法》規定的法定量刑情節頗具“特色”。除了個別國家刑法典規定了減輕與免除處罰選擇適用的條款之外,例如《德國刑法典》關于對象不能、手段不能的未遂犯(第23條第3款),日本《刑法》關于防衛過當(第36條第2款)、避險過當(第37條第1款)、未遂犯(第43條)等為數不多的幾個情節之外,基本上都是只規定為“減輕”或者“加重”情節,而且是單功能情節,不會出現“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連用的三功能量刑情節,如俄羅斯《刑法》第61條“減輕刑罰的情節”、第63條“加重刑罰的情節”等都是單功能情節;②有學者認為,俄羅斯《刑法》中規定的減輕或加重處罰,其實相當于我國《刑法》中的從輕和從重處罰。參見趙微:《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1頁。另外,刑法典對減輕、加重的方法、順序、比例或者幅度均有明確的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49條之“特別之法定減刑理由”,第50條“減刑理由的競合”等規定。而我國《刑法》中的量刑情節卻出現了許多的特別之處,包括多功能情節的設置、應當與可以的區別、從輕與減輕的區分、法定減輕與酌定減輕的不同規定等等,彈性如此之大、選擇性如此之多、關系錯綜復雜令人咋舌,已經遠遠超出了立法與司法的傳統關系。立法的過度授權無疑會不當擴大法官的選擇可能性,使得本來可以輕易確定的量刑情節,變得指向模糊、層次不清、難以操作,在司法實踐中出現量刑結果差異較大、量刑不均衡的現象。我國《刑法》之所以采取如此這般的立法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是擔心《刑法》在復雜的社會現實面前“不堪勝用”,擔心出現立法事先考慮不周的事情難以應對,擔心罪刑的匹配難以滿足刑事政策的需要,從而延續“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窄”的立法思想,以備“不時之需”。所以,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主張,取消“可以型”的量刑情節,①參見陳航:《試論“可以”情節的取消——以未遂犯的處罰原則為例》,載《現代法學》1995年第4期。取消多功能量刑情節。②參見陳航:《取消多幅度情節立法的思考——兼論“從重”、“從輕”、“加重”及“免除處罰”規定的重構》,載《蘭州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當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國《刑法》關于減輕處罰原則的規定以及理論上對減輕處罰的不同理解,加之量刑思維上沒有明確區分處斷刑與宣告刑的界限,沒有法定刑的修正與狹義的量刑情節的觀念,也是導致我國當前立法模式形成的個中緣由。因此,我國減輕處罰的立法模式究竟如何,還需要在探討減輕處罰適用原則之后才能有所結論。
二、減輕處罰適用原則的司法困境
我國《刑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大多數為多功能量刑情節,而《刑法》第63條第1款又特別規定“減輕處罰原則”為“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通說認為應當分別適用《刑法》規定的不同條款或者相應的量刑幅度,即“量刑幅度說”。此種學說與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別無二致,即“在法定刑以下減輕處罰,應是指低于法定刑幅度中的最低刑處罰”,從而否定了“刑種說”,因為“在同一法定刑幅度中適用較輕的刑種或者較低的刑期,是‘從輕處罰’,不是‘減輕處罰’。”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如何理解和掌握“在法定刑以下減輕”處罰問題的電話答復》(1990年4月27日)。“量刑幅度說”相比較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請示中所傾向采取的“刑種說”減輕的幅度更大,更加有利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為犯罪人架起一座復歸的“金橋”,也更加符合從輕與減輕處罰的“邏輯關系”,但是卻導致《刑法》第63條的適用過于僵硬,司法實踐中難免出現量刑不均衡的現象。例如,共同犯罪中具有減輕處罰情節的共同犯罪人刑罰減輕幅度過大的問題一直難以解決。④參見陳忠:《對減輕處罰的理解和法律適用》,載《江蘇法制報》2005年4月19日。同時,堅持該學說還存在其他的許多司法適用難題。例如,當管制為法定最低刑時如何適用的問題,⑤參見張波:《減輕處罰之“法定刑”含義新探》,載《法治論叢》2003年第6期;亦可參見肖松平:《減輕處罰適用中的一個難題及其解決——兼談〈刑法〉第37條的理解和運用》,載《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兼具兩個以上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時如何適用的問題,⑥參見周連勇:《自首又立功能否兩次減輕處罰》,載《江蘇法制報》2006年7月12日。等等;另外,“量刑幅度說”是否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因為刑事責任的考證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僅僅因為一個量刑情節便大幅度地跨越刑期甚至數個刑種予以減輕,不僅淘汰掉了諸多的需要考慮的因素,如影響違法性大小和有責性大小的細節性因素,即使僅僅從形式上來看,也有過于簡化之嫌。如此,司法實踐的難題便是:一方面,由于減輕處罰的幅度過大,常會導致量刑的不均衡;另一方面,為防止不均衡現象的出現,法官又憚于適用減輕處罰,想盡千方百計予以回避,這些都是量刑情節適用的不規范現象。
為了解決減輕處罰在司法適用中存在的各種難題,我國刑法理論作了多頭探索,試圖通過刑法解釋而不是立法修正的方式對《刑法》第63條在司法實踐中的僵化表現進行化解。有學者提出“刑格說”,即應當減到下一量刑格,“減輕處罰的范圍是相應法定刑與其下一格之間的幅度”;⑦王恩海:《“減輕處罰”含義新探——對最高人民法院〈答復〉的質疑》,載《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4期。有學者則建議將法定刑理解為法定最高刑,認為減輕處罰是一個法律上的方法問題,減輕處罰應當包括刑種的減輕和刑期的減輕;⑧參見張波:《減輕處罰的含義新探》,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有學者則提出“二次量刑說”,認為第一次量刑僅是概括性的刑罰裁量,即對刑種或法定刑期幅度的選擇,裁量的結果即是《刑法》第63條第1款所指的“法定刑”;⑨參見李翔:《論我國刑法中的減輕處罰——兼評修正后〈刑法〉第63條第1款》,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9期。有學者則提出將《刑法》第63條第1款立法修改為一個授權性條款,“刑罰裁量中,司法人員被立法賦予一定的在法定刑以下處刑的權力,但必須受到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限制。如果是酌定減輕情節,則必須受到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程序性的限制。”①黃京平、蔣熙輝:《減輕處罰情節的適用歸責探究》,載《人民法院報》2004年6月7日。以上學術觀點②早期的學術觀點還包括“罪名說”,即法定刑是某個罪名的整個量刑幅度,不論某罪有幾個量刑幅度,減輕處罰都是指在整個法定刑的最低限度以下判處刑罰。參見常鐵威:《“減輕處罰”的理論與實踐》,載《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此種觀點更容易引起量刑的不均衡,并無多少支持者。在立法修正之時均未得到采納,2011年5月25日頒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仍然堅持了“量刑幅度說”,將《刑法》第63條第1款修正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法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③從修改內容上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八)第5條實質上是對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司法解釋的立法確認。在此基礎上,將司法實踐中容易導致刑罰裁量不均衡難題的第68條第2款(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情節)刪除了之,從而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的情節不再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轉化為自首和重大立功兩個量刑情節,均為“可以型”量刑情節。這一修正,從技術手段上來講沒有問題,雖然說所謂的“可以”其實也是“一般應當”的表達,但我國刑法理論通說還是認為所謂的“可以”其實是“可以考慮也可以不考慮”的字面含義,④參見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頁。那么,“應當型”的三功能情節和“可以型”的三功能情節,前者如《刑法》第27條從犯,后者如第19條又聾又啞或者盲人犯罪,究竟有什么區別呢?只能說是,如果是“應當型”的三功能情節,在量刑時至少要“從輕”,而且只要是“從輕”就算是符合了《刑法》的規定,當然也有可能免除處罰;而“可以型”的三功能情節,雖然按照《刑法》的規定此種情形甚至可以免除處罰,但是卻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予考慮,即完全不予從輕也是符合《刑法》規定的,因為無論考慮與否都是“可以”的。但是,刪除第68條第2款規定的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情節,將不利于鼓勵犯罪嫌疑人揭發檢舉他人重大犯罪行為、幫助破獲重大案件等;更為重要的是,真若如此解決減輕處罰所遇到的司法實踐難題,則實在是“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
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的多種方案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減輕處罰適用原則的司法困境。以最新的規范性文件為例,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簡稱《意見(試行)》)和《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試行,這兩個規范性文件對于全國量刑規范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在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⑤參見劉軍:《量刑如何實現均衡——以量刑規范性文件為分析樣本》,載《法學》2011年第8期。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簡稱《意見》),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施行,但是基本內容與《意見(試行)》變化不大,相關問題依然存在;對于量刑情節的部分,由于《意見》對量刑情節的功能沒有嚴格區分(如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沒有區分多功能量刑情節的優先或排序,沒有明確區分應當情節與可以情節,沒有區分法定情節與酌定情節而是予以同等對待,具有多種量刑情節的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減”的方法確定全部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后再對基準刑進行調節,結果必然會導致法官機械地進行數字換算,量刑行為程式化痕跡濃重。⑥參見劉軍:《從法定刑到宣告刑之橋梁的構建——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為藍本對量刑基準的解讀》,載《當代法學》2011年第3期。當然,《意見》區分總則性的量刑情節與其他情節并分別進行調節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意見(試行)》頒布后,各地省高院均出臺了《實施細則》。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年11月19日發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于2010年12月1日施行;2014年9月25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又頒布了《〈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在量刑情節中區分了罪中量刑情節和罪前、罪后量刑情節,在量刑方法中分別適用連乘公式和同向相加、逆向相減公式。⑦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在附則中規定,“多個罪中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連乘公式’:A×(1±α1)×(1±α2)×(1±α3)…【注:A代表基準刑,α代表量刑情節調節比例,±根據量刑情節是從嚴情節還是從寬情節確定】”;“多個罪前、罪后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同向相加、逆向相減公式’:A×(1±α1±α2±α3)…【注:A代表基準刑或罪中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后的刑期,α代表量刑情節調節比例,±根據量刑情節是從嚴情節還是從寬情節確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后來頒布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在“量刑的基本方法”第2條“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方法”第(2)項中仍然保留了“連乘”和“同向相加、逆向相減”的不同計算方法,但是在附則中卻沒有繼續保留計算公式,原因不明。可以如此理解,即罪中量刑情節不僅反映刑事責任的大小(包括違法性大小和有責性大小),同時也能反映其改造可能性和特殊預防必要性的大小,而罪前、罪后量刑情節反映的主要是后者,因此應當區別對待。易言之,在量刑過程中應當明確區分關于該當或者危險的量刑情節,并明確二者對量刑的不同影響。①參見劉軍:《該當與危險:新型刑罰目的對量刑的影響》,載《中國法學》2014年第2期。這兩個公式相比較而言,在調節比例相同的情況下,適用連乘公式調節的幅度更大一些。此可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大創新。
量刑指導意見以及實施細則不但規定了量刑原則、量刑步驟和方法,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比例,而且給出了15個常見罪名的量刑起點、增加的刑罰量等非常細致的規定,仿佛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但其實這仍然是一筆不小的“糊涂賬”。且不論基準刑的計算(即在量刑起點以及在此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究竟從何而來,亦不論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比例為何如此這般,單單就《意見》未能區分量刑情節的功能而言,就已經是南轅而北轍了。以“從犯”量刑情節為例,在刑法典中,從犯屬于應當型的三功能量刑情節,但是,《意見》在“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中規定,“對于從犯,應當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實施犯罪實行行為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減少基準刑的20% -50%;犯罪較輕的,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這一規定可作如此解讀,即無需事先確定從犯這一量刑情節在該案件中究竟是從輕還是減輕處罰,而是直接以估算的比例(減少基準刑的20%—100%)調節基準刑即可。如果調節的結果是在法定刑以下,那么便是“減輕”處罰,反之,則就是“從輕”處罰,如果達到了減少基準刑的100%就只能是“免除”處罰了。很明顯,如此的“可操作性”其實是倒置了因果,而且直接違背了《刑法》的規定。因為根據我國《刑法》第63條第1款規定,“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才“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所以,首先應當是判斷該量刑情節是否是“減輕”處罰情節,而不是先“估算”調節基準刑的比例。
不過,《意見》所設計的量刑方法和步驟也有自身的優勢,即如果存在多個量刑情節,尤其是兼有減輕和從輕、從重量刑情節的時候,可以全面地平衡多個量刑情節對于量刑結果的作用,而不會因為首先適用減輕量刑情節,或者個別從輕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過大,而導致其他的從輕、從重量刑情節被忽略。僅就此而言,《意見》的探索也非常值得稱道。那么,域外國家或者地區是如何處理這一量刑難題的呢?
三、減輕處罰量刑過程的域外比較
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刑法一般只規定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從輕處罰則授權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自由裁量,而且減輕處罰只是對法定刑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而不是直接適用另外一個業已規定的法定刑幅度,與我國規定的“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有較大差異。以《德國刑法典》為例,對于法定減輕情節,第49條第1款規定了具體的減輕方法和幅度,包括以下三種情形:一是,終身自由刑由3年以上自由刑代替,這樣同時限定了上限和下限,因為第38條第2款規定有期自由刑最高為15年;二是,有期自由刑上限采“比例制”,可判處的刑期可達最高刑的3/4刑期,下限采“直減制”,直接規定可以減輕的下限,最低自由刑為10年或5年的,減為2年;最低自由刑為3年或2年的,減為6個月;最低自由刑為1年的,減為3個月。其他情況依法定最低刑為準;三是,罰金刑上限亦采“比例制”,即日額金3/4為最高額,下限不低于刑法關于日額金的規定,即最低5單位日額金。②參見《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如此細致的規定,使得“相關構成要件的刑罰范圍以完全確定的方式被降低,而且——只要有上下限——既可以降低量刑范圍上限,也可以降低量刑范圍的下限。”③[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2-1073頁。
下面以德國波恩州法院就一起故意殺人案所制作的判決書為例,④參見《德國波恩州法院關于一起故意殺人未遂案的判決書》,馮軍譯,載馮軍主編:《比較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453頁。簡要說明德國司法實踐中,實際案件的量刑過程和思維進路:首先,在該案判決書的E部分,認定被告人哈逖姆·馬斯洛依(Hatim Maslouhi)的危害行為是刑法典第212條意義上的未遂的故意殺人,而不是第211條的謀殺;其次,在F部分,排除了被告人具備第213條故意殺人的減輕情節,從而按照第212條確定適用5年至15年自由刑的法定刑幅度;再次,考慮到止于故意殺人的未遂,適用第23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的減輕處罰,在量定具體的個別刑罰時,法庭應從2年至11年3個月的刑罰幅度出發(下限直接減為2年,上線為最高刑期的3/4);再其次,考慮到存在第21條的各種前提(限制刑事責任),法庭再一次根據第21條、第49條第1款的減輕處罰的規定降低這一刑罰幅度,因此確定處斷刑的范圍為6個月至8年5個月(下限直接減為6個月,上限則再次乘以3/4),具體的刑罰量定應當從這一刑罰幅度出發;最后,在考慮了全部有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況之后,法庭認為,為了抵消被告人的責任,判處4年的自由刑是必要的和適當的(基本上是處斷刑的中間部位),并從特殊預防考慮依據第63條的規定將被告人收容于精神病院。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雖然廣義的量刑是從定罪以后就開始了,但是卻經歷了選擇刑罰幅度(包括減輕或者加重構成要件的適用與否)、形成處斷刑(減輕或者加重情節的適用)、決定宣告刑(具體刑罰的量定,即狹義的量刑)三個大的階段。這三個階段相互鏈接、先后繼起,是從法定刑到處斷刑再到宣告刑的過程,總則減輕、加重情節的適用是對分則具體個罪刑罰幅度的修正,在此基礎上可以考慮所有的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的情節,并決定是從輕還是從重,最后量定刑罰。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允許法官自由裁量的僅僅局限在狹義的量刑階段,而且仍然需要考慮責任的抵償、特殊預防或者社會復歸等刑罰目的,仍然需要在判決書中說明理由并進行論證,仍然需要注意量刑的均衡(包括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案件等之間的量刑均衡)問題。在廣義的量刑過程中,形成處斷刑是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通常具有的階段,其依據是刑法規定了基于法定事由可以對法定刑進行修正。例如,日本《刑法》第68條規定,除了死刑、無期徒刑的減輕之外,其他的減輕處罰均采取“比例制”,所適用的刑罰幅度的上限與下限同時減輕,如第(三)項規定,“有期懲役或者監禁減輕時,將其最高刑期與最低刑期減去二分之一”;①參見《日本刑法典》,張明楷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再如,我國臺灣地區2002年修訂的《刑法》第66條規定,“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第67條規定,“有期徒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由此,處斷刑是經由對法定刑修正所得來的,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只有在刑法規定了法定刑可以修正的情形下,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處斷刑,②參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頁。像我國關于減輕處罰原則的規定,并未規定可以對法定刑進行修正,因此就不能說我國存在處斷刑情形,從量刑的宏觀過程來看,這或許是我國《刑法》關于量刑與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最大區別。
處斷刑是一個銜接立法與司法之間的階段,是法定刑到宣告刑的過渡,當然,前提必須是刑法明文規定并且出現了法定的情形,③一些國家刑法允許法官裁定對法定刑進行酌定減輕,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條-2規定,“除第62條規定的情節外,法官還可以考慮其他一些情節,只要他認為這樣的情節可以成為減輕處罰的合理根據。”參見《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黃風譯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需要對法定刑進行一定的修正,易言之,形成處斷刑并非所有案件的必經階段,而只是依據刑法規定而為之,但卻是將法定情節作為修正法定刑的情形,而并非直接影響宣告刑的情形。
四、減輕處罰量刑規則的修浚完善
我國《刑法》關于減輕處罰的量刑過程與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相比較,顯著的區別在于缺乏處斷刑的階段,④張明楷認為,在我國刑法中除了數罪并罰類似于處斷刑的作用之外,“處斷刑不是我國刑法中的概念”。參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頁。并不能通過修正法定刑形成新的處斷范圍,這樣的結局便是當前關于減輕處罰原則的規定,只能在法定刑以下處刑;而且量刑情節往往同時具有多種功能,法官選擇情節功能的內心歷程難以量化,加之不同功能之間差異較大,容易造成量刑的不均衡。另外,對于量刑情節的競合問題在當前減輕處罰立法體制下也難以恰當地處置。因此,借鑒域外關于處斷刑的立法經驗,探索量刑過程的進一步完善也就勢在必行。
從性質上來看,處斷刑屬于對法定刑的修正,本質上仍然屬于法定刑。當存在加重或減輕事由時,通過修正法定刑確定一個處斷范圍,在此范圍內最后決定宣告刑,因此,這里的加重或減輕事由是加重或減輕法定刑的事由,而不是直接加重或減輕宣告刑的事由。①參見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頁。之所以處斷刑本質上屬于法定刑而非宣告刑,在于其“通用”屬性,即只要符合法定適用的要件,則均應當按照《刑法》的規定適用于所有的案件,在這一問題上法官并無自由裁量之權限。惟有可以由法官依據個案情形“酌科”的刑罰,在性質上才屬于宣告刑。易言之,該影響量刑的事由僅屬于個案,且并無嚴格的量化指標限制,并不突破法定刑范圍,可以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進行刑罰裁量,如此酌科之后的刑罰便是宣告刑。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刑法,在法定刑通往宣告刑的路途之上嵌入了一個處斷刑,其功用究竟如何,主要在于維持罪刑之均衡:一是,因為法定刑可以加重或減輕,從而使得各基本法定刑之本刑在立法之初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契合罪刑之均衡,防止因為顧慮無法涵蓋現實中的特殊情形而故意加大法定刑的涵蓋面,從而導致法定刑跨度太大、伸縮無度的局面出現;二是,通過修正法定刑以確定宣告刑的處斷范圍,從而另一個方面,在出現特殊事由時可以適當地伸縮罪與刑的匹配,在新的范圍內確定宣告刑,整個量刑思維其實就是從一般到特殊再到個別的過程;三是,對刑罰加重或減輕事由予以規范化,明確適用的條件和場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例如,加重或減輕事由可以區分為總則性加減事由和分則性加減事由,構成要件加減事由、違法性加減事由和有責性加減事由,以及區分為與犯罪輕重有關的加減事由和與刑事政策有關的加減事由等等,②我國臺灣地區實務界認為,“刑總之加減,因非法定本刑之變更,應如何加減,法院在規定范圍內,自有裁量之權限,并非一律應加重或減輕至所定比例。”此種見解即使在臺灣地區也頗尚有爭議。參見靳宗立:《臺灣刑法有關刑罰加重與減輕之探討》,載京師刑事法治網,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pkID=31236,最后瀏覽日期2014 年12 月31 日。這些加減事由的適用條件、作用場域和方向均有所不同,對于加減的緣由、幅度、順序等均可一目了然,便于監督。綜上,處斷刑在本質上仍然屬于法定刑,是在司法層面對法定刑的修正,但是卻又不同于各基本法定刑之本刑,更有異于司法裁判所作的宣告刑。作為立法與司法、法定刑與宣告刑之間的中間環節,處斷刑是一般中的特殊、抽象上的具體,在保持法定刑通常適用的情況下,補足了靈活性與適應性。因此,加入了處斷刑環節的量刑,是一個從一般到特殊再到個別的過程,符合基本的思維規律與習慣,具有獨特的優勢。
既然如此,我國《刑法》有必要考慮借鑒域外立法模式,考慮增加處斷刑的階段,以完善量刑過程、縝密量刑思維。為此需要修改《刑法》第63條第1款的內容,立法規定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修正法定刑以形成處斷刑,法定刑的修正建議采取德日刑法典的模式,即不同刑種直接減降、同刑種比例減降或倍比增加,③德日刑法略有不同:德國刑法是以“規定最低自由刑”的方式降低刑罰的下限,而日本刑法則是同比例減降;另外,德國刑法典關于累犯的規定已于1986年廢除,因此已經沒有加重刑罰的規定;日本刑法典則保留加重處罰,并實行倍比制,第57條規定的再犯刑罰要求處犯罪所規定的懲役的最高刑期的兩倍以下。從發展趨勢上來看,除了并合罪以及分則個罪規定的加重構成要件之外,總則性加重處罰規定的立法模式勢必趨于式微。而且刑罰的上限和下限最好同時增減以形成處斷刑。因為如果不按照如此方式進行增減,所形成的處斷刑范圍仍在法定刑范圍或幅度之內,則實質上僅僅是從輕或從重處罰而已。④如俄羅斯《刑法》第62條規定的減輕情節的刑罰裁量規定,“刑罰的期限和數額不能超過本法典分則相應條款規定的最高刑種、最高刑期或數額的四分之三。”第68條累犯規定,“所判的刑期不得低于相應犯罪的最重刑種、最高刑期的二分之一;對于危險的累犯,不得低于三分之二;而對于特別危險的累犯,不得低于相應犯罪的最高刑種、最高刑期的四分之三。”這些“減輕”或“加重”處罰的規定實質上僅僅是從輕或者從重處罰而已。參見趙微:《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3頁。雖然對法官的裁量范圍也進行了非常重要的限制,但是并沒有達到設立處斷刑的目的。當然,處斷刑與原法定刑在范圍上存在相當大的重合部分,因此雖然經過減輕,但是最終的宣告刑仍然有可能落入原法定刑的范圍,即宣告刑仍然是受具體案件刑事責任大小(違法性大小和有責性大小的乘積)的決定,依據可譴責性大小的排序以及在現有(或給定)的刑罰手段中所處的恰當序列來確定刑罰量。⑤參見:Paul H.Robinson.“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Modern Desert:Vengeful,Deontological,and Empirical.”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67(2008),p.151.如果其可譴責性大小的排序較高,仍然有可能在處斷刑的范圍內適用較重的刑罰,從而落入到減輕處罰以前的原法定刑范圍之內。這樣也就很好地解決了前文談到的憚于適用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而且使得大多數多功能情節的存在成為不必要。至于是否允許法官在法定增減的比例內根據個案情形另行裁量增減的比例,筆者認為,既然處斷刑也僅僅是一個處斷的范圍而已,在此范圍內仍然需要綜合考慮刑事責任的大小才能最終決定宣告刑,因此,無需也不宜由法官在此階段另行裁量增減的比例,應當直接增減至法定比例或刑罰。
最后,處斷刑的立法模式,能夠妥當地處置量刑情節的競合問題:一是,多個減輕處罰量刑情節的競合問題,由于處斷刑是法定刑的修正,本質上仍然是法定刑,因此,如果出現量刑情節競合的情形時,則仍然可以再次進行修正,并再次形成新的處斷刑,亦即可以遞減或遞加。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70條規定,“有兩種以上刑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此種情形也適用于減輕處罰與加重處罰競合的情形。基于有利于被告人解釋的原則,一般應當先加重再減輕,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71條對之有明確的規定,“刑有加重及減輕者,先加后減。有兩種以上之減輕者,先依較少之數減輕之。”再如,日本《刑法》第72條規定,“同時加重和減輕刑罰時,按照下列順序:再犯加重、法律上的減輕、并合罪的加重、酌量減輕”。①參見《日本刑法典》,張明楷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頁。另外,加重處罰不得跨越刑種,即無期徒刑不得加重為死刑,有期徒刑不得加重為無期徒刑等。從加重處罰的情況來看一般僅限于累犯,而且當前的立法趨勢是僅僅將之作為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二是,減輕處罰與從輕、從重處罰的競合。由于減輕處罰僅僅是修正了法定刑,而從輕、從重處罰情節則是在處斷刑的范圍內進行考慮并最終形成宣告刑的“純正”的量刑情節,二者互不沖突,是順序遞接的關系。這一司法難題在處斷刑的立法模式下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三是,存在數個主刑時如何減輕處罰。定罪事實指向某一量刑幅度,但是在該幅度內存在多個主刑,如果需要適用減輕處罰,則應當對所有主刑按照減輕處罰的標準一并適用,然后最終確定經過修正所得來的處斷范圍。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69條規定,“有兩種以上之主刑者,加減時并加減之。”假設立法規定死刑減輕處罰由無期徒刑代替,無期徒刑減輕處罰由25年有期徒刑代替,其余自由刑減輕至原法定刑期的3/4,則上述法定刑幅度經過減輕后形成的處斷刑范圍為無期徒刑、7年6個月至25年有期徒刑。當然,這個例子僅僅是一種假設的情形,實際立法應當更加細密而周全。
綜上,通過改變減輕處罰的適用規則,借鑒處斷刑的概念,諸多的立法難題與司法困境均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即便為了維持刑法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保持當前各法定量刑情節的立法現狀不變,司法實踐的操作也變得簡便順暢而且符合思維邏輯,并有助于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