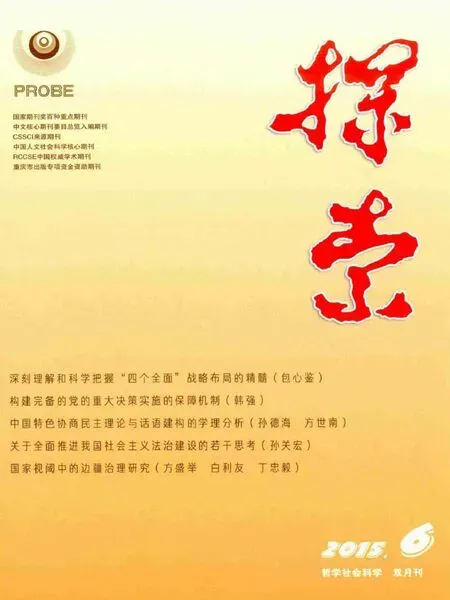美國大學智庫的功能及其對我國大學智庫建設的啟示
(山西大學外國語學院,山西太原 030006)
進入21世紀,數字化、網絡化以及由此加快前進步伐的全球化為社會發展帶來了諸多的機遇,但同時也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環境治理和網絡安全等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有創新性、前瞻性的政策方案去把握機會并應對問題。而大學智庫因以科學研究和對新的發展趨勢的認識見長是專業化的知識與日益復雜的政策問題間的橋梁,大學智庫的能力建設和對決策的影響力日益重要。大學智庫在美國智庫中是一支重要而富有活力的力量。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2015年發布的報告,美國有1 830家智庫,超過一半是隸屬于大學的[1]。大學智庫的研究員和專家也常為雜志、報紙撰文就熱點問題發表見解;作為政策專家接受媒體采訪;去國會相關委員會及分委員會作證;為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助理提供政策咨詢以及被選入國防部、外交部等行政部門及總統的執政班底任職。同時各智庫經常舉辦各種形式的政策研討會為國會議員、政府官員、政策專家和媒體人士提供交流平臺。他們還利用學術研究的優勢與國防部和能源部等政府部門簽約就重大問題進行合同研究。他們還以學者的獨立身份進行外交斡旋發揮第二軌道外交作用。因此,美國大學智庫不是單純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它們的政策研究和影響已成為美國政治中不可忽視的存在,他們的政策主張往往會成為美國內政和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故本文將以哈佛大學的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為例通過分析美國大學智庫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探討其對我國大學智庫建設的啟示意義。
1 美國大學智庫簡況
有別于單純進行學術研究的研究所或中心,美國大學智庫是指從事政策研究的、旨在通過政策研究與分析影響政策或政策環境的與大學有隸屬關系的研究所、中心或項目。他們或以一個院系為依托,或為獨立的研究所或中心,研究人員大多來自于大學的相關院、系和所,如哈佛大學的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設于其肯尼迪學院,而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則相對獨立。智庫的管理則由相對獨立的顧問委員會負責。貝爾弗中心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向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和其它研究與工作人員提出建議。設于哈佛文理學院的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是該大學最大的國際研究中心,除顧問委員會外,還設有行政委員會和負責項目資助的指導委員會。胡佛研究所則有獨立的監察委員會。萊斯大學的詹姆斯·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的管理由顧問委員會負責。
此外,有些大學智庫與美國政府有隸屬關系,尤其在安全與國防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國防大學的技術與國家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海軍戰事學院的海軍戰事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和陸軍戰爭學院的戰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就數量而言,美國近一半的智庫是隸屬于大學的。如,僅就國際事務與相關政策的研究,哈佛大學就設有國際發展中心、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和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等;斯坦福大學除胡佛研究所外,還設有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和弗里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普林斯頓大學有國際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科學與全球安全項目、尼亞豪斯全球化與治理中心、民主政治研究中心和中國與世界研究項目(普林斯頓-哈佛)(China and World Program,Princeton-Harvard)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賴肖爾東亞研究中心(Edwin O.Reischauer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跨大西洋關系研究中心和外交政策研究所等。
其資金一般來源于基金會或個人捐贈。美國大學智庫與其他獨立智庫和教育、慈善機構一樣被美國國稅局劃為501(C)3范疇,對其捐贈可免稅。如,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創建得益于福特基金會的捐贈,其研究領域的拓展則與羅伯特和芮內·貝爾弗家庭基金會的捐助有關。有時大學考慮到某些項目對教學及研究的重要性也會在其智庫設立研究所或研究項目,如:斯坦福大學的弗里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由弗里曼·斯波利私人股本公司捐款設立,該所的亞太研究中心則是由美國地產大亨沃特·索任斯汀(Walter H.Shorenstein)的捐贈設立,但該中心的中國項目由斯坦福大學設立副校長負責其行政管理。此外,大學智庫同樣具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胡佛研究所比較保守,故受到保守派的斯凱夫基金會(Scaife Foundation)和沃爾頓家庭基金會(Walton Family Foundation)等的支持;喬治·梅森大學的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由于其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策調控的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ism)立場而得到科赫家族基金會(Koch family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
“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2015年發布報告,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大學智庫中美國有六家,包括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的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以及哈佛大學的國際發展中心、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研究所、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和萊斯大學的詹姆斯·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1]。
2 美國大學智庫的功能
2.1 思想掮客
提出政策理念是美國智庫的基本任務,美國大學智庫不僅進行政策研究提出政策方案且以各種形式和渠道溝通政策主張,為決策者提供智力支持。肯特·韋弗(Kent Weaver)認為智庫在美國政策制定領域發揮五大功能,最基本的就是“政策理念之源”。“智庫承擔的共同任務就是探索和推廣短期看來尚不可行的政策建議,逐步讓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它的價值,使之有足夠的支持者,并最終成為政策法律。”[2]智庫也是政策理念和公共政策之間的橋梁,戴安娜·斯通認為“在政治中觀念是無形的”[3]1,故應該有智庫這樣的組織促進對認識、主張的提出、探索和傳達。智庫作為思想掮客還是“研究經紀人”使相關的學術發現和評估被非專業人士所接受[4]。
貝爾弗中心設有四個互為補充的研究領域:國際安全,科學、技術和公共政策,環境及自然資源和外交及國際政治。政策理念的提出主要通過出版書籍;發表學術性研究論文和報告;為國防部和外交部等政府部門簽約就重大問題進行合同研究;為報刊、雜志撰文和發表時事評論;提交政策簡報、去國會聽證會作證和在研討會和論壇發言等。
如,對中國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中美關系、能源與地緣政治、中國與核安全和中國與網絡安全。從2011年5月到2015年5月5年間出版書籍12本,其中包括約瑟夫·奈伊的《美國的世紀結束了嗎?》、史帝文·米勒的《薩拉熱窩百年紀念:1914和中國的崛起》、理查德·羅斯克蘭斯的《下一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和美中交鋒的危險》、梅甘·奧沙利文的《能源、大戰略和國際安全的相互糾纏》等。發表學術性研究論文和報告126篇,包括澳大利亞前總理和外交部長,現任貝爾弗中心研究員陸克文撰寫的研究報告《21世紀的中國與美國:習近平領導下的中美關系的未來》;羅恩·林賽的《中國對網絡安全的影響:虛擬及真實摩擦》;查爾斯·格雷澤《美中討價還價?軍事競賽和相互包容間的艱難抉擇》以及亞當·里夫的《奔向悲劇:中國的崛起,亞太的軍事競賽和安全困境》;為報紙、雜志撰文和發表時評203篇,包括國防部負責政策前任副部長米歇爾·芙樂諾伊、現為該中心研究員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經濟增長是國家安全事項》;約瑟夫·奈伊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中國的崛起將不會終結美國世紀》;史帝芬·沃特在《外交政策》發表的《平衡中國時我們的怎樣劃線不越界?》和《別理睬窗簾后的熊貓》等①資料來源為貝爾弗中心網站,閱讀文章內容請登錄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index.html?groupby=1&=&filter=136。
提出政策理念只是作為思想掮客的第一步,智庫還通過主辦刊物、發行通訊、舉辦研討會、政策理念發布會、項目工作組會議和新書發布會等推廣與溝通政策理念。如,貝爾佛中心主辦有季刊《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就中美關系近5年來刊登了關于中美作為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與事實上的強國(established power)間的關系是走向沖突還是管控危機面向未來;中國的軍力增長給美國帶來的挑戰;能源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核安全、中美關系與東亞的安全困境等方面近30篇文章,且包括不同觀點間的辯論,如,就中國外交方面是否“越來越強硬(assertive)”的爭議、中美是否一定要發生軍事沖突和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是合作共贏還是制約中國的發展的辯論。
此外,正如持精英論的學者所批評的那樣,大學智庫的專家或董事會成員還在多家智庫、學術機構和企業任職,這樣他們所提出的政策理念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傳播與溝通,他們在相關領域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同時他們作為思想掮客的作用就大大增強。如,貝爾佛中心的國際委員會董事約瑟夫·奈伊,同時又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董事之一和精英政策規劃組織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北美分部的主席,他同時還被選入具有極高聲譽和威望的美國外交協會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中心主任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還是三邊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并任職于外交關系委員會、美國能源部的俄羅斯不擴散項目工作組、國際原子能委員會、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委員會和國際能源公司等機構和公司。馬休·邦恩(Matthew Bunn)入選美國科學促進會,同時任職于武器控制協會和全球安全伙伴等組織。
2.2 建設跨國政策網絡
梅甘在2015年發布的“智庫與公民社會”的報告中總結了智庫發展的14大趨勢,放在首位的就是全球化,他認為:“全球化使智庫跨國發展成為趨勢。”“智庫建立了自己的網絡并利用這些聯系相互協作、共享和開展對話。”“有了這些網絡學者就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傳播自己的主張和政策方案。”[1]戴安娜·斯通還強調了跨國網絡的專業性,她指出,這種更精英化的認知社區“由專業人士、研究人員和科學家組成,憑借他們的專長和學術資格在參與決策方面具有特權”[5]。此外,斯通還強調跨國政策理念傳播應注重“軟”推廣也就是規范的推廣,作為“對政策工具、結構和作法等硬手段的補充。”她認為:“經濟規范如透明性、資本流動、可兌換和避免通脹等也影響國家行為和遵守自由民主的國際經濟秩序,如華盛頓共識。”[6]智庫通過認知共同體進行這種對規范和標準的推廣可使其在有關全球治理的氣候、環境、網絡安全和能源等領域擁有更大話語權,進而主導規則的制定。
大學智庫因以學術研究,尤其是以先進科學技術研究見長,故在氣候變化、能源、核安全、網絡安全和國際貿易等方面形成跨國網絡更具優勢。貝爾佛中心的跨國網絡主要包括合作研究和資助他國研究人員到中心做研究或邀請某一領域權威主持某一研究項目。戴安娜·斯通認為“人際網絡的作用不應低估。它是更為重要的互動的基礎……這種交往對于有效溝通和富有成效的合作至關重要。”[5]
貝爾佛中心目前所設立的14個項目均在這方面有所行動,尤其是能源技術政策創新,氣候協議,網絡項目,管理原子能,科學、技術與全球化和能源的地緣政治等。如,能源技術政策創新(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針對美國、中國、印度和包括歐洲、中東和北非等地區,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進行研究。該項目認為對不同國家而不是一國開展研究增強了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并更便于尋求合作,且能夠在對不同的研究對象的情況和策略的比較中得到新的啟示。針對中國的主要項目包括中國與環境可持續(China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和水-能源聯系(Water-Energy Nexus)。中國與環境可持續項目始于2001年當該研究與中國科學與技術部合作研究中國語境下的能源與技術策略之時。并且與中國汽車技術與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等進行合作,能源技術創新已經就中國的能源和環境政策開展了多年的深入研究。水-能源聯系則探索政策和技術創新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水能源的高效利用的作用,因為在人口增長和區域氣候與水循環變化的情況下日益需要將能源與水系統整合計劃與設計,目前的主要研究對象包括中東、中國和美國。對這兩個項目均提供研究職位,資助科研人員進行研究且博士后和已有在研項目的能說漢語的研究人員優先考慮。從2015年開始中國與環境可持續項目將資助在中國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中參與實際工作的人員到中心做研究。研究工作以分析為加強中國的環境與能源目標進行設計、開發或執行政策時的機遇與挑戰為主。此外,2014年能源技術政策創新研究還與清華大學就中美排放協議背景下能源技術創新共同舉辦了研討班①詳情參見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roject/10/energy_technology_innovation_policy.html。。
又如,為了給2015年將在巴黎召開的氣候大會提供政策建議,爭取話語權,該中心的氣候協議項目(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于5月7-8日召集來自大學、智庫、世界銀行和企業的專家討論如何使巴黎氣候大會的新協議包括靈活的緩和措施并且發表了包括“通向2015氣候協議的大膽設想”和“對G20化石燃料補貼協議的政策監控”等一系列討論文稿。研討會由該中心、國際排放交易協會和世界銀行碳市場行動網絡共同主辦②詳情參見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roject/56/harvard_project_on_climate_agreements.html。。
2.3 與決策者的互動
美國大學智庫的作用還體現在它們是政府的人才儲備庫,即智庫與美國政府之間存在一道旋轉門。旋轉門使智庫不僅僅是政策規劃網絡的一份子而是真正加入了政策制定團隊。“超過60%的國務院助理部長來自于智庫”[7],政策專家聚集在智庫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被選入政府部門就職,施展抱負。曾任美國外交部政策規劃處主任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認為:“這一作用對于美國政治體制來說至關重要。”[8]前國務院官員現為布魯金斯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科恩認為“這一‘影子政府’功能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不一定是壞事,在美國反對黨沒有像在英國那樣成立‘影子部門’,我在國務院從事政策規劃時,我認識到一旦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沒有人還能學習什么東西。他們的工作取決于之前的智力資本。”[7]另一方面,智庫也被稱為“非正式的外交事務影子內閣”[9]6或“流亡政府”[9]153,離任的政府官員借助智庫,以局外人的眼光和“身在此山中”時所達不到的境界,審視美國當前的內政與外交事務和未來的挑戰[2]。對于貝爾弗中心而言與決策者的互動極為密切。最為著名的就是中心前科學與國際事務部主任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數度在政府任職并于2014年12月被奧巴馬任命為國防部長。貝爾弗中心主任格雷厄姆·埃里森稱贊他是實踐“中心使命的典范。”③見埃里森對卡特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后發表的評論,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820/Ashton_b_carter.html.Dec.5,2014。而埃里森曾任克林頓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其他典型的范例有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現任奧巴馬的總統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主席,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主任,曾任中心科學、技術與公共政策部主任。此外,前國防部負責政策規劃的副部長米歇爾·芙樂諾伊(Michele Flournoy),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創始人之一,現任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中心董事會成員,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約瑟夫·奈伊曾數度出任政府職務,克林頓政府時期任國防部副部長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現為國務院外交事務政策委員會成員和國防部軍事政策委員會成員;中心另一位董事和國務院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在國務院任公共事務助理國務卿;董事會成員勞倫斯·薩默斯也曾數次出任政府要職包括奧巴馬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克林頓政府時期任財政部長。
貝爾佛旋轉門“名人錄”還包括馬休·邦恩曾任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顧問,曾主導1995年總統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主持的保密性質的關于核安全的研究,成為美國核材料安全政策的基礎;亞倫·阿諾德,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和司法部不擴散和反擴散顧問;理查德·克拉克,曾是前三任總統的全球事務特別助理、安全與反恐國內協調員和總統網絡安全特別顧問;杰夫里·富蘭克爾,曾為克林頓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等。
全球化時代,這道旋轉門還有國際化的趨勢,如,澳大利亞前總理、外交部長陸克文應邀加入貝爾佛中心并主持“中美關系未來的選擇”的研究項目,并于2015年4月以中、英文發表研究報告“習近平治下中美關系:以建設性的現實主義,來實現中國的使命”。
3 對我國大學智庫建設的啟示
由此,美國大學智庫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尤其是進入21世紀政策環境日益復雜,需要約瑟夫·奈伊所說的對復雜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判,并能把握發展機遇的環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10]xvii。我國大學智庫近年來得到了長足發展,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認為美國大學智庫的一些經驗值得學習與借鑒。
第一,充分發揮大學智庫在科學技術和對社會發展新趨勢的認識與把握方面的優勢,提出有前瞻性、針對性和即時性的政策方案。大學智庫有別于大學的研究所,不應以單純學術性的研究為主,而為解決現實問題提出具體的政策方案是智庫能力的核心。
第二,保持智庫在政策研究上的獨立性。美國大學智庫如哈佛大學的貝爾弗中心等是由相對獨立于大學的監察委員會負責項目設立、資金的使用和研究員的聘請等。獨立性使智庫能夠從更為多元的角度審視問題,能更為有效地為決策者提供智力支持。如貝爾弗中心研究員對于美國的中國政策的辯論。
第三,重視人才的儲備和對青年的培養。人才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智庫旗下主持研究的業內知識權威和專家是其影響政策的重要因素,且美國大學智庫還是政府的人才儲備庫,但智庫的影響力還來自于對于未來領袖的培養。例如,貝爾弗中心提出它有兩大使命:在提出與最重要的國際安全方面的挑戰以及在科學、技術、環境政策和國際事務相交叉的關鍵領域的政策觀念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為這些領域培養領袖。
第四,加強與決策者間的溝通與互動。同決策者進行廣泛接觸和密切溝通,尋求各種機會為政策制定者獻計獻策。美國的大學智庫不但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直接參與決策而且常以邀請政府官員到智庫發表講話,參加研討會;遞交政策研究簡報和加入政府部門的政策委員會等各種形式影響政策。
第五,致力于建設跨國政策網絡,在事關全球治理和區域性的事務中增加存在感和話語權。美國大學智庫建設跨國政策網絡采用在他國設立分支機構、合作研究或資助他國研究人員到該中心做研究或邀請某一領域權威主持某一研究項目。這種跨國政策網絡不僅使美國大學智庫在全球性和區域性的事務中擁有話語權,而且就面向未來的氣候變化、環境、能源和網絡安全等事務推廣自己的規范與標準。我國大學智庫應借鑒貝爾弗中心的經驗加強跨國政策網絡建設,將國際認可的知識權威和專家的研究納入我國智庫的研究視野以便能在環境、能源、氣候變化和網絡安全等面向未來的政策領域爭得更多話語權,因為話語權就意味著在全球治理事務中制定規則的權力。
參考文獻:
[1]James McGann.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cholarly Commons.[2015-06-16]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tanks/8,(10),(13-14).
[2]Kent Weaver.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J].PS.Political Science,Sept.1989,(568),(569).
[3]Diane 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London:Frank Cass,2002.
[4]Kent Weaver and 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in a Time of Change,in James McGann Ed.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5-6.
[5]Diane Stone.Think Tanks Across Nations:The New Networks of Knowledge[J/OL].NIRA Review,Policy Community[2015-05-26]http://www.nira.or.jp/past/publ/review/2000winter/stone.pdf.(37),(36).
[6]Diane Stone.Transfer Agents and Global Networks in the“Transnatonalisation” of Policy[EB/OL].[2015-07-06]University of Warwick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2004.http://dx.doi.org/10.1080/13501760410001694291.(1-2),(12-14)
[7]Peter W.Binger.Washington’s Think Tanks:Factories to Call Our Own[J/OL].Washingtonian,August 2010 issue.[2015-06-09]http://www.washingtonian.com/articles/people/factories-to-call-our-own/
[8]Richard Haass.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A Policy Maker’s Perspective[EB/OL].I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S.Foreign Policy.[2015-01-19]U.S.Foreign Policy Agenda,vol.7,No.3,Nov.2002,http://www.scribd.com/doc/3210628/the-role-of-think-tankin-us-foreign-policy.pdf,(7).
[9]Donald Abelson.A Capito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M].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6.
[10]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M].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