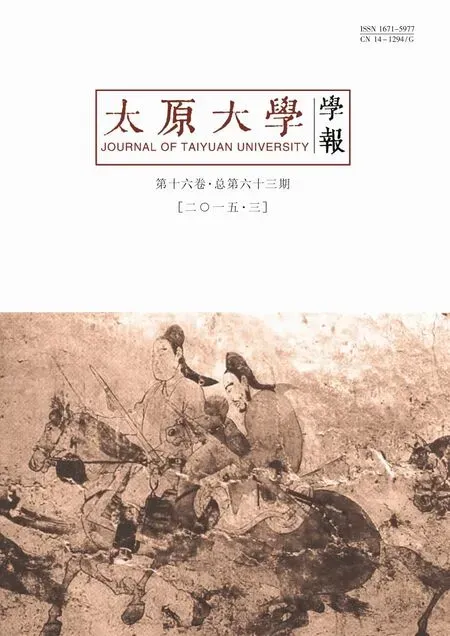論福克納與莫言的酒神精神
朱 崢 琳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論福克納與莫言的酒神精神
朱 崢 琳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福克納與莫言的比較研究歷來備受學者關注,他們的創作帶有強烈的酒神精神,這與他們的生命歷程密不可分。在寫作上,他們注重敘述的狂歡之美,在人物的塑造上充分體現人性的自然之美。酒神精神在他們的小說《喧嘩與騷動》與《紅高粱家族》中有著深刻的體現,彰顯了福克納與莫言在生命與藝術上的狂歡。
福克納;莫言;酒神精神;《喧嘩與騷動》;《紅高粱家族》
尼采說:“我是哲學家狄奧尼索斯的最后一個弟子。”[1]101狄奧尼索斯(Dionysus)即酒神,是古希臘神話中釀酒及釀酒植物的保護神。19世紀70年代初期,尼采最早提出了“酒神”的概念,認為“酒神狄奧尼索斯象征主觀情感的放縱,酒神精神是人類自古有之的大創造,大破壞的精神”。80年代之后,尼采的思想漸趨成熟,在多部著作中論述“酒神精神”這一概念——“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異樣最艱難的問題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這為酒神精神。”[1]101這樣一種肯定生命的酒神精神,正是貫穿福克納與莫言的生命歷程以及文學作品的核心精神。福克納與莫言分別是1949年和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雖相隔半個世紀,但無論是從影響研究的角度,還是從平行研究的角度,這兩位擅長寫故事的作家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改革開放以來,譯介福克納的作品便成為熱潮,其小說包括《喧嘩與騷動》、《八月之光》、《我彌留之際》等,都是中國文藝界的寵兒。近幾十年來,我國對福克納的研究早已形成體系,并具有專門的研究組織。對于莫言的文學作品,眾多學者也早已展開學習與研究,成果頗豐。隨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莫言更是名聲大振,《豐乳肥臀》、《紅高粱家族》、《蛙》等諸多作品一時之間銷售一空,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
一、生命的狂歡——福克納與莫言的酒神精神
酒神,是宙斯與忒拜國王卡德摩斯的女兒塞墨勒所生之子。塞墨勒因受天后赫拉的誘騙而被雷電燒死后,宙斯從其腹中取出胎兒縫入自己的大腿中,因而走起路來像瘸子一樣。后來宙斯將其取出,取名為狄奧尼索斯,意思就是指“瘸腿的宙斯”。古希臘悲劇起源于酒神祭祀,在祭祀禮儀之前人們常常會喝得酩酊大醉,他們載歌載舞,情緒亢奮,沖破了平時的禁忌,在無意識之中追求精神的解放。在狂歡的氛圍中創作的歌謠充滿生命感與力感,痛苦仿佛成為了藝術的興奮劑。由此可見,酒神精神就是整個情緒系統亢奮的狀態,在這樣狂歡與迷醉的狀態下,人的原始生命力得到充分擴張,理性逐漸隱退,而人的本能欲望、自然原始的生存狀態得以釋放。因此概括來說,酒神精神在于“提倡一種特殊的人生態度,即積極肯定人生,尤其是肯定生命的非理性方面”。[2]
福克納與莫言肯定生命意志、追求人性自由、歌頌原始生命活力,他們在“大醉”之中,尋找著渴求已久的酒神精神,這種精神與他們的人生經歷有著深刻的聯系。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年出生在美國密西西比州新奧爾巴尼的一個沒落莊園主家庭,其曾祖父是個有名的歷史人物,一直被福克納視作自己的人生向標,他就像一個在大地上仰望著曾祖父的小孩,“像我曾祖父那樣”是他的口頭禪。福克納身材矮小,而且氣質上也有些女性傾向,與母親更為相像,常被認為是“母親的兒子”。他自認為不夠男子漢,因而在心中隱藏著自卑的種子,當自己心愛的女孩艾斯黛爾跳舞時,他只是一聲不吭地、靜靜觀看她與別的男孩子跳舞。福克納的童年生活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愛,他在父親和母親的勢不兩立中長大,母親莫德不滿意丈夫的軟弱無能,而父親則待人冷漠、不易相處,這樣的環境對幼年福克納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在他的很多小說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溫馨和諧的親情,家庭關系是陰冷的、異化的。福克納的一生有太多的角色:講故事的孤僻少年、版本多樣的傳奇老兵、流浪漢、酒鬼、郵政局局長、好萊塢寫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等等,然而他本質上始終是一個作家,這些不同尋常的經歷都成了福克納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他寫了一些書,然后死了”——這是他理想中的墓志銘。
福克納始終對自己的母親有著深深的敬意。在母親的指導下福克納看了很多書,從初級的童話故事到狄更斯之類的經典作品,母親用這樣的方法把“對文學執著的愛”傳播給自己的孩子。莫德是一個非常堅強的母親,雖然個子矮小但個性極強,她在廚房里用木板掛上自己的信條“不抱怨,不解釋”,這種頑強對待生活的精神對福克納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很多作品中的白人老太太身上都有著莫德的影子,這些人物在小說中像是沉悶暗夜里閃現的一道亮光,照亮了讀者沉悶壓抑的眼睛與心靈。福克納是一個酒鬼,一生浸泡在酒精中,他甚至在準備去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還喝得酩酊大醉。無論福克納是為了慶祝喜事或借酒澆愁,還是他能夠在酒精麻醉下的“大醉”狀態中尋找更多的創作靈感,他都讓自己在“醉”的境界中探尋人生、對待生命,“由于福克納經常生活在自己虛構的世界里,可能他自己有時都分不清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他想象的產物。”[3]20曾經有記者采訪他的家庭情況時,福克納“神情認真”地回答道:“我于1826年由一個黑奴和一只鱷魚所生——他們的名字都叫高興的石頭。”相信這樣匪夷所思的答案只有這位會編故事的福克納才能信口說來吧。1921年12月,福克納開始擔任密西西比大學郵電所所長,從此以后郵電所再也沒有確定的開門時間,他有時候很久都不分發信件報刊,有時候又迅速的把信件加急發送,碰到一些有趣的雜志,他就自己拿過來看上好些天,遭到投訴后依然我行我素,做了差不多三年“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郵電所所長”。*轉引自Minter,William Faulkner,p.42.由此可見,福克納無疑是一個自由散漫的怪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他蓄上胡子,光著腳在街上或者是在樹林里漫無目的地走,有時候甚至在廣場上站幾個小時,呆呆地對人視而不見,他就像是不斷在思索著困擾他的問題的流浪漢,在面無表情的平靜中進行著思想的大狂歡。
莫言曾說過:“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成功,很可能成為終身伴侶,如果話不投機,大家就各奔前程。”[4]由此看來,莫言與福克納的談話很成功。莫言在《自述》中寫道:“我一邊讀一邊歡喜,對這個美國老頭許多不合時宜的行為感到十分理解,并且感到很親切。”1955年生于山東高密的莫言有著與福克納相似的童年生活,他們從小在民間的口頭故事中長大,自己也是講故事的能手,福克納甚至以講故事作為交換,讓小伙伴們替他干活。其次,莫言與福克納都有著豐富的文學儲備。盡管莫言因文革輟學在農村勞作,但是他還是讀了很多書,為了得到閱讀別人家書的權利,他常常去給人家干活。相比較而言,福克納則具有更為便利的條件,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莫德在福克納很小的時候就指定文學作品讓他閱讀,“10歲時就開始讀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和康拉德”。[3]16他們如海綿一般努力吸收,為以后的寫作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礎。再次,他們的童年生活并不美好。莫言曾坦言“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饑餓伴隨著我成長”,莫言的家庭成員很多,因而很容易成為被忽略的孩子,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被遺忘、被侮辱的黑孩兒一般,這種充滿愛與傷痛的成長經歷為莫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題材。而福克納的童年是在對自己身高、性格等各方面的自卑以及家庭關系的貌合神離中度過。最后,他們都有著驚人相似的創作動機:實現自身愿望。福克納以自己的曾祖父為榜樣,而他的曾祖父曾經發表過小說,是個很有名氣的作家,因而福克納上三年級時就想要成為一名作家。另外,福克納還希望通過寫作滿足心理要求,“他很希望做一件既使他顯得與眾不同又令人羨慕、崇敬的事情,來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優勢。”[5]23莫言最初決心當一個作家是因為聽到別人說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頓餃子。另外,莫言在《小說的氣味》中說:“其實,鼓舞我寫作的,除了餃子之外,還有石匠家那個睡眼朦朧的姑娘。”懷著對饑餓的恐懼和對美好愛情的向往,莫言創作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學作品,他從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等作家身上學習到魔幻現實主義,結合自身對家鄉、對中國真實歷史的了解,將“鄉土”的推向全世界。
雖然經歷過痛苦和饑餓,但是福克納與莫言的生活也并不缺乏關愛,他們在家鄉的土地上成長,遭受打擊和批評,但是他們始終離不開這片熱土,就像生命力頑強的植物一樣,圍繞著酒神狄奧尼索斯且歌且舞,在半夢半醒中編織著他們的文字王國。
二、藝術的狂歡——文學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狂歡化”是美學范疇的命題,由巴赫金提出。狂歡化的敘事追求沉醉和熱烈,并將一切狂歡節式的隨心所欲滲透在文學創作中。尼采認為,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是一種拋棄傳統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
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通過四個人的不同視角講述了康普生家族的興衰: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康普生家的女兒凱蒂,凱蒂因失身懷孕不得不與另一男子結婚,被丈夫發現后拋棄了她,便將私生女小昆丁寄養在母親家。哥哥昆丁因凱蒂失去貞操而失去精神平衡,在凱蒂結婚后不久投河自盡。大弟弟杰生是一個實利主義者,他將自己沒有得到銀行里的職位歸罪于凱蒂,因而他恨凱蒂,也恨小昆丁,在他的虐待下,小昆丁終于在1928年復活節那天取走杰生的不義之財,同一名流浪藝人私奔。班吉是凱蒂的小弟弟,1928年的時候他三十三歲,但是卻有著三歲孩童的智力,他沒有思維能力,分不清大腦中事情的先后順序。《喧嘩與騷動》的書名取自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中的臺詞:“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正如這句話,先天性的白癡班吉是第一個敘述視角。通過班吉顛倒時序的敘述,雖不能夠全面地了解具體情節,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凱蒂是一個自然、勇敢并富有同情心的女孩。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也是圍繞一個女性“我奶奶”戴鳳蓮逐步展開,她敢愛敢恨,遵循自己的生命意志,蔑視道德規范,與“我爺爺”在茂盛的高粱地里譜寫了最原始粗野又最自然純真的愛情交響樂。“我爺爺”是一個“最美麗最丑陋、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人物,他撒在酒簍子里的一泡尿奇跡般地釀制了奇香的“十八里紅”。他一生殺人無數,打死過土匪頭“花脖子”、襲擊過日本鬼子,是紅高粱養育的北方硬漢,在“我爺爺”身上有著中華民族壓抑已久的蓬勃生命力,他徹底擺脫了傳統禮教的奴性,敢作敢為。羅漢大爺是一個堅毅的漢子,他被日軍拴在馬柱上剝皮零割示眾,“劉面無懼色,罵不絕口,至死方休”,[6]11這些震撼的場景描寫,讓讀者在心驚肉跳之余大呼過癮。
(一)敘述的狂歡之美
福克納與莫言在小說創作上有著共同的地方,他們都力求新變卻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首先,他們都追求獨特的小說結構。在《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通過班吉、昆丁、杰生和迪爾西四個不同視角,使事件不斷清晰呈現,四個小部分就像是四個樂章,并且結構也并非按照時間順序,而是跳躍穿梭的,先寫的是1928年4月7日,將我們帶入白癡的視角,混亂而毫無邏輯,接著跳轉到1910年昆丁自殺那天,然后又跳回到1928年4月6日,通過這一天杰生的心理活動展現出康普生家族的頹敗,最后是1928年的4月8日,通過黑人女仆迪爾西的眼睛展現出康普生家庭扭曲的人際關系。而《紅高粱家族》的結構雖說并沒有清楚的分為四個時間段,但它是由五個部分組成的,“采用即興說書的的敘述方式,在時間上跳躍反復,而不是采取直線進行的因果敘述”,[5]185整部小說有兩條主線,一條是“我爺爺”余占鰲的戰斗生活,是按照時間的順序,從冷水伏擊戰開始,到加入鐵板會,再到抗擊日本軍。另一條線索是圍繞余占鰲、戴鳳蓮以及我“二奶奶”戀兒的情感糾葛展開,莫言采用閃回的方法,不著痕跡地進行著零散的片斷回溯,使整個故事有條不紊地呈現,由此可見莫言爐火純青的敘事能力。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明顯的“狂歡化”傾向。巴赫金指出:狂歡化人物的精神原型具有某些佯狂化的人物特性,如傻、癲狂、滑稽、瘋子等等,“他們不與世界上任何一種相應的人生處境發生聯系,他們看出了每一種處境的反面和虛偽。”[7]231福克納與莫言的小說中,多采用小孩或者是癡傻人的視角,借助兒童或者癡傻人的眼光或口吻進行敘述。批評家李喬說過:“以‘幼稚觀點’敘述,可以讓人領悟成人世界的愚昧可笑;以‘癡呆病態觀點’敘述,可以暗示所謂健康正常人間的可憐病態來。”[8]124《喧嘩與騷動》中的白癡班吉就有著異于常人的天賦,雖然很多事情他不懂也無法理解,但是他的感官非常敏銳,“我已經一點也不覺得鐵門冷了,不過我還是能聞到耀眼的冷的氣味”,[9]41921年他父親去世那晚班吉聞得到死亡的氣味。對他來說凱蒂身上有樹的香味,當凱蒂長大噴香水時,班吉就大吵大鬧把凱蒂往衛生間推。凱蒂失去貞操的那天,班吉更是瘋了一樣把凱蒂往衛生間推,然而這次卻永遠沒有樹的香味了。昆丁也是一個處于癲狂狀態下的人物形象,小說中他所敘述的那一部分發生在他要自殺的當天,因而精神處于極度癲狂之中,他在那天砸碎了折磨著自己的祖傳手表、打包自己的行李衣物、幫一個迷路的外邦小女孩回家、在回憶和現實的恍惚中與別人打架……他有板有眼地做著這些對于一個瀕死之人無關緊要的事情,從容不迫、安心等待著死亡。昆丁不斷回憶著妹妹失身后他們之間的對話,他無法接受凱蒂失去貞操的事實,一心想要說是自己與妹妹亂倫,從而能夠和妹妹兩個人墜入地獄,“純潔的火焰會使我們兩人超越死亡,到那時我們兩人將處在純潔的火焰之外的火舌與恐怖當中”,這種在世俗禮教壓抑下形成的病態心理導致了昆丁的悲劇。《八月之光》中的癡情女子莉娜,帶著“一種內心澄明的安詳與平靜,一種不帶理智的超脫”踏上尋找情人的路,她仿佛有一顆嬰兒般的心,無所懼怕、毫不擔憂,具有堅韌的生命力和超然的人格,這樣一個光輝的形象,正是福克納所贊美的“心靈深處的亙古至今的真情感受、愛情、榮譽、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10]254在莫言的《紅高粱家族》中,采用了“我父親”豆官的視角,當時豆官還是一個半大小子,跟著余司令四處打仗。“我父親”在小說中是一個全知視角,他像是整個事件的目睹者,見證了小說中每個人物的一生。在“我奶奶”出嫁的路上,轎夫們拼了命的顛晃新娘,不把她顛得嘔吐不罷休,這竟然是一種高密鄉的風俗。像這樣匪夷所思的類似于狂歡節一般的風俗還出現在《豐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被選為“雪公子”,在“雪集”上負責撫摸村子上女性的乳房,并寄托美好的祝福,并且在“雪集”上買賣不可以說話,整條街寂靜無聲。另外,“我奶奶”和“我爺爺”在高粱地里的野合,這種粗魯而原始的欲望,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狂歡色彩,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當頭一棒。我“二奶奶”戀兒的奇死也是讓讀者看得冷汗淋漓,她莫名其妙的靈魂出竅以及被神怪附體的可怖描述,讓人身臨其境。他們小說中這些癲狂的、獨特的、非理性化的人物形象,無論美丑,都真實得讓人落淚。
最后,他們的敘述風格別具特色。第一,在文學創作上有著不羈的想象力。中國古代就有劉勰“神與物游”之說,沒有想象力便不會有成功的文學創作,而從小就是編故事能手的福克納和莫言自然以想象力見長。福克納曾說過,一個作家需要的三件工具就是經驗、觀察和想象力,而莫言也認為想象力是一個作家最寶貴、最重要的素質。他們在自己家鄉的基礎上構建了“郵票般大小”的藝術世界,在這個超級王國中講述著一代代家族的歷史興衰,描繪了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福克納側重于人物心理活動的內部想象,在《喧嘩與騷動》中,他塑造了班吉這個白癡的形象,通過想象他為我們呈現了傻瓜的思維方式:他會因為聽見的聲音或是聞到的氣味而聯想到大腦中過往的印象。福克納采用意識流的手法,恰到好處地將讀者引領到一個傻子的混亂思維中。相比較而言,莫言則比較善于外部的想象。在他的筆下,紅狗、綠狗、黑狗齊聚一堂,拉幫結伙啃食人尸;高粱酒因為“我爺爺”的一泡尿變得香醇無比,成了酒坊的釀酒秘方;戰斗中犧牲的啞巴雙眼圓睜,大口洞開,像是要吼叫……莫言的語言并不精煉,他鋪張浪費地使用著天馬行空的字眼,展現出“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東北高密鄉。第二,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自成一格。福克納擅長角度多元化的敘述,如《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等小說都是由若干個人物的獨立講述逐步呈現的。在福克納的小說中很少出現“他想”、“他說”這樣的字眼,很多對話以及想法像是從人物頭腦中直接涌出來的,從一個思緒跳到另一個思緒。尤其是在昆丁部分,一些反復出現的文字片段如“忍冬的香味”、“你有姐妹么”等等在正常的敘述中不斷閃現,體現了昆丁極度亢奮的精神狀態。在《喧嘩與騷動》中有一個打秋千的描寫,班吉的大腦里出現二十年前凱蒂趕走情人來安撫自己的場景,然而回到此刻卻是對著自己破口大罵的凱蒂的女兒小昆丁,這種蒙太奇的手法讓讀者產生強烈的對比,也極大地深化了家族道德淪喪的主題。而在莫言的小說中,大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或第一人稱敘事。全知視角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隨心所欲地敘述,極大地促進了小說敘述的狂歡。另外莫言重視民間文化,獨特的語言詞匯使他的小說別具特色。例如為了凸顯羅漢大爺的高大形象,他被打之后,“民夫們看著他血泥模糊的頭,吃驚的眼珠亂顫”,這樣的語言不僅給讀者帶來強烈的視覺沖突,讓人想象出“眼珠亂顫”的畫面,更能夠從側面表現出羅漢大爺的漢子氣魄。他還在作品中使用很多粗俗的比喻和詞匯,在第三章《狗道》的最后,豆官看到一個老頭子,小說中用了一句話來描述:“那老頭子渾濁的眼睛像兩攤鼻涕一樣粘在眼眶里”,就這么一句話,卻能夠形成強烈的畫面感,難怪會有人說莫言的小說不是電影更勝電影!莫言喜用色彩詞,通過色彩的變化表現人物情感,給人物的主觀感覺賦予色彩。《紅高粱家族》中有一段描寫戰斗時的場景,負責吹號的劉大號,“一條腿跪著,舉起大喇叭,仰天吹起來,喇叭里飄出暗紅色的聲音”,這種陌生化的效果給讀者帶來獨特的閱讀體驗,神經不斷抽跳著,讓人印象深刻。福克納與莫言不受理性控制的敘述方式,正是在酒神精神影響下的自然體現,這種敘述的狂歡之美,也正是對酒神精神最好的詮釋。
(二)人性的自然之美
佛斯特說過:“我們可以對人性不喜歡,但如果我們把它從小說中祛除或滌凈,小說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廢字。”[11]18由此可見,文學即人學。福克納與莫言都十分注重對人物的塑造,無論是英雄、惡棍還是少女、婦女,在他們筆下都被刻畫得深入人心,在文學的長河上熠熠閃光。
福克納善于揭示人性的弱點。在小說《喧嘩與騷動》中,幾乎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局限性,福克納透過細膩的描寫展現出來。康普生家庭籠罩在灰蒙蒙的壓抑氣氛中,康普生先生醉醺醺地消極處事、康普生太太自私冷酷又愛無病呻吟、昆丁懦弱消極又神經質、杰生懷著仇視的目光看待一切、白癡班吉整天哼哼唧唧、就連逐漸長大的小昆丁也對著偏袒自己的女傭迪爾西罵罵咧咧……這些被現代社會的金錢、虛榮、安逸所異化了的一群人,在福克納筆下栩栩如生。因為妹妹凱蒂的不貞潔,昆丁的精神陷入了掙扎之中,福克納運用大量的意識流和閃回的手法,將讀者帶入昆丁混亂的精神世界。身為長子,昆丁自認為身負維護家族聲譽和舊傳統的重任,他將妹妹的貞潔與之相聯系,然而他是如此的軟弱,在與達爾頓·艾密司決斗時,在對方根本沒有打自己的情況下“像一個女孩子那樣的暈了過去”!然而在這樣一個沉悶陰暗的環境中,凱蒂像是一抹亮色,深為福克納心愛,福克納甚至說:“我愛上了我的人物中的凱蒂。”*轉引自M.E. Coindereau,The Time of William Faulkner(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17),p.41.凱蒂和兄弟們在水邊玩耍,弄臟了內褲,這時候昆丁就在一邊數落她,這個細節十分重要,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筆。內褲臟了,暗含著凱蒂的失身,而兒童時期的昆丁對妹妹的數落也隱喻昆丁對妹妹貞潔的重視。大姆娣去世的時候,孩子們被禁止呆在家里,只有凱蒂爬上了樹偷看。她像一個假小子,大嗓門、喜歡當國王讓別人聽自己的命令、像媽媽一樣照顧自己的白癡弟弟班吉。可以說凱蒂給了班吉如母親般的關愛,她為了班吉拋棄香水、離開情人,這些都體現了凱蒂的自然和善良。她像普通女孩子一樣向往愛情,并為之奮不顧身終不后悔。小說中有一段昆丁與凱蒂的對話,昆丁詢問凱蒂是否愛達爾頓·艾密司,“她瞧著我接著一切神采從她眼睛里消失了這雙眼睛成了石像的眼睛一片空白視而不見靜若止水”,[9]196凱蒂把昆丁的手放在自己的咽喉上,讓昆丁說達爾頓的名字,“我感到一股熱血涌上她的喉頭猛烈地加速度怦怦搏動著”。這段文字讓人動容,顯而易見凱蒂是愛著達爾頓的,她毫不避諱自己的喜歡,坦然地面對家人的非難。盡管在小說中凱蒂是墮落的,她最終為了家族的名譽而流落在外,成了納粹軍官的情婦。但是福克納依然對凱蒂有著特殊的情感,凱蒂曾對自己的哥哥昆丁說過“我反正是個壞姑娘你攔也攔不住我”,而小昆丁也對自己的舅舅杰生說“我很壞,我反正是要下地獄的,我不在乎。”但是凱蒂是一個身上有著樹的香味的自然之女,她的身上閃現著人性光輝,盡管凱蒂最終是悲劇收場,但是她對愛情的追逐、對人性自由的追求是頗受肯定的。
相比較而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的色彩就比較濃烈,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有狂歡之美。如果說在《喧嘩與騷動》中,大部分的人性是被壓抑著的,那么在《紅高粱家族》里,人性的自然之美被渲染到了極致。“河灘上的狗蛋子草發瘋一樣生長,紅得發紫的野茄子花在水草的夾縫里憤怒的開放”,[6]226這種瘋狂怒放的狀態,正是東北高密鄉最自然原始的生存狀態。小說中有一段對“我奶奶”哭聲的描寫,尤為動人:“哭聲婉轉,感情飽滿,水分充沛,屋里盛不下,溢到屋外面,飛散到田野里去,與夏末的已受精的高粱的綷縩聲響融洽在一起”,[6]80將“我奶奶”的哭聲與大自然相結合,可見“我奶奶”是大自然孕育的女兒,她在高粱地里初嘗愛情之果、在高粱的庇護下風生水起地經營酒坊、在殷紅的高粱地中如蝴蝶般翩然死去……無疑“我奶奶”不僅是抗日女英雄,也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范。她剪的梅花鹿的窗花,在背上生出一枝紅梅花,以一種自由獨立的姿態,昂首挺胸地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奶奶”活得自然,想哭的時候便哭,想笑的時候就笑,她敢愛敢恨,當“我爺爺”為了“二奶奶”戀兒搬到別的村上時,“我奶奶”毫不示弱地跟了鐵板會的頭子黑眼,“我爺爺”和黑眼為了她爭斗,她“頭發溜溜的亮,臉頰艷艷的紅,眼睛灼灼的明,模樣實實的可愛又可恨”。“我奶奶”愛得瘋狂、恨得灑脫,她蔑視人世間的堂皇說教和道德,當子彈穿透她挺拔的乳房時,“我奶奶”的英魂也在這片茂盛的高粱地里翩然紛飛,天地間充斥著異常壯麗的色彩!
福克納在1949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說:“我拒絕接受世界末日的觀點……我不認輸。我認為人類不僅會延續,還會勝利。”莫言也曾在《紅高粱家族》的卷首寫道:“僅以此書召喚那些流浪在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他們的小說都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熱切肯定生命。福克納的作品中,無論是黑人小廝還是南方淑女,都力求擁有鮮活的生命,勒斯特渴望去看戲、迪爾西用自己的錢給班吉買生日蛋糕、凱蒂從不否認自己內心對自然人性的渴望。而莫言更是在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張力的形象,英雄身上充滿血性和匪氣、母親有著寬厚博大的內心、女性身上充滿了自由和獨立……福克納與莫言都肯定生命中非理性的方面,呼喚原始的生命強力,同時他們也深刻地意識到了民族“種”的倒退。他們似乎都對“過去”有著強烈的崇敬,推崇過去,認為今不如昔,著眼于當下的情形以襯托出昔日的輝煌。《喧嘩與騷動》中,康普生家族由勝轉衰,不僅僅是往日的輝煌不在,更是“種”的衰落。這也與福克納自己家族的發展有關,在他曾祖父時代如此輝煌,然而到了他父親的時代便光輝不再。康普生先生身上有著福克納父親的影子,他們都嗜酒、都沒有勝任壯大家族的歷史使命。《紅高粱家族》更是熱烈地歌頌原始生命力,小說處處透露著如純種紅高粱般強韌、茂盛、壯麗的色彩。“如果秋水泛濫,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紅色的高粱頭顱擎在渾濁的黃水里,頑強的向蒼天呼吁”,這樣高昂著頭顱的生命力,正為莫言所歌頌:“這就是我向往的,永遠會向往著的人的極境和美的極境。”[6]361
無論是在敘述上,還是在對人物的塑造、對人性的描寫上,福克納與莫言都處處體現酒神精神。福克納的人物有著掙扎狂歡的內心世界和自然原始的人性之美,莫言筆下的人物有著強烈的生命意志和原始的欲望追求,他們運用異曲同工的方法,將人性的扭曲和聳動的野性美展現在讀者面前,在酒神精神指引下進行著藝術的狂歡。
三、酒神的歡歌——福克納與莫言酒神精神的美學價值
20世紀時期的歐美現代文學,重視對個人的內心世界的探索,摒棄理性,作家如龐德、艾略特、喬伊斯、沃爾夫、福克納等人,無論從作品內容還是從他們的創作手法來看,都深受狄奧尼索斯精神的影響。福克納小說中充滿了非理性的敘述,“他的獨白就是他本人的非理性,他把它放入他所寫人物的心靈。人物的獨白和作為講述者自己的獨白合而為一,也來回于往昔之間。”[10]120福克納坦言《喧嘩與騷動》是自己花費最多心血的作品,一共寫了五遍,用足了功夫。他通過對人物命運的創設,通過讓人難以理解的晦澀語言以及毫無過渡機制的意識流手法,為讀者展現了康普生家族的悲劇歷史、美國南方的受難史。福克納對酒神精神的表現是壓抑著的,他從反面來描寫,通過對人物內心的細致描述,表現壓抑酒神精神所導致的悲劇:凱蒂最終聽從命運的安排,嫁作他人婦,不再為了自己的愛情和幸福抗爭,她沒有像自己之前說的那樣“你攔也攔不住我”,而是順從地放棄了抗爭,最終她無家可歸淪落風塵;昆丁是清教主義的維護者,然而他懦弱的肩膀承擔不起維護家族榮譽的重任,凱蒂的失身使他失去精神平衡,他否定凱蒂的真愛,一味地渴望妹妹是被迫的,他蒙蔽自己,生活在過去與現實的虛幻中,最終自殺;杰生在金錢利益下迷失自我拋棄親情,在銅臭的錢眼里扼住自己的欲望,甚至對自己的情人也防之又防,他不懂什么是愛,只有悲哀的活著,正如小說中的描述“他那無形的生命有如一只破襪子,線頭正在一點點松開來”[9]342;班吉的可悲在于他本是個白癡,他的母親認為班吉是上帝給她的懲罰,因而整天無病呻吟,凱蒂因為他拋棄過自然的原始情感,因為追逐放學的女學生,班吉毫無概念地接受了非人道的閹割手術,最終在1933年被送進精神病院……雖然福克納對自己創造的人物有著特殊的情感,但是并不代表他贊同人物在過去的做法,《喧嘩與騷動》中,金錢取代了家庭內部的感情:杰生想盡辦法占有凱蒂寄給小昆丁的生活費;小昆丁不在乎母親說了什么,只關心寄來了多少錢;康普生太太愚昧地以為燒掉凱蒂的支票就可以證明自己與女兒毫無關系……小說中每當聽到哭聲,班吉就會說聽到有人在唱歌,這是一曲資本主義金錢世界的哀歌,是資產階級道德淪喪的哀歌。在尼采的哲學闡述中,古希臘悲劇源于酒神祭祀,而希臘悲劇的人文主義就是酒神精神,當人與人之間的裂痕極為強烈時,酒神精神引導人們回歸大自然、復歸原始生命,此時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等級卑賤之分,在酒神精神的支配下,人的每個細胞都充滿著狂喜與幸福,一切原始沖動都得到釋放。而福克納的小說正是充滿了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對種族問題和女性問題的關注,成為對酒神精神最好的詮釋。
莫言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演講時,曾坦言“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使他明白了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然而莫言也意識到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為了保有自我,莫言很快逃離了他們,構建有著自己獨特味道的文字王國。相比較而言,莫言對酒神精神的表現是熱烈的,他的作品讓讀者深刻感受到酒神迷狂、沉醉,不受世俗束縛、追求自在生命原欲的特點。莫言筆下的語言文字達到了狂歡的極致,它們隨心所欲地組合堆砌,使自己擁有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莫言也深愛著自己筆下那些有著強大生命力和自然原始的人性欲望的男女,他們敢愛敢恨、敢作敢為,他們抗爭、奔走、哭號、豪飲、野合……這些肯定生命本能的活脫脫的生靈,在滿是殷紅血淚的大地上頑強生長,如同一茬又一茬的紅高粱,茂盛地歡唱!《紅高粱家族》中洋溢著一種精神,一種能夠洗凈“可憐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了靈魂的”孩子們的肉體和魂魄的“純種紅高粱精神”,莫言以尼采式的吶喊呼喚人性的復歸,使他的人物永遠充滿著不死的生命力。他敏銳地意識到現代人“種”的退化,指出這種退化體現在民族性格、心理素質以及民族生命活力上,“面對生命世界的大法則,那些世俗世界的小倫理顯得那樣虛弱不堪;面對酒神那英雄的迷狂和洶涌的詩意,日神統治下的理性、道德、一切功利化的價值判斷,則顯得那樣渺小卑俗;面對‘既殺人放火又精忠報國’的爺爺奶奶壯麗的人生,‘我’‘深切地感到種的退化’”。[12]而酒神引領著我們不惜一切努力尋找到那株生長在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的純種紅高粱,“高舉著它去闖蕩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6]362小說中的“純種紅高粱”就是自然生命的象征,它燃燒著生命之火、欲望之火,而“高粱酒”則是酒神精神的象征,莫言在西方文化的啟發下,創作出《紅高粱家族》這樣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狄奧尼索斯式”的經典,開辟了一條獨具莫言特色的文學道路。
酒神精神帶有砸碎一切道德束縛、釋放生命原欲的狂歡壯闊之美,酒神式的作品則具有狂放不羈,充滿野性、激情和感性等特點。福克納與莫言的作品中洋溢著酒神精神,他們在各自的文學王國里大顯身手,盡管敘述手法和對人物的塑造各有特色,但是都追求狂歡的敘述之美和自然原始的人性之美。他們用細膩的筆觸描寫人物內心、敏銳地注意到現代人“種”的倒退、關懷人類命運、關注種族與婦女問題,渴望人性平等、歌頌健康的原始生命活力……正是在這種酒神精神的引領下,福克納與莫言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更為深邃、更加生機勃勃的世界,用酒神狄奧尼索斯的歡唱,喚醒人類最為原始、最為美好的靈魂。
[1]尼采.偶像的黃昏[M].周國平,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
[2]王晉生.論尼采的酒神精神[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
[3]肖明翰.威廉·福克納——騷動的靈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莫言.童年的讀書夢[J].新一代,2011(5).
[5]朱賓忠.跨越時空的對話——福克納與莫言比較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6]莫言.紅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7]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8]李喬.小說入門[M].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9]威廉·福克納.喧嘩與騷動[M].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10]李文俊.福克納評論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11]E.M.佛斯特.小說面面觀[M].蘇炳文,譯.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
[12]張清華.敘述的極限——論莫言[J].當代作家評論,2003(2).
[責任編輯:姚曉黎]
On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s Dionysian Spirit
ZHU Zheng-lin
(School of Lit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Their creation has strong Dionysian spirit,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life course. In writing,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beauty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carnival. Their image shaping is full of natural beauty of human. Dionysian spirit has profoundly been reflected in the novel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d “Red Sorghum Family”, which shows the carnival in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s life and art.
Faulkner;Mo Yan;Dionysian spirit;“The Sound and the Fury”;“Red Sorghum Family”
2015-06-23 作者簡介: 朱崢琳(1991-),女,江蘇徐州人,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1671-5977(2015)03-0102-07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