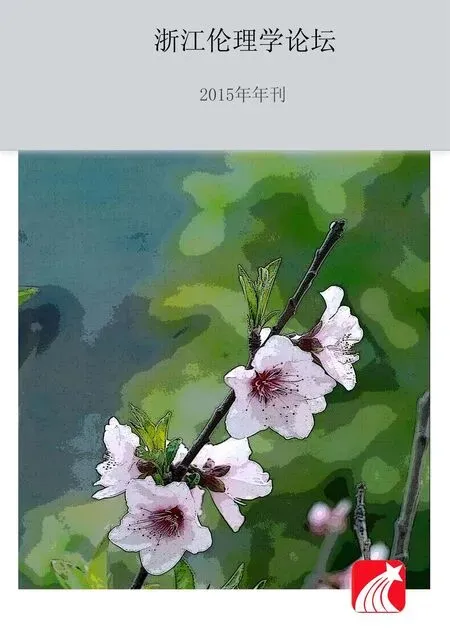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誰的困境?
——兼與李建華、胡祎赟和龔群先生商榷
方紅慶
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誰的困境?
——兼與李建華、胡祎赟和龔群先生商榷
方紅慶①
德性倫理學(xué)以行動者為中心,關(guān)注道德主體自身的品格,區(qū)別于規(guī)范倫理學(xué)以規(guī)則為基礎(chǔ)的根本特性,但是其當(dāng)代復(fù)興之路卻遭遇了現(xiàn)代困境。根據(jù)阿奎那的教誨,一條可能的出路在于把德性倫理建立在道德的自我性基礎(chǔ)之上,并且根植于善的形而上學(xué)之中,從而為道德自我注入實質(zhì)內(nèi)容和統(tǒng)一性基礎(chǔ)。總之,德性倫理學(xué)的現(xiàn)代困境首先是現(xiàn)代社會本身缺乏統(tǒng)一的道德自我或?qū)е伦晕业钠扑榛?其次才是德性倫理學(xué)的困境,即缺乏強有力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兩者既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秩序顛倒。
德性倫理;困境;自我性;善的形而上學(xué);阿奎那
德性倫理的復(fù)興是當(dāng)代倫理學(xué)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現(xiàn)代倫理學(xué)和現(xiàn)代社會雙重困境的反思結(jié)果。但是當(dāng)代德性倫理學(xué)的復(fù)興之路并非一帆風(fēng)順,有學(xué)者認(rèn)為它在現(xiàn)代社會必然會遭遇困境,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就是麥金泰爾的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社會困境論,即德性倫理學(xué)根植于傳統(tǒng)社會,因此,它不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而必然會面臨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的困境。
李建華和胡祎赟的《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一文基本上沿襲了麥金泰爾的思路,并最終得出結(jié)論說:“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的公共轉(zhuǎn)型乃是導(dǎo)致傳統(tǒng)美德倫理(學(xué))逐漸式微并陷入深刻危機的最終原因。”②李建華、胡祎赟:《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哲學(xué)動態(tài)》2009年第5期,第39頁。龔群的《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回應(yīng)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論》③龔群:《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回應(yīng)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論》,《哲學(xué)動態(tài)》2009年第5期。對這篇論文做出了回應(yīng),他堅持德性倫理學(xué)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必要性,并提出三條理據(jù):(1)反對麥金泰爾的自我的碎片化觀點,主張在現(xiàn)代社會中發(fā)生的只是人格的變化;(2)現(xiàn)代社會依然需要德性,只是相對于傳統(tǒng)社會,德性的位置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3)功利主義和道義論沒有窮盡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需求,而德性倫理是它們的重要補充。但是,實際上龔群依然沿襲了麥金泰爾對于現(xiàn)代社會和德性倫理的基本關(guān)系的界定,而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在于在現(xiàn)代社會提倡德性倫理的失敗到底意味著德性倫理的一般困境,還是僅僅表明古代德性倫理在現(xiàn)代的困境。筆者認(rèn)為德性倫理學(xué)與社會轉(zhuǎn)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德性倫理學(xué)的真正困境在于它缺乏可靠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
一、德性倫理與社會轉(zhuǎn)型
社會轉(zhuǎn)型是否是倫理轉(zhuǎn)向的充要條件?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兩個子問題: (1)一門倫理學(xué)是否必定要同某一個時代或某一社會類型相聯(lián)系?(2)一門倫理學(xué)是否有其自身存在的內(nèi)在根據(jù)?對于第一個問題,筆者認(rèn)為,武斷地給一個理論貼上時代或社會類型標(biāo)簽的做法是危險而又不近情理的。麥金泰爾在回顧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傳統(tǒng)的時候,就把倫理學(xué)與城邦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系問題視為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否則就會危及整個亞里士多德理論的結(jié)構(gòu)。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繼承思想,卻無法繼承時代,亞里士多德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已經(jīng)永遠(yuǎn)去如黃鶴了,如果亞氏倫理學(xué)同他的時代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我們?nèi)绾文軌蛘嬲^承他的倫理學(xué)呢?
當(dāng)代很多研究德性倫理學(xué)的學(xué)者們把它們之間的不可分離性作為一個前提,進而得出德性倫理在現(xiàn)代存在適應(yīng)性困難的結(jié)論。在筆者看來,李建華和胡祎赟就犯了這種錯誤:他們預(yù)先把社會劃分為古代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把倫理學(xué)也相應(yīng)地劃分為德性倫理和規(guī)范倫理,預(yù)設(shè)古代社會與德性倫理相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與規(guī)范倫理相適應(yīng),進而以我們所處的社會是現(xiàn)代社會這一事實為由,順理成章地得出德性倫理在現(xiàn)代社會必然遭遇困境的結(jié)論。同時,這樣一個結(jié)論也是混淆視聽的,因為,這個結(jié)論似乎告訴我們,出問題的只是德性倫理的一方,而現(xiàn)代社會本身卻沒有什么問題或至少在處理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時不用考慮,這實際上會遮蓋現(xiàn)代社會本身存在著深刻的危機這一事實,轉(zhuǎn)而單純?nèi)ジ脑斓滦詡惱硪赃m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從而完全忽視了用德性倫理去引導(dǎo)和改造社會這一倫理學(xué)具有的特殊的教化功能。
對于第二個問題,筆者認(rèn)為德性倫理學(xué)具有更為強烈的理想特征,因為它涉及的是我們行為者本身的道德品質(zhì),一種單純內(nèi)在的特質(zhì),并不是直接可觀察的,總之,德性倫理要求更高的道德自律。所以,它從誕生以來一直便同現(xiàn)實社會,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現(xiàn)代社會,保持著相當(dāng)?shù)木嚯x。從歷史的角度看,古代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zhuǎn)型并不一定會導(dǎo)致德性倫理的毀滅,德性倫理的理想特性恰恰是它在劇烈社會變革下的生機所在,因為人性總是存在某些穩(wěn)定持久的東西,或者說,人類社會不管如何變遷,總是崇尚某些共同的道德品質(zhì),諸如勇敢、果斷、誠信等等。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xué)的人性論固然是我們所要拋棄的,但是我們并不一定要接受完全歷史性的人性。因此,筆者同意龔群說:“因此,并非是在一般意義上,德性倫理在現(xiàn)代社會遭遇困境;如果說有困境,也僅僅是在傳統(tǒng)德性的意義上。即使如此,人們也不能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式的德性倫理對于現(xiàn)代生活沒有意義。”①龔群:《德性倫理與現(xiàn)代社會——回應(yīng)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論》,《哲學(xué)動態(tài)》2009年第5期,第43頁。但是他的論證卻顯得有些拙劣而且犯了同李建華先生一樣的錯誤,他說:“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契約社會,一個通過契約來確定身份的社會,人們有著自由的身份。在現(xiàn)代社會,職業(yè)領(lǐng)域的規(guī)則要求而不是德性要求成為倫理學(xué)關(guān)注的重心,責(zé)任或義務(wù)成為現(xiàn)代倫理學(xué)的中心概念。因此,復(fù)興德性倫理學(xué),把傳統(tǒng)社會的規(guī)范倫理學(xué)模式推廣到現(xiàn)代社會,必然不合時宜。”②同上,第41頁。
這是一個典型的乞求問題(question-begging)論證,因為它事先預(yù)設(shè)了現(xiàn)代社會同德性倫理學(xué)是不相容的,進而以此為據(jù),得出德性倫理學(xué)的現(xiàn)代復(fù)興是不合時宜的結(jié)論。也許龔群先生會說他只是認(rèn)為德性倫理學(xué)不能夠成為現(xiàn)代倫理學(xué)的中心,然而,這并不能表明德性倫理學(xué)不能在現(xiàn)代社會得到推廣,而只能說德性倫理學(xué)應(yīng)該作為規(guī)范倫理學(xué)的一個有益補充。筆者相信這也是龔群所要表達(dá)的一個基本思想,然而即使是這樣一種觀點,在筆者看來也是偏頗的,因為它在骨子里依然蘊含著這一預(yù)設(shè),而我們的問題恰恰是:德性倫理學(xué)為什么不可以凌駕于規(guī)范倫理學(xué)之上成為現(xiàn)代倫理學(xué)的中心呢?這便涉及如何定位倫理學(xué)的問題。筆者認(rèn)為,“倫理學(xué)的首要任務(wù)似乎應(yīng)當(dāng)是處理基本生活領(lǐng)域,而非自我實現(xiàn)的事情”③李建華、胡祎赟:《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哲學(xué)動態(tài)》2009年第5期,第36頁。這樣一種對倫理學(xué)的定位在根本上是錯誤的。首先我們拋開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不管,單單把德性倫理學(xué)視為是一種關(guān)于自我實現(xiàn)的倫理學(xué)在根本上就已經(jīng)錯誤了,筆者稍后將詳細(xì)論述這一點。
筆者深為擔(dān)憂的是,國內(nèi)學(xué)界把麥金泰爾的德性倫理的現(xiàn)代社會困境論當(dāng)成理解倫理學(xué)與現(xiàn)實社會關(guān)系的一個基本范式。事實上,這種論調(diào)的根源在于社群主義,正如瑞斯特(J.M.Rist)批評社群主義包含了兩個錯誤的觀點:(1)強調(diào)傳統(tǒng)的反個體主義方面;(2)傳統(tǒng)會隨時間推移“合理地”發(fā)展。前者導(dǎo)致對道德的客觀安全基礎(chǔ)的隨意態(tài)度;后者則導(dǎo)致不能區(qū)分個人傳統(tǒng)的本質(zhì)特征和偶然特征。①John M.Rist:Real Ethics:Re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5.
總之,當(dāng)代倫理學(xué)的德性轉(zhuǎn)向表明,單純的規(guī)范或制度不足以滿足整個社會的倫理需求,倫理學(xué)也不應(yīng)該成為一門單純的技藝學(xué),也許我們可以在尼采身上尋找到靈感:形而上學(xué)地看待道德。當(dāng)然,我們不是要把倫理學(xué)視為一門形而上學(xué),而是要讓倫理學(xué)保持形而上學(xué)的特性。筆者認(rèn)為,德性倫理學(xué)很好地實現(xiàn)了這一點,并且它應(yīng)該在格位上高于規(guī)范倫理學(xué),因為前者是后者的向?qū)c最終指向。
二、麥金泰爾的德性概念及其缺陷
麥金泰爾企圖在歷史傳統(tǒng)中尋找一個統(tǒng)一的、核心的德性概念。這個概念的一個特征就是“它的運用總是需要承認(rèn)對于社會和道德生活中的某些特征的某些在先的解說,因為對它的界定與解釋必須依據(jù)這些在先的解說”②[美]A.麥金太爾:《追尋美德:道德理論研究》,宋繼杰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頁。,麥金泰爾把這種在先的東西稱為“概念背景”,它構(gòu)成了德性概念的先決條件。麥金泰爾把這個德性的核心概念分為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各自不同的概念背景,但是前一階段嚴(yán)格地決定后一階段,反之則不然,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當(dāng)代德性倫理理論。
德性的核心概念的第一要素就是“實踐”,意指任何融貫的、復(fù)雜的并且是社會性地確立起來的、協(xié)作性的人類活動形式。通過實踐,內(nèi)在于該活動的善可以實現(xiàn),這意味著它必須在某些卓越標(biāo)準(zhǔn)之下活動,即同善的規(guī)則保持一致。第二個要素就是人生的敘事秩序,總的說來,它為我們提供了過完整的生活所必需的統(tǒng)一性,并且構(gòu)成了自我的意義的源泉。第三個要素就是道德傳統(tǒng),這便同某個共同體相關(guān)。麥金泰爾認(rèn)為,“我”的生活故事始終穿插在“我”從其中獲得“我”的身份的那些共同體的故事中。這句話不僅點明了第二個要素為第三個要素提供了本質(zhì)性內(nèi)容,而且反過來說明共同體的故事又對自我本質(zhì)的塑造提供修正方案。總之,自我本質(zhì)是有個人身份、社會身份和歷史身份共同塑造的。
進而麥金泰爾給出了德性定義:“德性是一種獲得性的人類品質(zhì),對它的擁有與踐行使我們能夠獲得那些內(nèi)在于實踐的善,而缺乏這種品質(zhì)就會嚴(yán)重妨礙我們獲得任何諸如此類的善。”①John M.Rist:Real Ethics:Re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42.因此,麥金泰爾的德性依然是社會性的、歷史性的德性,缺乏形而上學(xué)的根據(jù)。事實上,麥金泰爾依然受語言哲學(xué)轉(zhuǎn)向以來對形而上學(xué)保持某種隔絕或?qū)徤鲬B(tài)度的影響,它直接導(dǎo)致了麥金泰爾的德性倫理學(xué)缺乏形而上學(xué)維度,只想在歷史實踐的維度內(nèi)尋找德性的根基。從上面對德性的定義來看,這種定義表現(xiàn)出一種令人絕望的“形式”特征,因而,麥金太爾對康德倫理學(xué)的形式特征的批評反過來同樣適用于他自身。
形而上學(xué)研究和道德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這個傳統(tǒng)源自于柏拉圖,他試圖通過對自然本身基本性質(zhì)的探究來證明存在一種自然的和客觀的道德,即為道德提供實在論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對于柏拉圖來說,《理想國》的目的在于解釋由智者們所導(dǎo)致的道德相對主義問題的嚴(yán)重性,道德必須建立在一種特定的形而上學(xué)之上。在下一節(jié)中,筆者將引入阿奎那的德性倫理學(xué),他作為一個新柏拉圖主義者,實際上踐行了柏拉圖的這一傳統(tǒng),正如斯坦普(E.Stump)和克賴茨曼(N. Kretzmann)所說,“他的倫理學(xué)完全建立在他的形而上學(xué)之上”②E.Stump,N.Kretzmann:Being and Goodness,From S.Macdonald(ed.):Being and Goodness: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in Metaphysics and Philosophical Theolog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98.,而德洛里奧(Andrew J.Dell'Olio)則更進一步認(rèn)為“阿奎那的倫理學(xué)不僅根植于更大的形而上學(xué)觀點之中,而且這個形而上學(xué)觀點在本質(zhì)上是有神論的”③[美]安德魯·J.德洛里奧:《道德自我性的基礎(chǔ):阿奎那論神圣的善及諸德性之間的聯(lián)系》,劉瑋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
此外,對道德的充分論述既依賴于我們對人性的詮釋,也取決于我們劃分人性的方式,正如瑞斯特所說,倫理學(xué)或明或暗地與人性相關(guān),而最好的道德理論是與更真實、更可辯護的人性解釋相關(guān)聯(lián)的。④John M.Rist:Real Ethics:Re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7.許多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的批評者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在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中占主導(dǎo)地位的做法是以特定的客觀原則或準(zhǔn)則確定正確的行動,而不是以一個主體的品格為標(biāo)準(zhǔn)去描述好人,即個體的道德自我。筆者認(rèn)為,這樣一個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能得出德性倫理關(guān)注的只是“自我實現(xiàn)的事情”這一結(jié)論,因為任何一門倫理學(xué)都是一門關(guān)乎自我完善的事業(yè),只是關(guān)注的重點不同而已。麥金泰爾批判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缺乏一個統(tǒng)一的道德自我概念,究其根由,是因為現(xiàn)代道德把道德義務(wù)的概念植根于普遍原則或規(guī)范之正當(dāng)性的啟蒙籌劃:現(xiàn)代的道德自我同所有欲望相分離,自我成為了一個完全自主的行為主體,一個缺乏實質(zhì)的形式自我,從而遠(yuǎn)離個人可能獲得的任何性格特征,只從一種單純普遍和抽象的視角做出判斷。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的一個主要批評者伯納德·威廉斯認(rèn)為:“一個特定的個體具有他自己的一套欲望和關(guān)注,或者就像我經(jīng)常說的那樣,具有他自己的生活計劃,而那些計劃有助于構(gòu)成一個品格。”①[英]伯納德·威廉斯:《道德運氣》,徐向東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中的自我不是一個道德自我,因為它缺少善的概念,因而無法對道德選擇做出評斷。另外,因為其本質(zhì)上的形式特征使得它缺乏在任何特殊方向上的塑造能力。因此,為了確定人類完善自我所需要的品格特征或德性本質(zhì),我們就需要首先考慮是什么構(gòu)成了人類的善。
總之,麥金泰爾對德性概念的定義涉及一個重要概念,即實踐的善,然而他的善概念在根本上是缺乏實質(zhì)的。麥金泰爾的實踐的善不過是整個人生的目的,然而因為德性的第二階段即人生的敘事結(jié)構(gòu)的目的在于決定一個人的行為并建立起他完整的善,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實踐的善與德性概念不過是在相互規(guī)定,原地打轉(zhuǎn),而要使德性獲得實質(zhì)內(nèi)容就必須像亞里士多德或阿奎那那樣構(gòu)建起一種客觀善或者說引入善的形而上學(xué)維度。此外,倫理學(xué)總是同“自我”這一概念息息相關(guān),尤其同德性和善的概念相關(guān),所以接下來我將圍繞德性、自我和善的概念來揭示德性倫理學(xué)的前世今生,從而得出德性倫理學(xué)必須具備某種形而上學(xué)維度才能立足于現(xiàn)代社會的結(jié)論。
三、德性、自我與善:德性倫理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
美德是一個人達(dá)到完善所需要的品格特征,因此,對它的本質(zhì)的思考必須從人的自我完善的本質(zhì)開始,那么到底什么構(gòu)成了人類的善呢?善的形而上學(xué)構(gòu)成了阿奎那的德性倫理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加拉格爾(D.M.Gallagher)所說:“對托馬斯來說,善首先是一個形而上學(xué)概念。”②D.M.Gallagher:Aquinas on Goodness and Moral Goodness,From D.M.Gallagher(ed.):Thomas Aquinas and His Legacy,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4,p.27.因此,在筆者看來,阿奎那給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能夠為德性倫理學(xué)在現(xiàn)代社會所遭遇的危機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
阿奎那把善分為自然的善和超自然的善,前者是可以通過人類的自然能力達(dá)到的,后者則需要神圣恩典的注入,它們分別構(gòu)造人類的自然目的和超自然目的。但是這種雙重性對道德自我的統(tǒng)一性構(gòu)成了威脅,挽救方式就是要把人類的善建立在一個足夠豐富,因而可以容納雙重終極目的的關(guān)于善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之上。這里的“形而上學(xué)”指的是建立一個整體的“世界觀”的嘗試,而阿奎那的形而上學(xué)就是上帝中心論,他認(rèn)為上帝是最具實在性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源泉,一切存在的目標(biāo),不管這一個觀念是通過理性還是通過啟示達(dá)到的。總之,阿奎那的倫理學(xué)植根于其善的形而上學(xué)。
許多研究者認(rèn)為,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論題構(gòu)成了阿奎那倫理學(xué)的元倫理學(xué),事實上也是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它源于奧古斯丁的“因為我們存在所以我們善”①Augustine:On Christian Doctrine,M.Dods(trans.),T.&T.Clark Co.,2004,pp.1871—1876.。存在與善互換的路徑有兩個:柏拉圖主義的“分有”路徑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路徑。柏拉圖主張善的理念是所有理念的理念,因而一切理念都分有了善的理念,即所有的事物都通過善的流溢過程而進入存在,并最終回歸善。所以,在柏拉圖看來,善的缺失就是存在的缺失。
亞里士多德是以目的論的方式來理解善的。善本身是通過本質(zhì)的滿足或完成而得到理解的,而同時這個本質(zhì)又規(guī)定了事物的存在,所以善的滿足就是存在的實現(xiàn)。一個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是因為通過展現(xiàn)其固有能力而實現(xiàn)了內(nèi)在于它的善,所以實現(xiàn)了的善就是一種內(nèi)在于自然事物的一種狀態(tài)。
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主義的“分有”路徑很容易為基督教神學(xué)所利用,只要把永恒的理念變成上帝就可以了。事實上,基督教的新柏拉圖主義就是這么做的,因而“分有”路徑很自然地被阿奎那用于解釋人類的超自然的目的或善的神圣恩典的注入,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路徑則用于解釋人類“自然”目的或善的實現(xiàn)方式。進一步而言,“自然”路徑其實是“分有”路徑的某種形式,因而,在自然的善與超自然的善之間并非截然兩分的:自然的善和超自然的善只是人類分有神圣善的兩種方式,前者從屬于后者,并且這兩種善構(gòu)成了自然和超自然德性之間聯(lián)系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
那么,自然的善究竟意味著什么?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同自然的善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自然的善又何以必須服從于超自然的善呢?“善”總是同“完善”的概念相聯(lián)系,“完善”意味著事物的“完成”狀態(tài),因而預(yù)示著到達(dá)事物發(fā)展的終點或目的,只有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事物才是現(xiàn)實的,才是“善的”。“因此,在阿奎那看來,成為完善的就是進入‘實現(xiàn)’,也就是一事物將潛在完全表達(dá)出來的狀態(tài)”。事物從潛在向存在的過渡也是事物成為善的過程,這也是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的論題的真正含義所在。
自然的人類善是由“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所構(gòu)成,這種生活方式由那些使個人完善的所有善和行為構(gòu)成,并且由實踐理性以最完滿的方式規(guī)定。然而,問題在于理性本身是否足以構(gòu)成倫理的基礎(chǔ),或者說,理性是否能夠足以成為道德行為的標(biāo)準(zhǔn)。
阿奎那當(dāng)然認(rèn)為理性可以成為衡量我們?nèi)祟惿茞旱臉?biāo)準(zhǔn),因為他說:“我們通過訴諸理性談?wù)撊祟愋袆拥摹啤c‘惡’。”①T.Aquinas:Summa Theologiae,McGraw-Hill,1968,p.892.理性使我們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種類,理智和意志分別是我們的認(rèn)知和意欲的理性能力,前者使得我們有意識地去從事實現(xiàn)我們自身本質(zhì)的行為,實現(xiàn)潛在向現(xiàn)實存在的過渡;又因為人類行為道德行為是意欲的對象,因而后者使得我們實現(xiàn)本質(zhì)的行為成為道德的、善的行為,使得存在與善保持同一。然而,我們不能單憑理性的沉思達(dá)到人生的完整,因為正如德羅里奧所說:“在阿奎那看來,不是人類理性自身,而是理性靈魂(即理智和意志兩種力量)的滿足或完善,構(gòu)成了人類的善。由于理性靈魂不能通過自然理性所能獲得的真或善達(dá)到其完善,人類理性自身的實現(xiàn)就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的。”②[美]德洛里奧:《道德自我性的基礎(chǔ):阿奎那論神圣的善及諸美德之間的聯(lián)系》,劉瑋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人類理性自身具有局限性。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理想來切近人類的終極目的,卻永遠(yuǎn)無法超越,這時需要的是神圣恩典的注入,即超自然的神圣的善或德性的存在。總之,人類的善不僅包括被有限的人類本質(zhì)所規(guī)定的善,還有神圣的善,兩者共同構(gòu)成善的形而上學(xué),從而為德性倫理學(xué)奠基。
那么,德性的本質(zhì)究竟是什么呢?德性又是如何植根于善的形而上學(xué)之中的呢?總的說來,阿奎那的德性定義可以歸結(jié)為如下四點:
(1)一種持久的性格特征,即整個個人的一種穩(wěn)定的性格或習(xí)慣;
(2)使一個人采取一致的良好的行動,即現(xiàn)成地、便利地和快樂地行動;
(3)朝向人類善的實現(xiàn)這一目的;
(4)貫穿整個一生的時間。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首先,德性同習(xí)慣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其次,德性總是同行動保持著某種因果聯(lián)系;再次,德性總是同善或人類的終極目的保持一致性關(guān)系;最后,德性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結(jié)果,它是我們靈魂的一種品質(zhì)。
從傳統(tǒng)角度看,“習(xí)慣”這個詞帶有強烈的形而上學(xué)意味。亞里士多德把它當(dāng)成一種永久的、難以改變的性質(zhì),進而認(rèn)為各種知識和德性都是習(xí)慣。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范疇篇 解釋篇》,方書春譯,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版,第30頁。為了更好地體現(xiàn)阿奎那的習(xí)慣的趨向性和目的性,最好把它理解為現(xiàn)代哲學(xué)意義上的“性格”。性格總是體現(xiàn)了存在狀態(tài),因而習(xí)慣也總是代表著朝向某種完成或?qū)崿F(xiàn)這一存在狀態(tài)的目的,同時也代表著我們總是預(yù)備著采取行動,因而習(xí)慣其實就是阿奎那的德性定義的核心。
然而,以習(xí)慣為核心的德性為什么總是朝向善呢?難道是習(xí)慣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價值取向?這當(dāng)然不可能,習(xí)慣總是有好有壞,習(xí)慣只是限定靈魂的能力,使這個能力以某種方式行動,因而習(xí)慣最終只不過是有可能實現(xiàn)善的一種中間狀態(tài)。實際上,在此我們遭遇了德性倫理學(xué)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但是這種困難的起因還是在于我們把德性倫理學(xué)視為是一門什么樣的倫理學(xué)的問題。倫理學(xué)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門學(xué)科,尤其是不同于自然科學(xué),它的前提是一種價值設(shè)定。德性倫理學(xué)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對人類終極目的或善的設(shè)定。在筆者看來,它同規(guī)范倫理學(xué)的根本沖突就在于規(guī)范倫理學(xué)不承認(rèn)這種設(shè)定,甚至認(rèn)為根本無需這種設(shè)定,因為它們主張以規(guī)則為基礎(chǔ),認(rèn)為規(guī)則本身就能提供道德的標(biāo)準(zhǔn)。另外,正如約翰·格雷所說的:“要討論倫理問題,我們并不需要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相反,我們探討倫理問題僅僅是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并不能結(jié)合在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中。”②[英]格雷:《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倫理學(xué)可以無需形而上學(xué)的奠基,相反,由于對體系的承認(rèn)已經(jīng)默認(rèn)了它的存在。所以,對德性倫理持過分悲觀的態(tài)度的原因不是出在德性倫理學(xué)本身,而是他們自身的合理性標(biāo)準(zhǔn)出了問題,倫理學(xué)永遠(yuǎn)不可能完全合理。
筆者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德性,乃至于麥金泰爾在當(dāng)代對它的改造都無法完全為德性倫理學(xué)找到堅固的基礎(chǔ),阿奎那意識到了自然主義無法為德性倫理學(xué)筑基,人類的善或德性必須要尋求一種高于自然秉性的超自然的善或德性的存在。在中世紀(jì),阿奎那綜合了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或奧古斯丁的傳統(tǒng)之后,德性倫理學(xué)似乎也窮盡了它的理論可能性;此后,隨著近代哲學(xué)的誕生,再加上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之后規(guī)范倫理走向了一個巔峰,德性倫理學(xué)幾乎消聲滅跡。綜觀當(dāng)代德性倫理學(xué)的復(fù)興,無論是以麥金泰爾為代表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德性倫理學(xué),還是以德羅里奧為代表的阿奎那式的超自然德性倫理學(xué),它們都沒有脫離出傳統(tǒng)框架的范圍。這不禁讓我們想要追問: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種中間道路?或者說,是否有一個東西可以取代上帝的形象?然而答案似乎都令人絕望,麥金泰爾在《追尋德性》之后對形而上學(xué)的默認(rèn),但又對阿奎那的神學(xué)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這些都反映了雖然德性倫理需要形而上學(xué)筑基,但是卻始終無法以一種自信的態(tài)度在現(xiàn)代社會中尋找到一個可以取代上帝的價值形象。然而,這也是現(xiàn)代社會的困境所在,而不僅僅是德性倫理的困境。
更為激進一點地說,筆者認(rèn)為德性倫理學(xué)所謂的困境根本不算困境,更加沒有同現(xiàn)代社會的適應(yīng)性困難。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拋棄對倫理學(xué)不可錯論的偏見,認(rèn)為倫理學(xué)必須能夠解決社會的各種倫理困境,進而更要正確理解德性倫理學(xué)的本質(zhì)。德性倫理學(xué)不是關(guān)于自我實現(xiàn)的倫理學(xué),它是關(guān)注道德的自我筑基的倫理學(xué),這是現(xiàn)代道德哲學(xué)所嚴(yán)重缺乏的東西,規(guī)范或規(guī)則在本質(zhì)上是外在于自我的。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貧乏的社會,自我無可奈何地破裂,而新的統(tǒng)一的自我卻杳無蹤跡,規(guī)范倫理既因此而盛,同樣也將因此而衰。
四、結(jié)語:當(dāng)代德性倫理學(xué)復(fù)興的內(nèi)涵與展望
當(dāng)我們回顧德性倫理學(xué)幾千年歷史的時候,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德性本身的框架或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發(fā)生了數(shù)次改變,因而當(dāng)代德性倫理學(xué)的一大任務(wù)就是如何在現(xiàn)代社會中發(fā)現(xiàn)德性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正是在這個方面,阿奎那對于當(dāng)代德性倫理學(xué)具有特殊的啟示意義。他向我們提供的這種關(guān)于德性的形而上學(xué)框架原理表明,德性倫理學(xué)本身必須關(guān)切人類總體的生存論狀況。對這種生存論狀況的把握是每一個時代的任務(wù),只有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wù),德性在這個時代才有了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才能契合這個時代的精神,滿足這個時代迫切的倫理要求。然而,現(xiàn)代社會正處于一個人類生存境遇極度不穩(wěn)定的狀況中,它導(dǎo)致了我們把握德性內(nèi)涵的困境,從而也是我們時代的倫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人類生存境遇同德性的如此密切的聯(lián)系決定了我們時代對德性倫理的呼喚,德性倫理當(dāng)代復(fù)興必須依循這個思路才有出路。
有鑒于我們時代的癥候,筆者認(rèn)為德性倫理應(yīng)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倫理。不過,現(xiàn)代倫理的格局必然是眾星拱月式的,但是它絕對不會像規(guī)范倫理在過去幾百年間所采取霸權(quán)式的做法,即排除其他倫理生存空間。德性倫理在格位上應(yīng)該高于規(guī)范倫理,并且它的應(yīng)用范圍不應(yīng)該定位于具體的道德行為,這是規(guī)范倫理應(yīng)該主導(dǎo)的領(lǐng)域,德性倫理應(yīng)該統(tǒng)攝人類整體的道德生活。我們始終相信麥金泰爾的一個觀點:“現(xiàn)代道德話語和實踐只能被理解為來自古老過去的破碎了的殘存之物,并且,在這一點被很好地理解之前,它們給現(xiàn)代道德理論家所造成的不可解決的問題將始終是不可解決的。”①John M.Rist:Real Ethics:Re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39.現(xiàn)代道德吸取并發(fā)展了傳統(tǒng)中具有實踐性較高的部分而放棄了作為其整個倫理核心的德性倫理,從而為倫理學(xué)的當(dāng)今的困境埋下了禍根。
現(xiàn)代社會的碎片化表明現(xiàn)代社會處于深刻的危機之中,但是我們不能反過來用危機中的現(xiàn)代社會當(dāng)作是德性倫理危機的根源,因為這不僅不是德性倫理的危機,反而是德性倫理的契機。麥金泰爾正確地認(rèn)識到?jīng)_突和對立同道德知識之間的關(guān)系:“對立與沖突在人類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是人類德性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人類德性實踐的一個重要環(huán)境。”②Ibid.,p.207.德性倫理的當(dāng)代復(fù)興正是為了解決現(xiàn)代社會的危機,而作為進行“危機公關(guān)”的角色的德性倫理是它的當(dāng)代復(fù)興的最主要內(nèi)涵。至于德性倫理能否妥善地處理這場危機,進行一個好的危機公關(guān)則要看如何成功地定位德性倫理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德性倫理的本質(zhì)。
另外,筆者忍不住想到中國倫理學(xué)的境遇,當(dāng)西方人可以向上帝求援的時候,中國人又可以向誰求援?中國沒有上帝。我們總說我們處在一個傳統(tǒng)道德分崩離析,而新的道德體系又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轉(zhuǎn)型期社會: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已經(jīng)充斥著各種規(guī)則,當(dāng)然更需要關(guān)注的是它們?nèi)绾蔚玫角袑嵉膱?zhí)行;但是筆者認(rèn)為還有更為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為新的道德體系尋找到一個深厚的道德基礎(chǔ)。這也揭示了我們要向古代思想攫取養(yǎng)分的方向:不要“形似”,要“神似”。我們的社會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過多的“形似”的傳統(tǒng)道德的復(fù)興,比如“跪拜禮”的重現(xiàn),“守貞課”的出現(xiàn),等等,不一而足。
①方紅慶,浙江義烏人,浙江工業(yè)大學(xué)政管學(xué)院講師,哲學(xué)博士,主要研究康德哲學(xué)和當(dāng)代西方知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