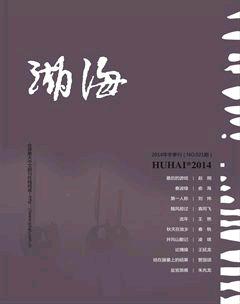低保
周益龍
路的兩邊是種了三十多年的承包田,它在莊稼的侵蝕下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地朝著不遠處的大路掙扎蜿蜒。
這兒是城市的東郊。
秋月一年四季只做一件事,為她生命里的男人操持家務。丈夫顧衛兵患上了風濕病,長年臥床;兒子顧冬在城市西郊的一家化工廠當進料工,騎大型號電瓶車上班,一天下來累得肢麻腰弓不說,還得在路上耗費一個多小時。晚餐張羅停當后,秋月就倚門盼望,電動車明亮的燈光照進秋月的心里,暖洋洋的,也把春花院落前的水泥路照得無比亮堂。顧冬不走自家的蛇道而拐上春花家的大路讓秋月多少有些想法,可顧冬的想法很陽光也很現實,放著這么寬暢的大道不走我傻呀!他不想摻乎大人之間的恩怨。
秋月與春花遷移到這里之前就是一個莊上的人,算是淵源頗深的近鄰。兩家人姐妹似地好過,但也牙齒碰舌頭般地鬧過。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好像有堵墻將兩家生生地隔開,碰面時變得異常地客氣,是讓人生分的那種。
顧冬回到家里,過著豬一樣的生活,吃飽喝足躺下便睡,睡醒后漱口洗臉吃飯上班,母子間很少交流。秋月時常抱怨,她這輩子最大的造化是嫁給了木偶,又生了個木偶連她自己都要變成木偶了。
顧冬扒完飯隨手扯過幾張衛生軟紙將亂草叢中的嘴巴一番亂抹,伸著賴腰又惦念上了給他溫暖給他好夢的床。心愛的姑娘時不時地出現在他的夢中,近在咫尺卻又不可企及,她叫星星,是他的初戀女友,已經走到了談婚論嫁這一步,可還是分手了。
秋月堵住了顧冬的去路。哪個做母親的能忍受兒子的頹廢:“顧冬,你總不能一輩子沉溺于豬的世界。你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你已經三十出頭了你知道嗎?你得成家立業娶妻生子啊!好歹得給我這個當媽的一個交待吧!”顧冬傻傻地笑:更年期果真是個可怕的魔鬼,奪走了母親身上的諸多優點,讓她變得絮絮叨叨;有時更像個孩子,需要他這個當兒子的寵著。顧冬調侃道:“媽,您老人家想唱哪一出都行,我這個當兒子的保證洗耳恭聽,精彩處再給您來些掌聲,咋樣?”秋月被逗笑了:“臭小子,走,去你爹那兒,咱仨今晚開個家庭會議,就咱家今后的生計問題好好地合計合計。”
秋月瞅一眼顧衛兵:“老頭子,為了咱家的生計,你老悶著也不是個事兒。”
顧衛兵用干咳抗議。他不想說,只要他一張口,秋月就像找到目標的狙擊手,彈雨如注。
每次的家庭會議都在爭論中不了了之。顧冬樂意做耙子,為父親擋子彈。他堅持自已的觀點:想把這件事辦成非得找春花阿姨。秋月立即制止:“不行,‘人窮志短,咱們可不能應了這句老話。”
如今找鄰居幫忙辦事的可多了。俗話說,低頭不見抬頭見,人不親水親。鄰居家有了事,哪有不幫不襯的道理?可秋月的心里有道坎橫著,繞不過去又無法跨越。
孩提時代的顧冬與春花的兒子李春旺整天跌爬滾打在一起。有一天,秋月家的雞蛋不冀而飛,誰能想到幾個雞蛋竟能在兩個家庭之間筑起一道堅固的柏林墻。
“除了找春花家的春旺,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辦法?”秋月把期待的目光投向顧冬。顧冬說:“除了請春旺幫忙,我實在想不出其它辦法了。如今,親戚、朋友怕我們開口向他們借錢,連電話都不敢接了,還能指望他們為我們辦這種事兒?辦低保、非得找春旺。我把話撂這兒了。老媽,你要是不采納我的意見,往后您就別再念叨低保的事了。”秋月連連擺手:“不行、不行。昨夜我還做了場惡夢,春旺剁指發誓,結果剁了頭。那一幕現在還在我眼前晃動呢。”
“當時,我和顧冬就不讓你過去。你說也就是過去隨便問問,可有你這么問的嗎?連八歲的顧冬都聽出來了,你分明是賴上春旺了。要是換了我,我也會把手指頭剁給你看。”顧衛兵終于找到了說話的機會,他認為與春花家關系搞得那么僵,責任在秋月。
那時,秋月每年都要散養幾只生蛋的草雞。秋后,秋月便將蛋窩從屋后挪至屋前,惦記舊窩的雞子把蛋下在了舊窩旁邊的大白菜地里了。
“挑起刺來,挺麻利的,一點也不結巴?”秋月瞪了顧衛兵一眼,繼續奚落:“吹什么牛啊!就你這德行,剁手指?你要真有這血性,早當市長了,還能讓咱娘兒倆跟著你受窮。”
顧冬忍耐的底線被突破,他勒緊了鴨子嗓:“每次的家庭會議,都充斥著無休無止的埋怨。管用嗎?我問您們,知不知道錢多的人為啥比錢少的人幸福度指數要高出很多?”
秋月急于邀功:“這還不簡單,有了錢,吃穿不愁,一句話,有了錢,就等于啥都有了。對不對,兒子。”
“錯!大錯特錯!”
顧衛兵見狀后捂著嘴樂,秋月暗中踹了顧衛兵一腳,算是回敬。
“窮人互相埋怨,鬧得雞飛狗跳,能幸福嗎?富人呢,懂得相互欣賞,想不幸福都不行。”
秋月被顧冬說得直點頭,繼而又若有所悟,抓起搟面杖揍兒子:“臭小子,看把你能的,挖個坑讓老娘跳是不是?”
“心虛了吧!”顧冬說完做昂首挺胸狀:“好,給您打兩下,下次再想打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呢?”
顧衛兵沉不住氣,問:“你咋啦?”
“明天起我要食宿在廠里了,乘我還沒崩潰先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你要真走了,三天后回來給老爸收尸。”顧衛兵也想學兒子,來點幽默,可惜學藝不精,畫虎不成反累犬。
顧冬樂意與父親逗,故作驚詫:“老爸,就眼前這么點困難,您老不至于想不開吧?”顧衛兵續演:“小子,誰想不開了?你媽的唾沫能淹死人。”
“我困死了。”走出房門后又扭過頭說:“明天這個時候能不能聽到我的段子就看咱媽的了。”
真是應了那句俗語:解鈴還需系鈴人。
午餐后,秋月將顧衛兵安置在門前屋檐下的躺椅上曬太陽。秋月不時的向春花門前的菜園窺探。說是菜園,八成花木,只有中間的一小塊種稙了各種各樣的蔬菜,名為菜園子,其實是個花園。
春花的習性秋月多多少少的知道一些:春花不愿意鉆進城里的鴿子籠,太悶,門對門的見了都裝作不認識,門整天關得死死的,找個能聊聊天的人比找個死人還難;而鄉下,卻是另外一種情形,自在,串門方便、空氣新鮮。春花的生活很有規律,大清早的做個操跑個步的,下午串門聊天,要不就侍弄侍弄菜園子。
秋月琢磨著如何與春花搭訕,乘她尚未出門進她的家,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好是好,可秋月缺少抹下老臉的勇氣;待春花出門后呆在自家的門口招呼,春花不予理睬也就罷了,萬一春花將強占宅基地的事翻出來,那就連鉆地縫都來不及了。
年輕時,憑著那股子潑辣勁,太逞強了。怪來怪去只怪顧衛兵太軟弱,她這樣做還不是為了免遭四鄰八舍的欺負。回頭看看,有些地方確實做得太過份了。
心急吃不得熱豆腐,自我勸慰后秋月的心變得淡定:凡事得隨緣,急不得。
秋月從屋子里拿了把鋤頭進了自家的菜地,走進自家的菜地感覺如同走向春花的菜園子,這種恍惚的感覺使她心酸:兩個家靠得都不能再近了,怎么說不搭理就不搭理了吶?往日的情誼又怎么說沒就沒了呢?對于春花,秋月幫她的忙還少嗎?春花男人患肺疾,家里的力氣活那一項不是顧衛兵干的?春花,就為了怎么一丁點兒小事,果真記她的仇?這人哪,真的一點意思都沒有。難道真的幫人不如養狗?再說春旺也不該這樣呀,阿姨不就多問了兩句嗎?用得著記一輩子仇嗎?阿姨家困難,別人不知道難道你也看不見?秋月突然把鋤頭對準了抽苔的青菜一陣猛刨。惹得顧衛兵哇哇大叫:“這是留著收菜種的,發神經啊?”秋月的眼睛就成了泉眼,不住地涌。過了一會兒心里果然好受了些,而顧衛兵一聲重似一聲的嘆息再次把她的心揪緊。她覺得很對不起顧衛兵,但不這樣她會瘋掉,痛苦怕什么?總比瘋了強,她一直這么想。
“春花!春花!”是顧衛兵在嚷。秋月在心里罵開了:你個死老頭子,我還沒瘋你先瘋了,好事都讓你給搶走了。可她轉過身卻看到了彎腰鋤草的春花。春花帶著眼鏡,耳朵里還好像塞了什么東西。
春花!”秋月輕輕地喊了一聲。春花好像怔了一下,然而直起身子轉身回家。秋月不知從哪兒來的勇氣,大聲喊道:“春花,春花姐。”
春花停下了腳步并轉過身來。她摘下眼鏡掏出毛巾擦拭鏡片,然后又將塞于耳中的東西擺弄了一番。臉上顯出幾分驚奇:“哦,是秋月。”
“春花,過來坐會兒吧!”顧衛兵再次大聲招呼。春花走過來與顧衛兵寒暄。秋月以茶爐子水開為由進了屋子。可她的耳朵沒敢懈怠。
春旺有出息了,當了市長。但春花積勞成疾,五年前的那場大病又奪取了她半條性命。如今,春花已經耳聾目眩,風燭殘年。眼鏡,助聽器都用上了。秋月嘆息,春花也不容易,老伴離世后,供春旺上學。這幾年不在家,是因為生病,不是躲她。可沒想到的是,心結解開后,心里更不好難,似有老鼠在撓。
秋月隔三差五的讓顧冬給春花送些龍蝦、黃蟮、山藥等土產,雖說不值幾個錢,但可以表個心意。誰料春花竟回贈些野生鱉、大閘蟹、高檔茶葉等名貴特產。原本想增進友誼不經意的反欠下了人情,好像有求于人的是春花而不是她秋月。唬得秋月再也不敢貿然出手。
與春花的關系得到改善后,請春花幫忙辦低保可謂水到渠成。但由誰來向春花或春旺開這個口卻又成了一個新的難題。秋月讓顧衛兵跟春花說,顧衛兵死活不依:一個大男人向市長伸手討要低保,傳出去,他那張老臉往哪兒擱?而顧冬更是余悸未消:一個多月前,顧冬寫了張低保申請報告,村里蓋了章卻不劃撥計劃,村主任肚子里的苦水不比他顧冬少,說上面給的指標很有限,而需要政府救助的卻不在少數,可謂僧多粥少,村里實在是愛莫能助。臨走時,村主任建議顧冬去上級相部門反映情況,看能否解決。在秋月的催促下,顧冬帶著相關材料又去了民政局。那里的辦事人員用奇怪的目光打量著顧冬;更有甚者,顧冬前腳出門,后面甩過來一句:“低保、低保,你他娘就是張孕育懶漢的溫床。”從那刻起,顧冬徹底打消了吃低保的念頭,他決心用自己的雙手活自己和家人。他認為困難只是暫時的。顧冬態度明朗地對秋月說:“媽,咱就別惦記那吃低保的事了,自食其力吧!”秋月回道:“為什么?憑啥呀!比咱家條件好上百倍的人都吃了低保。這不明擺著欺負人嗎?”顧冬說:“媽,您兒子沒本事才掙不了大錢,這也不能怪政府呀。”“哎,孩子說得也是。”顧衛兵也小聲嘀咕了一句。秋月對顧衛兵父子倆打腫臉充胖子的做法十分惱火:“我說你們倆個大老爺們,怎么都成了孬種。說好了的事咋又反悔了呢?”顧衛兵笑了:“顧冬的意圖是讓你主動與春花和好,別讓四鄰八舍的笑話咱。你還真以為顧冬會摻和這種破事。”秋月更惱了:“外人欺負我也罷了,連你爺倆也給我耍心眼。這低保的事拿不下來,我秋月咽不下這口氣。”
兩束強烈的燈光撞擊著窗玻璃,是春旺的車。春旺是個孝子,晩上經常回來看母親。顧冬看著秋月,在往常,這樣的燈光會刺傷秋月的眼睛,她會用被子把頭蒙住,可今晩她迎著燈光,眸子比貓眼還亮。還突然嚷了一聲:“啊!春旺回來了!”顧冬怕秋月讓他去找春旺說情,打上了預防針:“媽,您為了低保這事兒,托人找關系什么的,兒子想攔也攔不住。但您也嫑指望我摻和這事兒。”秋月笑著:“兒子,瞧你那熊樣。好,低保這事兒媽已經跟春花說了。”顧衛兵插嘴道:“春花咋說的?”秋月回道:“春花說就咱們家目前的情況,早該吃上低保了。”秋月停頓了一下又說:“下午送廢品時,張姨問及低保的事。張姨說她家的低保拖了五六年都沒辦成,跟咱家的情況類似,一家人的生計成了人家腳下的皮球被踢來踢去的。后來找關系托人送了紅包,事情很快就解決了。”顧衛兵聽不下去了,奚落道:“政府的人在你們眼里就這么壞?再說了,你想送禮就早說嘛,何必繞這么大圈子,煩不煩哪?”顧冬對秋月說:“要送您送遠點,您可千萬別去害春旺。再說了,咱家送禮的錢都有了,還要較著勁吃低保,這合適嗎?”秋月說:“我又不敲鑼打鼓的去大街上宣傳,咋就害了春旺了。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小子認為媽的做法不合情理是吧?你給我搞清楚了,是政府的人不給咱家辦低保,媽才這樣做的,要說不不合情理的是他們。”顧冬覺得他那個媽就是個兵,而自己就是那束手無策的秀才。他朝秋月笑笑:“因為您是我媽,我不跟您爭了。”秋月覺得冬兒和他爸心地太好,又因為心地好而厚道。為此她更要挺身而出,為這個家仗義執言。“媽是占著理吶。”秋月像是對自己說。
秋月臨睡前將鬧鐘鈴聲定在早晨五點。其實鬧鐘的鈴聲壓根兒就沒發揮作用,因為她整夜沒合眼,因而她五點前就起床了。顧冬喝粥時肚子里沒少灌冷氣,秋月不時地竄出去門去朝春花的園子里張望。顧冬朝秋月笑笑,他知道母親在等著春旺吶。“媽,有事與爸商量著辦。”顧冬撂下一句話上班去了。
春旺打開門,就撞見了秋月。春旺怔了一下好似微機在搜索信息,當然很快就作出了反應:“秋月阿姨,您凍著了沒有?快進屋里坐吧!”說著轉身就沖屋內喊:“媽,秋月阿姨來啦。”秋月說:“春旺,讓你媽多睡會兒。一會兒你阿姨還得往灶膛里添柴吶。”春望說:“阿姨,您真儉樸。”秋月說:“能省就省唄。這么多年,你又是上學又是援藏的。現在好不容易到了家門口工作吧,又成年累月的為咱們百姓操勞。”春旺不迭聲地說:“應該的,應該的。”邊說邊捋袖子看表。秋月說:“春旺,平常多注意休息,別累壞了。天冷了,阿姨給你織了件毛衣,你可別跟阿姨見外喔。”說著就把裝著毛衣的方便袋塞給了春旺,然后對欲收還卻的春望催促道:“快去上班吧。”春旺坐進車子后伸出頭來向秋月揮手告別。
做完了這一切,秋月像害了場大病似的,癱軟下來。
半個月后的一天。張姨突然造訪,說有個什么旺市長的涉嫌受賄,目前正在排查登記。負責排查登記的人剛從張姨那兒離開,張姨是特地來向秋月宣布最新消息的,并追問秋月有沒有送錢給那個什么旺市長。臨走時又反復叮嚀:別抹不開面子,只要你舉報了,飛走的鴨子準能又飛回來。
“沒有,沒有。你看我秋月是干那種蠢事的傻子嗎?”秋月還沒將張姨送出視野之外,就狠抽了自己一巴掌。自己怎么就這么倒霉吶,春旺啊春旺!啥時辰不能出事?偏趕在你阿姨錢已經花了可事情還沒辦成這種節骨眼上出事吶。八千元人民幣啊,大半是借的。舉報了,真能全部退還?如果政府不但不退款還定你個行賄罪,關上幾天再罰點款,那就更慘了。
飯桌上,秋月一根木頭杵半天,那心中的愁緒全網在了臉上。顧冬對失魂落魄的秋月說:“媽,您這是咋啦?”秋月說:“沒事,沒事。”顧衛兵說:“有事就跟兒子說說,別憋在心里。”顧冬說:“該不會又被哪些個嚼舌頭的忽悠住了,要不就是給春旺送禮了,被低保的事迷了心竅。”要是往常,秋月準會對顧冬夸上幾句。可眼下,誰的話都讓秋月感到惱心:“你小子什么時候成了諸葛亮了,連媽的心事你都敢胡亂猜測。”顧冬回道:“是否猜中,這并不重要。但我要向您重申,您要是害了春旺,我不會愿諒您的。”顧衛兵用哀求的語氣勸秋月說:“你凡事得顧及兒子的感受。”秋月瞪眼說:“啥時候你父子倆穿上了一條褲子。”
秋月把桌子上的碗筷往鍋里一放,雙手在抹灶布上搓了兩下上了鋪。她心里憋氣、別扭。她心里的話還沒掏出來,那父子倆對她施了個先下手為強的硬招,制住了她的死穴,給她一個坐以待斃的份兒。
秋月犯了迷糊。
在秋月舉報的當天,春旺被關了起來。秋月不僅拿回了自家的八仟元人民幣,還得到了政府的兩仟元獎金。在秋月高興的當兒,春花沖進了她的家,潑婦一般扯咬哭罵。罵秋月是個陰毒的惡婦。從前,嫉妒春旺學習成績好賴春旺偷她家雞蛋;現在,嫉妒春旺當了市長又想方設法給春旺下套。是個背信棄義無惡不作的卑劣小人,就是到了陰曹地府也絕不放過她。嚇得秋月出了一身冷汗,醒了。
蘇醒后的秋月喘著粗氣,借此緩解心里的驚恐。心里卻犯了嘀咕:這春旺難道是天上的星宿不成,有神仙護衛,在夢里向她發出了警告,不許她舉報。然后又覺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誕。如此這般的翻來覆去,秋月的思緒成了一團亂麻,無法理清了,而且徹底迷糊。
秋月清醒時,發現自己在醫院的病床上躺著。她意識到自己病了而且好像還病得不輕。
張姨來醫院探視,告訴秋月,政府已經將五仟元禮金退還給她了。然后就握住秋月的手說:“心里有事就說出來,千萬別獨自擔著。那樣會悶出病來的。”秋月說:“你們怎么全都成了仙子了,我沒事,真的沒事。”張姨說:“你的心事全都寫在了臉上,傻子都能一眼看破的事,還想瞞著,你這不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嗎?”然后湊近了問:“秋月,你送了多少?是六仟還是八仟?”
秋月閉上眼睛說:“我累了,想歇上一會兒。”其實秋月真的累了,她什么都賴得想了。
“媽,媽!”是兒子顧冬的聲音。秋月嗔怪道:“說好了去上班的,怎么又回來啦?”顧冬說:“媽,您看誰來啦!”秋月見來人身穿制服手拿公文包,腦袋瓜子頓時炸了。她對穿制服的人說了一大堆不著邊際的話:“我從來沒有給春旺送過錢,我也不相信春旺會收人家的東西。這些沒良心的東西,有難事找春旺幫忙,事成之后又去害春旺。”顧冬制止道:“媽,您說什么吶?春旺正忙著開會,他聽說您病了,委托張秘書來看您。”秋月一塊石頭落了地:“怎么說,春旺好著吶!”張秘書從公文包內拿出一大沓人民幣,對秋月說:“市長讓我把它交還給您,市長晚上來看您。”
“春旺來看我。春旺沒生我氣?”秋月興奮得兩眼發光,她盯住顧冬問道:“那旺什么市長的事到底是咋回事?”顧冬回道:“那個腐敗分子叫汪新,辦低保索要紅包不假,但他不是什么市長,是民政局的一個科長。春旺發現您送紅包的當天就忙著去外地參加招商活動了,接著又是出國訪問什么的,昨天才回到市里。”秋月掀開蓋被,說:“我要回家。”顧冬說:“您說什么糊話?”秋月說:“我沒病,我要回家給春旺包餃子去。”說著大步走出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