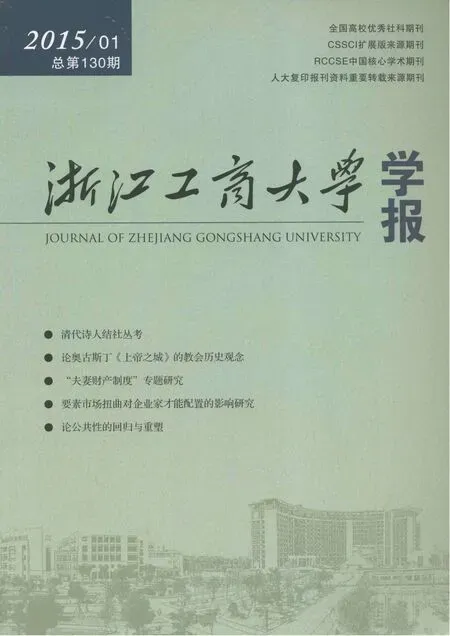文學VS政治:帕慕克的文學思想探源
劉蘇周
(1.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241; 2.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淮北 235000)
文學VS政治:帕慕克的文學思想探源
劉蘇周1,2
(1.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241; 2.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淮北 235000)
摘要:帕慕克以創作聞名世界,而其文學思想尤其是有關“文學與政治”的論述獨樹一幟,迄今尚未引起學界重視。本文參照其創作實踐,并將相關論述與當代西方文論進行廣泛比較發現:首先,帕慕克將“文學與政治”問題作出解說;其次,他提出另一種文學的政治性,并討論了非西方的壓迫社會的文學與政治的悖論關系,提醒人們文學批評與研究不能忽視文學作品的虛構性此一重要特點;最后,他重新定義“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盡力創設一種超越文學與政治二元對立框架的閱讀文學的方法框架,加深我們對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的理解和研究。
關鍵詞:帕慕克;文學理論;第三世界文學;政治;文學性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以下簡作“帕慕克”)是飲譽當代文壇的著名作家。1952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23歲從土耳其科技大學退學,矢志成為一個小說家,7年之后發表處女作《塞夫得特先生》,此后共創作出版了以《我的名字叫紅》(1998)為代表的長篇小說8部、隨筆集2部、講演集1部和電影劇本1部。20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世界矚目。迄今為止,已有11部作品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不僅激發了廣大讀者的閱讀興趣,也促成了我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為新世紀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筆者查閱中國知網的論文統計發現,目前國內學界對帕慕克的研究論文有600余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其小說人物形象、創作技巧的探討;第二,對其小說主題東西方文化沖突與身份危機的分析;第三,對作家的鄉愁情懷(“呼愁”)與其創作之關系的論述。然而,有關其文學、藝術理論的研究尚未成為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本文擬從正面研究帕慕克的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并將其相關論述與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相關闡釋進行對比,以期更好理解帕慕克的文藝理論。
無論是按照中西文藝理論的歷史脈絡來觀察,還是依據無數經典作家的“現身說法”,我們都能發現,任一作家的創作歷程與其文學、藝術理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研究作家的文學、藝術理論便尤為必要。帕慕克亦非例外。他的《天真與感傷的小說家》《別樣的色彩:關于生活、藝術、書籍與城市》《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為我們探索這一問題提供了入口。2009年,應哈佛大學諾頓講座邀請*哈佛大學“諾頓講座”始于1925年,所邀請的講者遍及文學、建筑、音樂、繪畫等領域世界一流的藝術家和學者,如T·S·艾略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艾柯等都曾先后在此發表演講,博爾赫斯的《談藝錄》、卡爾維諾的《新千年文學備忘錄》、艾柯的《悠游小說林》等也都是他們在“諾頓講座”所發表的演講記錄。,帕慕克發表了6次著名演講,后據此結集出版的《天真與感傷的小說家》一書相當完整地表達了作家對于文學、藝術的復雜性的理論思考。帕慕克說:“我希望談論我的小說創作旅程,沿途經過的站點,學習過的小說藝術和小說形式,它們加于我的限制,我對它們的抗爭和依戀。同時,我希望我的講座成為小說藝術的論文或沉思,而不是沿著記憶的巷道走一趟或者討論我個人的發展。”[1]168
借助于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對“天真”(naive)作家與“感傷”(sentimental)作家所作的著名區分*在席勒看來,“天真”作家的寫作是靈感乍現,而“感傷”作家則具有反思性和明確的寫作創意。參見席勒:《席勒文集.6.理論卷》,張玉書選編,張佳玨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帕慕克揭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寫作與閱讀過程。但毫無疑問,將自己對文學與藝術的理解統攝在“天真與感傷”這一主題之下,也是受到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ck)的詩集《天真與經驗之歌》(TheSongofInnocenceandTheSongofExperience)啟發的結果。然而我們深知,包括作家本人在內,樂于承認自己受啟發、被影響這個事實,不能削弱我們對其創造性的評估。事實上,盡管開拓傳統與對傳統的繼承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但開拓傳統時所彰顯的創造性卻構成了帕慕克之為帕慕克的根本。
一、 “文學與政治”的歷史語境
帕慕克首先反對將作家的政治意識與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的政治性等而同之,并且將文學的政治性概念泛化,推論出文學即政治、一切即政治的判斷——例如新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特雷·伊格爾頓在撰寫《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時即宣稱“我從頭到尾都在試圖表明的就是,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乃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歷史的一部分”[2]。帕慕克在紐約告訴美聯社的特稿作者娜哈爾·圖西(Nahal Toosi):“政治沒有影響我的作品;不過,政治一直影響著我的生活。事實上,我在盡最大的努力,讓作品遠離政治。”[3]他還以那種認真而又不無揶揄的口吻說道:“寫作小說的創造性沖動源自用詞語表述圖畫性物品的熱情和意志。每一部小說背后當然也有個人的、政治的和倫理的動機,但是這些動機可以通過別的渠道得到滿足,如回憶錄、訪談、詩歌或新聞報道。”[1]95
在《天真與感傷的小說家》第五章,帕慕克重申了這一判斷:“說到小說,我們卻不經常談政治或小說里的政治,在西方尤為如此。……政治小說是一種有局限的體裁,因為政治包含一種不去理解非我族類者的決斷,而小說藝術則包含一種要去理解非我族類者的決斷。但是政治可以被納入小說的程度是無限的,因為當小說家努力理解那些異己的人,以及那些屬于不同社會、種族、文化、階級和國家的人們之時,他恰恰具有了政治性。最具政治性的小說是那些沒有政治主題或動機而盡力觀察一切事物、理解一切人并且建構最大整體的小說。因此,那種努力實現這種不可能任務的小說具有最深沉的中心。”[1]134-135通過上述的描述,我們似乎會得出一個結論:哪怕是“純文學”作品中,其政治性無處不在,而且這種政治性是小說家而非小說中的人物在理解另一個人時所賦予的。但是,這種政治性如何為讀者心領神會,或被誤解?另一個與之緊密相關的問題是:為什么那些我們通常見到的最具政治性的文學卻因為“文學性”不足而被指責?歸根結底,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文學的“政治性”?
以200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雪》為例,我們或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這部被帕慕克認為是自己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創作的政治小說里,詩人卡和大學女同學伊佩珂的故事串聯起他們對理想的人性與愛情的追尋,而發生在伊斯坦布爾、卡爾斯等地的選舉、政變、宗教沖突,則凸顯出小說主人公難以排解的文化認同與身份危機[4],暗含作者希望伊斯蘭社會能夠自我反省的呼吁。小說一經問世,即在土耳其引起巨大爭議,但在國際范圍內卻贏得了廣泛支持。可以說,這部最具有政治性的小說不僅沒有損傷其“文學性”,反而因為著意處理而非回避政治的糾葛而別具魅力。那么,這一“政治小說”的魅力源自何處?作家在“諾頓講座”上予以明確回答:“小說藝術不是在作者表達政治觀點的時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在我們努力理解某個與我們在文化、階級和性別上不同的人之時才具有政治性。這意味著我們在作出倫理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判斷時,要懷有同情之心。”[1]64-65
我們平常所說的政治性,實際上有著兩種不同的含義,“其一是指作家關注表現的是一種政治社會性的題材,其二則是指文學為政治服務。”[5]追溯帕慕克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我們不難看出喬治·奧威爾(George Owell)對他的重要影響。但帕慕克對“文學的政治性”的理解超越了奧威爾所謂的、顯而易見的“作家的政治動機、政治意識”的層面,并且重新定義了“文學與政治”關系:文學中的政治性,只有在作家對異己之人的書寫中才能體現出來,最具政治性的小說是沒有明顯地處理任何政治主題、事件、行為的小說。這一洞見首先有助于修正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傳統理解,特別是我們一貫所提倡的那種要求文學作品必須具有與現行政治意識形態相配合的政治性的理解以及過分拔高,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那種“立場”(alignment)和“黨性”(commitment)非常明顯的“傾向文學”數次發表措辭嚴厲的批評。[6]
重要的是,帕慕克的思索還有助于我們對題材、主題批評的限度進行反思。可以說,包括聚焦于一部作品的政治性在內,任何聚焦于文學作品的題材和主題的批評與研究,固然有助于我們定位一類相同題材、主題的作品中的某一部的特性,但它幾乎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局限性,這局限性即是未能充分體貼、討論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它的成功往往是以犧牲有關“文學性”的討論作為代價的。以至于我們不禁想問:形形色色的題材批評、主題批評,而今依然大行其道,但它們真的像它們所表現出的那樣關心文學?假如有一種最具政治性的文學,它又豈能那么容易被我們解讀出?甚至,為何我們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如此執迷于“政治性”?
與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奧威爾之類的獨立作家不同,帕慕克除了將自己對“文學與政治”的理解還原到一個具體的歷史語境,亦即在20世紀東西方政治沖突、文明沖突的大背景下,被殖民國家和地區意欲實現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同時還須著手如何走向現代。無論在當時還是當下,一定程度上,“西方”即等同于“現代”“進步”,被殖民國家和地區則是“傳統”和“落后”的代名詞。[7]267-268被殖民國家和地區到底是向西方學習,完成西方式的現代進程,還是立足傳統,開拓傳統,從國家和社會內部尋找現代的可能性,是這個語境中社會、經濟和文學革新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特別是當被殖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目睹宗主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所實施的血腥與殘暴統治,而且牢牢控制著何謂文明、何謂野蠻的話語權時,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無疑將更為痛苦,甚至可能被道德上的正義感和情感上的厭憎所統馭。[8]25-26但是,文學難道不可以超越地域、國族和社群的界限?真的有什么可以稱之為第三世界文學嗎?在不墮入粗俗和狹隘的前提下,有沒有什么可能為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建立其文學的基本特點?
帕慕克曾以秘魯作家馬里奧·馬爾巴斯·略薩(以下簡稱“略薩”)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集中討論,他發現,還是“有一種敘事小說很明顯是特屬于第三世界國家的。……這種小說的創意與作家生活的地方關系不大,而主要是因為作家知道他的寫作遠離世界文學中心,并能在內心感覺到這種距離。如果第三世界文學有什么獨特之處,那決不會體現在它賴以產生的貧窮、暴力、政治或國家動亂上,而是體現在作家意識到,他的作品多少遠離了中心,并在作品里反映了這種距離。在這里,他的藝術史(小說藝術史)由他人來撰寫。在這里,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著從世界文學中心被流放出來的感覺。”[7]194
這種被流放的感覺與精神狀態,讓第三世界的寫作免于“影響的焦慮”而能全心全意探索自己的獨創性和真實性,汲取本國文學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學傳統的靈感[8]109-110,并將西方現代文學的形式與技巧完全翻轉過來,服從于自己不同的目的(比如像略薩那些書寫反抗殖民的歷史),很有可能鑄就自己特立獨行的文學。此時的略薩尚未獲諾獎,而帕慕克卻能獨具慧眼,發現略薩筆下那非比尋常的文學創造力,顯出其一流的文學批評眼光。饒是如此,就被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文學以及我們熟悉的第三世界文學的總體而言,究竟是執著于批判“西方文學”“現代文學”的政治性,還是同時有力地揭露本國和本地區的殘忍和罪惡,抑或有能力創造出一種嶄新的去政治性、無對抗性的文學,這一不得不直面的生存境遇恐怕決定了我們對“文學與政治”關系既執迷其中又倍感困惑的復雜情緒。我們還必須接著思考,如果有一種嶄新的去政治性、無對抗性的第三世界文學,可否被我們察覺、認知?
二、 “非西方的壓迫社會”的“文學與政治”
帕慕克諳熟于笛福、菲爾丁、塞萬提斯以來的西方現代小說傳統,使他深感不滿的是,“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小說在英國和法國興起的歷程,知道了小說觀念是如何在這些國家形成的。但是,我們并不太熟悉作家們將小說藝術從英國和法國進口到自己的國家后,所做的種種發現和解決辦法——特別是,他們如何讓西方人贊同的虛構觀念適合本國的閱讀群體和民族文化。這些問題的中心以及由此興起的新聲音和新形式,就是西方的虛構性觀念為適應本土文化所經歷的創造性的并且合乎現實的改造過程。”[1]35-36也就是說,當第三世界的作家將西方現代文學的形式與技巧翻轉過來,努力使之服從于自己不同的目的時,他們還要向讀者告白并希望讀者能夠接受一個基本觀念——小說(文學)是虛構的產物。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呢?“非西方的作家覺得自己有義務反抗獨裁政權的諸多禁令、禁忌和壓制,”但“反抗獨裁政權的諸多禁令、禁忌和壓制”恰恰是不被第三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歡迎的“政治性”,因此,為了書寫和表達的自由,他們就不得不“用舶來的小說虛構觀念,以說出無法公開表達的‘真理’——就像小說以前在西方使用的情形”。只有文學的“虛構性”(承認文學是虛構、想象的產物,是早期現代文學理論與創作得以展開的基礎)這一看法被人們廣泛接受,另一種文學的政治性,亦即文學對政治(不止是本國政治)的反抗,才得以幸存。
長期生活于土耳其且一直使用土耳其母語創作的帕慕克,之所以能作出這一深刻的判斷,或是由于目睹了自己和同時代許多作家因為一部大膽的作品而面臨巨大風險的結果,但他對文學的“虛構性”的推崇正是因為他擺脫了“單語主義”作家的局限,察見“殖民主義”和“殖民”的深淵[9],清醒地認識到不獨土耳其、印度等東方國家,也不僅僅是第三世界,甚至是整個“非西方的壓迫社會”里,依賴于“虛構性”的保證而生發的與另一種文學的政治性有關的文學革新現象其實相當普遍:“如果我們能夠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一位作家接一位作家,徹底研究在那些非西方的壓迫社會中從19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末,虛構性是如何被小說家們運用的——一個復雜而又非常令人著迷的故事——我們將看到創造性和獨特性大多產生于對這些矛盾愿望和要求的反應。”[1]37此處帕慕克雖引而未發,但循其思路,我們當能推知其要義:正是非西方的壓迫社會對文學的“虛構性”的堅持,保證了這另一種文學的政治性的存在,大多時候也為文學的創造性和獨特性準備了必要條件。
我們注意到,這里帕慕克在完成了對“文學與政治”的重新定義之后,還指出了兩者之間難以回避的悖論和張力,即一方面,在非西方的壓迫社會,以反抗政治為宿命而開端的“虛構”文學,固然已成為文學革新的源頭,生生不息,成績斐然,但文學的“虛構性”卻要求它盡量遠離“政治”,避免“政治”的過度介入,稍有不慎,則可能陷入圖解現實或政治宣傳的泥淖。舉例來說,面對一部作品,批評家們無論持何種觀點,至少首先都對虛構場景、人物、事件以及對話和敘述者自己對世界、人生或人類境況的認識作重要區分,然后展開自己的文學批評,但批評家也好,普通讀者也罷,“讀者自己的道德觀、宗教信仰和社會觀念與一部作品所肯定或暗示的道德觀、宗教信仰和社會觀念一致或相異的程度決定著他對作品的解釋、接受程度和評價。”[10]職是之故,關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討論如果不能回歸具體的歷史語境,不能結合具體作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對作為批評家或普通讀者自身的立場予以反思,而是幻想著有一個普遍意義上的評價標準,視文學為社會現實的忠實反映,從而套用于任何一部作品,又何異于緣木求魚?奧威爾也曾指出,在西方文學史上,那些曾經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作品,往往是教誨、訓誡文學的末流,充滿了陳詞濫調和浮夸之辭,等而下之者則墮入宣傳品一流。
另一方面,“政治正確”的文學又被非西方的壓迫社會的意識形態召喚,“虛構性”除了可以部分地保護文學的純粹審美價值乃至文學家的創作自由,其實不得不與主流的政治文學展開競爭。因此,無論文學的“虛構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帕慕克的這一發現,提醒我們: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非西方的壓迫社會,文學的“虛構性”具有不同功能與不同讀者接受基礎,但有一個共通的特性是,文學作品的“虛構性”無論被強調到何種程度,仍對于構建、重構現實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帕慕克服膺的“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沃爾夫岡·伊瑟爾”的看法,我們可以將文學視為現實、虛構與想象“三元一體”(a tried)的融匯,那么,在現實、虛構與想象之間的越界書寫,正充當了文學的開放結構的意義之源,向讀者提供了無窮無盡的經驗和詮釋的空間。[11]而將文學定義為人類的表演行為之后,文學的“虛構性”的重要地位在伊瑟爾的論述里固然有所削弱,但他通過對文學固有的多義性、非確定性等維度的強調,在事實的層面依然表現出他對文學的虛構、幻想、想象這一根本特點的尊重,而這也呼應了20世紀中后期世界范圍內那種呼吁讓“文學性”回歸的觀念。誠然,當世人飽經政治危機、軍事沖突和流離失所之痛,只有“文學性”可以安撫人們久已疲憊不堪的身心,文學(這里不單是指紙質文學作品,如喬納森·卡勒所說,應是一切具有“文學性”的藝術,乃至新媒體藝術)則成為人們最后守望的精神家園。
正如帕慕克的創作所示,他不僅能夠突破19世紀以來的土耳其文學傳統[12],且能師法于東西方文學傳統而開拓創新,其文學與藝術理論雖非如出一轍,亦能因故就新。探究其所以別具一格的原因,首先無疑是受益于其創作實踐,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仍然是他開拓文學傳統的結果。在與歌德、席勒、威廉·布萊克、E·M·福斯特、奧威爾等人的對話中,與西方音樂美術等領域的經典作品、中國山水畫作的“朝夕唔對”里,他的思考、質疑、辯難既深深地根植于傳統,又不斷地努力從傳統中掙扎而出,進行自我的革新與創造,最終收獲了有關文學與藝術的卓思特識。
三、 超越“文學與政治”的閱讀框架
在我們認識帕慕克文學與藝術理論的過程中,他對“文學與政治”的歷史語境,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辨析,對“非西方的壓迫社會”的“文學與政治”發表的相當獨特但也可能引起爭議的看法,已經予以探討,但比這更重要的是,他試圖由此創設出一種超越“文學與政治”二元對立的閱讀框架,提出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我們應是在理解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反應之間取得平衡。這與我們熟悉的文學的政治讀法(如毛澤東解讀我國四大古典小說)、寓言讀法(如詹姆遜將魯迅及第三世界文學視為“民族創傷的寓言”,精神分析一派的批評家最擅長將一部小說中的諸多意象輕易判定為“陽具的擁有或匱乏”)等取向頗為不同。
帕慕克自陳,這種反思性的認識的建立是源于他數十年來的閱讀經驗:“四十年來,我一直在閱讀小說。我知道,我們可以對小說采取多種姿態,我們可以采用多種方式把我們的靈魂與意識投入到小說之中,既可以輕松地,也可以嚴肅地對待小說。正是這樣,我已親自體驗獲知閱讀小說的多種方式。閱讀小說,我們有時候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有時候只以目視,有時候要用想像力,有時候半心半意,有時候以我們自己希望的方式,有時候以小說要求我們的方式,還有的時候則需要撥動我們生命的所有脈絡。”然而,“我們閱讀小說的時候,意識和心靈之中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些內在的感覺與看電影、看油畫、聽詩朗誦或者是史詩吟誦有什么不同?”[1]4-5帶著對兩個問題的思考,他逐漸體會到,能夠體會閱讀與創作樂趣的讀者首先需要區分想象與基于體驗的不同,“絕對天真的讀者”和“絕對感傷-反思性的讀者”注定都無法擁有文學的美好體驗:“1.絕對天真的讀者,他們總是把文本當做自傳或喬裝的生活體驗編年史來看,無論你曾多少次提醒他們所閱讀的是一部小說。2.絕對感傷——反思性的讀者,他們認為一切文本都是構造和虛構,無論你曾多少次提醒他們所閱讀的是你最坦誠的自傳。”[1]51然而,僅憑這兩點就能幫助我們認識“文學與政治”的糾葛嗎?如所周知,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中西文論家早已有過探索,在此我們無須贅述,而諸多作家也不乏深入探討。這中間,尤其以創作《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等反映政治主題的作品而馳名世界文壇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討論最為重要,前文曾一再提及。但此處若將奧威爾與帕慕克的相關論述作一比較,或許會指引我們對文學的閱讀、創作體驗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有所了然。
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奧威爾就曾反復地思考上述我們所提及的這些問題。在論述作家的創作動機之一——政治方面的目的時,他發表了類似的看法:“政治——最最廣泛意義上的政治”,“這里所有的‘政治’一詞是指它最大程度的廣義。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變別人對他們要努力爭取的到底是哪一種社會的想法。再說一遍,沒有一本書是能夠真正做到脫離政治傾向的。有人認為藝術應該脫離政治,這種意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對于一個作家而言,“你對自己的政治傾向越是有明確意識,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動而不犧牲自己的審美和思想上的獨立完整。”正是強烈的政治批判意識驅使著奧威爾進行文學創作,《動物莊園》就是他把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努力融為一體的第一本書。那么,奧威爾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識是什么?我們知道,是同時批判英美等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天真,批判包括蘇聯在內的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對于這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而言,如果不是在西班牙看到左翼政黨的內部運行情況,被打成托派實施清洗的話(蘇聯國內的大清洗大屠殺也在同時發生),他不會在共產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年代就有如夢初醒的感覺:“從感情上來說,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擺脫政黨標簽才能保持正直。”也就是說,只有擺脫了黨派偏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宣傳,才有可能獲得文學作品所必需的“文學性”(literariness)[13],這也正是文學作品與宣傳品根本不同的地方。
奧威爾還舉了一個特別的細節讓我們弄清楚那種表面幾乎看不出什么政治性的文學(也就是我們一直認為的“純文學”)里隱藏的政治性。例如,在20世紀中葉以前的歐美的主流文學傳統之中,有一類以埃及、印度、非洲等異域風情和殖民者在當地的殘暴統治為主題的作品如康拉德《黑暗的心》、吉卜林《基姆》《叢林之書》,E·M·福斯特《印度之行》向來備受關注,然而自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啟發我們,盡管美國和歐洲對“東方”的定義不同,但他們的“東方主義”想象卻從未褪色,“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利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14]從此出發,我們方能對這類作品的政治意識——或隱或顯的殖民主義意識,乃至來自宗主國的作家身上無法掩藏的優越感和對殖民地人民毫不猶豫的貶低——有所體悟。在奧威爾看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可以反證作家自身的階級意識或在階級問題上的真正感情,也會讓我們對作家的政治意識作出準確而有效的觀察。反過來,那種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識的文學又是怎樣的呢?是不是好的文學?依據自己的創作經驗,他對這一問題予以斷然否定:“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毫無例外地總是沒有生命力的,結果寫出來的是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盡是沒有意義的句子、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話。”[15]這暗示出他心目中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識的文學不會是好的文學。然而,奧威爾對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把握全部建立在一個預設之上,即作家的政治意識等同于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的政治性。可是,這個預設真的正確嗎?
顯然,帕慕克同意奧威爾對于文學的“政治性”的定義,甚至連最具政治性的小說是表面幾乎看不出什么政治性的判斷都是繼承了奧威爾的論述,但他企望建立的一種超越“文學與政治”二元對立框架,以及在理解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反應之間取得平衡的閱讀方法,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對文學的閱讀、創作體驗不同于對音樂、美術、電影、戲劇等藝術品類的閱讀、創作體驗。換言之,如果完全相同,我們還需要文學嗎?那種將文學與政治聯接起來,反復辨析二者應該如何和諧、或如何沖突的論述是不是忽視了普通讀者的閱讀、創作體驗,混同了文學與政治宣傳品、音樂、美術、電影、戲劇等藝術品類的根本差異?帕慕克比奧威爾走得更遠,他在揭示文學的政治性與文學性無法剝離這一文學作品的本質屬性之后,還提醒我們,接下來,重要的不是去區分、辨別這兩者的楚河漢界,而是在經驗、審美、感性的層面承認文學“虛構的真實”,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保持一個開放、流動的立場;對于文學創作而言,在尊重“虛構性”的大旗下文學關注政治,但不過度介入政治,從而有可能保持文學的純粹審美特性的同時獲得文學的政治性。換言之,對文學的閱讀、批評可以因人而異,不必強求定于一尊,而文學創作的新機或也內蘊其中。殖民與后殖民文學,亦宜作如是觀。
參考文獻:
[1]奧爾罕·帕慕克.天真與感傷的小說家[M].彭發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96.
[3]康慨.奧爾罕·帕慕克——政治沒有影響我們的作品[N].中華讀書報,2006-11-15(08).
[4]楊中舉.奧爾罕·帕慕克小說創作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195.
[5]遲夢筠,王春林.重建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從略薩獲諾貝爾文學獎說開去[J].名作欣賞,2011(1):114-115.
[6]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王爾勃,周莉,譯.洛陽: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211-212.
[7]奧爾罕·帕慕克.別樣的色彩[M].宗笑飛,林邊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奧爾罕·帕慕克.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M].何佩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德希達.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M].張正平,譯.臺北: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0:26-27.
[10]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M].7版.吳松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93.
[11]沃爾夫岡·伊瑟爾.虛構與想象[M].陳定家,汪正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83.
[12]帕慕克,陳眾議.帕慕克在十字路口[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35-49.
[13]周小儀.文學性[J].外國文學,2003(5):51-63.
[14]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8.
[15]喬治·奧威爾.奧威爾文集[M].董樂山,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263.
(責任編輯楊文歡)
Literature VS Politic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Discourse of Orhan Pamuk’s Literary Thought
LIU Su-zhou1,2
(1.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udy,HuaibeiNormalUniversity,JiangsuHuaibei235000,China)
Abstract:Ferit Orhan Pamuk is a world famous writer for his novels, while his literary thought, especially his unique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has not aroused attentio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e paper, consulting Pamuk’s creative practice and comparing extensively with relativ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history, firstly points out that, rest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o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Pamuk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the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s obsessed with and confused about it; secondly, Pamuk proposes another kind of politics of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the parado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non-Western oppressed societies, which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fictional nature of literature in ou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search; finally, Pamuk re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tries to create a new reading method which transcends the dualistic framework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hu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Key words:Pamuk; literary theory; third world literature; politics; literariness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1505(2015)01-0021-07
作者簡介:劉蘇周,男,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在讀博士研究生,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09&ZD071)
收稿日期:201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