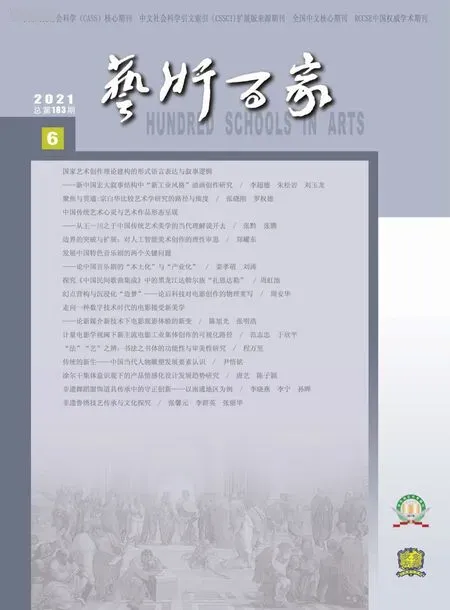回不去的鄉村美學
金惠敏
摘 要:當代流行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模擬”。這種“模擬”并非要替代原本、回到原本,或者說,在原本不在場時聊勝于無。原本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對原本的“模擬”。質言之,“模擬”僅止于“模擬”。從來的“鄉村美學”都是對鄉村文化的模擬,都不是鄉村文化本身。在波濤洶涌的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下,鄉村土崩瓦解,本真的鄉村文化與鄉村趣味也一起煙消云散。看起來好像是逆城市化而動,“鄉村美學”,諸如“農家樂”旅游、“鄉愁”哲學和文學等等,實則是對城市化的補償、豐富和增強,而鄉村卻是回不去的: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在中國傳統山水畫中,回不去;在日甚一日的城市化大潮中,在“模擬”的鄉村美學中,更回不去。“返鄉”似乎要尋找一個暌違已久的對象,然則陷入“模擬”美學的“返鄉”卻并不在乎這一對象的真實存在。“模擬”是一種沒有對象的認識論。要找出這一對象,不能通過“返鄉”,而只能是“在”鄉,此“在”是海德格爾的“此在”。“返鄉”是對象化,“在鄉”則是取消對象,從而取得與對象的同一。
關鍵詞:城市文化;鄉村文化;鄉村美學;鄉愁;城市化;審美現代性;《返鄉》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當今已經沒有鄉村。鄉村已經崩潰。鄉村的崩潰表現為:第一,鄉村被空殼化。凡有技能的或者僅僅依靠體力生存的紛紛涌向城市,成為農民工、保姆、保安等等。也有留在鄉村的,那多半是老弱病殘。鄉村被荒棄了。鄉村的生命枯竭了。第二,鄉村作為城里人的旅游目的地。目前有不少城里人周末假日到鄉村體驗“農家樂”;然而,當鄉村遍地都是“農家樂”時,真正的鄉村生活其實也就終結了。農家樂與其說是農家生活的展示,毋寧說是城里人對鄉村的想象剩余,是城市生活的差異性補充。城市時代的一切民俗都是偽民俗,它們是被生產出來的,被用于觀看的。第三,“鄉愁”的泛濫。這主要表現在例如沈從文、孫犁、劉紹棠這類作家的創作中,以及海德格爾的家園哲學。它們與農家樂無異,是城市化的幫襯,如果不是幫兇的話。在不可抗拒的城市化大潮中,任何以“返鄉”為主題的文學和哲學,都將是為城市張目,為城市化療傷——以便繼續城市化。城市化成了社會主導話語;鄉村話語看似以鄉村為本位,堅守此本位,而實則是作為對城市話語的補償,作為對城市意識形態的強化。當拜讀過著名散文家張天福先生的散文集《返鄉》①之后,我心中多少是感到一些不安的。這不安絕非因為作家的文筆不夠優美,情感不夠充沛,結構不夠謹嚴。非也!集子里可謂篇篇佳構,字字珠璣,激情澎湃,情境相諧,立意雅正。其序文“走進本源”甚至堪稱當代中國文學家最深湛的哲學論文。這不安,或準確地說,是惋惜,來自于意識到此等天上文字非我時代所可接納,其間似有一趣味上的鴻溝。我感覺,今日的讀者怕是再也無法消受它“天”賜的“福”分了。“天”意味著自然,“福”意味著滿足,“天福”不祈求命運的偶然和垂青,現代人若是自己決定復歸自然,那便是得其天福了!如今的閱讀趣味清晰地朝向如下幾個方面發展:一曰求“信息”,即追求信息“量”、信息“流”,所以新聞報道成了“一代之文學”,或時代之文體,如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清之小說,等等。信息類似于從前所謂的“真理”或“求知”,但真理和知識均具有絕對和終極的意味,而信息則是流動的、變化的、瞬間的,沒有目的或信仰。信息以信息自身為目的或信仰。信息求異,真理求同;信息逐新,真理趨返,所謂“反者道之動”。二曰求“震驚”,但凡奇聞異事、隱私八卦、血腥色情永遠是當今讀物的熱點。現代主義文學曾向新聞報道學習,其成果就是對“震驚”效果的追逐;不僅是要新,還要奇,更要產生震撼,給人以持久的沖擊。這“震驚”貌似有“崇高”的效果,但缺乏深度和理念,不留回味和思索的間隙。三曰求“安慰”,這是那些于丹一類心靈雞湯的東西,這只老母雞可以是孔老夫子,可以是佛祖,也可以是耶穌。這種安慰確可以多少彌補人在追新逐奇中所產生的虛幻感,使人得到暫時的滿足,但結果也可能是更為無邊的虛幻感、幻滅感。歸納起來說,這是“現代性閱讀趣味”,而促成此種趣味的當是英國社會理論家鮑曼所指出的“流動的現代性”——現代性使“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它亦信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訓,但其“新”不再承載些微的神圣的“天命”和意義。在傳統的意義上,《返鄉》堪稱鄉村美的典范、古典趣味的再生。這里沒有時間概念,沒有故事情節,有的只是以慢節奏對自然風物的精雕細刻,其中仿佛一切都停滯了。欣賞這類文字需要足夠的耐心。這里沒有知識,沒有真相,有的是文化“傳說”、民間故事,一種與歷史真實無關的想象(如關于秦相李斯的傳說)。欣賞這類文字要先把自己變得樸質,即赤子化。這里可能是逃避世俗的心靈港灣,即作者所謂的“返鄉”,但現代人未必就進得去。《返鄉》不是心靈雞湯,那是大眾的、大眾可接近的,而它是唯美的、精英的,設置了高高門檻的。閱讀《返鄉》這種美文,很容易聯想到陶淵明的田園詩以及中國的山水畫。但那并非“鄉村美”,與農民的心理、旨趣毫無關系。那是文人士大夫的視角和趣味,是屬于精英主義的。在他們那里,鄉村只是表達其隱逸情結的素材。“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讓人多么陶醉的鄉村美景啊!它是溫暖的、親切的;你若愿意,是也可以把它讀作鄉思、鄉愁的。但曲終一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則敗露出一個不和諧的鄉村局外人的形象,我們對于“鄉村”美的暢想和幻想在此尷尬而止。農民沒有“久在樊籠里”的經歷和經驗,也當然不會有“復得返自然”的感受和感嘆。“自然”是“文化”的發明,就像“原始人”是19世紀“文明人”的發現一樣。竊以為,如同陶淵明,作者也是有精英主義或“文化人”的情結的,盡管精英主義和文化未必盡是壞事。 《返鄉》以鄉村美景、鄉村親情、鄉村倫理對抗城市或城市化的丑陋、冷酷和邪惡。其中《帶血的黃土》一篇是此種對抗之令人驚悚的表達。城里務工的兒子在一個漆黑寒冷的早春之夜與伙伴們輪奸了因擔憂他而出來接他回家的母親。在這個故事中,一方是城市,一方是鄉村;一方是被城市資本主義污染了的孩子,一方是在鄉村生活因而保留了最自然的人類情感——母愛——的母親。鄉村與城市的對立被表述為善與惡、美與丑的對立。這是現代文學的一種思維定勢了,如在哈代、勞倫斯、沈從文、路遙那里所突出地表現的。然而,這種對立性的設置根本上卻是有問題的。正如威廉斯在其《鄉村與城市》中以英國經驗所證明的,鄉村有鄉村的美,也有鄉村的丑,而城市同樣是美丑兩面性的。②假使,與哈代們相反,將城市視作文明、進步,那么鄉村則必然是愚昧、落后。例如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中就說過,資產階級所創造的“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在全球范圍內說,它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主要在城市里生活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使農業的、“未開化和半開化的”“東方”從屬于工業的、“文明的”“西方”③。 顯然,馬克思的立場是站在城市一邊的,而城市顯而易見在他就是“文明”、“進步”之同義語。我們無意評論馬克思視角的對錯,借此我們只是想舉證,不同的視角產生不同的鄉村和城市及其相互關系。但是,任何視角對于鄉村美本身都將是遮蔽性的。可以說,幾千年來鄉村美很少得到過如其本然的呈現。鄉村美一直是由與農民毫無相干的文人雅士如維吉爾、陶淵明、華茲華斯、沈從文來表現的,他們筆下的美與農民的情感體驗毫無關系。鄉村美要么被作為逃避世俗的桃花源,要么被作為對工業文明的解毒劑,它從來不是它自身。真正的鄉村美是無言的,它不能被任何人代言——“言而非也”。它需要我們俯下身來,靜靜地諦聽。諦聽是麥克盧漢的“聽覺空間”,是擯棄了“視覺空間”之透視主義而對整體世界的擁抱。諦聽是莊子所謂的中央之帝“渾沌”,不“倏”不“忽”,在“統覺”中交通世界。諦聽是孔子的“克己”,是列維納斯的對絕對他者的承認。④
諦聽就像是肖洛霍夫、柳青、陳忠實,甚至浩然,忘我地浸入鄉村生活的流動與本色,不是“代”農民言說,而是“讓”農民言說:“讓”沒有強迫的意思,它至多只是提供一種契機;“讓”是作家主體的躲開,留出縫隙,讓真理自我呈現。雖然這些作家的創作并非沒有意識形態的剪裁,但這剪裁恰好反證了消極“無為”之“讓”之于彰顯本源的積極意義。 天福有原生態的鄉村故事,高雅與粗俗,愛情與色情,理性與狡黠,奉獻與自私,以及拒絕任何歸類的本真經歷與體驗。我相信,當其拋棄流行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審美現代性”架構,而轉致于諦聽“本源”之鄉,將“返”鄉修正為“在”鄉,他是一定會為我們提供另一幅鄉村圖景的。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責任編輯:楚小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