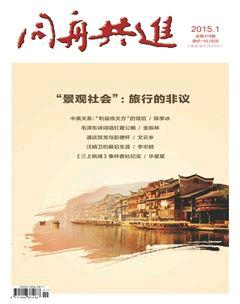流浪者蕭軍
何立波
被譽為“東北作家群”領頭人的蕭軍,是中國現代作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也給人留下了很多的疑問。蕭軍骨子里散發著一種“流浪漢”氣息,他是現實的跋涉者、漂泊者。他天性愛好自由正義,不斷地同舊世界、舊生活、舊環境發生本能性、必然性的沖突和對抗,不斷地向新的光明世界和人生開拓、追求,這幾乎構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內容。從東北到上海,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山西,從山西到延安,從延安到成都,又從成都到延安……“文壇獨行俠”“十足的流浪漢”,幾乎成為蕭軍的代名詞。
從東北軍憲兵到作家
蕭軍在童年時期飽嘗了人世間的苦難與不幸,生母早逝、父親冷酷、繼母寡情、家庭敗落,似滴滴苦水灌滿他的心田,滋育了他本來就桀驁不馴的性格。1924年,蕭軍讀到高三第一學期時,因反抗一個不正派的體育教員的欺辱,被學校開除學籍。父親對他失望透頂:“我不想跟在你的身后吃官司。從此以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自謀生路去吧!”
1925年,18歲的蕭軍獨自一人闖蕩人生,開始了真正的人生漂泊。在吉林,蕭軍在東北軍閥部隊當騎兵。1927年,蕭軍來到沈陽,在東北陸軍講武堂當憲兵。受訓8個月后,1928年被分配到哈爾濱實習3個月。憲兵在哈爾濱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隨意地吃、喝、嫖、賭、受賄、欺壓無辜。但富于正義感的蕭軍卻在骨子里同這樣的生活難以融合,決定“一定要離開這第一個黑色的沼澤,發著臭味的坑,去走自己的路吧!”
1929年,蕭軍轉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炮兵科。這種行蹤不定的行伍生涯,持續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蕭軍與朋友組織抗日義勇軍,不幸失敗,被迫離開吉林,逃到哈爾濱。
在哈爾濱,蕭軍正式開始文學生涯。他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哈爾濱左翼文藝運動。
魯迅、毛澤東:父輩與兄長
在所有和魯迅關系密切的青年人當中,蕭軍與蕭紅得到的關懷和支持最多。而蕭軍一生對魯迅懷有無比誠摯的感情,他視自己為“魯門弟子”,以傳承魯迅的衣缽為己任。他曾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而毛澤東只能算是我兄長。”
蕭軍是魯迅一手扶植起來的青年作家。在魯迅的晚年,與他有過密切交往的青年作家當中,蕭軍與蕭紅,這對當時正流亡在上海的東北作家夫婦,無疑是從他那里獲得關愛最多的兩位。
蕭軍和魯迅的師生之情,緣于1934年兩人的首次通信。當年,在朋友們的資助下,蕭軍、蕭紅在東北出版了署名“三郎”“悄吟”的小說散文合集《跋涉》,這也是“二蕭”唯一的合集。6月15日,遭到通緝的蕭軍、蕭紅被迫流亡青島。9月,蕭軍繼續創作《八月的鄉村》,蕭紅完成了《生死場》,決心向魯迅求教。10月初,蕭軍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魯迅在復信中回答了蕭軍的疑問:“不必問現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
蕭軍接到回信興奮異常,將《生死場》的抄稿和《跋涉》,連同“二蕭”的“美麗合影”一起寄給了魯迅。就在這時,青島的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蕭軍工作的報社出了事,他和蕭紅只能選擇再次流亡,乘坐日本輪船離開青島,來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下午,經過令人心焦的等待,蕭軍、蕭紅終于在內山書店見到了神交已久的魯迅。由于蕭軍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蕭紅在上海的困境告訴了魯迅,臨走時,魯迅掏出了20元錢,交給了他們,還另給了乘車的零錢。這令蕭軍和蕭紅感動不已。半月后,魯迅為慶祝胡風兒子滿月,在梁園豫菜館舉行宴會,特邀“二蕭”參加。后來魯迅又把“二蕭”介紹給胡風,胡風專程登門看望他們,并為蕭紅的小說定名為《生死場》,寫下了熱情洋溢的后記。
1934年,葉紫、蕭軍、蕭紅三人組成了“奴隸社”,他們的小說《豐收》《八月的鄉村》《生死場》被列為“奴隸叢書”,由魯迅分別寫序,推薦出版。在魯迅傾力扶持下,《八月的鄉村》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蕭軍一炮打響。張春橋化名“狄克”,撰文對這部小說進行了批評,指責作品“不夠真實”。魯迅當即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還擊,愛護之心,溢于言表。
1936年5月,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前往陜北紅軍根據地之前,在上海拜訪了魯迅,與之進行了長談。當斯諾問到“自1917的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涌現出來的最優秀作家有哪些”,以及“包括詩人和戲劇作家在內,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時,魯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軍(即蕭軍),并為斯諾所選編的《活的中國》一書推薦了蕭軍的兩篇文章。日本作家山本實彥請求魯迅推薦幾位中國進步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改造》雜志上刊登,魯迅首推了蕭軍的短篇小說《羊》。就這樣,在魯迅全方位的愛護和幫助下,東北流亡作家蕭軍,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壇站穩了腳跟。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周海嬰回憶道:“七八點鐘以后,前來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動作仍然很輕,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聽到樓梯咚咚一陣猛響,外邊有一個人掄起快步,跨進門來,我來不及猜想,人隨聲到,只見一個大漢,直奔父親床前,沒有猶疑,沒有停歇,沒有俗套和應酬,撲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地號啕大哭。他撲向父親胸前的時候,一頭扎下去,好久沒有抬頭,頭上的帽子,沿著父親的身體急速滾動,一直滾到床邊,這些,他都顧不上,只是從肺腑深處,旁若無人地發出了悲痛的呼號,傾訴了對父親的愛戴之情。我從充滿淚水的眼簾中望去,看出是蕭軍。”
1938年3月21日,蕭軍頭戴一頂舊氈帽,肩上斜掛著一個小包,穿著一雙半舊的鞋,拄著一根行杖。這一經典形象,表明了他是從那歷史的深處一路走來,懷著物質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息跋涉著的“流浪漢”,他最終到了延安這塊神圣的黃土地。他來延安,是為尋找精神的歇憩,他也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陜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陳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共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碗里的酒,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使蕭軍終身難忘。蕭軍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是有關系的。毛澤東也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在這期間,蕭軍與毛澤東經常通信,蕭軍不斷地將收集到的文藝界資料寄給毛澤東,也經常到毛澤東那里暢談,有時一談就是一整天。
蕭軍來到延安,自然有一種親切感。但和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卻并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后“歸宿”;對于真正的流浪漢,精神“圣地”永遠只在“遠方”,在“彼岸”,在別處。經過整風,延安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了“皈依”過程。許多原本持有個人立場的作家放棄了原有風格,將個人融化到了時代的主流文化之中。而蕭軍則依然故我,維護著個人的叛逆天性,自由自在地四海漂浮,還是個精神的流浪者,不馴服的野馬。
1935年3月10日,蕭軍就“自己身上的野氣要不要改”,曾寫信請教魯迅。魯迅回信說:“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偽。粗自然比偽好。”1941年8月2日,毛澤東在給蕭軍的信中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毛澤東所說的要蕭軍“故意的強制的省察”的“毛病”和“弱點”,正是魯迅建議蕭軍不要故意改的“野氣”,這野氣里有爽直,更有反叛和不馴服。從其后歷次政治運動中蕭軍的行述看,不能說他完全沒有聽從毛澤東的“勸”,但總體上仍然堅守著魯迅的嘉許。蕭軍用他的實際行動標明了魯迅和毛澤東在自己精神坐標上的位置。
毛澤東之于蕭軍,是當年天性氣質相通的兄長,而這種相互引為弟兄的情感,在二人各自身份地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后漸行漸遠,并最終消散于歷史的無涯中。魯迅之于蕭軍,一是文學的影響,一是思想的影響,一是人格的影響。這三者之中,按照程度而言,人格最重,思想次之,文學又次之。蕭軍至死念念不忘的,始終是對魯迅人格魅力和精神氣質的尊崇。魯迅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獨立的精神立場。以這種個體獨立性為參照,敢于對一切抹殺差異的途徑持疑和持異,寧可承受深刻持久的內心孤獨也在所不惜。魯迅所持有的精神立場,成了日后蕭軍敢于力抗時俗的道德勇氣的重要資源。
彭真的懇切之問,蕭軍的延遲入黨
1942年的一天,蕭軍去毛澤東家串門時,見到毛澤東正與人談話。毛澤東一見蕭軍,立即微笑著介紹說:“這位是彭真同志,他原來的名字叫傅懋恭。”一邊說一邊在一小張宣紙上寫了“傅懋恭”三個字遞給了蕭軍,又向彭真說:“這位是作家蕭軍,東北人,就是寫《八月的鄉村》的田軍。”
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是山西人,蕭軍是東北人,兩人雖然不是同鄉,卻一見如故,越談越親熱。后來,蕭軍常去看望他。彭真的樸實、正直、熱誠使蕭軍視之為知己,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之后,1943年文協撤銷,改成中央組織部招待所。作家們大都下放與工農兵相結合,體驗生活。1943年冬,蕭軍因為受不了招待所負責人的冷遇,一氣之下到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劉莊落戶當了農民。
1944年3月3日,毛澤東派秘書胡喬木在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陪同下,來到偏僻的劉莊勸蕭軍回城。蕭軍深為毛澤東對自己的關懷所感動,考慮再三后回到了中央黨校第三部。蕭軍從劉莊一回到延安,即特意前往拜訪彭真。針對毛澤東在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蕭軍首次鄭重其事地提出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意愿。蕭軍還帶去了他在劉莊寫的日記,并把自己“為什么要入黨”的那部分拿給彭真看。彭真覺得個性極強的蕭軍能夠克服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散漫等缺點,有了入黨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他在表示真誠歡迎的同時,還懇切地提出:“黨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你的頂頭上司不一定比你的能力強,大多數人的意見有時候也不一定正確,你能夠具體服從嗎?”蕭軍考慮了一會兒,也同樣誠懇地袒露心跡,毫不掩飾地說:“不能!如果決議對,我服從;如果我認為不對,我絕對不能服從,不能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看來我還是不夠黨員資格,我還是在黨外跟著跑跑吧,別給黨找麻煩!”就這樣,蕭軍自己又撤回了入黨申請。
1945年4月,中央黨校三部整風學習結束以后,蕭軍被分配到魯藝文學系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后,彭真被派往東北工作,蕭軍也被批準回東北工作。1946年8月7日,《東北日報》宣布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由蕭軍任院長。為盡快將工作開展起來,彭真派人專程到張家口接蕭軍。1946年11月10日,蕭軍離開哈爾濱去佳木斯東北大學“魯藝”任院長。但是蕭軍覺得自己更希望創辦一家出版社。經彭真同意后,蕭軍辭去了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之職。1947年5月4日,蕭軍創辦《文化報》并任主編。
1948年7月25日,蕭軍向凱豐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信中這樣寫道:“多少年來,我留在黨外,這絕非從任何個人動機出發,而是從革命客觀需要出發——這是我個人的認識——幾次和彭真、毛澤東以及其他同志談到入黨問題,我在堅持這看法的同時也覺得自己思想、感情還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請你轉達東北局,如何考慮給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轉達并托他口述一切。”很快,蕭軍要求入黨一事,由已經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做了專門匯報。8月,經中共中央、毛澤東同意,批準接受蕭軍為中共黨員,并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文化報》創刊于1947年5月4日,到1948年11月2日被迫終刊,共計81期,在當時東北解放區產生了極為廣泛的政治影響。當時,《八月的鄉村》的作者、魯迅的學生和來自延安的老干部等頭銜和身份,對東北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天真、率直、自信、傲氣的蕭軍,熱火朝天地投入工作,沒有體察身邊環境的復雜性。好心的朋友們開始提醒他,要他趕緊收斂,否則后果不堪設想。蕭軍卻不以為然,然而事實很快證明,朋友們的擔心并非杞憂。1947年夏,《生活報》在哈爾濱創刊,由當時東北局秘書長劉芝明領導,宋之的主編。《生活報》一創刊,就把矛頭指向蕭軍,指責蕭軍和國民黨反動派一樣,“誣蔑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接著,《生活報》連篇累牘發表圍攻蕭軍和《文化報》的文章,對蕭軍的思想、言行、創作進行了多方面的毀滅性的所謂“批判”。盡管蕭軍及替蕭軍鳴不平的同志寫系列文章答辯,但都無濟于事。1948年5月,東北局公布了《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蕭軍問題的決定》《東北文藝協會關于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劉芝明也親自寫了長達萬言的批判文章,以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的姿態,實際上宣布蕭軍的政治生命和文藝生命結束了。從此以后,蕭軍便被釘在“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恥辱柱上,從文壇上消失了。緊接著,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蕭軍本人也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自然,參加黨的生活一事也就泡了湯。直到晚年,一提及當年《文化報》的事件,以及頭上那頂戴了30年之久的“三反”帽子,蕭軍的心境就難以平靜。
一生難解女人花
早在1922年,按照鄉俗,15歲的蕭軍就結婚了。女方叫許淑凡,長蕭軍一歲,是下碾盤溝村附近一個普通農家的姑娘,他們婚后一起生活了10年。1932年2月5日,日軍占領了哈爾濱,馮占海的抗日部隊撤退后,蕭軍和方靖遠在哈爾濱繼續參加地下黨反日活動,由于政治環境惡劣,蕭軍下定了以死報國的決心,把妻子打發回錦縣老家,并告訴她,自己以后要漂泊天涯,抗日救國,生死未卜,為免誤青春,請她另行改嫁,從此,兩人斷絕了夫妻關系。
蕭軍是因為同情蕭紅而與之相識的。1911年6月2日,蕭紅誕生于黑龍江省呼蘭城的一個大財主家庭,她在這幢小屋里度過了不幸而蒼涼的童年。當蕭紅出落成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時,由于父母包辦,和汪殿甲相識,兩人在哈爾濱的一家旅館里同居了很久。之后,汪殿甲扔下懷孕的蕭紅揚長而去。重病纏身的蕭紅走投無路,給當地的報館寫信求援。報社青年編輯蕭軍得知消息前往旅館探望,這個求援的少女蕭紅含著眼淚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難身世,她寫下的小詩美麗而又哀怨,震撼了這個筆名為三郎的東北大漢。在一個暴風雨的黑夜,趁著洪水泛濫,孤苦無助的蕭紅終于投入了蕭軍火熱的懷抱。
蕭軍與蕭紅的結合因緣際會,偶然性和現實性的因素較多。由于缺乏較深厚的情感基礎,蕭軍總是扮演保護人和救世主的角色,而蕭紅總是處于被動和消極的地位,對她來說這在患難之初是需要的,可以容忍的。但隨著蕭紅在文壇的崛起,她的文學成就使她成為全國聞名的作家時,二人之間的裂痕便進一步擴大,他們之間發生了沖突,爭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蕭軍甚至動手打了蕭紅。在蕭紅的身體和心靈深處遍布著難以醫治的創傷。后來人們這樣對比蕭紅和蕭軍之間的差別:一個多愁善感,另一個坦蕩豪爽;一個是長不大的女孩,另一個是血性漢子。蕭軍說:“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蕭紅說:“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個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他們只適合亂世兒女情,性格和命運使得他們注定不能天長地久。
與蕭紅分手之后,蕭軍在西北遇到了與他相伴一生的妻子王德芬。1938年4月,蕭軍、塞克、王洛賓等到蘭州采風,蕭軍認識了《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王德芬。來蘭州后的第五天,蕭軍就約王德芬出去“散步”,兩人很快墜入愛河。盡管家里反對,她卻義無反顧,在不滿19歲時就把“終身”托付給了蕭軍,跟隨他漂泊一生。蕭軍在給王德芬父親的信里,斬釘截鐵地寫下這樣的話:“我只屈服于‘真理,卻不能對‘暴力低一低頭的。”“德芬已經是我的,我也是德芬的,即使刀放在脖子上也要愛到底。”
1938年6月,蕭軍帶著王德芬離開蘭州。從此后,他們相依相偎、攜手走在了漫漫人生風雨路上。他們先從蘭州到西安,從西安又輾轉到達成都,然后又從重慶赴延安,又先后到過張家口、齊齊哈爾、哈爾濱和佳木斯、富拉爾基等地。后又來到沈陽、撫順,最后定居在了北京。最讓人難以承受的是心靈上的苦,一次次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并沒有將他們擊垮,而是歷難彌堅。“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蕭軍冒著生命危險傳出一封信給他的孩子們。信是這樣寫的:“好好關心你們的母親!她的身體多病,又沒經過什么風浪的折磨,她天真的猶如一個孩子!……她是這世界上唯一能諒解我的人。盡管我們思想常難一致;我們的生活習慣、為人作風——各不相同,但我們卻是不可分解的一對!”
蕭軍還有過一段鮮為人知的婚外戀。1951年,44歲的蕭軍正處于人生最艱難困苦的階段,被排擠出文壇。為了爭取生存空間、保存寫作權利,1951年初,蕭軍以養病為由來到了北京,經人介紹,租住了張公度家的房子,成了鴉兒胡同48號的房客,一住就是幾十年,直至去世。就這樣,蕭軍走進了房東女兒張大學的生活。張大學視他如落難英雄一般,在尊敬中對蕭軍產生了深切同情。張大學的字寫得很漂亮,蕭軍的《五月的礦山》的書稿抄寫,便出自她的手筆。這種患難之交的感覺,迅速拉近了他倆的距離,促進了感情的升溫和升華。
1952年夏,張大學懷孕了。蕭軍決定離婚,給張大學一個婚姻。張公度夫婦讓女兒去打胎,并且執意要把蕭軍告上法庭,遭到張大學的拒絕。張公度斷然與女兒斷絕關系,將她拒之門外。1953年3月17日,蕭軍的女兒出生,蕭軍為她取名蕭鷹,而張大學堅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將孩子取名“張蕭鷹”。蕭軍曾答應給張大學合法婚姻,但已很難實現了。王德芬不肯離婚,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兒女。張大學心地善良、性格軟弱,最后不得不做出選擇——離開蕭軍、離開北京,當然也意味著離開自己的孩子。在畢業分配時,她婉拒了學校的挽留,要求到最邊遠的地方去。張大學去過浙江、到過山東,做過教師、搞過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員,但是她從沒有打算調回北京。1957年,她在遠離北京、遠離父母和孩子、遠離蕭軍的他鄉,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盡管一生都在為與蕭軍的關系承受痛苦,但她從未抱怨和責備過蕭軍,反而一直在關注他、關心他。
蕭軍建國后經歷坎坷。1979年11月,耄耋之年的蕭軍重返文壇,參加了全國第四屆文代會,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作協理事。他詼諧地說:“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現在從土里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隨后,蕭軍被選為北京市作協副主席。1980年4月,經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批復,北京市委做出正式結論,確認“蕭軍是一位真正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具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結論否定了1948年對蕭軍的錯誤批判和對他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
1988年6月22日,蕭軍因病逝世,享年81歲。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