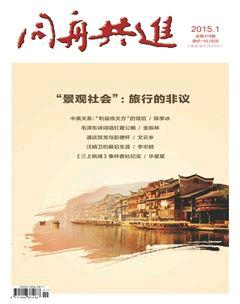中美關系:“利益攸關方”的背后
陳季冰
自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幾年前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概念后,東海和南海局勢逐漸升溫。從很大程度看,中日與中越、中菲圍繞東海和南海島嶼領土爭議的急劇升級,皆能在美國的這一戰略轉向中找到根源。
因此,21世紀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說到底取決于中美關系。
互為“利益攸關方”的中美關系
在如何看待中國發展的問題上,當今西方的主流意見大致可以用所謂的“中國不確定論”來概括,即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但中國崛起的內政外交方向則是不確定的。因此,對西方國家來說,未來中國既可能是“威脅”,也可能是“機遇”。而到目前為止,中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布什總統曾將中美關系描述為一種“復雜關系”,其含義是:美國不希望與中國對立和沖突,但也難以消除對中國的戒心。
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立克對中國的新定義更加精確地概括了這種“復雜關系”,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利益攸關方”。佐立克正確地看到,中國和以前美國的冷戰敵人蘇聯之間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形態,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斗爭。“最重要的是,中國并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于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于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系。”佐立克表示希望中國能夠進一步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在這幅針對中國的戰略藍圖中,美國是有兩手準備的:一方面將加深與中國的接觸,推動中國更徹底地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發生更大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將繼續強化自身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并加強與其盟國的關系,以便制衡中國日益增強的力量。這顯然與簡單的“遏制”“圍堵”或“擁抱”“融合”都不同。如果說美國政壇的對華政策歷來在所謂的“擁抱熊貓派”(或“接觸派”)和“屠龍派”(或“遏制派”)的主張之間搖擺的話,那么這一最新戰略毋寧是一種更為務實的折中。而對持這一態度的美國政界人士,有人送上了一頂有趣的帽子:“熊貓騎墻派”,亦有人生造了一個單詞,稱之為“遏制加接觸”派。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話很有代表性,在他看來,把中國說成“威脅”或“機遇”都是不當的,比較合適的應當是“挑戰”一詞。因為“挑戰”所帶來的結果歸根結底取決于如何應對,應對無方“挑戰”就會演變成“威脅”,應對有方則“挑戰”就會轉化為“機遇”。
中美新型關系的隱憂
這種對中美關系的新型定義目前看來是雙方都能接受的,但它是非常不穩固的,其中包含著顯而易見的隱憂。
首先,雖然中國認同美國提出的“利益攸關方”的提法,但對這個概念,雙方存在著不同的解讀。焦點當然集中在“負責”的“對象”上,即“對誰負責”這個問題。對美國來說,答案非常簡單:中國應當對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負責,說穿了,也就是對西方負責,對美國負責。很多諸如貿易、知識產權、人權、伊朗和朝鮮核問題等都是在這個責任領域展開的,易言之,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行為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是美國衡量中國是否“負責任”的指標。
但中國對“責任”卻有著自己的看法。正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中國項目主任戴維·藍普頓所指出的,“中國希望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因為它認識到該體系符合其總體利益。但是像華盛頓一樣,北京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確定自己的責任。”以當下的表現而論,在中國眼里,所謂“負責任”主要是指尊重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的權威,并在國際法的框架內處理國際事務。這樣一來,中國的一些國際行為——如與伊朗、委內瑞拉等美國的“敵人”開展貿易等——經常被美國視為“不負責”,或者“負責不夠”,甚至是“威脅”;但反過來,美國的許多行為也被中國看作是不負責任和不能接受的。
其次,不同于相對穩定的“敵友”關系,這種“利益攸關方”是一種極不穩定的動態關系,需要雙方時刻把握平衡。維持動態平衡本身就已不易,而在雙方實力又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更加難上加難。坦率地說,中美雙方雖然都在努力向對方釋放自身的誠意,但對對方戰略意圖的疑慮、猜忌乃至防備是不會在短時期內輕易改變的。戴維·藍普頓稱之為“戰略性相互猜忌”。在這種情勢下,實力相對強大的美國這一方會試圖給自己“上好保險”,以確保事態變得最壞時也不會受到太大的損害,這就是藍普頓所指出的過去七屆美國政府所采取的“帶有保險的融合”的對華政策。換一句大白話來說,當前中美之間的真實關系很可能是這樣的:美國認為中國現在還不是威脅,但不可不防;中國則既無能力也不想挑釁美國的現有地位,但同時又堅定地認為,如果美國一定要逼得我們走投無路,那我們也不得不奮起反擊。這種相互間的防備本身就可能破壞原有的平衡,使之朝壞的方向演變。
最后,互為“利益攸關方”的美中關系新定位本身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一方面,下一屆美國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一關系,是基本繼承還是大幅度地改造?這是一個難以預料的變數;另一方面,中國這一邊也存在類似的變數,這將主要取決于中日關系和臺海局勢的走向。
要在未來避免發生沖突和對抗,并推動這種動態平衡關系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光在口頭上說“加強了解、加強信任”是遠遠不夠的,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恐怕有兩方面:第一,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中美雙方都應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加強相互溝通、了解和協調,盡量避免單方面改變現狀;第二,在幾乎所有方面,雙方不僅要加強交流,更需要努力地尋找、發現甚至創造共同利益,因為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增進信任的可靠保證。對于第一點,美國方面要做的是:放棄在中國周邊建立起一個反中國的“圍堵”戰略聯盟的努力,并盡量清晰地表明自己在各方面的一些基本底線,例如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接受中國軍力的增長等;而中國方面也應當努力使自己的意圖變得更加透明和可預期。值得慶幸的是,最近一兩年里中美軍方的交流和互動明顯增多,顯示了一種良性態勢。后一點相對難度較小,也更容易在短期里見效。事實上,無論是經貿往來、國際反恐還是朝核問題等,中美之間都存在著廣泛合作的需要與可能。
真正的威脅是中國的失敗
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西方明智之士已開始認識到,試圖阻撓中國的崛起“就好像用繩子綁住火箭一樣徒勞”,那樣做的唯一結果就是為自己的未來制造一個強大的敵人。更加本質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才是中國真正的“威脅”?無論是對中國自己還是對世界來說,如果說中國的崛起是一種“威脅”的話,倒不如說真正的威脅是中國的失敗。可以想象,一旦中國不能很好地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從而在其漫長的現代化過程中再度受挫而陷入混亂,那么,考慮到中國的巨大規模,整個世界都將受到極大的考驗。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早在20年前就曾說過,“即使今日我為美國公民,也要告訴所有美國人,如果中國不能適當地找到它的歷史地位,決非人類之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說:“中國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世界應當共同努力,保證中國能夠成功地融入國際社會,幫助中國實現和平崛起。”
當然,伴隨著中國的重新崛起,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時候還是十分痛苦的。但對西方來說,真正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不是將這種競爭看成“威脅”并試圖堵塞中國的民族復興之路,而是如何保持和進一步提高過去300年里西方賴以成功的那些優勢。藍普頓問道:“中國已成為美國耗費了極大力氣才建立起來的全球競技場上的一個能力越來越強的競爭者,中國想與美國比賽。問題是:美國會在這場比賽中并在它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場地上好好表現嗎?”
中國與西方:理解但不必認同
人類在21世紀的前途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與西方,特別是中美兩國能否和睦相處,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雙方在未來付出幾十年持續不斷的艱苦努力。從1793年9月7日大英帝國公使馬戛爾尼在熱河覲見大清帝國乾隆皇帝到今天,歷史已翻過了兩個多世紀。不過,究其本質而言,當前橫亙在中西雙方之間的最大障礙卻與當時的情形并無實質性的改變——依然是深深的理解上的隔閡。當然,當今中國和西方的精英早已不同當年,應當說,現代中西的相互認識是建立在對于對方的翔實可靠的知識之上。但是,拋開這些調查數據和分析報告,我們會發現,雙方對于對方的傳統文化、社會價值和民族心理的理解遠遠沒有提升到它應有的高度。
對西方來說,最大的困難在于很難對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做到感同身受。過去300年是世界歷史的“西方時刻”,雖然西方自身在其間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這種變化是由西方的內在動力催生的,因而是一種自然演進。近代以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從未受到過外來異質文明入侵和統治,從未被看成過是“劣等人”,西方的精神傳統也從未因無力應對外來挑戰而陷于徹底崩潰……因而,西方人幾乎不可能理解普遍彌漫于中國人民心靈深處的那種民族自尊感。將自由、民主這些根植于個人權利的理念的現代西方人經常驚詫于中國人為什么對諸如臺灣和西藏這類領土問題會如此敏感,在他們看來,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反應是過激甚至非理性的,大部分根源皆在于此。在評述歐盟對華武器禁售問題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異常深刻地指出,對中國人而言,其實這主要是個“面子問題”,中國并不需要西方的武器,中國完全有能力制造核潛艇和航空母艦。“令中國人不能忍受的是,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不應有的歧視。”更糟糕的是,潛意識里的自我優越感使得西方在處理不同文化傳統的其他國家的事務時,不僅不能妥善照顧到對方的情緒,反而動輒擺出一副發自本能的居高臨下的傲慢姿態,這會更加激起中國人的對抗心理。亨利·基辛格因此警告說,“美國需要明白,恃強凌弱的語氣會使中國想起帝國主義國家的傲慢態度,在與一個4000多年以來一直實行自治的國家打交道時采用這種語調是不合適的。”
對于最早提出要以“中國眼光”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戴維·藍普頓而言,用“中國眼光”看待中國問題并不意味著他贊同中國人的觀點,而只是為了更加全面透徹地理解中國。這確實是一種理性而明智的態度,盡管誠如他所言:“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可能永遠也無法真正做到完全和中國人一樣看問題,但我試圖盡可能地接近中國人的視角。”反過來,這也應當是我們看待西方的正確態度,即理解但不必認同。對中國而言,困難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
首先,由于中國幾乎從未受到過民主政治的洗禮,無論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還是現代社會現實中也都缺乏對民主理念的真正理解。普通中國人對西方政治權力運作的程序和機理是十分陌生的,因而容易產生認識上的偏差。例如,往往會把西方和美國單一化,認為美國政府的觀點就是整個美國的觀點,或認為美國政府也像中國政府那樣能夠做成它想做的任何事情。事實上,美國是一個各種各樣聲音和力量并存制衡的社會,國會、政府、不同的黨派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不同的見解,而最終的現實政策則是各種力量博弈和妥協的折中產物。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包括政府高官——能夠取得永久性的壓倒優勢,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雙邊關系中的所有政策問題。再如,中國人常常以一種憤怒的心態對待西方媒體關于中國的負面報道,似乎這些媒體是刻意與中國作對。事實上,這是對言論自由之下的西方媒體傳統缺乏了解。美國媒體甚少歌功頌德,即便是針對美國自己的事務。可以說,中國的一句俗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是西方媒體遵循的永恒法則。需要進一步指出,中國民眾比較容易以善惡二分法的道德眼光去看待西方主張“中國威脅論”或其他不利于中國政策的人士。應當明白,其實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之所以鼓吹上述主張,不完全是因為他們本人對中國懷有特殊惡意或仇恨(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對中國一無所知),而純粹是由于選票——他們只是站在自己背后的各個利益集團的傳聲筒而已。最后,即便是這些利益集團,鼓吹“中國威脅”的也未必因為對中國有多少偏見或敵意,而是為了現實利益。例如,叫囂“中國威脅”和“中國饑餓”最響亮的分別是美國的軍火商和農產品出口商利益集團,它們也許不一定討厭和反感中國,只是為了多賣掉武器和抬高糧食價格而已。只有深刻解剖并精通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才有可能找到問題的關鍵對癥下藥,采用各種技巧參與并利用這種博弈,獲得我們想要的理想結果。
中國另一個巨大困難存在于國家戰略層面,也就是對自己的未來作什么樣的角色定位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一直秉承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確立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維。然而,形勢是在不斷變化中的,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所有問題上一味韜光養晦,一方面不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越來越難以做到這一點:在許多問題上,即便我們自己不想作出明確表態,外部世界也會逼迫我們這么做。在迫使中國作出明確的立場選擇這個問題上,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是截然不同的。對西方而言,中國會不會在不久的將來利用自己日益強大的實力推翻現有國際秩序,這正是所有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中最核心的問題。雖然中國自己在所有場合不厭其煩地保證,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永不稱霸,但看起來這種宣示并不能有效地打消西方的疑懼。“冷戰”結束后的10多年里美國的單極強權早就讓許多非西方國家——甚至還包括一部分西方國家本身——產生強烈的抗拒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希望看到中國力量的崛起,甚至期望中國能夠扮演美國勢均力敵的挑戰者的角色,因為這會讓它們在國際上擁有更多選擇,從而在左右逢源中牟取最大的自身利益。
中國需以“確定”應對“不確定”
面對世界對于所謂“中國不確定論”的擔心,中國需要有一個“確定的”發展戰略,并且向世界宣明自己的這一追求。保持自己角色的相對模糊在很多時候能夠帶來戰術上的靈活性,因而是必要和機智的,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贏得尊重、信任和威信;中國一直不像前蘇聯那樣高舉意識形態旗幟,這幫助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外部對抗,但作為一個舉世矚目并且是“負責任”的大國,對自己所努力追求的目標缺乏明確的宣示,這使中國只能被動地對國際事件作出反應,而無法主動地進行組織和協調。正如西方分析人士指出的,要成為并扮演好一個世界級大國,光靠外交上的聰明機智是遠遠不夠的,單有購買力也是不夠的。雖然美國的外交政策已令許多國家心生厭煩,但它畢竟建立在讓國際社會聽得懂(不管它們接受還是不接受)的明確理念基礎之上。對于拭目以待中國將如何崛起的國際社會來說,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遲早必須填補。
但對當下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異常困難的任務,問題的核心仍在于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了,而且在高速發展過程中自身內部又積累了太多嚴峻的現實問題。面對未來,世界和西方最急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中國的承諾和保證,而是中國在“未來世界應該是怎樣的”這個問題上的清晰主張。在它們看來,只有這樣,它們才能根據自身的情況做出必要的調整,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任何一個真正的大國,都不可能在這些核心價值問題上長期隨波逐流。
可能要不了多久,中國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走到了戰略上的又一個十字路口。的確,中國自身也許永遠都不會接受“新世界領袖”的地位,但不接受不意味著別人不會把你當作“世界領袖”來看待、對待和期待,更不意味著你的對手就會不把你當作最大的威脅來防備和對抗。這是中國隨著自己的重新崛起而面臨的抉擇。中國必須做出選擇,但選擇會越來越困難。在21世紀上半葉的幾十年時間內,中國必須在美國的追隨者與挑戰者之間尋找到第三條道路,美國必須在“非友即敵”的傳統二分法之外尋找到一條與自己實力相當的大國和睦共處之道。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