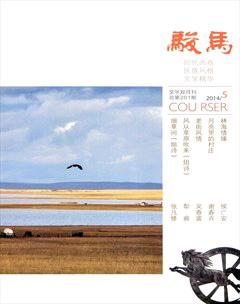隨園拾穗
陳湘濤
畢業于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現從事教育行業。先后在《南方周末》《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雜文月刊》《雜文選刊》《讀者(原創版)》《視野》《微型小說選刊》《微型小說月報》等報刊發表作品,開過報紙專欄。系新疆作家協會會員、烏魯木齊市作家協會理事。
狀元雖好卻非郎
去年六月的一天深夜,新出爐的武漢理科高考狀元黃翌青在人人網上更新了一條留言:“得到了全市的美譽,得不到你的駐足”,引起了大家的關注。網友從中讀出了“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的淡淡憂傷。學霸的再次表白顯然不是很成功,后來他悻悻地發了條微博,說:“匿了。”算是宣告徹底放棄,偃旗息鼓了。
才子沒有佳人配,往往是現實。英雄抱得美人歸,終究是戲文。倘若黃翌青同學心目中的女神,只是因為他考中狀元,就委身于他,這感情來得就太功利了。
武漢理科狀元的遭遇,讓我想起了袁枚的《隨園詩話》里記錄的一個故事:“汪應銓中狀元時,年已四十余,面麻,身長,腰腹十圍。”他在老家就有一位結發妻子。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美少女對他傾慕不已,上門提親主動要求當妾的絡繹不絕。這當中有一個家住京城的陸小姐,尤其主動。陸小姐讀過書,平日里最愛看的就是才子佳人劇,誤認為狀元都是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如戲中的男主角一般。她一再讓家人派人上門提親,要給汪狀元做妾。汪狀元欣然同意了這一門親事。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第一次見面,燭光之中,陸小姐看到汪狀元的相貌后,大失所望,又見狀元飲酒后酩酊大醉,粗俗不堪,越想越悔,五更天時,竟懸梁自盡了。這一起由婚姻引起的悲劇在當時鬧得滿城風雨。后有好事者送汪應銓一副對聯:國色太嬌難作妾,狀元雖好卻非郎。
有人說,浪漫主義就是主體把審美的愿望投射到一個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對象上去,通過對該對象的詩化的理解來宣泄對現實的不滿,心理上滿足內心未遂的愿望。這位陸小姐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癥患者。郭沫若曾用十個字總結古代戲文套路:相公纏姑娘,奸佞害忠良。戲里面的相公,往往出身寒門,或是受迫害沒落的忠良子弟,偏偏有傾國傾城貌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或青樓頭牌喜歡,最后通過努力,都中了狀元,并娶回了心儀的姑娘。也許是覺得身邊的男人不如戲文里的狀元才子出眾,也許是認為自己的生活不如戲文里名門小姐精彩,陸小姐有了入戲扮演角色的機會,就不顧一切地去抓它。等到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又不愿接受現實,因此喪了命。
想起有一次同學聚會時,大家玩一個真心話的游戲。讓參加聚會的同學,每人說一個上學時心儀的對象,限定在本班范圍。那時班里有個品學兼優、家境優越的男生,用清代文人張潮的話說就是: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都以為女生會一致指向他,誰想到竟然沒有一個人提他。私下一問才知道,原來女生們都覺得他缺少一點親和力,不好打交道。甚至有女生說他不知風月,不懂生活,似乎對女生不感興趣。想必這也是優等生的一種通病吧,像武漢理科高考狀元黃翌青這樣一心二用者,實在少之又少。
現實中那些杰出人物身邊的女人,也未必總能幸福。很多人的生活就像張愛玲筆下華美的睡袍,里面生滿了虱子。印度圣雄甘地的結發妻子嘉斯杜白就是如此。甘地憂國而忘家,家里經濟狀況很差,老婆孩子要吃要喝,甘地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柴米油鹽的事情搞得圣雄很煩。甘地又長期禁欲,嘉斯杜白自然不滿,時常向他哭哭啼啼。圣雄發怒了,竟完全忘記了他的非暴力主張,狂怒下大興家庭暴力,對老婆拳打腳踢后逐出了家門。這樣一個人,外面當圣人,家里當魔鬼,女人遇上都會倒霉的。
當然,一定也有才情不凡、懂得生活、事業有成的“狀元郎”。能遇到并嫁了的,那才真正是前世福慧雙修得來。
誤它千歲鶴歸來
《隨園詩話》里有個故事說:江西某太守要砍伐一株古樹,有客得知,事前在樹上題詩一首云:“遙知此去棟梁材,無后清蔭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它千歲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遂命不伐。
故事中的無名客有著相對超前的環保意識,太守也有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兩人一勸一從,不僅保住了一棵古樹,也留下了一段佳話。
更早的時候,也有一段寫詩阻人砍樹的故事,找的理由同樣是歸鶴無枝可依。勸阻者卻大大有名,是宋代濟癲和尚,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濟公。他為了勸阻臨安趙府尹伐凈慈寺門前的松樹,也寫了一首詩,末尾句就是:最苦早間飛去鶴,晚回不見舊時巢。這很可能是《隨園詩話》中故事的母本,只是不知道趙府尹聽沒聽瘋和尚的勸告。
人生際遇無常,偏偏造化弄人,張冠李戴,鳩占鵲巢,人海孤鴻,無枝可依,悲苦常生于此。
早期的香港電影里,周潤發善演孤膽英雄,導演往往還會給他加一些苦情的戲份,使得劇情更波瀾,人物更豐滿。最苦情的戲不是《喋血雙雄》里殺手小莊與盲歌女彼此呼喚著相向爬過,卻沒找到對方,而是林嶺東執導的電影《俠盜高飛》中,高飛被判官打傷,女友誤以為他死了,投身高飛的好友沈四的懷抱。高飛回來后,先是躲躲藏藏,等到三方相見,都痛苦不堪。
吳宇森在《縱橫四海》里,也設置了這樣的情節,不過他處理得更加高明,阿海、阿占、紅豆,三個人表面上不動聲色,但難掩尷尬和糾結。三人都有大智慧,明白覆水難收的道理,都默契地選擇了尊重現實。沒有傷感的眼淚,沒有虐心的告白,沒有激烈的爭吵,沒有虛偽的謙讓,只是鸚鵡的一句“紅豆妹妹”,表露出阿海的心跡,但也只是增加了一點點尷尬氛圍。電影的結局也頗有喜劇性,阿海竟然成了阿占和紅豆的保姆。
兩部電影時隔兩年,編劇不同,橋段相似:男主角死里逃生,卻發現琵琶別抱,無家可歸了(美國電影《珍珠港》中,也有同樣的劇情)。情未斷,緣已了,明知是命運安排錯了,卻無力糾錯,只好忍受現實的尷尬和內心的煎熬。
現實中也有這樣的故事。
1939年秋天,趙丹告別了妻子葉露茜與同伴來到新疆,準備在那里開辟新的戲劇事業,被軍閥盛世才逮捕入獄。為此,葉露茜長途跋涉到新疆,到處奔走,設法營救丈夫,不成,只好又回到重慶。 1943年2月,傳說趙丹被盛世才槍殺,葉露茜痛不欲生,并打算以身殉夫。還是在友人的多方勸阻下,考慮到趙丹的兩個孩子,葉露茜才打消了輕生的念頭。隨后,葉露茜為了兩個孩子的生存,與趙丹的好友、劇作家杜宣結婚。
1945年的清明節前后,趙丹從新疆突然逃回了重慶。此時,葉露茜已懷上了杜宣的孩子,她對趙丹說:“我已經毀了一個家庭,我不能再毀另一個。”兩人就此徹底分手。趙丹沒有埋怨葉露茜,只說了一句話:“一句謠傳,害得我妻離子散。”
“想人生最苦離別。雁杳魚沉,信斷音絕。”這是劉庭信的《折桂令》中的句子,道盡了離人之苦。其實離別未必最苦,還有一種苦,叫“苦相逢”。
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