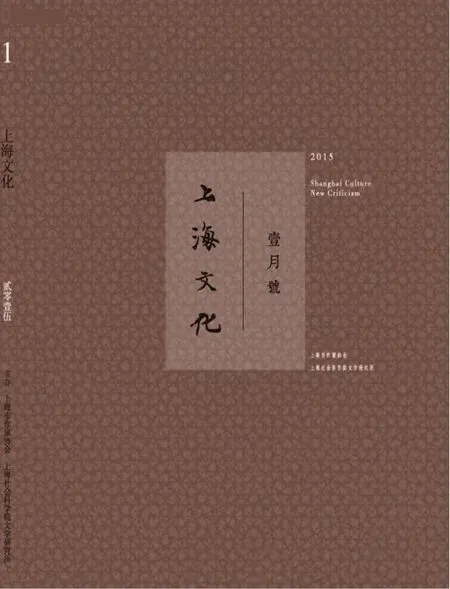徽章的力量張嘉佳《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項靜
徽章的力量張嘉佳《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項靜
一
每一個人之于這個“全世界”來說,都是飄蕩的碎片,但它們拒絕成為漫長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
張嘉佳鋪排華麗而揉捏到位的文藝腔調,孤注一擲坦白給世界看的風格,廢話流般讓人沒有喘息空間的語速,讓我們在集體妄圖現實主義的焦慮中放了個風。如果我們把張嘉佳的作品稱為小說,小說的本體論人物就在于為我們重新找回昆德拉漂亮地稱之為“生命的散文”的東西,而“沒有任何事物像生命的散文如此眾說紛紜”。
一旦被列入生命的散文這樣寬泛而沒有現成章法的體裁,就會發現張嘉佳的小說世界也是豐滿而又誘人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是一部后青春回憶錄,是一部摻雜了七情六欲的青春奏鳴曲,他的“全世界”從作品來看,就是愛情、青春、友情、游歷、放蕩、豪邁、不羈等等,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到處串場,轉身卻又不見。有溫暖的,有明亮的,有落單的,有瘋狂的,有無聊的,也有莫名其妙的,還有信口亂侃、胡說八道的,每一個人之于這個“全世界”來說,都是飄蕩的碎片,但它們拒絕成為漫長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
邁克爾·伍德在論及昆德拉的小說人物時說,不管在小說里還是小說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們的需要對我們而言是否真實,我們是否能夠想象他們的人生。所有令人難忘的小說人物,既是真實的,也是想象的歷史的片段,是搜集起來用語言重新創造的歷史的片段,所以他們像我們見過的人,而且比這更好的是,也像我們還沒有見到的人。
“他們的需要對我們而言是否真實”這個標準應該有兩層意思。第一,用毛姆的話說,可能就是人物的個性。他們的行為應該源于他們的性格,決不能讓讀者議論說,某某人決不會干那種事的,相反,要讓讀者不得不承認,某某人那樣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次,還是一個“他們是怎樣的人”與“他們是誰”之間的差別,很多專注內心的小說一直纏繞的問題是他們是怎樣的人,而有縱深感覺的小說才會關注他們是誰的問題。張嘉佳小說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怎樣的人?我們可以簡單組合一個群落:他們有過微時的落魄,他們說著廢話流抵御著生活中的那些傷害,分手或者離婚;他們有過賺錢的幻想,被打擊了之后沉迷于游戲;他們愛著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姑娘,用全部的心血和熱情,但有的成功共同回憶往事,有的失敗完成自我成全;他們愛著自己的狗伙伴梅茜,他們知道不是狗離不開他們,而是他們離不開那只狗;他們愛著那些消失了的人:姐姐或者某個讓你心動的姑娘;他們離開腳下的土地,去放開那個被捆縛住的自己。他們是一些面目不甚清爽、真實生活著的青年人,他們的生活因為張嘉佳的敘述而有了一種戲劇性,但萬宗歸一,他們就是《那些細碎卻美好的存在》中玄虛而言的那種普普通通的存在者,“不想那些虛偽的存在,這世界上同樣有很多裝逼犯,我偶爾也是其中一個。如果尚有余力,就去保護美好的東西”。
如果所謂的“歷史”是重大事件的話,這一代人幾乎沒有進入過“歷史”,張嘉佳不是去復制經歷過的生活,而是來營造一種與其說是差強人意的歷史感覺,不如說是一種熟悉感。世紀之交的這一段時間,異地戀的校園電話卡這種時光漸逝的見證物,初戀的兵荒馬亂的情緒,還有那些具體而又潛藏著共同記憶的生命中的時間,制造了一種熟悉感——比如“1999年5月,大使館被美國佬炸了。復讀的我,曠課奔到南京大學,和正在讀大一的老同學游行”;“2000年,大學宿舍都在聽《那些花兒》。九月的迎新晚會,文藝青年彈著吉他,悲傷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去呀,她們已經被風吹走,散落在天涯’”;“2001年10月7日,十強賽中國隊在沈陽主場戰勝阿曼,提前兩輪出線,一切雄性動物都沸騰了,宿舍里的男生怪叫著點燃床單,扔出窗口”;“2002年底,非典出現,蔓延到2003年3月。我在電視臺打工,被輔導員勒令回校。4月更加嚴重,新聞反復辟謠。學校禁止外出,不允許和校外人員有任何接觸”(《末等生》)。
他們像我們見過的人,而且比這更好的是,也像我們還沒有見到的人
接下來一個更需要追問的話題是,而他們是誰?他們來自哪里?可能是來自東北的一個姑娘,可能是江蘇的某個小城市男孩,與當代中國電影電視劇中的小鎮青年面目相似。他們所歸屬的是城市的中等階層,如今他們有著不錯的收入或者還是一些來歷不明無需確證的富二代,他們能夠轉身就離開困境,下個決心就能去周游世界。比如在《駱駝的姑娘》中,朋友失戀了,就可以勸他,老在家容易難過,出去走走吧。他點點頭,開始籌備去土耳其的旅行。這不是一個普通凡俗的人可以擁有的選擇,他們非常便利地追尋和享用旅行的意義,“意義不是逃避,不是躲藏,不是獲取,不是記錄,而是在想象之外的環境里,去改變自己的世界觀,從此慢慢改變心中真正覺得重要的東西。就算過幾天就得回去,依舊上班,依舊吵鬧,依舊心煩,可是我對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變都沒有發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書,我這本也比別人多了幾張彩頁”(《美景和美食》)。他們篤信“美景和美食,可以抵抗全世界所有的悲傷和迷惘”(《美景和美食》)。
張嘉佳的敘述是直白而坦誠的,這些人在流行文化中長養著,并被流行文化塑造了人生和世界
張嘉佳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接受了大學教育,無論對這個制度是嘲諷還是無動于衷,他們基本都坦然接受了大學教育。除此之外,看不到更多的明晰的文化背景,或許從小說中人物的自我“坦白”可以瞥見某種端倪。《旅途需要二先生》中提到過早年看的《大話西游》和美國公路片,和淚共唱的《一生至愛》。《河面下的少年》中則有一大段關于我們青春的排比堆砌的各種流行文化符號,“我們喜歡《七龍珠》。我們喜歡北條司。我們喜歡貓眼失憶后的一片海,我們喜歡馬拉多納。我們喜歡陳百強。我們喜歡《今宵多珍重》。我們喜歡喬峰。我們喜歡楊過在流浪中一天比一天冷清。我們喜歡遠離四爺的程淮秀。我們喜歡《笑看風云》,鄭伊健捧著陳松伶的手,在他哭泣的時候我們淚如雨下。我們喜歡夜晚。我們喜歡自己的青春”。張嘉佳的敘述是直白而坦誠的,這些人在流行文化中長養著,并被流行文化塑造了人生和世界,它們是這一代人的文化基礎,是他們表達自己的情緒基礎,也是他們情感共同體的入場券。男歡女愛的模式,對情感的態度,還有自我解脫的方式,戲謔而無奈的語調,基本上都是來自于這種流行文化的滋養。
張嘉佳的作品不是這個時代的孤例,可以推而廣之。韓寒的一個APP,他新拍的電影《后會無期》;新媒體上的非虛構寫作“記載人生”、“果仁小說”等;寫《誰的青春不迷茫》、《你的孤獨,雖敗尤榮》,以“坦白說”作為口頭語和個人標志,分享自己的成功與失敗捕獲大量在校生擁躉的劉同;《最小說》中厲害的寫手安東尼,寫作從來不加標點符號,擅長從平淡生活中發現閃光點,捕捉生活小情趣,筆下文字自成一統,充滿童話夢幻色彩。他們都可以在一個寬泛的意義上歸為同類。如果從“同時代人的寫作”最表面的意思來看,他們的確是在制造一種半徑最大的共同體情感,我們的青春,我們的愛恨情仇,我們的粗糙與不經,不悔與悲壯,尋找與迷茫。劉同的讀者在給他的留言里說:“《孤獨》卻讓我深受震撼——正在經歷的孤獨,是迷茫;經歷過后的孤獨,是成長!青春是一本書,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故事,這些故事或悲傷,或愉悅、或留在記憶里成為不想觸碰的紅色區域、或成為隨時都想與朋友分享的光輝事跡……不論是什么樣的故事,都離不開親情、友情、愛情的主題。”他們是以平等分享的方式來面對自我經驗的。長期以來我們評判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基本基于如下的原則,不是它能在哪些方面服務于我們,而是看它讓我們擺脫怎樣的思維定勢。但張嘉佳們是逆行于這一原則的,它首先是服務于讀者的,是體貼入微的寫作,更重要的,他是跟你在一起的。尤其是對1980一代人來說,他非常樸素地喚起了一代人的共同生活圖景,當然那也只能是一個曾經非常樸素的生活時代,才能在目下煊赫的時代,引來念念不忘之回響,“在空閑的時候,我和大家說睡前故事,從來不想告訴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是告訴你活著會有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每個人都不同,所以不需要別人的教導。只需要時間,它像永不停歇的浪潮,在你不經意的一天,把你推上豁然開朗的海闊天空”(《寫在三十三歲生日》)。
當然張嘉佳幾乎每一個故事的最后必然有一顆對世界的熾熱之心,拒絕指向虛無與悲觀,這反而與嚴肅文學或者說文學雜志上的文學有一道明晰的界限。幾乎所有文學期刊上的人生故事,都沉浸在一種青年失敗者的氛圍中,“這個時代有點糟”,“我們是一群失敗者”成為難以克服的最終反應。他們在強力的時代洪流和宏大的社會運轉中,沒有獲得先機,于是隨波追流,陷入平庸與重復,跌入虛無的深淵中。在《獵頭的愛情》中,獵頭的女友崔敏曾經被人懷疑偷了錢,他們打工賺錢,想還給被偷的女孩,讓她消除錯誤的猜測,但等到他們攢夠錢,彼時女孩已經轉校。十年之后的聚會上,獵頭的男人誓言是,“一旦下雨,路上就有骯臟和泥濘,每個人都得踩過去。可是,我有一條命,我愿意努力工作,拚命賺錢,要讓這個世界的一切苦難和艱澀,從此再也沒有辦法傷害到她”。雖然這個故事里面有命運的無常,生活中淡淡的艱辛,但張嘉佳始終讓整個故事沒有離開既有的跑道,這個無常并沒有改變他們生活的本色,他們依舊有著回憶時刻的萬丈光芒。張嘉佳這種毫無遮蔽之意的文字,大概是在這個時空中所能做到的最不虛無的,雖然這些文字的底色說到底還是虛無的,人終有一死。或者如奈保爾《河灣》的開首語,“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聽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這世界上沒有位置”。在人生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方法的時候,或者說這個部分是個人努力與奮斗所無法觸動的銅墻鐵壁的時候,這些可口的文字是精致包扎后送到跟前來的一個看上去完美但又粗糙、簡單的生命“解釋”:“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會讓你付出代價,照顧好自己,愛自己才能愛好別人。如果你壓抑,痛苦,不自由,又怎么可能在心里騰出溫暖的房間,讓重要的人住在里面。如果一顆心千瘡百孔,住在里面的人就會被雨水打濕。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會讓你付出代價,但最后,這個完整的自己,就是上帝還給你的利息”(《寫在三十三歲生日》)。
納博科夫說,風格與結構才是一部作品的精華所在。張嘉佳當然形成了自己的簡單粗淺的風格,他喜歡機關槍一樣的語速,樂在其中,奇異的排比句,句子的空洞而炫麗,說過好像沒有說過一樣,可能他們與讀者的快感全在于說出的這個華麗麗的過程。那些呢喃的話語的確具有按摩治愈的療效,死于列車出軌的朋友多艷,就是靠著這種排比句,從悲痛、愧疚轉而消弭到青春無悔的模式去中了,“紀念2008年4月28日。紀念至今未有妥善交代的T195次旅客列車。紀念寫著博客的多艷。紀念多艷博客中的自己。紀念博客里孤獨死去的女生。紀念蒼白的面孔。紀念我喜歡你。紀念無法參加的葬禮。紀念青春里的乘客,和沒有返程的旅行”(《青春里沒有返程的旅行》)。
張嘉佳幾乎每一個故事的最后必然有一顆對世界的熾熱之心,拒絕指向虛無與悲觀,這反而與嚴肅文學或者說文學雜志上的文學有一道明晰的界限
張嘉佳的語言文字以及唯美的故事容易讓人沉迷,以至于我們會暫時擱置這一代人不言自明的生活語境,憧憬著有一種生活如他們一樣綻放或者放浪。他們無一例外都不談時代的艱難,沒有腐敗、礦難、貧富差距、自我囚禁、時代板結,沒有徹底的絕望,龐然怪物般的空虛。當然他們也很少以正面的方式談論歷史、政治,這些幾乎都是一種簡單的裝飾性背景,是作者不管如何回避經驗都無法摩擦干凈的歷史痕跡。比如“文革”,以他習慣的“鑲嵌”方式出現在一篇故事中。一個老三屆的媽媽,教訓年輕兒子不敢表白愛情,“我上山下鄉,知青當過,饑荒挨過,這你們沒辦法體會。但我今兒平安喜樂,沒事打幾圈牌,早睡早起,你以為憑空得來的心靜自然涼?老和尚說要見山是山,但你們經歷見山不是山了嗎?不趁著年輕拔腿就走,去刀山火海,不入世就自以為出世,以為自己是活佛涅槃來的?我的平平淡淡是苦出來的,你們的平平淡淡是懶惰,是害怕,是貪圖安逸,是一條不敢見世面的土狗。女人留不住就不會去追?還把責任推到我老太婆身上!呆逼”(《老情書》)。沉重的歷史、殘酷的往事,以一個老太太戲謔的方式拉平到愛情的俗套上。這是時下多數文學的通病,只不過有病理深淺的區別。
現在的張嘉佳是一個定制版的綜合體,我們可以在張嘉佳的暖男體小說中時時遇到熟悉的聲調、故事
有一種說法,在一個涌動著無數暗流、貧富差距每天都制造不同故事的時代,如果不涉及現實,不主動擔負起歷史責任就是不道德的。而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這種道德基本是針對嚴肅文學的,也會在許多偶然時刻,比如它們太招搖過市時,成為揮向通俗文學的定制武器,雖然結果都是各說各話。從經典文學的角度來衡量、蔑視、忽視甚至鄙薄通俗文學是容易的,就像我們一直所做的那樣,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歷史傳統,也有鮮明案例。而現在雞湯文的命名是最便捷的方式,只要被歸入這個范圍,就像刺上紅字的奸夫淫婦,愿意吐上一口罵上一句固然是正常的人類選擇,最高傲的方式莫過于“轉過頭去視而不見”,當然這也是一句非常流行的雞湯文。
無論我們如何談論通俗流行文學,也或者避而不談,都不能阻止這種文學的突然瘋狂成長,或者一直成長。張嘉佳的睡前故事大概是今年最為暢銷的文學類書,據說在上海書展期間銷售量僅次于郭敬明。當有大約二百萬的人都在閱讀一個80后作家絮叨睡前故事的時候,加上王家衛拍成電影,這個數量還會以更狂暴的方式上升,還是有一種壯觀的即視感。參加過這一次張嘉佳的見面會,一個城市里湊起來的人群,大部分是年輕的女人,年紀相差在五歲左右的范圍,有過共同經歷的一代人,當然還有一些老的小的文藝青年。伴隨著柔和輕緩的音樂,飽含午夜電臺文藝散文朗讀腔調的女聲,駕輕就熟地讀出張嘉佳的那些與狗狗梅茜的故事——《給我的女兒梅茜,生日快樂》:“我們要沿著一切風景美麗的道路開過去,帶著你最喜歡的人,把那些影子甩在腦后。去看無限平靜的湖水,去看白雪皚皚的山峰,去看芳香四溢的花地,去看陽光在唱歌的草原……去遠方,而漫山遍野都是家鄉。”一個愛護動物又不是激烈的貓狗平等主義者,一個情貼心靈的麥田守望者,一個敏感不屈滿懷熱情的靈魂,一個歷經滄桑初心永葆的大眾暖男的作家形象,呼之欲出。
銷量和影響大到成為現象的此類通俗大眾文學,改革開放以后是從瓊瑤風靡開始的,歷經岑凱倫、安妮寶貝,知音體、讀者文、張小嫻、連岳、陸琪等,其實我懷疑村上春樹、昆德拉部分也是被以通俗文學的方式接受的,在這個名單上似乎還可以加上王朔、王小波、石康等。不管是經典作家,還是二流段子手,在大眾讀者接受的角度上可能都是被扯平了的,都是我們心靈的按摩師。而不得不說的是,現在的張嘉佳是一個定制版的綜合體,我們可以在張嘉佳的暖男體小說中時時遇到熟悉的聲調、故事,有波拉尼奧式漫游的不羈,有王朔式的痞氣,有青春的粗糙雜亂,也有周星馳式的戲謔無厘頭,有瓊瑤愛情女神的執著,有連岳、陸琪的雞湯風范,還有韓寒電影中的類似的“沒有看過世界,怎么會有世界觀”的行動哲學,還有許多其他面目熟悉的二手哲學。總之,這個張嘉佳不是橫空出世,而是慢慢浸染中成長出來的一顆飽滿碩大的果實。
張嘉佳的小說幾乎沒有特別鮮明的都市志痕跡,城市只是他小說故事的發生地
三
張嘉佳,198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通市的姜灶鄉,典型的南方小鎮,母親是教師,父親是公務員,典型的中國小康家庭的唯一的孩子。張嘉佳的個人生活,除了學習成績忽上忽下無奈去復讀外,看起來沒有什么坎坷。他不是眾多文學作品中那種備受壓抑、心緒發達、內心敏感、帶著痞氣掙扎在社會邊緣的典型小鎮青年。張嘉佳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小鎮神童,三歲時候就通過識字卡片認齊了基本漢字,開讀《神雕俠侶》。小學之前,把小鎮上能找到的金庸小說都讀完了。雖然母親是數學老師,但張嘉佳的數學卻很少及格,母親甚至有時幫他做作業。四年級時,學校舉辦書法、圍棋、作文等各種各樣的比賽,張嘉佳說:“第二天升旗儀式,所有比賽(我)都是第一名,在小鎮出名了。”小鎮生活留給他的另一部分回憶就是,稻田、河流、村莊的炊煙、金燦燦的油菜花;抓知了、摸田螺、偷鴨子,率領三百條草狗在馬路上沖鋒……小鎮是張嘉佳心中的童話世界,日后在自己的小說里反復出現。而張嘉佳在小鎮上的人生以升入大學劃上逗號,跟所有當代中國的小鎮青年一樣,他們都迅速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但張嘉佳似乎并沒有經歷過從城市與鄉村的巨大的心理差距(至少從他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不出來),而這種心理落差幾乎是近五十年來當代文學中一個最為重要的母題,并且成為支撐起當代文學半壁江山的故事原型,從《霓虹燈下的哨兵》到路遙的《人生》、李佩甫的《羊的門》,甚至80后作家韓寒這種上海周邊小鎮出生的作家,也都先天有一種反抗都市的意味在作品和言談中。另外,張嘉佳小說中也沒有都市在地青年的那種天然的存在感,以及故意聲張的“地方志”心態,這些東西日后都以迷茫自戀(憐)、沉溺式的都市青春小說的方式發泄出來。張嘉佳的小說幾乎沒有特別鮮明的都市志痕跡,城市只是他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除了幾個南京地名,我們很難看到他對都市生活巨細靡遺的細節性的熱愛,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城市生活本身的表述。由此,那種寓居都市生活的屈辱、奮斗、掙扎的心態都可以略去不表,都市生活文學呈現的陳詞濫調省略不說,這就造就了一種極為簡潔、流暢,語速極高,具有速度美的故事流線和抒情語流,也為他小說中的自由隨意的心態提供了一種合理性,為小說的輕逸擺脫了多重負累。連人物形象他都開始拒絕往人性深處伸展了——這幾乎也是當代文學的另一個母題(人性的復雜、人心的暗夜等)。他的小說人物都是那種具有“飛蛾撲火”式美學意味的人物,他們說走就走,不計得失,甚至沒有了現代人的算計,離婚的男人動不動就凈身出戶,以表示對曾經愛情的尊重;暗戀的女人們也都深埋愛情,為那個感受不到愛的男人付出到底。這一切讓在現實中翻滾的人們看來,的確是一個具有誘惑力、幻想性,并且因為小說中生活語境的鋪陳又具有一定現實可行性的類“仙境”。
我們都在訴說自己,對忠實地想象他人的生活,失去了興趣,或者喪失了這種能力
四
在嚴肅文學(或者說雜志、出版社文學)之外,當代中國一直有一批擁躉眾多的作家,他們很難說屬于通俗文學,但他們屬于和鳴最多的作家。他們輕剪人們心翼上的星點,有時候也不過是蹈常襲故,但他們始終是體察時代人心的一條明晰的線索。從張嘉佳到劉同、安東尼,以及新的微信寫作,好像我們都在訴說自己,對忠實地想象他人的生活,失去了興趣,或者喪失了這種能力。莫里斯·迪克斯坦特別關注美國文學中20世紀60年代作品中的坦白趨勢,這種趨勢試圖把文學從某種停滯不前的形式主義中解放出來,使之接近于個體的體驗。張嘉佳類似的創作傾向當然無法與美國1960年代文學傾向類比,但大體的歷史情境頗多類似之處。我們也面臨某種停滯不前的文學形式,作家們延續著重新模擬事實發生的世界,并由此模仿前輩作家們的思想承擔,并幻想獲得道德和責任上的光榮與夢想,對現實發出一種聲音。此外,新的文學形式比如網絡小說等以乖張龐雜的形式吸引了大量欲與欲求的讀者,但這又很難獲得渴望精神食糧的青年一代的芳心。張嘉佳們的作品拒絕、回避承擔透視生活的窗口的作用,它是寫給自己和同類的,就像公眾微信號“記載人生”的口號,“和對的人在一起”。相對于想象他人的生活,為自我構想一個可能的人類情境,這些作家更在意自己同類人的世界。在形式上,他們的作品更像是隨筆或是小品文而不是小說式的敘述,每一個人都有許多故事要訴說,每一個人都有許多情感要傾吐。
“唯我一代”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懈怠,過于關注自我,或者缺乏想象力而造成的,但也可能和某種文化氛圍有關,貶低技藝和創新、鼓勵自我表達的文化氛圍。將創作者代入作品,可以消除幻想和對生活的平庸模仿,使得讀者聽眾更加關注形式。坦白式的寫作方式,不需要辛辛苦苦地設計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性格和周遭環境,也不需要提出曾經讓現實主義小說榮耀一時的歷史洞見。按照莫里斯·迪克斯坦的意見,這些小說的作者“僅僅是作者自己,而不是就現實和再現的關系提出問題,進行反思。他們沒有讓我們走到幕后,去看藝術創作的過程,看作品在表述中如何觀看自身,但是他們也不是完全虛構出來的人物,擁有無限可能的神秘和意外,他們只是寫作的人:對他們而言,當務之急是要將那些素材寫下來,盡管他們也讓故事的主人公陷入愛情與戰爭,但人物角色只可能生活在作者無處不在的光環之下”。
郭敬明為安東尼《陪安東尼度過漫長的歲月》寫過一個序言:
他一直有一只玩具兔子,他取名字叫不二,走哪兒都帶著,一直帶去了墨爾本。他會和兔子說話,和它聊心事,和它分享心情,為它拍照(……),帶它出去散步(……),并且在我有一次稱呼不二為玩具的時候,和我鬧了一個星期的脾氣。
他甚至養了一棵像是食人花一樣的植物,并取名字叫GUZZI(好像是這個名字吧,忘記了)。他也會和它說話……他有一天告訴我GUZZI心情不好,我問他:“GUZZI是你女朋友啊?”他說:“不是啊,你看!”于是他開了視頻,把攝像頭轉向他房間的角落,于是我看見了一棵心情不好的食人花……
這是一段非常呆萌的文字和一個讓人無法自矜的形象,讓人萌生出促狹短暫的愛與溫柔,為了一只玩具兔子鬧一個星期的脾氣,又或者跟一株植物說話。這都是唯我的氣息,我們可以體會那種短暫的氣息停留與眼神顧盼,或者也竟能付之于蕩氣回腸的愛與戰爭。最重要的是,它們就是生活與空氣,即使外面的人一直吶喊著要戳破生活的假象與幻影。但他們所寫下的愛情故事,細節的真實,萌動的思緒,還有大城市夜晚的每一條街道,廣袤世界的任何一個為我而存在的地方,都是一枚擲地有聲的徽章,散發著它微小而頑強持久的力量。奈保爾說,每個作家都是帶著一個社會、一種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給予他的安全感來寫作,他被這樣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所保護、所支撐,他永遠也做不到像海明威那樣去寫巴黎,帶著探險家的自得其樂去描寫狂熱去描寫狂斟豪飲和性奇遇,卻從不涉及街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海明威能夠以一個作家的身份來簡化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巴黎,而奈保爾卻無法把自己放在一個類似的位置上。他心里清楚,在1930年代,一個像他這樣出身的人絕無可能去到巴黎,就在這樣簡單的層次上已被拒絕。張嘉佳他們當然也是在許多簡單層次上已經被拒絕的作家,依靠著自己的安全感來寫作是許多作家沒有選擇的選擇,它只能是袖子上的一枚徽章,不會成為一具軀體,但我們能看到它各個角度的閃亮。
羅蘭·巴特說過,自己的任務是探索一種文學記號的歷史。他講過一件軼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論家埃貝爾在寫作時,總愛用一些“見鬼”和“媽的”這樣的字眼。這些粗俗的字眼并不表達什么,然而,這種寫作方式卻是當時革命形式的需要,它把一種語言之外的東西強加給讀者,形式的歷史表現了寫作與社會歷史的深層聯系。張嘉佳們的小說、散文是我們這個時代有意義的一種文學記號,或者是肩膀上的徽章,或許正是靠著他們所提示的形式,才會指引下一次文學形式的變革,如果還會有變革的話。小說家卡薩塔爾不只把作家看作藝術家,也看作見證者,看作有偏見有人性、愿意學習的人,他認為我們需要從關心這個世界的人身上反觀這個世界。但從唯我一代這種寫作傾向的作家身上,似乎看不到對世界的關心,卻有享受的熱情和耐心。在平滑、鮮亮、炙熱、奶白色的光韻之外,伸展的是一片霧氣和不安的深淵。但有時候,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大城市夜晚的每一條街道,廣袤世界的任何一個為我而存在的地方,都是一枚擲地有聲的徽章,散發著它微小而頑強持久的力量
編輯/吳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