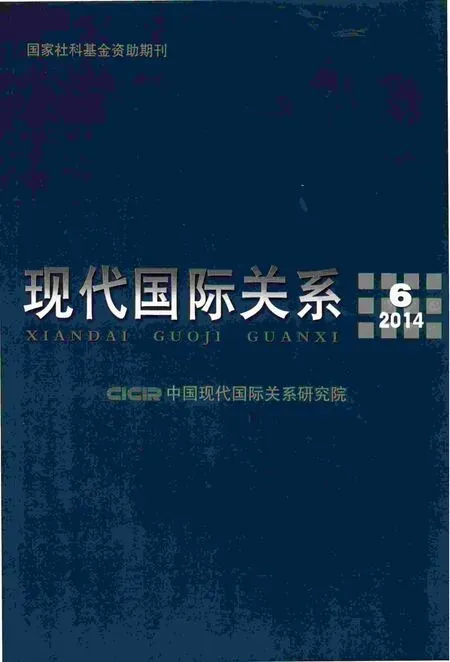美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評析*
劉建華 陸華東
“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與安全相關(guān)的機構(gòu)從事的任何共同活動,通過一致工作而非獨立行事來增加公共價值,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①[美]尤金·巴達赫著,周志忍、張弦譯:《跨部門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頁。經(jīng)過長期探索,美國形成了以總統(tǒng)為核心的各種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全面考察美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對于正確理解其內(nèi)涵、運作方式、優(yōu)點及存在的問題均有重要意義,也對中國正在摸索中的國家安全體制建構(gòu)具有啟發(fā)意義。
一、制度化的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
制度化的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是指在事關(guān)國家安全的議題領(lǐng)域,由依法設(shè)立的專門委員會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跨部門安全政策。這種委員會往往根據(jù)安全環(huán)境變化由國會立法創(chuàng)設(shè)。它有相對固定的人員、組織結(jié)構(gòu)和運作程序,一般定期召開會議,委員會首長直接向總統(tǒng)負責,充當“政策顧問”。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國土安全委員會(HSC)和國家經(jīng)濟委員會(NEC)。
但是從委員會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運作程序的復雜程度來看,制度化的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和委員會層級協(xié)調(diào)兩種模式。
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涉及到的安全部門比較少,處理的安全事務(wù)也相對集中,一般不需要設(shè)計十分復雜的運作體系。這種協(xié)調(diào)模式涉及的部門和人員大都具有相似的專業(yè)知識和背景,比較容易在特定的安全政策領(lǐng)域形成共識并采取一致行動。正因為如此,該類委員會在遇到安全問題時,一般只需要相關(guān)部門的主要代表聚在一起,討論并進行決策即可。除HSC、NEC外,美國“國家情報總監(jiān)辦公室”(ODNI)、“國家反恐中心”(The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等機構(gòu)雖無“委員會”之名,但實際上承擔所負責安全領(lǐng)域的協(xié)調(diào)任務(wù),因而也可以劃入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HSC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人員規(guī)模僅有NSC的1/4,其職能主要是反恐和維護美國本土安全,主要成員也基本上都是與國土安全相關(guān)的部門,如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海岸警衛(wèi)隊等。NEC則是在1993年成立的,目的是綜合應(yīng)對經(jīng)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jīng)濟風險,其參與協(xié)調(diào)的主要是與經(jīng)濟和貿(mào)易安全有關(guān)的部門。②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31.ODNI負責協(xié)調(diào)包括CIA在內(nèi)的15個美國情報界機構(gòu)的情報活動。“國家反恐中心”的人員來自所有相關(guān)機構(gòu),通過將來自多個部門和機構(gòu)的專家聚集在一起,整合和分析與反恐有關(guān)的情報并集體策劃行動。
除常設(shè)委員會協(xié)調(diào)外,美國還設(shè)立了一些臨時的類似委員會的組織,負責協(xié)調(diào)和監(jiān)督海外重大且復雜的安全行動。例如小布什政府時期設(shè)立的“美國自由軍團”(U.S.A.Freedom Corps),該組織的領(lǐng)導委員會類似NSC,包括內(nèi)閣成員。“自由軍團”主任起著“總統(tǒng)的副主管”作用,他在“白宮辦公室”負責協(xié)調(diào)所有參與機構(gòu)的政策輸入和對“自由軍團”計劃實施的監(jiān)督。①President George W.Bush,Executive Order 13254,January 29,2002,“Establishing the USA Freedom Corps”,F(xiàn)ederal Register,Vol.67,F(xiàn)ebruary 1,2002,pp.4869 -4871.
與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不同,委員會層級協(xié)調(diào)模式是NSC“政策協(xié)調(diào)委員會-常務(wù)副部長級委員會-部長級委員會 -國安會”(PCCs—DC—PC—NSC)正式會議協(xié)調(diào)模式,常被稱為“斯考克羅夫特”模式,最早由老布什總統(tǒng)任內(nèi)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協(xié)助創(chuàng)立。②孫成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模式變遷及思考”,《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2014年,第1期,第31頁。該模式與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不同,具有明顯的層級性,其關(guān)注的是較為復雜的安全任務(wù)和跨部門協(xié)調(diào)過程。因此,NSC一般會將管理危機和安全事務(wù)的責任賦予一些次一級的“跨部門委員會”(Interagency Committees)。
NSC體系的政策協(xié)調(diào)可劃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NSC正式會議”,“部長級委員會”(PC),“常務(wù)副部長級委員會”(DC),“政策協(xié)調(diào)委員會”(PCCs)。③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p.35 -37.各層次協(xié)調(diào)無論是在級別、人員組成,還是在處理的安全事務(wù)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層級性。
“NSC正式會議”是NSC層級協(xié)調(diào)體系的最高層次,一般由總統(tǒng)出面召集,主要成員包括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國務(wù)卿、國防部長等。這類會議十分正式,主要用于協(xié)商和制定重要且宏觀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與政策。但是此類會議常常是在總統(tǒng)認為需要的情況下召開的,因此這類會議的召開頻率在不同總統(tǒng)任期內(nèi)具有很大的波動性。“部長級委員會”扮演總統(tǒng)高級別政策評估和協(xié)調(diào)組織的角色,是商討和處理國家重大安全事務(wù)的高級論壇,其具體成員隨著總統(tǒng)領(lǐng)導風格的變化和安全議題的不同而變化,經(jīng)常性的成員包括國務(wù)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等。國家安全顧問是這類委員會的主席,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不參加PC會議(除小布什時期副總統(tǒng)定期參加PC會議外)。④Alan G.Whittaker,F(xiàn)rederick C.Smith and Elizabeth McK-une,“Th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rocess: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agency System”,p.23,http://www.dtic.mil/get- trdoc/pdf?AD=ada502949.(上網(wǎng)時間:2013年5月25日)PC會議經(jīng)常召開,遠比NSC的正式會議頻繁,主要負責審查并決定重大的國家安全事項,“保證呈送給總統(tǒng)的是部門間盡可能達成的決策共識”。⑤Alan G.Whittaker,F(xiàn)rederick C.Smith and Elizabeth McK-une,“Th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rocess: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agency System”,p.23,http://www.dtic.mil/get- trdoc/pdf?AD=ada502949.(上網(wǎng)時間:2013年5月25日):2014年3月15日)“常務(wù)副部長級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由各安全部門的副部長級內(nèi)閣官員組成,在“次內(nèi)閣”(Sub-Cabinet)層面上協(xié)調(diào)跨部門安全合作,負責審視和監(jiān)督跨部門協(xié)調(diào)小組的工作進程,就國家安全政策的進展和執(zhí)行建言獻策。“政策協(xié)調(diào)委員會”比“常務(wù)副部長級委員會”低一個層級,其成員通常是助理部長等級的官員、NSC部分成員以及來自其他相關(guān)組織的代表。該類委員會按所涉安全議題的地域(如歐洲、東亞等)和功能(如國防、金融、情報等)設(shè)置。例如小布什政府時期設(shè)立了6個“區(qū)域性協(xié)調(diào)小組”和14個“功能性協(xié)調(diào)小組”,分別按世界的不同地區(qū)和不同的安全問題領(lǐng)域負責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⑥Gabriel Marcella,Affairsof State:the Interagency and National Security,2008,p.11,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chǎn)rmy.mil/pdffiles/PUB896.pdf.(上網(wǎng)時間:2013 年5月15日)PCCs時常會制作一些簡報和問題文件以補充DC和PC的工作,以輔助DC、PC層次的協(xié)調(diào)。另外,PCCs還肩負著監(jiān)督安全政策實施狀況的責任。⑦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0.值得一提的是,總統(tǒng)有時候還會將一些安全研究任務(wù)交給一些層級更低的“臨時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s)。例如尼克松總統(tǒng)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就曾將138個研究項目中的67個研究項目交給這些“臨時工作小組”。⑧John p.Leacacos,“The Nixon NSC:Kissinger’s Apparatus”,F(xiàn)oreign Policy,No.5,1971,pp.22 -24.
這種層級協(xié)調(diào)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對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的細化,它集中關(guān)注的是跨部門協(xié)調(diào)的具體過程和操作程序。這種模式就像一個分工明確但又相互合作的政策系統(tǒng)。從政策形成的角度看,所有的安全事務(wù)都被納入其中并進行分析、分類,以確定問題的輕重緩急,接下來再將重要性不同的安全問題分別交給PCCs、DC和PC去協(xié)調(diào)和處理;從政策輸出和執(zhí)行的角度看,重要的安全政策一般由總統(tǒng)參加的NSC正式會議制定,然后再依次下放到PC、DC、PCCs去逐步細化、協(xié)調(diào)、執(zhí)行和監(jiān)督。
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具有諸多優(yōu)點。首先,將各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召集在一起,部門間可及時溝通,減少分歧與誤會,增加互信。其次,可集思廣益,掌握更全面的信息,制定更加科學、可行的政策;同時也可有效地監(jiān)督各部門的政策執(zhí)行情況,有利于相關(guān)政策或決定與總統(tǒng)的總體國家安全戰(zhàn)略保持一致。①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2011,pp.5 - 10,http://www.crs.gov/.pdf.(上網(wǎng)時間:2014年3月20日)正是由于這種層級協(xié)調(diào)模式的存在,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才得以有效運轉(zhuǎn),相關(guān)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才能在實施過程中大體保持一致性與完整性。
但是,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一是正式化和制度化程度不夠高。這些委員會雖然都是依法成立,職能也有相應(yīng)規(guī)定,但是都不夠具體,人員設(shè)置和辦公制度也不是很完善。例如,NSC正式會議召開的次數(shù)就很不穩(wěn)定。1989年NSC共召開了38次正式會議,而1992年僅召開了4次。②White House Historical List of NSC Meeting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30 September2008,http://clinton4.nara.gov/WH/EOP/NSC/html/historical/Meetings.htal.(上網(wǎng)時間:2013年8月15日)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能和權(quán)限也具有模糊性,常常與國務(wù)卿和國防部長產(chǎn)生權(quán)限沖突。二是“議而不決”與“妥協(xié)折衷”問題突出。委員會協(xié)調(diào)一般主要采用召開會議的方式,但在委員會內(nèi)部每個成員的地位相同,很難較快形成有權(quán)威的協(xié)調(diào)中樞以領(lǐng)導該層面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眾多的部門往往在會議上爭論不休,造成大量的時間浪費和“議而不決”。此外,由于多元政治思想的影響,委員會協(xié)調(diào)的最終結(jié)果往往是各個部門妥協(xié)的結(jié)果,這樣的結(jié)果有時就像沒有協(xié)調(diào)一樣。這也正是很多美國總統(tǒng)不愿意召開正式的NSC會議的主要原因。例如,在決定是否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NSC就召開了多次會議,但是由于國防部和國務(wù)院的意見相左,會議常常是無效率的。③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1.三是過于依賴總統(tǒng)。各委員會成員基本上均由總統(tǒng)指定,總統(tǒng)的風格和偏好對委員會的工作影響巨大。例如NSC在不同總統(tǒng)任期內(nèi),其規(guī)模和權(quán)限就有很大的波動。④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2011,p.6,http://www.crs.gov/.pdf.(上網(wǎng)時間:2014年3月20日)
二、“牽頭機構(gòu)”與“政策總管”協(xié)調(diào)模式
為了彌補以上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的不足,同時也是為了減輕委員會特別是NSC政策協(xié)調(diào)的負擔,美國總統(tǒng)常常授權(quán)或者指定某一特定機構(gòu)或者個人負責協(xié)調(diào)特定的跨部門安全任務(wù)。根據(jù)主要負責主體的區(qū)別,該類協(xié)調(diào)模式又可以具體劃分為“牽頭機構(gòu)”協(xié)調(diào)模式和“政策總管”協(xié)調(diào)模式。
“牽頭機構(gòu)”(leading agency)協(xié)調(diào)指的是如果一個議題主要涉及一個部門或機構(gòu),總統(tǒng)會授權(quán)該部門單獨或主導協(xié)調(diào)相關(guān)部門共同行動。例如,在“自由伊拉克行動”期間,國防部起著臨時充當“牽頭機構(gòu)”的作用;國務(wù)院“重建與穩(wěn)定協(xié)調(diào)辦公室”承擔負責協(xié)調(diào)應(yīng)對復雜緊急事態(tài)的責任,并扮演一種永久性的“牽頭機構(gòu)”角色。⑤“NSPD-44:Management of Interagency Efforts Concerning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December 7,2005,http://www.irisc.net/site/Library/nspd-44.pdf.(上網(wǎng)時間:2013年4月28日)此外,美國“聯(lián)邦緊急事務(wù)管理署”在應(yīng)對“卡特琳娜”颶風災(zāi)害時,也扮演了這種“牽頭機構(gòu)”的角色。
必須強調(diào)的是,此種模式絕非“牽頭部門”的單獨行動,而是屬于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只不過參與部門的作用在特定問題領(lǐng)域并不對等。牽頭機構(gòu)之所以能夠成為主導,是因為它在這一問題領(lǐng)域掌握較多的資源、信息與經(jīng)驗,能力比其他部門更強,但是特定安全任務(wù)的完成仍然需要與其他部門協(xié)調(diào)合作。此外,這種“牽頭機構(gòu)”并非固定不變,只要問題領(lǐng)域轉(zhuǎn)變,相應(yīng)的“牽頭機構(gòu)”也會隨之易主。這種協(xié)調(diào)模式充分發(fā)揮“牽頭機構(gòu)”的專業(yè)優(yōu)勢與經(jīng)驗積累,厘清了合作中的權(quán)責關(guān)系與主次地位,有利于問題的快速和有效解決,是專業(yè)化分工與合作相結(jié)合的充分展現(xiàn)。但是,這種模式在具體操作中也暴露出一些棘手問題。一是“牽頭機構(gòu)”常常由強勢部門擔任,忽視了民主化與專業(yè)化標準。如國防部擁有強勢資源和人脈,經(jīng)常成為各種跨部門安全任務(wù)的主角,從而壓制了其他部門專業(yè)職能和經(jīng)驗的施展。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國防部在諸如經(jīng)濟重建、外國警察訓練、人道主義救助方面的多種外事活動中承擔了過多的角色,其所扮演的角色和占用的資源都“侵犯”了國務(wù)院、國際開發(fā)署等民事機構(gòu)的權(quán)限。①Catherine Dale,Nina M.Serafino,Pat Towell,“Organizing the U.S.Govern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Overview of the Interagency Reform Debates”,CRS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18,2008,p.7.二是存在官僚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障礙。合作中,其他部門對“牽頭部門”往往很難有效配合,因為這些部門覺得聽從“牽頭部門”的指令有損自己部門的利益和尊嚴。此外,部門官僚主義的拖沓、刻板和墨守成規(guī)往往不利于跨部門合作與創(chuàng)新。三是這種模式易使一項安全任務(wù)過度依賴一個部門,忽視安全任務(wù)的變化和問題解決方式的不同,缺少靈活性,最終可能導致政策的失敗。從以往的安全政策實踐來看,過度依賴一個部門的安全任務(wù)往往是無法完成的。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索馬里軍事介入和布什政府時期的伊拉克戰(zhàn)爭都是在前期過度依賴國防部,初期成效明顯,但是隨著時間延長,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給美國帶來了重大損失。②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p.122 -123.
“政策總管”(Czar)協(xié)調(diào)模式指的是總統(tǒng)可能賦予某個人以特殊的權(quán)力來協(xié)調(diào)不同部門之間的行動。由于這些“政策總管”具有很大的權(quán)力,人們常以“Czar”(“沙皇”)稱之。③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38.理論上講,應(yīng)當由 NSC負責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但是NSC的任務(wù)和工作往往過于繁重,使得其在特定任務(wù)或特定問題上無法投入全部精力和時間。為此,總統(tǒng)就需要任命一位有威望、有資歷的個人代表來協(xié)調(diào)不同的安全部門,集中應(yīng)對特定的或突發(fā)的安全問題。前國防部長蓋茨就曾形象地說道,“這個人的工作本應(yīng)由國家安全顧問來做,但只是由于他沒有時間罷了。”④David Sanger,“4 Years On,the Gap between Iraq Policy and Practice IsWide,”The New York Times,12 April 2007.例如,里根總統(tǒng)在“毒品戰(zhàn)爭”時也曾任命一名“政策總管”來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各部門共同反對和打擊毒品犯罪。小布什就曾任命根·魯特(Lt.Gen.Lute)負責全權(quán)處理伊拉克戰(zhàn)后的各項事宜,⑤Peter Baker and Robin Wright,“Bush Taps Skeptic of Buildup as‘War Czar’,”TheWashington Post,16 May 2007.還任命總統(tǒng)國家安全顧問和副顧問分別負責協(xié)調(diào)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個重大復雜行動中行政部門的工作。⑥Catherine Dale,Nina M.Serafino,Pat Towell,“Organizing the U.S.Govern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Overview of the Interagency Reform Debates”,CRS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18,2008.
“政策總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對NSC和國家安全顧問工作的分擔與補充,可以快速推動特定安全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但是,“政策總管”的政策協(xié)調(diào)能力及其權(quán)力范圍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總統(tǒng)對他的授權(quán)。一些“政策總管”的設(shè)立主要是為了表明政府對某一問題的關(guān)注,總統(tǒng)并沒有及時地授予“政策總管”足夠的權(quán)力和配備必要的資源去解決這些問題,使得“政策總管”的協(xié)調(diào)效率低下。此外,部門和機構(gòu)間早已存在的授權(quán)體制也經(jīng)常會給“政策總管”的協(xié)調(diào)帶來相當大的阻力。更為重要的是,當“政策總管”顯示出無法協(xié)調(diào)跨機構(gòu)政策和戰(zhàn)略的能力時,總統(tǒng)也會減少對其授權(quán)和支持。⑦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 ,Turning Ideas into Action,PNSR,2009,p.54.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奧巴馬政府在“政策總管”協(xié)調(diào)的具體過程上進行了有益創(chuàng)新。這些“政策總管”在組建自己的協(xié)調(diào)團隊時,往往將各個部門的副手納入其中,使得各個部門覺得自身利益得到了重視,進而比較樂意協(xié)助“政策總管”的工作。
“政策總管”模式增加了協(xié)調(diào)的靈活性,分擔了總統(tǒng)和NSC的負擔,但也存在難以避免和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和短板。一是“政策總管”很難找。此類個人除了需擁有總統(tǒng)的信任之外,還需在政府、國會和軍界等擁有相當?shù)馁Y歷和影響力。然而具備這些條件的人物在美國政界是很難尋找的,這也是總統(tǒng)任命的很多個人協(xié)調(diào)失敗的重要原因。二是“政策總管”的存在有可能不利于決策的民主化。合格的“政策總管”往往具有相當充分的總統(tǒng)授權(quán),同時也具有雄厚的背景和人格魅力,這往往使得被其協(xié)調(diào)的部門和個人不敢提出與“政策總管”不同的意見與建議,或者即使有不同意見提出,“政策總管”也容易將其忽視。
三、非正式的“小圈子”協(xié)調(diào)模式
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特別是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極大地便利了總統(tǒng)采用非正式跨部門協(xié)調(diào)模式處理相關(guān)安全問題。①Smith Hedrick,The Power Game:How Washington Works,Random House,1988,pp.600 -601.總統(tǒng)通過白宮地下的“情況室”(Situation Room)可以及時掌握國內(nèi)外各類安全信息與情報,而不必去召開正式安全會議從各部門首腦那里獲得信息,這就使總統(tǒng)可以在了解情況后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模式快速處理相關(guān)的跨部門安全問題。自肯尼迪總統(tǒng)以來,以各類“早餐會”、“午餐會”和“晚餐會”為形式的“小圈子”協(xié)調(diào)模式被越來越多地采用。許多美國總統(tǒng)并不喜歡頻繁召開正式的NSC會議,所以經(jīng)常找一些親信到白宮和自己一起用餐,探討重大的國家安全問題。這種“小圈子”的人數(shù)很不固定,完全以總統(tǒng)的偏好和想法確定人員,少則兩三人,多則十幾人,但通常以五到六人為主。
“小圈子”的成員大多都是國會、政府和軍界的權(quán)威人士,當發(fā)生危機或者形成政策僵局時,總統(tǒng)經(jīng)常會舉辦各類餐會。這種場合往往有利于總統(tǒng)加深與重要助手之間的私人關(guān)系,也有利于總統(tǒng)調(diào)解助手之間的矛盾,化解分歧,有力地推動跨部門合作。例如,約翰遜總統(tǒng)利用“周二午餐會”進行越戰(zhàn)問題的協(xié)調(diào),卡特總統(tǒng)利用“星期五早餐會”進行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②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4.里根總統(tǒng)時期的“國家安全計劃小組”類似于約翰遜總統(tǒng)時期的“周二午餐會”。③Karl F.Inderfurth and Loch K.Johnson,F(xiàn)ateful Decisions:Insid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75-76.即使最不偏好非正式程序的艾森豪威爾也被有的學者認為最終還是在橢圓形辦公室依靠少數(shù)人決策和協(xié)調(diào)。④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2011,pp.9 - 10,http://www.crs.gov/.pdf.(上網(wǎng)時間:2014年3月20日).對非正式程序的需求一方面反映了總統(tǒng)對決策權(quán)控制的偏好,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速協(xié)調(diào)進程、嚴防泄密以應(yīng)對危機或緊急情況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小圈子”模式并不專屬于總統(tǒng)一個人,總統(tǒng)的主要安全助手有時也采用這種非正式的機制。比如在卡特和克林頓政府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國務(wù)卿以及國防部長就經(jīng)常舉辦各類午餐會討論并解決相關(guān)的跨部門安全問題。⑤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5.
顯而易見,這種“小圈子”協(xié)調(diào)模式的形式和過程比較簡單、靈活,適合危機管理和化解僵局,是正式的委員會協(xié)調(diào)模式的補充。但它也存在諸多問題。首先,這個由總統(tǒng)親信組成的“小圈子”極易走向僵化、專斷,形成一個封閉的小團體,總統(tǒng)不喜歡的意見和人很容易被排斥在圈子之外;其次,這類“小圈子”往往會使NSC的作用大打折扣;最后,此類“小圈子”協(xié)調(diào)不正式,制度化程度低,在復雜安全問題上難以形成深思熟慮的決策,容易導致安全政策的失敗。
除上述聯(lián)邦政府中央層級協(xié)調(diào)模式外,在海外,美國設(shè)有地區(qū)(regional)層次和單一國家層次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組織,前者由國務(wù)院地區(qū)事務(wù)局長官與隸屬于國防部的地區(qū)指揮官及其他部門地區(qū)事務(wù)長官參加的“聯(lián)合跨部門協(xié)調(diào)小組”組成,后者則由大使領(lǐng)銜協(xié)調(diào)駐在國涉及美國安全利益的機構(gòu)——“駐受援國小組”(country team)組成。在國內(nèi)地方層次,美國設(shè)有負責處理地區(qū)、州、地方(市、縣)反恐、救災(zāi)等跨部門安全事務(wù)協(xié)調(diào)組織,如在超過100個城市建立了“聯(lián)合反恐工作組”(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這些海外協(xié)調(diào)模式、國內(nèi)地方協(xié)調(diào)模式與聯(lián)邦中央層級的跨部門協(xié)調(diào)模式形成互補,共同構(gòu)成美國完整、嚴密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體系。
四、幾點思考
通過上述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的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美國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設(shè)計得比較靈活,也從側(cè)面反映出跨部門協(xié)調(diào)的難度。具體來說,美國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第一,總統(tǒng)是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動力源泉、領(lǐng)導核心與協(xié)調(diào)中樞。在美國,任何一項成功的安全政策的形成、實施與結(jié)果都與總統(tǒng)直接且持續(xù)的干預息息相關(guān)。由于官僚惰性的影響,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在開始階段困難重重,這就需要美國總統(tǒng)出面干預,及時建立和完善各類形式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以確保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過程的維系。沒有總統(tǒng)的親自參與,“牽頭機構(gòu)”和“政策總管”缺乏指揮整合的權(quán)威,①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59.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弱點和困難就很難克服,整體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也無法有效實施。②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25.例如,在處理東帝汶危機時,只有當克林頓親自出面干預和協(xié)調(diào)美澳關(guān)系并敦促相關(guān)的跨部門安全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后,才實現(xiàn)了有效的管控。③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24.但是總統(tǒng)的干預并不能確保有良好的收效,過度依賴總統(tǒng)常常會使跨部門安全任務(wù)在總統(tǒng)的注意力轉(zhuǎn)移時出現(xiàn)問題。一是總統(tǒng)每天要處理的安全任務(wù)很多,不可能在每一個安全任務(wù)上花費太多的時間與精力。二是即使是一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也包括研究、制定政策、實施與監(jiān)督等多個階段,總統(tǒng)根本不可能時時干預和指導整個跨部門協(xié)調(diào)過程。④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p.125 -128.這就使得很多跨部門安全任務(wù)在得到總統(tǒng)的充分關(guān)注時已經(jīng)演變成難以收拾的局面。例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剛開始時并沒有得到卡特總統(tǒng)的關(guān)注,因此相關(guān)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也沒有及時展開,最終使得伊朗政權(quán)發(fā)生了美國極不愿看到的更迭。⑤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28.更重要的是,過度依賴于總統(tǒng)既會加重總統(tǒng)的負擔,又會限制跨部門組織和體系的能力發(fā)展,這種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也恰恰反映了美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機制的脆弱本質(zhì)。⑥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27.
第二,國家安全顧問和相關(guān)安全部門首腦在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中均存在角色沖突。由于總統(tǒng)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很多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具體工作都是由國家安全顧問和其他安全部門首腦負責實施,因此國家安全顧問和其他安全部門首腦在整個跨部門協(xié)調(diào)體系中就顯得十分重要,這在委員會協(xié)調(diào)和牽頭機構(gòu)協(xié)調(diào)模式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但是來自強力部門的內(nèi)閣部長們基本上被置于相互沖突的角色位置,他們各有自己的機構(gòu)利益需求,這與需要犧牲部門利益來實現(xiàn)跨部門使命相沖突。“部門成員必須在它們作為總統(tǒng)顧問的角色與其建立、管理和保護強有力部門能力的法定義務(wù)之間求得平衡。”而且,一旦在任,內(nèi)閣部長就被強有力的離心力拉開其與總統(tǒng)的距離。他們的職責是執(zhí)行法律和回應(yīng)國會的質(zhì)詢,這樣的職責又被內(nèi)閣成員的官僚生涯追求和滿足他們所服務(wù)的利益集團加強。⑦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7.內(nèi)閣官員調(diào)和其角色沖突的一種方式是使總統(tǒng)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他們部門有利的就是對國家有利。這就解釋了為何在內(nèi)部決策和協(xié)調(diào)時眾多內(nèi)閣官員繞開NSC正式程序而直接面見總統(tǒng)。此外,總統(tǒng)國家安全顧問及其助手也需要平衡其沖突角色,亦即國家安全顧問在NSC決策過程中作為“誠實的掮客”,既要公正地向總統(tǒng)反映各部觀點和建議,又作為總統(tǒng)最親近的外交政策助手和“整合”視角的首要助手,需要向總統(tǒng)提出更可行的政策建議。平衡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沖突是困難的,只有當國家安全顧問贏得了強力部門官員的信任時才能做到。⑧Ivo H.Daalder and I.M.Destler,“How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See Their Role”,in The Domestic Sources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James M.McCormick,5th edition,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pp.185 -197.
第三,協(xié)調(diào)形式靈活多樣。美國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比較靈活,既有正式的合作機制與程序,如NSC機制,也有非正式的協(xié)調(diào)模式,如“小圈子”協(xié)調(diào);既有常設(shè)的,也有臨時的;既有委員會的組織協(xié)調(diào),也有授權(quán)個人的協(xié)調(diào)。值得一提的是,各種非正式模式常常是為了應(yīng)對安全危機而產(chǎn)生的,這是因為安全危機的時間壓力很大,情況瞬息萬變,運用正式的協(xié)調(diào)模式往往耗時長,難以在短時間形成決斷,所以總統(tǒng)經(jīng)常采用非正式的、臨時的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加以應(yīng)對。①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20.更為重要的是,各種非正式協(xié)調(diào)模式常常發(fā)展為正式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機制,例如NSC制度,這就使得美國的整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機制能夠不斷完善與更新,創(chuàng)新意識也得到了較大激發(fā)。
但是這種形式上的靈活性也會產(chǎn)生一個問題,那就是總統(tǒng)為了方便常常會繞開正式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邀請極少數(shù)的政府官員參與決策和協(xié)調(diào),這很容易使國家利益集團化、私人化,更不利于整體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實施。②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18.缺少NSC正式協(xié)調(diào)也導致了一些政策的失敗,如“豬灣事件”、“伊朗門丑聞”等。此外,非正式模式常常缺乏透明度,使安全體系的其他成員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行動方能為特定的安全任務(wù)做出貢獻。這種無明確標準與規(guī)則的機制往往缺乏令體系內(nèi)成員普遍信服的獎懲制度,無法有效地調(diào)動各部門協(xié)調(diào)行動的積極性。更為嚴重的是,長期采用非正式機制會使得總統(tǒng)在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時形成一種慣性與偏好,不利于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正式化與規(guī)范化。③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6.
此外,強調(diào)協(xié)調(diào)與合作的同時也注重分工與專業(yè)化,但是“強勢部門文化”對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阻礙作用仍不容忽視。美國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在強調(diào)合作的同時也注重安全任務(wù)的分工,即協(xié)調(diào)更多存在于戰(zhàn)略層面和計劃層面,具體的分析與實施工作仍然由“協(xié)調(diào)中樞”根據(jù)各部門的能力進行專業(yè)化分工。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只是為了確保各個部門“朝同一個方向前進”和“保證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一致性”。④Madeleine Albright,Madam Secretary,New York:Miramax Books,2003,p.88.這是因為各個部門在安全任務(wù)的不同領(lǐng)域和不同階段分別掌握著無法替代的專業(yè)知識與能力,專業(yè)化分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強勢部門文化”在現(xiàn)今的美國國家安全體系中仍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影響也較為深遠,以至于合作與信任的文化在整個體系中影響有限且發(fā)展緩慢⑤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F(xiàn)orging a New Shield,PNSR,2008,p.149.。這種文化使得相關(guān)部門,特別是強力部門在跨部門安全任務(wù)中更加關(guān)注部門利益,主張運用自己部門偏好的方式解決問題。在這方面,美國的國務(wù)院和國防部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
美國各種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都是在二戰(zhàn)以后由不同總統(tǒng)建立的,與每一屆總統(tǒng)所處的安全環(huán)境和面臨的跨部門安全任務(wù)息息相關(guān)。因此,美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總是處在動態(tài)的變化之中,經(jīng)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多樣的發(fā)展過程,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均在不斷提升。比如,雖然杜魯門總統(tǒng)首創(chuàng)NSC協(xié)調(diào)模式,但當時的運行機制很不成熟,最多只能算作單一委員會協(xié)調(diào),處理復雜安全任務(wù)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但是后來的每屆總統(tǒng)基本上都對NSC進行了調(diào)整,特別是在老布什執(zhí)政時期,在國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的協(xié)助下,設(shè)立了PCCs-DC-PC-NSC層級協(xié)調(diào)模式,使之變得正規(guī)、高效,并成為以后每屆總統(tǒng)固定的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⑥Gabriel Marcella,Affairsof State:the Interagency and National Security,2008,pp.11 -13,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chǎn)rmy.mil/pdffiles/PUB896.pdf.(上網(wǎng)時間:2013 年5 月15 日)
中國作為一個日益崛起的新興大國,參與的國際事務(wù)越來越廣泛,面臨越來越多且變幻莫測的國內(nèi)與國際安全問題。無論是日益嚴重的國內(nèi)恐怖主義威脅,還是風險日增的海洋與網(wǎng)絡(luò)安全問題,都迫使中國政府加快轉(zhuǎn)變安全應(yīng)對方式,改革現(xiàn)有的國家安全體制,加強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能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先后宣布設(shè)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網(wǎng)絡(luò)安全和信息化領(lǐng)導小組”,提出了“總體安全觀”,這些均表明中國政府和領(lǐng)導人已經(jīng)認識到了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的重要性,并在努力探索自己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體系。由于國情和體制的差異,中國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不可能照搬美國模式。不過,中國領(lǐng)導人在設(shè)計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機制時,美國靈活多樣的跨部門安全政策協(xié)調(diào)模式的組織框架、運作方式以及經(jīng)驗教訓可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