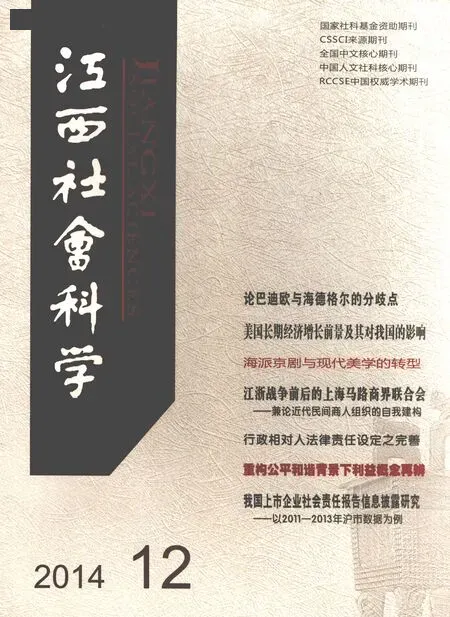論巴迪歐與海德格爾的分歧點
■牛宏寶 馮 原
海德格爾與巴迪歐各自建立了獨特且較為完整的哲學體系,不僅為哲學領域的學者提供了理論框架,其影響范圍還超出了哲學領域。巴迪歐長期以來不斷探求何為真理,如何思考真理,以及如何實踐真理。身為20世紀末聲名鵲起的哲學家,巴迪歐浸潤在法國特有的,與海德格爾哲學有著曖昧關系的學術氛圍中。他自己也承認,海德格爾不可避免。巴迪歐的“事件”概念或多或少受海德格爾影響。但他的哲學,尤其是真理理論,必須與海德格爾劃清界限。不同于薩特、德里達、列維納斯等許多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并未明確繼承海德格爾哲學,也沒有系統地指責海德格爾哲學某些方面的缺憾,以彌補或超越這位宣布傳統形而上學終結的大師。他對海德格爾的批判或闡述散見于不同著作的不同章節,或為斷言,或為陳述,有時甚至帶著不敬情緒,而少有充分的論證。除了一些政治話題,巴迪歐避免就哲學理論直接對抗海德格爾。但他的理論框架、問題域范圍、本體論闡述、真理運作方式,多多少少都與海德格爾遙相呼應,結論卻往往相去甚遠。可以猜測,對于海德格爾,巴迪歐采取了策略上的迂回戰術。他沒有直接出擊試圖推翻海德格爾,而是建立了與海德格爾哲學立論相左的框架,以求重新闡釋真理的源頭,肯定哲學的地位。
一、數學本體論與事件
巴迪歐在《存在與事件》中比較明確地勾勒了不同于海德格爾的理論框架,雖然此后出版的《世界的邏輯》多有修正,與《模式的觀念》、《主體理論》在理路上更為接近,讓《存在與事件》顯得有些孤立,但巴迪歐對本體論、對真理、對事件、對主體的定位變動不大,足以體現他與海德格爾的不同。他突出本體論的地位,分析主體對真理的運作方式,并肯定哲學的有效性。他認為哲學涉及兩種話語(或兩種實踐):其一是數學,是關于存在的科學,屬本體論范疇;其二是事件,是關于介入(intervention)與變革的原則,決定著真理。事件與數學本體論之間存在著斷裂,巴迪歐則試圖闡述真理性運作(或實踐)如何出自于這種斷裂。
巴迪歐認為數學討論“多”與“可數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本體論,但不屬于真正的哲學。數學表達著“存在之所為存在”(l’être-en-tant-qu’être,being qua being),體現出“元本體論”原則。數字進行計數,“存在之為存在”的重點并不在于任何形式為“一”樣態,而指涉“非一”,指向純粹的多(pure multiples)。本體論在本質上是“非一”的,源自無限的、純粹的多,不計其數,不能被任何形式的整體包含。這便是數學本體論的基礎:無限多的無限性(infinities of infinite multiples)。
無限的多分為兩類:連貫(consistency)的多與不連貫(inconsistency)的多。前者可分辨、可命名、可計量,可被“計數為一”(count-as-one),是對多性的(multiplicity)一種呈現,通常表現為具有連貫性的情勢(situation)。相反,純粹的多并不連貫。它超越了任何一種對多的連貫性表達,屬于不可觸及的真(real),無法在計數上被規約。不連貫的多是連貫性的基礎,是數學本體論的核心。如何通過操作和計數,將無限、純粹、不連貫的多呈現為一種連貫性,屬本體論探討范疇。
純粹且不連貫的多與被計數為一的連貫性之間存在著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巴迪歐在此引入事件。本體論層面,事件無法被連貫性呈現,無法被捕捉,但它促發了不連貫向連貫性的轉化,在給定情勢中留下痕跡,表現為一種虛無,在本體論層面被稱之為“空”(或空集)。空指向連貫性之外的不連貫事件,是“計數為一”的失效點,影射了突破連貫性的溢出的樣態。巴迪歐認為真理來自于空,能夠戳破“計數為一”的連貫性,使之在某一程度上失效。他定義作用于空的真理性運作為減除運作(subtraction)。
在此,巴迪歐巧妙地引入集合論,以解決空與情勢的關系。情勢對應集合論中的集或子集,空則對應空集,數學本體論對應了集合論相關范疇。在集合論層面,空集不屬于(belong to)任何集合,但被所有集合包含(included)。巴迪歐于是聲明,在本體論層面,空不屬于任何情勢,但能被所有“計數為一”的情勢包含。根據冪集公理,如某集合擁有無限元素,它也包含了無限子集,所有子集集合(即冪集)的無限性高于這一集合元素本身的無限性。即,二者并不連貫,前者的計數范圍溢出于后者。溢出運作始于對空集的包含(include)關系。巴迪歐數學本體論中連貫性與不連貫的關系,對應著“屬于”與“包含”兩種不同方式的計數運作。情勢的表現(presentation)狀態對應著“屬于”關系。情勢狀態的再現(representation)模式,對應了“包含”關系。后者與前者的不連貫性,體現著后者對前者“計數為一”模式的突破與溢出,屬于真理的脫殊(générique、generic)程序。空或空集則標記了連貫與不連貫之間的介入(或僭越)點。
為促發真理,巴迪歐強調主體的作用。情勢中的空正是主體作用的起點。如果空標記了連貫與不連貫、屬于與包含關系中本體論層面不可超越的死局(impasse),主體則能夠“力迫”(forcing)此鴻溝,促成由不連貫向連貫性的跨越,突破單純的“計數為一”。主體在情勢中總是有限的,但它可以不加論證,確信真理的有效性,肯定事件的不連貫,并勇于在事件發生的基礎上,追求一種新的連貫關系。巴迪歐特別強調主體對于事件的忠誠。事件的發生就如同在“計數為一”、邏輯連貫的拓撲平面上生成一個突兀的奇點(singularity)。巴迪歐要求主體忠于事件奇點,認定事件的介入性,作為操作者,促成事件發生后的介入過程,最終造就具備全新連貫性的情勢(或情勢狀態)。
《存在與事件》出版后,巴迪歐在數學本體論基礎上,對他的理論框架進行了充實與修正。他采用縫合(suture)概念,提出真理無一例外,縫合于科學、藝術、愛情或政治四類條件領域(condition)。哲學委派于條件,思考依附于真理,縫合過程得以實現。四類條件領域帶來事件和奇點,哲學思索的連貫性因之不斷遭受侵蝕、切割、創傷,但也得以拓展、更新或再造。巴迪歐指出,哲學從來不附著于某單一條件,而是依據本體論的可能性,闡述各個條件領域帶來的真理性變革。哲學自身不促發事件,所以也無法構成條件領域的一份子,無法與單一或若干類條件等量齊觀。它只能根據相應的真理發生過程,去思考、闡述、并踐行對條件領域的縫合(或去縫合)過程。
以上只是對巴迪歐思想關鍵點的簡要摘取與闡述(不包含《世界的邏輯》),以作為立論背景,對比海德格爾哲學,闡明巴迪歐如何按照自己的哲學框架規約海德格爾。
二、巴迪歐綜論海德格爾
《存在與事件》伊始,巴迪歐指出海德格爾是最后一位廣受認可的哲學家,這是世界哲學的現狀,也是歐陸哲學的絆腳石:海德格爾闡述了西方思想的終結,將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劃歸為一部遺忘史,希望回歸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希臘哲學。巴迪歐試圖重估海德格爾哲學的價值,以尋求一種后海德格爾哲學。
巴迪歐承認與海德格爾有共通之處。他們都面臨20 世紀現代性危機,希望突破西方哲學的僵局。海德格爾對本體論問題的探求,對真理解蔽過程的討論,都與巴迪歐的問題域相合。巴迪歐的真理、主體、減除運作、介入理論,也與海德格爾的理論道路相互交錯。巴迪歐希望破除海德格爾哲學存在與真理之間的關系,讓主體參與真理運作,而非回溯希臘源頭。他的真理理論不尋求解蔽,只追求對異質的連貫性的綜合構建。他承認,海德格爾的理論也包含此類構建。
巴迪歐提出當代關于真理問題的四個維度。[1](P58)前兩者圍繞海德格爾:一是,海德格爾認為詩性指向真理的道路,為突破海德格爾,需構造真理的不同路徑;二是,后海德格爾理論不可順應哲學終結的歷史路徑,不應認為真理難以觸及,解蔽已然迷失。巴迪歐哲學構成了真理問題的后兩個維度:一是,對事件的忠誠能夠促發真理,改變現有知識結構;二是,真理的本質——事件——屬于思想的否定層面,難以定奪、難以辨識、難以促成、難以命名。這四個基本維度道出了巴迪歐推翻海德格爾的切入點:西方哲學的僵局能被打破;無限的真理運作可以取代海德格爾的解蔽真理。
巴迪歐同時分析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四種模式,雖有低估與錯讀成分,但也指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一些盲點。
第一,海德格爾的真理理論出自傳統。[2](P35)真理來自時間的“綻出”(ek-stasis,或超升),指導個體經驗向真理變形(metamorphosis)的道路。這一理路始于海德格爾早期宗教現象學,在《存在與時間》中有所發展,并體現在本有(Ereignis)一詞中。巴迪歐認為,海德格爾的“綻出”呼喚眾神,即使不與具體宗教相關,也具有宗教性的神圣啟示意味。
海德格爾思想的第二種模式與政治相關。巴迪歐相信,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否定,對德語或古希臘語的推崇,均源自德國國家主義政治立場。德國式的決斷與技術統治的虛無見諸海德格爾哲學,影射了海德格爾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曖昧關系,需從根源加以批判。巴迪歐自身的左翼政治傾向與哲學框架也作為前提條件,影響著他對海德格爾的評估,不過本文篇幅有限,無法討論兩位哲學家的政治立場。
第三種模式植根于解釋學傳統:重估西方哲學價值。海德格爾將西方思想描述為一部遺忘史。哲學是一種解釋方法,能澄清存在的本真意義,帶來真理。遮蔽與解蔽,技術世界與哲學敞開,都屬于海德格爾解釋學成雙配對的概念。巴迪歐反對解釋學傳統,認為海德格爾是他的對立面。
第四種模式顯示了海德格爾所宣揚的德國詩歌。他將荷爾德林推為詩人的典范,將詩人視為與思者享有特權的對話人。海德格爾肯定語言的哲學價值,甚至認為只有特定語言才能拯救當代思想。存在最初由希臘語展現,隨后是德語,只有這兩種語言能決定西方哲學的命運。巴迪歐強調,這種詩人與思者的耦合關系依然支配當代哲學,延續至今,需被棄絕。
三、巴迪歐與海德格爾:柏拉圖轉向
可以說,巴迪歐與海德格爾的分歧發端于對歷史的評估。海德格爾推崇前蘇格拉底哲學詩性言說,認為詩化語言解蔽真理,柏拉圖哲學則開啟了西方思想的遮蔽時代。巴迪歐肯定柏拉圖,認為柏拉圖思想介入了前蘇格拉底的內生(immanent)哲學。巴迪歐屬當代柏拉圖主義者。他依據柏拉圖理路,建立了數學本體論。
海德格爾認為柏拉圖是西方思想的轉折點,首先勾畫出大寫的理念,去統領存在。他依照真理的解蔽與遮蔽過程,重述了柏拉圖洞喻,以說明理念論是真理的退化形式,讓前蘇格拉底哲學受到遮蔽。柏拉圖之后,存在與真理的本真狀態——解蔽(Aletheia)——開始受理念、形式、命題等確定性標準的桎梏,不再敞開,淪為不同標準之下正確與否的判定結果。柏拉圖的形式思想自此貫穿西方形而上學,真理被貶低為單純再現,最終導致了技術世界的單一化統治。為打破柏拉圖的束縛(yoke),海德格爾提出,真理的本質并非固定或僵化的存在(quidditas or realitas),而是本質性的運動與變化。前蘇格拉底哲學,尤其是巴門尼德思想,融匯了思與言、存在與開啟、呈現與解蔽。海德格爾結合λεγειν 與λóγο? 兩詞,追溯二者的源頭,指出語言的本質即是使其當面呈現、鋪展,與邏各斯相通。運思棲居于語言,解蔽過程即是對形而上學思想整體的變革。
巴迪歐則認為柏拉圖突破前蘇格拉底哲學,肯定了存在的“多”。當代解釋學的闡釋方法,分析哲學的邏輯規則,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對“多”性的描述,都仰仗著語言對思想的權威。這一現象成為“我們時代的先驗判斷”,導致了哲學和形而上學的解構。巴迪歐相信,“多”不由語言決定,需被數學本體論描述。柏拉圖作為數學運思的發端者,應受肯定評價。
巴迪歐將古希臘詩歌與哲學的關系分為三類。[2](P38)第一類屬于巴門尼德模式:詩歌的主體與言語的真理和而融洽,形成哲學。語言在此顯現神圣之光,既帶有前蘇格拉底哲學的神秘性,也具有內生展現的狀態。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與真理理論,都源自巴門尼德詩性言說的神圣性。第二類關系根植于柏拉圖:數學開始介入真理言說,哲學與詩歌之間的關系拉開距離。柏拉圖對立數學(matheme)與詩歌,傾向于否定詩歌的真理性,驅除詩性權威,以崇尚理念、形式與數學。第三類關系來自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詩歌屬知識范疇,在哲學統籌下分門別類,與其他種類的知識并行,并不更加接近或遠離真理。所有事物都處在由哲學的分類原則下,作為某種對象,各居其位。巴迪歐總結:第一種關系,哲學羨艷詩歌;第二種關系,哲學排斥詩歌;第三種關系,哲學將詩歌劃類歸門。
巴迪歐將數學與本體論等量齊觀。他認同海德格爾重建詩歌的真理,不再局限于命題語句、受限于哲學分類。亞里士多德傳統將詩歌歸為美學,海德格爾推崇詩歌,也是對過往美學的一種批判。海德格爾揭示了詩性言說與哲學論證之間復雜緊張的關系,雖說明了柏拉圖對詩人的徹底放逐并不成立,但卻錯誤地認為,只有詩歌有能力承擔哲學運思,最終造就“詩人時代”(后浪漫主義詩歌)。在巴迪歐眼中,哲學只在一些特定時刻為詩歌敞開大門,接受危機與挑戰。
因此巴迪歐從根本上反對海德格爾對歷史的評估。后者雖然發現了柏拉圖轉折點,卻低估了柏拉圖數學運思的重要性。這在巴迪歐眼中是一種極大錯誤。海德格爾解構現代理性,但沒有對存在進行徹底的去神圣化。巴門尼德的神圣言說只顯現出詩性權威,屬于哲學的前奏,與赫拉克利特相同。海德格爾也只重現了前蘇格拉底的神圣權威,表現為一種救贖。他的哲學根植于德國現象學,總為宗教縈繞,導致他晚年呼喚“眾神回歸”(return of gods)。他的神屬現象學范疇,未必與世俗神學(基督教)相關,但其詩性的啟示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神圣性,一方面認定人類對存在的遺忘,一方面否定柏拉圖數學的理性。巴迪歐則認為,哲學只能在去神圣化中展開,海德格爾的神圣哲思需要世俗性的數學本體論加以打斷,才能產生真正哲學。
在此,巴迪歐展開了他對海德格爾的反抗,以重構詩與思之間的關系:無關聯(dé-rapport,non-relation)。他將詩歌歸為真理的四種條件領域之一,具有決定作用,但并不唯一。當代哲學既需破除知識的桎梏,也需驅逐任何形式的神圣性。為說明與海德格爾截然不同的道路,巴迪歐在西方思想的源頭析出兩種理路。[1](P126)二者的此起彼伏、交替變換,統治了西方哲學的整個命運。其一是前蘇格拉底詩性語言,昭顯著古希臘的原初思想,存在的充盈與呈現,批判后世形而上學的固化與忘卻。其二是柏拉圖的數學理性,提供了形而上學的模式與框架,強調匱乏、斷裂,以及對存在的減除。前者是詩性的本真在場,后者是數性的本體論缺減。巴迪歐將海德格爾歸為前者,自己歸為后者。他不準備徹底否決第一種理論,而試圖說明,隨時代變革,前蘇格拉底詩性的言與思,應遭棄絕。
巴迪歐拒絕詩性語言與此在的結合,尤其是德國浪漫主義因素。他堅持柏拉圖、伽利略、康托爾一脈,相信形而上學的數學核心不會導致海德格爾提出的遮蔽與遺忘。他肯定柏拉圖的轉折作用。詩性語言在其他地域也有出現,并非希臘時代獨享,也不能決定西方思想與眾不同之處。真正的轉折點只出自柏拉圖的數學理路,代表西方哲學的精髓。柏拉圖驅逐詩人,驅逐缺思少智的詩歌于哲學王國,對前蘇格拉底思想進行了去神圣化和去詩性化。巴迪歐因此希望離開“詩人時代”,重新確立柏拉圖的地位。柏拉圖的真理理論屬數學形式主義。巴迪歐認為當代數學發展與柏拉圖遙想應和,能夠突破“詩人時代的籠罩”。
四、巴迪歐與海德格爾:語言之于哲學
海德格爾的語言哲學在早期作品中并不清晰。《宗教現象學》對語言少有提及。《存在與時間》中,言談(Rede)根植于領會和現身樣式,使其可知、可被觀照。領會比言談更為基礎,但言談能指向領會的整體意味,呈現為文字。語言則是言談的表達道路,體現語言整體性,扎根于對在世的理解。語言與言談在《存在與時間》中并沒有獲得清晰定位,有時沉默與言說同等重要,本真的領會則更為接近此在。20 世紀30 年代,海德格爾思想發生轉變,稱本真且原初發生的事件為本有(Ereignis)。本有包含三個維度的含義:事件或發生;歸屬或持存;呈現或觀看(eigen 與augen 同源)。《哲學論稿》嘗試將本有與言說等量齊觀,體現言說的歷史性(geschichtlich),讓詩歌重新奠基西方思想。但書中語言與本有的關系尚不明了,海德格爾更加重視對本有的描述。
《語言的本質》與《走向語言之途》雖出版較早,但成書晚于《哲學獻詞》。此時,海德格爾對語言本質的思考更為深入,在此只引入涉及運思經驗的關鍵語句進行解釋:“語言的本質——:本質的語言”[3](P166)(Das Wesen der Sprache:Die Sprache des Wesens,The being of language:the language of being)。海德格爾希望存在與人、與語言的關系得到根本轉變。他區分了兩類語言,一種屬形式化且退化的現代語言,另一種屬原初且自由的言說。“語言的本質——:本質的語言”即是說明,原初語言如何脫出形式化語言,得以變革。
海德格爾批判的形式語言一方面來自技術科學清晰明了的系統邏輯,對世界與人類進行客觀化。另一方面,這類語言定義了傳統西方形而上學思想,揭示了存在最為死板的關系。海德格爾希望人類突破形式語言的束縛。但他不準備創造新的語法,而只回溯語言古老的根源,從源頭開啟改變。不同于自然科學陳述、語言命題或形而上學話語,詩性言說構成展現轉變的真理性語言。①但海德格爾認為言說也出自形而上學-技術語言,發生并交織在既有的網絡中,能夠形成自我持存的領域,帶來改變。自我持存并面向語言整體,不具系統性或分層性,與海德格爾的“世界”概念密不可分。言說是展示、是開敞、是在場,是解蔽,集中體現了海德格爾的諸多立場:反科學主義,重視語源學、現象學、解釋學,希望回歸古希臘,并推崇詩歌與運思之間的緊密關系。因此,海德格爾要求語言述說語言,使語言自身在場。
海德格爾特別選取了動詞形式的本質,以形容詩性言說;名詞形式的本質,則描繪形式化語言。“語言的本質——:本質的語言”中,冒號前的本質(Wesen)一詞詞性為名詞,冒號后Wesens 為動詞。海德格爾作品中名詞Wesen,通常被譯為本質、自然、顯示、實體,意味著西方傳統思想不加變化的身份,決定著形式語言和技術話語的本質。相反,動詞Wesung 或比較古老的Wesen 代表能夠變動的本質,意味著去存在、去持存、以持續、以發生。很明顯,海德格爾恢復了已被棄用的本質的動詞形式,希望闡明,真理的本質來自并不僵化的古代源頭。他試圖說明,語言對真理的轉變與解蔽,來自本質的動態變化,即,由確定的名詞狀態,變為不確定的動詞狀態。
海德格爾繼而使用本有(Ereignis)一詞,以表現語言如何發生變革。《走向語言之途》與《語言的本質》中,本有表示以下三重含意:在場可見,居于言說,原初發生。本有是自身運動,自身給予的過程,是最為宏大的懸置且持存的結構。它潛在于形式語言或技術邏輯中,是言說的饋贈。技術-形而上學語言與言說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對立,都能在本有當中轉化。言說是本有道出自身變革的方式,也是本有的棲居之處。因而本有與言說密不可分,都是開敞、解蔽、呈現與在場的過程。語言的本質由名詞意味變為動詞意味,也屬于本有的運作過程。可以說,語言本質的變革方式,即為本有。海德格爾同時相信,詩人并不使用詞句,只為詞句服務,貢獻于詞句。言說移動大地,變革萬物,棄絕主客之分,解蔽真理。海德格爾因此希望消除主體,尤其是形而上學主體,讓人類放棄自我,投入并體驗本有的變革。因此,人類主體的地位低于言說、居于言說、受統于本有,人類因之獲得自由與解蔽。
巴迪歐雖不同意海德格爾讓哲學聽命于詩歌,讓思想與言說歸同,但對他而言,語言之于哲學仍很關鍵,是意義即將丟失、言辭危如累卵的所在。他認為哲學具有普遍性,不會被海德格爾詩性言說的深廣取代。語言并非真理的最終邊界。哲學并不比語言享有更多特權,反之亦然。海德格爾正確地將詩歌減除于知識,以揭示真理,但卻錯誤地將哲學歸于詩歌。
巴迪歐總結了海德格爾詩性哲學的四個方面。第一,海德格爾的詩人脫離主客之分,去縫合于傳統哲學的科學邏輯。詩歌捕捉了語言的模糊之處,展示了在場的邊界。第二,海德格爾推崇詩歌,認為只有詩歌能保存哲學,給予哲學力量。第三,海德格爾認為希臘語更接近真理。古希臘哲學的言說能祛除當代哲學弊端。第四,海德格爾重新創造了“詩人時代”,將數性等同于單純知識,利用詩性與數性的對立,彰顯真理與知識的區分。[4](P73)
不同于海德格爾,巴迪歐認同近現代科學,尤其是集合論。他認為詩歌無法徹底消除客觀化的困擾,解決技術世界的弊端。當代哲學需要新的方向,取代海德格爾對詩歌的推崇,不再求諸語詞饋贈。巴迪歐的詩學理論不是在場詩學,而遵循減除邏輯,依附于數學本體論。他確定了哲學與數學的縫合關系,以數學本體論的命名原則,取代海德格爾的內生(immanent)詩學。命名帶來詩性真理,其過程觸及語言邊界,是客體世界的消解點(或奇點),擁有數學的抽象。
巴迪歐對當代語言哲學存疑,他的真理理論留給語言的位置不多。《存在與事件》中,只有對事件的命名構成真理發生的重要環節。命名行為介于情勢與情勢狀態之間。命名的源頭來自情勢中的空,來自無可把握的純粹的多。“空”命名了不連貫性和溢出的起點,導致不連貫性突破連貫性,促發真理。巴迪歐承認語言的主權(sovereignty of language),“計數為一”控制了語言的連貫性。“多”可被解釋為兩種關于語言的命題:語言的無限性和語言的異質性。每一個自然境遇的多,都只屬于一種命名方式。但在新命名伊始,對未知的肯定將破壞原有語言系統的邏輯連貫,以空為起點,造成無限溢出,形成了異質語言。當無可捕捉的事件被命名,無法思及的純粹的多將超出原有的語言情勢,真理思維由此開始。巴迪歐認為,語言雖無法支撐純粹的多,但在語言毀滅之處,命名的重要性得到凸顯。②
巴迪歐強調主體,在命名之處,只有主體能跨越事件真理過程與本體論情勢之間的深淵。主體無法從自然語言中獲得真理。[1](P396)只有當主體力迫并忠實于“新”的命名,將命名連接到真理的條件領域中,真理過程才能不斷實現。對事件的命名僅來自有限且局限的主體。它受困于情勢,但有能力開啟不受局限的、無限的真理過程。主體利用命名,捕捉事件不連貫、不可分辨的痕跡。主體作為指涉者,促成的命名行為可不依托自然情勢。主體通過命名、宣稱真理,超出了其局限性,促成無限真理過程。因此命名也成為有限個體連接無限真理的橋梁。
巴迪歐所描繪的命名并非詩意在場,而依賴主體忠誠,講究命名的空余與減除運作。他所推崇的詩歌也總在減除語言的存在,在空余處溢出,標記事件逃逸位置,破除語言表層,取消語言權威,不同于海德格爾。在他眼中,詩歌需顯示命名的激進狀態。他希望拯救哲學于詩性言說,因此更多地閱讀馬拉美、策蘭、貝克特等詩人或作家。他對詩歌語言的描述體現了他的哲學觀:詩歌對事件的命名。詩是條件領域之一,與其他藝術一樣屬真理程序。當巴迪歐首次提出條件領域時,詩歌作為藝術條件領域獨特代表,被特別強調。
巴迪歐的詩歌是“非美學”的。海德格爾,或更為寬泛的浪漫主義立場,成為巴迪歐攻訐的對象。巴迪歐仍認為哲學不能僅縫合于一種真理條件,而不摧毀自身意義與地位。他定義的詩歌一方面產生藝術真理程序,另一方面對語言進行減除運作。與前文討論的三種關系不同,他提出第四種哲學與詩歌的關系。他讓詩歌的真理條件領域與哲學分離,同時肯定詩歌擁有生產真理的特殊位置,哲學可以配置詩歌。詩歌選擇尚無明確含意、尚無明確定位,不可分辨的真理,亟待生成新的連貫性。哲學雖然為其服務,但詩歌無法獨自支撐真理程序。詩性總來自對真理的命名,在語言邊緣、在意義匱乏處捕捉意義。因而詩歌總介于兩種構成之間:語言統治——“計數為一的呈現”;事件的命名——溢出計數范圍。[2](P43)減數詩性屬數學語言范疇,只提供越界思考。哲學對真理的肯定,有時需要詩歌觸及語言邊緣。概言之,詩歌是巴迪歐哲學的一種真理條件,不高于哲學,不應被排斥,也不應被分類;只促發真理,但無法代替哲學。
巴迪歐在《世界的邏輯》中修正了自己的概念系統,提出本體論和邏輯二者區分:本體論決定存在,邏輯學決定某一世界當中的顯現(appearing-in-a-world)。[5](P118)前者具有本體論的普遍性、自明性、概念性,后者體現出顯現的連續性,指向世界與客觀,以表述激進變化等諸多問題。顯現的邏輯包含語言學的普遍意味,在命題與謂詞的規范之上,經由真理的操作者,獲取意義。巴迪歐認為,邏輯是語言將一些確定的規則謄寫為顯現,保證一個世界的連貫性。他希望闡釋一種主體運作,將世界的變化編織進入顯現的連貫當中。這一真理過程先于語言,反語言學轉向。
巴迪歐需要一種激進的主體真理(如圣保羅),使主體運作獨立于語言,打破詩與思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主體能通過前語言事件的休止力量,戳破顯現的連貫邏輯,并為新的連貫性奠基。在這里,語言邏輯的運作及解釋活動總依賴主體,對于真理的重要性也次于主體。[5](P173-174)巴迪歐延續了《存在與事件》中“屬于”與“包含”、知識(自然)與真理之間的對立關系,但并不準備繼續求助于“神秘的命名”。他認為,命名只導致結構與歷史之間蒼白的盲點,導致并不清晰的先驗結構。[5](P361)在《世界的邏輯》中,他不再將主體的行為要素等同于對事件的命名,而脫離命名,強調主體的辯證活動及其忠誠的作用。這一切并不必須與語言相關。
巴迪歐同時修正了他的詩歌理論。事件不會留下任何本體論痕跡。詩歌不再僅僅仰仗數學語言,而是可感可觸的,指向世界的存在。巴迪歐重新定義了“身體”。身體具有主體的形式體系,賦予真理具有現象學意義的客觀性。詩性是追尋事件痕跡的一種方式,有能力依賴語言,構成新的身體。詩歌也不僅具有命名功能,而一層一層、一點一點地構建語言,塑造新的語言以表現身體,詩歌隱射事件,但在本體論層面,不再依賴“神秘的命名”。屬于事件的都已消散,只留下事件陳述(evental statement)。概言之,巴迪歐不再將詩歌直接化歸于命名,而強調詩歌屬于“身體”,屬后事件運作。真理程序獨立于命名,依賴主體實現,屬于前語言范疇。
五、結語
巴迪歐與海德格爾都認為真理來自未知與驚奇。不過對于海德格爾,前蘇格拉底的詩性言說呈現并開啟真理,近現代科學技術則遮蔽存在。對于巴迪歐,語言的罅隙隱含著真理與哲學,只有數學才能決定本體論。他對比了海德格爾的“詩性-自然”與他自己的“數學-理念”,試圖從另一角度解釋語言之于真理的作用,強調數性與主體,以結束海德格爾所創立的“詩人時代”。巴迪歐與海德格爾代表了兩種理路,了解二者的分歧與聯系,能更好地讓我們看清當代西方哲學圖景。
注釋:
①德語中言說一詞為sagen,海德格爾解釋為使呈現、開啟、解蔽、敞亮,展現于世。言說與觀看(sehen)互相聯系。海德格爾也直接將言說等同于呈現(die Zeige 或zeigen,有指出、指向之意),以說明言說的在場與展現性。
②不過,在《存在與事件》中,巴迪歐對命名的定義仍比較模糊,但他肯定,命名在字面意義上創造了事物。
[1]Alain Badiou,Being and Event,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O.Feltham,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5,London/New York.
[2]Alain Badiou,Conditions,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Corcora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8,London/New York.
[3](德)馬丁·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5.
[4]Alain Badiou,Manifesto for Philosophy,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N.Madarasz,SUNY Press,1999,New York.
[5]Alain Badiou,Logics of Worlds,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A.Toscano,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9,London/New York,pp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