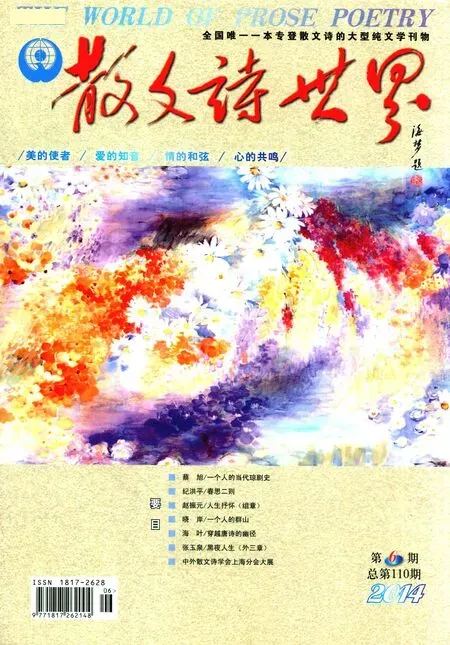夢(mèng)魘與現(xiàn)實(shí)交織的詩(shī)性直擊—唐朝暉《夢(mèng)語(yǔ)者》的后現(xiàn)代敘事解讀
陳曉莉 喻子涵
散文詩(shī)研究
夢(mèng)魘與現(xiàn)實(shí)交織的詩(shī)性直擊—唐朝暉《夢(mèng)語(yǔ)者》的后現(xiàn)代敘事解讀
陳曉莉 喻子涵
一本優(yōu)秀詩(shī)集是需要在時(shí)光的隧道里慢慢研磨,一箋馨香,如詩(shī)如畫(huà),如泣如訴,在幻想中徜徉,在靈魂的夾縫中生長(zhǎng),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穿行。神秘、魔幻與歷史、災(zāi)難交織,生與死自由對(duì)話,打破界限,或許是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但似乎又冥冥之中注入了一股“神力”,凌駕于經(jīng)驗(yàn)之上;或許是現(xiàn)象的指述,但恰恰又是生命本質(zhì)的揭示。唐朝暉的散文詩(shī)集《夢(mèng)語(yǔ)者》[1]便是這種將夢(mèng)魘與現(xiàn)實(shí)交織,情感與理智碰撞,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悖的表現(xiàn)個(gè)人“動(dòng)態(tài)生命景觀”的力作。
《夢(mèng)語(yǔ)者》這部散文詩(shī)集的構(gòu)架為七個(gè)模塊的拼貼,似無(wú)關(guān)聯(lián)但又同在一個(gè)世界:“古莊”以一種現(xiàn)代傳說(shuō)的魔幻表現(xiàn)手法揭示了現(xiàn)代人精神的荒原;“心靈物語(yǔ)”呼吁將心靈祭獻(xiàn)給大地,在宿命的褶皺里,打撈記憶的碎片;“歇斯底里與轟炸炸轟”呈現(xiàn)出欲望與囈語(yǔ)交織、重金屬的質(zhì)感、搖滾樂(lè)的狂放,魂靈如炙熱的巖漿奔涌而出,泥沙俱下,氣勢(shì)如虹。在“與城市相關(guān)”里,人群幽靈般閃現(xiàn),光怪陸離的世界里,漂移的浮影,心潮涌動(dòng),救贖在繁華中悄然謝幕;“他人即是面具”之“他”是令人窒息的死亡,“他”是暗處幽幽的泛著綠光的宿命,“他”是清晨轟然炸開(kāi)的露水里折射出的美好世界,或者“他”什么也不是,但卻始終與“我”同行,在寓言的洪流里,茍延喘息;“安·家”則是浮生若夢(mèng),跋涉于千山萬(wàn)水間,給心靈搭建一個(gè)小窩,飛翔、閑走是它的胎記;而“撲克牌”,眾生萬(wàn)象,時(shí)光的車輪緩緩碾過(guò),將靈魂拋向天際,在血雨腥風(fēng)中對(duì)峙鞭打,生命的焦慮一觸即發(fā),命運(yùn)女神正在重新洗牌。這部散文詩(shī)集,無(wú)疑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意識(shí)流”,具有后現(xiàn)代的審美品質(zhì),其夢(mèng)魘、回憶、潛意識(shí)、幻想、迷惘、沖動(dòng)、光與影的交織,黑暗與光明的對(duì)決,絕望之于希望,奇崛詭異的氛圍里一切感官的與心理的個(gè)體經(jīng)驗(yàn)感受,在無(wú)垠的宇宙星空里,發(fā)出一陣陣脆響,回蕩天際……
一、“破碎空間”的結(jié)構(gòu)重現(xiàn)
結(jié)構(gòu),是任何文學(xué)形式創(chuàng)作的肌理與紋路,是讓文學(xué)翩翩起舞的那雙“舞鞋”,相比以往傳統(tǒng)的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藍(lán)本,唐朝暉似乎有意的回避,甚至“孩子氣”似的將之付之一炬,大有另起灶爐之勢(shì)。《夢(mèng)語(yǔ)者》這部作品首先將破碎的結(jié)構(gòu)推到最前沿,以造成文本缺失感,進(jìn)而因“陌生化”的敘事方式衍生出的“問(wèn)題”意識(shí),無(wú)疑是讀者穿過(guò)層層“迷宮”通向深邃“彼岸”的通關(guān)文諜。而這種“破碎的結(jié)構(gòu)”,詩(shī)人主要是通過(guò)“冷漠的情感距離”、“多重的復(fù)指文本”、“自由與循環(huán)的時(shí)空體”等三個(gè)路徑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
《夢(mèng)語(yǔ)者》的書(shū)寫(xiě),唐朝暉選擇了一種近乎“自然主義”的不動(dòng)聲色的冷漠?dāng)⑹路绞剑芙^抒情,將眼前的一切加以敘述打包即可。“黃昏的河,流過(guò)草原里有著唯一一株紅楓樹(shù)的河堤的第七天,我才知道,我們必須離開(kāi)了。”(《人生》)冷酷到了極致;“一個(gè)男人吹著口哨,走進(jìn)巷子。她們都聽(tīng)見(jiàn)了。主人正在夢(mèng)中與影子打著招呼。”(《影子》)零碎化的組合,魔幻情調(diào)的再生,囈語(yǔ)般的飄忽不定,刻意的拉開(kāi)與文本、讀者、甚至是自我心靈的距離,極力營(yíng)造一種疏離、幻滅感,在冰與火、生與死、毀滅與重生間,織起了一張人性之網(wǎng),眾生萬(wàn)象,煎熬其中,升騰起濛濛霧氣。
多重的復(fù)指文本,按照張立群先生的觀點(diǎn),是指“在文中以一種文本指涉另一種文本,環(huán)環(huán)相扣,從而造成兩個(gè)文本互相兼容破壞,使文章整個(gè)結(jié)構(gòu)發(fā)生混亂”。[2]在唐朝暉的《夢(mèng)語(yǔ)者》中,詩(shī)人精心搭建了一個(gè)巨大的“多米諾”骨牌陣,文字的激流,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甚至瞬間凝聚成一股狂飆、摧毀一切的席卷之勢(shì),殘骸遍地。結(jié)構(gòu)與思緒上,一會(huì)兒斷裂中止,一會(huì)兒又接續(xù)相連;一會(huì)兒缺失,一會(huì)兒又完成文本內(nèi)的完整。這是多重的復(fù)指文本造成的“互相指涉”產(chǎn)生的特殊效果。“面具”系列、“黑桃”系列、“紅桃”系列、“方塊”系列、“梅花”系列等篇篇都類似于“同題作文”,在一個(gè)統(tǒng)一的“宏大主題”的感召下,一個(gè)個(gè)“個(gè)體”排列有序,相互之間銜接緊密,互相指涉,結(jié)構(gòu)卻相互背離,距離感應(yīng)運(yùn)而生。
自由與循環(huán)的時(shí)空體,也是《夢(mèng)語(yǔ)者》破碎結(jié)構(gòu)的重要表現(xiàn)和主要方法。通過(guò)這種“時(shí)空體”的創(chuàng)建,體現(xiàn)了唐朝暉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的新銳性以及他“在文本敘事上時(shí)間與空間意識(shí)的深層覺(jué)醒”(馬克·柯里語(yǔ))[3]。張立群先生在探討“自由式的敘事時(shí)間”時(shí)說(shuō)過(guò):“時(shí)間或歷史在后現(xiàn)代文本中像一個(gè)固定的書(shū)架一樣,敘述者可以從古至今亦可從現(xiàn)在到過(guò)去乃至將來(lái)任意穿行,而無(wú)論多么久遠(yuǎn)的時(shí)間在敘述者的手中不過(guò)是書(shū)架上的一本書(shū),可以被隨意打開(kāi)翻閱。”[4]唐朝暉的散文詩(shī),完全擺脫了語(yǔ)言邏輯和意義邏輯的限制;空間也被天馬行空般的信手拈來(lái),如神來(lái)之筆,任意組合、拼貼。如《1998年12月31日》、《過(guò)程》中的“出生,0歲至4歲”、“渾濁歲月,7歲至15歲”、“醒世,16歲至19歲”等,都體現(xiàn)了這種敘事特點(diǎn);在《12點(diǎn)鐘的門(mén)》《兩個(gè)小時(shí)》《一個(gè)瘋子的三分鐘》《一天上午的回憶》《火》中的“二月初六”“三月初七”“四月初八”“五月初九”等時(shí)間概念,《創(chuàng)世記》中的“星期一”到“星期天”等等,僅這些篇目都是以時(shí)間為題目或者以時(shí)間為主題的。在這種特定的題目下,詩(shī)人將敘事對(duì)象釘在時(shí)空交匯的“十字架”上,然而觀看歷史的視點(diǎn)卻如水波激起的千層漣漪擴(kuò)散開(kāi)去。由于敘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時(shí)間的洪流中,敘述的具體時(shí)間就自動(dòng)消隱,而敘事的對(duì)象則在一個(gè)固定的時(shí)間符號(hào)中任意漂流,直至發(fā)生空間上的逆轉(zhuǎn):“從出生到上學(xué),我似乎走在一條直線上,直至1986年12月23日,我的河流突然拐了一個(gè)彎,河水撞著前面的巖石。”(《轉(zhuǎn)折》)
二、“游戲狂歡”的語(yǔ)言盛宴
關(guān)于語(yǔ)言,德國(guó)著名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曾論述過(guò)相關(guān)問(wèn)題,“語(yǔ)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yǔ)言之家為家”。語(yǔ)言是散文詩(shī)的窗口,《夢(mèng)語(yǔ)者》首先讓“語(yǔ)言之家”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有時(shí)浸透一種對(duì)生命的悲憫,有時(shí)傳達(dá)一種社會(huì)問(wèn)題的關(guān)注和潛思,有時(shí)是一種對(duì)強(qiáng)悍生命力的驚訝和敬畏。在語(yǔ)言上顛覆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慣性語(yǔ)式,借助創(chuàng)作主體的想象來(lái)打破種種既定的框架,讓人物變成抽象符號(hào),實(shí)現(xiàn)文體跨越,借鑒小說(shuō)以及寓言的敘事經(jīng)驗(yàn),突出了語(yǔ)言的紀(jì)實(shí)感和荒誕感,通過(guò)一些虛構(gòu)的場(chǎng)景來(lái)打破尋常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同時(shí)以漩渦般的力量重建一個(gè)強(qiáng)大的語(yǔ)言磁場(chǎng),使作者在對(duì)千軍萬(wàn)馬的語(yǔ)言指揮中產(chǎn)生狂喜。這種突破文體的限制,融匯海納百川的語(yǔ)言,繁復(fù)而駁雜,不再如傳統(tǒng)散文詩(shī)一般通過(guò)感情來(lái)表象,獨(dú)辟蹊徑的“語(yǔ)言革命”,不遮蔽、不隱惡、不壓抑、不虛美生活,讓生活在語(yǔ)言文字中自然裸露,令陌生的組合與自然重復(fù)再現(xiàn),讓人看到母語(yǔ)寫(xiě)作的多彩繽紛,最終實(shí)現(xiàn)了一種原生態(tài)的“語(yǔ)言回歸”。盡管這種語(yǔ)言“回歸”,是松散的、斷裂的,甚至是反邏輯的,但傾向于形而上思索的語(yǔ)言,把文本拋向了哲學(xué)的浩瀚星空,使散文詩(shī)這種文體游離于哲學(xué)的邊緣,在玄妙中發(fā)人深省。總之,這種 “游戲狂歡”式的語(yǔ)言存在,讓我們?nèi)ジ兄徒邮埽屛覀內(nèi)ネ侗己腿谌耄屛覀內(nèi)ジ袆?dòng)和共鳴。
在《墳?zāi)埂芬徽轮校瞥瘯熡靡环N詭異的方式將語(yǔ)言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
躺
著
的
和
站著的人都沒(méi)有走動(dòng)
這段文字以獨(dú)特的排列方式,徹底摧毀了傳統(tǒng)的書(shū)寫(xiě)模式。 “躺著的”縱向排列著,“站著的”卻以一種橫向的方式“躺著”,這種悖論性的視覺(jué)沖擊,完全是一種來(lái)至語(yǔ)言的原始狀態(tài)的赤裸呈現(xiàn)。這樣的開(kāi)頭直陳詩(shī)意,喚起人們的經(jīng)驗(yàn)與想象,復(fù)原生命的跨時(shí)空對(duì)話,并由此竭力營(yíng)造了一種肅靜、冷峭的荒誕魔幻氣氛,而這正好也暗合了“墳?zāi)埂边@一主題意向,生與死的兩條線相交,生命交接的莊嚴(yán)儀式。
《火》《七名女子》《方塊6:坐天》、《紅桃5:回家的父親》等篇章融入了小說(shuō)的筆法,用語(yǔ)言搭建了一個(gè)個(gè)的敘事迷宮,極具寓言的意味。《黑桃7:死亡行為(第一天)》開(kāi)頭的文字?jǐn)⑹觯c其后的語(yǔ)言存在著跳躍,甚至斷裂的跡象,字句之間毫無(wú)邏輯,看似零散、碎片化的語(yǔ)言表達(dá),然而將人類惶恐不安的生命焦慮感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正是唐朝暉致力于語(yǔ)言的奇效之處。
三、“向死而在”的生命哲學(xué)
向死而在,是一種昂揚(yáng)恣意的生命狀態(tài),更是一種悲壯雄渾的精神境界,為絕望所生,為希望所遺棄。海德格爾認(rèn)為,人只要還沒(méi)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著。北野武也說(shuō):“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著的人與等候在生命盡頭的死亡之間的一種外在關(guān)系,人們不是一步步走向還在遠(yuǎn)處尚未到場(chǎng)的死亡,而是在我們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經(jīng)在場(chǎng)。”[5]唐朝暉正是在進(jìn)行不斷而嚴(yán)酷地自我“哲學(xué)”拷問(wèn),當(dāng)“死亡降臨,睡眼沉重地砸下來(lái)。我從一次沉睡中僥幸醒過(guò)來(lái)。”(《散步與方向》),正如古希臘神話中的戰(zhàn)神,身穿閃亮的盔甲,一身凜然,手持利刃,毅然決然地刺向那黑暗無(wú)邊的蒼穹。
死亡、肉體、疼痛、毀滅、墓地、墳冢、轟炸、幽靈、黑夜,這些散發(fā)著腐爛和陰魂氣息的字眼撥動(dòng)著敏銳的神經(jīng),刺激著日漸荒蕪的心靈,將尖銳的矛頭直逼內(nèi)心激發(fā)強(qiáng)烈的生命意識(shí)。“大地必須獻(xiàn)出我們:作為她向天空的祭禮。”(《死亡》)“一種氣,流向我。這是死亡的氣息,它來(lái)自天堂和地獄。我擺脫不了,也不想擺脫。”死亡無(wú)情地堵住了人類一切的精神避難所,查封了希望的灶臺(tái),甚至感到“改變現(xiàn)狀是一次誤診,也許只能讓位于死亡。”(《自我關(guān)照》)于是,“我們扼住了死亡的脖子,但手在發(fā)軟,我們害怕死亡的僵尸,就像握住一條蛇。”(《圍殲死亡》)然后爆發(fā)出一聲怒嚎:“我們?cè)趪鷼炈劳觯@是死亡的命運(yùn)。”(《圍殲死亡》)“我舉杯,慶幸自己曾經(jīng)活過(guò)。”(《死亡》)亡書(shū)在“我”與現(xiàn)實(shí)格斗時(shí)迎面撲來(lái),而“我”依然“感謝亡書(shū)降臨。我會(huì)終生聆聽(tīng)、記錄。”(《亡者之書(shū)》)擁有大智慧的人正是站在“死亡”的極巔上俯瞰生命全景和世間萬(wàn)物,從終極關(guān)懷角度來(lái)檢索、審視人生,以“死”的尺度來(lái)測(cè)量各種價(jià)值和輕重得失,由直面死的勇氣來(lái)填充生存意志的虛弱,“把生命拋出去,砸碎死神的頭顱。趁我還年輕,是塊石頭。”(《活》)
從唐朝暉的創(chuàng)作看來(lái),散文詩(shī)原來(lái)是可以具有多維書(shū)寫(xiě)空間的。他將飄渺的時(shí)間、浩瀚的空間以及人類細(xì)膩的思維和心理領(lǐng)域,豐富的生命層次與超驗(yàn)感覺(jué),進(jìn)行多角度多維度地層層交織、剖析,使“思想的密語(yǔ),靈魂的沉吟,人人皆夢(mèng)時(shí)代的吶喊”,鬼魅般的“無(wú)物之陣”,飄忽不定的虛無(wú)情緒,心靈的痙攣,靈魂的淬煉,一一呈現(xiàn)出來(lái),將理性砸得粉碎,任生命在“彼岸”呢喃。天馬行空的虛構(gòu)與想象,將斑駁的語(yǔ)言放逐天際,在夢(mèng)與現(xiàn)實(shí)之間架起一道直達(dá)靈魂深處的橋梁。如此,唐朝暉的散文詩(shī)集《夢(mèng)語(yǔ)者》,正是這樣的夢(mèng)魘與現(xiàn)實(shí)交織的“動(dòng)態(tài)生命景觀”。
陳曉莉,貴州民族大學(xué)2012級(jí)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碩士研究生。
喻子涵,貴州省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貴州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注 釋:
[1]唐朝暉:《夢(mèng)語(yǔ)者》,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引文除注明出處外,均引自《夢(mèng)語(yǔ)者》。
[2]張立群:《中國(guó)類后現(xiàn)代小說(shuō)敘事的策略》,《廣播電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年第2期。
[3]〔英〕馬克·柯里著,寧一中譯:《后現(xiàn)代敘事理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
[4]張立群:《論文學(xué)史視野中的中國(guó)類后現(xiàn)代小說(shuō)敘事》,《人文雜志》2006年第1期。
[5]〔日本〕北野武著,李穎秋譯:《向死而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