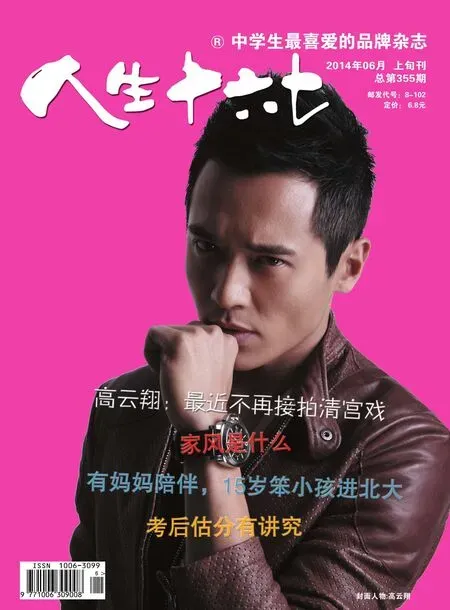無言的家風
馬智雍
無言的家風
馬智雍
馬智雍,一個個性十足的大男孩,屬虎,現為遼寧省實驗中學高一學生,校團委宣傳部部長。學會走路和識字后,就愛上了閱讀和旅游。讀書來者不拒,尤愛歷史和政治。9歲時隨《沈陽晚報》小記者團去香港,之后又游走“新、馬、泰”,歐洲四國(德、法、意、瑞)和澳大利亞。動筆善寫議論文,多有“豆腐塊”見報。兩次參加全國高中生“模聯”(模擬聯合國)活動均獲優秀學員。
2014年春節前后,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深入全國各地,當街問詢每個人的家風是什么。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爸爸的老家在農村,常常聽爸爸講一些老家的趣聞軼事,生活經歷,可我從來沒聽爸爸說過我們的家風是什么。
一天,吃過晚飯,看完新聞聯播,我認認真真地問爸爸,“爸爸,別人家都有個家風,那么,我們家的家風是什么呢?”爸爸聽我問后,思考了一會兒說,過去爺爺家雖然是個大家庭,通過辛勤的勞動,日子過得也算富足。但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農民,祖上并沒有留下什么文字記載的家風,可是,他們一代人又一代人都把家風寫在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又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我們家的家風是無言的,你爺爺用一生的行動告訴了我什么是我們家的家風。
爸爸接著講起了爺爺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爺爺馬友良1921年生于遼寧東部的一個小山村,小時候上山放豬,左大腿摔成了骨折。當時家里都以為只是扭了一下,養幾天就會好的。為此,錯過了治療的時機,爺爺終身落下了殘疾。
新中國成立前,太爺爺兄弟五個都在一起生活,加上各自的子女,全家上下七十多口人,男耕女織,勤儉持家,日子雖然過得并不特別富裕,但十分和諧。解放后,由于種種原因,大家庭必須分家了。
大家庭中別人對分家不大在意,可爺爺就難了。因為爺爺的父親一病不起,奶奶已生下了大大和兩個姑姑。家里可謂老的老,小的小,關鍵的關鍵是爺爺身體有殘疾。從此,爺爺拖著一條病腿,獨自承擔起了養活一家六口人的重擔,何況后來家里又多了二大和爸爸。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農村中的家家戶戶都很貧窮,爺爺家當然是貧窮中更貧窮的。爺爺白天要到生產隊里干活,晚上還要照看有病的太爺。家里本來就缺吃穿,可爺爺總是把家里最有營養的一點點兒東西給太爺吃。不管生活怎么難,爺爺從來不跟太爺、奶奶和孩子們發脾氣。所有的苦都自己吃,所有的難都一個人擔。太爺臨終時想吃魚,三九隆冬,爺爺一個人來到村外的冰河上,刨呀刨,找呀找,整整找了兩天兩夜,終于給太爺端回了半碗河魚。為了一家人糊口,爺爺白天到田里干活,晚上總得找點能掙些小錢的私活干干,不是編筐,就是紡麻,常常一干就到下半夜。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但爺爺從不抱怨。
爸爸說,從他記事時起,每天早晨睜開眼睛,都發現爺爺早已起身,不是下田干活了,就是在院里干活或上街打掃衛生。爺爺不僅勤勞,還心靈手巧,什么砌個墻,苫個房(用一種特殊的野草苫在房頂上遮雨),做個桌凳,打個犁杖,樣樣在行。在村里,爺爺雖然是個殘疾人,也是大家眼中的一個能人,因為他干什么像什么。
爺爺一生不沾煙酒,更無其它不良嗜好,年輕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維持一家人的溫飽上。晚年時,爺爺最大的愛好和享受就是聽收音機,聽京劇、聽評書、聽新聞,尤其愛聽國際新聞。
現在,人們常常講做事貴在堅持,可爺爺的這一堅持就是30多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81年,爺爺的村里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生產有了很大的自主權。當時已是六十歲高齡的爺爺,不顧兒女苦勸要他在家安度晚年,硬是到銀行貸款1000元,一個人住進深山里,種起了人參。從平整山地,到種養看護,必須出力氣,又要學技術,還要耐寂寞,面對這些年輕人都會望而卻步,可爺爺一堅持就是十多年。1993年,爺爺收參下山時,不僅給家里增添了十余萬元的存款,還在原人參地上種下了兩萬多棵落葉松。如今又二十多年過去了,爺爺已于2010年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可他留下的那片郁郁蔥蔥的松樹已成林成材,給兒孫后代,給社會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當然,比這兩萬棵松樹更珍貴的,就是爺爺那勤勞善良、通情達理、永不退縮的品格。而正是爺爺身上的這些優良的品質,凝聚成為我們家的家風。
爺爺臨終時,留給爸爸的最后一句話是,“兒子,記住,要勤奮做事,正直做人,你在外面做的一切事,都要讓爹在村里能直起腰、抬起頭。”講到這里,爸爸的眼里已噙滿了淚水。
聽了爸爸的一席話,我終于明白了如今已是五十多歲的爸爸為什么每天學習、工作都有使不完的勁兒。爸爸1959年出生在那個小山村,從小吃盡了苦,受盡了累,在“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他先從農村考上了中專,然后,考大專、念本科,最后讀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從農民、到教師、再到記者,直到現在做一家媒體的領導。爸爸工作一絲不茍,兢兢業業。我從小到大也沒看到爸爸睡一次懶覺,更沒聽到他對社會和他人有一聲抱怨。為什么他學習、工作、生活有如此動力,就是因為我們的家有無言的家風。
家風雖無言,但我將把它銘記在心里,溶入到血液中,用他去激勵我實現我的夢、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