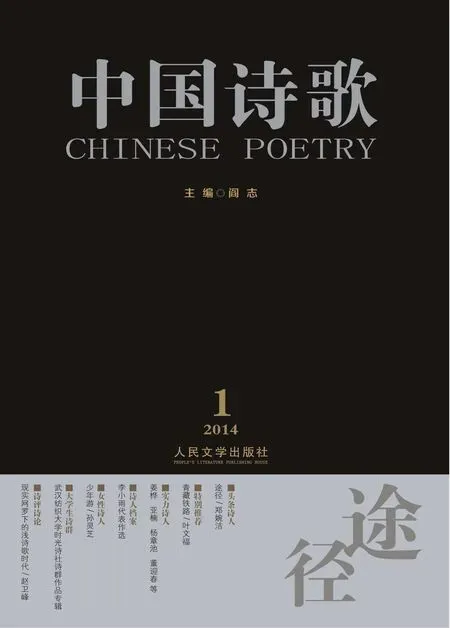詩學觀點
□王 婉/輯
蔭林莽認為就中國當下詩壇的整體而言,它如同一片自由生長的荒原,充滿了生機,但缺少了應有的秩序與方向。中國新詩還需要更有目的性的梳理和總結,中國的新詩教育還有待更根本的變革與調整。
而對于每一位詩人而言,面對詩歌藝術,是否有一顆虔誠的心,是否真摯地面對生活和詩歌進行創作,是否拋棄了那些虛妄的急功近利的世俗性,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國詩壇是中國現實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的各種形態同樣反映在詩壇上,詩壇同樣充滿了各種矛盾,同樣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積垢與問題。這些和藝術本質相悖的因素,同樣影響著中國新詩的繁榮與發展。一個詩人心靈的自律和對藝術的誠心以求,決定著他的藝術成就。
(《我對當前詩歌的一些看法》,《詩刊》2013年9月上半月刊)
蔭霍俊明認為陽子的詩歌祛除了當年中國女性寫作“雅羅米爾”式的精神疾病的氣息。她在日常世俗和精神想象互相呈現和打開的空間中不斷舒展出內心淵藪的潮汐和冷暖,在語型和書寫方向上也大體舒緩松弛。或者可以說陽子近年來的詩歌聲音和語調不再像以往那樣尖利,而是更多的時候在靜水流深中讓我們領略了女性的特殊之處以及那些隱現的神秘光芒和精神陣痛的閃電。在陽子這里,再次印證了我對女性寫作的觀感——女性詩歌幾乎不存在靜態式的寫作方式,即女性的精神狀態一直處于類似于茫茫大海上一只動蕩的小船對遙不可及的海岸的尋找之中。陽子顯然是當下女性寫作中具有方向感的少數者,而當下的女性寫作之間的面目越來越模糊而難以辨識。在此語境下陽子的明顯帶有方向性和精神提升與探詢式的話語方式就顯得不無重要性。這樣的具有方向性的詩歌顯然在那些仍然在老調常彈的女性、女權、黑夜和自白之外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素和詩歌經驗。
(《讀詩》,《詩歌月刊》2013年9月號)
●詩人范劍鳴認為向萬物致敬,是他一直以來的詩歌態度;或者說,是詩歌教給他的世界觀。現代社會的人類活動過于張揚自身的能力,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以精英為中心的社會觀,互相呼應著破壞自然和和諧。為此,詩歌為人類的解脫準備了一條可能的通途。這不是“齊萬物、一死生”的超脫,而是對萬物保持等觀和博愛的姿態。
詩歌是對個性經驗精華部分的提取。詩人的經驗世界里,人類的悲歡與萬物同在。他經歷的空間如此窄小,但生養他的鄉土已提供足夠豐富的情節,可以抵達心靈的圓滿。向萬物致敬,向眾生致敬,衍生的觀念是:一切死亡都值得尊敬,一切群體都應該關注。為此,他贊同憂世傷時的“新樂府”。但無論是破敗的鄉村,田園的牧歌,還是更龐大的生死場,只有提取最具審美意義的個性經驗,才能完成詩性的塑造。
(《向萬物致敬》,《詩潮》2013年9月號)
蔭耿韻認為詩人沈葦,一個他鄉的本土主義者,雖然遠離了對異域風情的迷戀,但他并沒有遠離富含心靈凈化力量的事物、沒有遠離對人性的潛能和寬闊的精神世界所懷有的激情,也不會遠離它時常出現的躁動。人們不能將其簡化為地域詩或邊疆詩,應該注意到沈葦詩歌語言透視的秘密:“荒涼”的地域里的社會學深度與歷史輪廓,族群與地域之間張力關系的描繪,它們賦予地域及景物以某種意義的政治視野。他揭示出荒涼在個人的與族群的生活方式上深厚的美學投影,揭示出地理學的“荒涼”(或相反,地理學的極其華美)投映在政治、經濟領域遺忘的陰影。在這一遠景中,沈葦詩歌話語變成了溝通或連接線,這是一束時隱時現的從窗外照進的光線,它照耀著,就像畫上的一道微光,賦予畫卷一種震顫,一種無法確定的力量。
(《荒涼與遺忘的證人》,《名作欣賞》2013年9月上旬刊)
蔭董迎春認為“第三代詩”提出的拒絕隱喻、冷抒情、詩到語言為止等詩學主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現象學等理論的影響,它們不斷清除與還原“朦朧詩”的美學規范與詩歌精神,以“還原”作為搶奪“話語權”的一種書寫策略。“第三代詩”,被大眾迅速接受并被當代詩歌史描述得最明顯的話語特征則是“轉喻”。“第三代詩”中“口語寫作”一脈提出“拒絕隱喻”,“詩到語言為止”等主張,解構了“朦朧詩”的精英主義、宏大敘事、崇高的英雄主義等抒情話語,他們主張用日常語言代替文學語言,把詩歌還原到日常生活,建立以“冷抒情”、“語感”等為文本策略的“轉喻”寫作,最主要的是由以往的“書面語”轉向了對“口語”的重視。而在從“朦朧詩”向“口語寫作”的轉換中,也體現出某種“連接關系”與“還原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修正了“朦朧詩”隱喻寫作中意象冗長、暴力抒情等失效的詩歌話語。
(《不合時宜的“還原”——論20世紀80年代詩歌話語的“轉喻”特征》,《南方文壇》2013年第5期)
蔭馬海軼認為詩是個人的,個人是孤單的。想要寫出某種東西而不能的時候,沒人能夠幫助,只有自我掙扎。每句詩都是從黑暗的海里打撈出來的。每次都是自我的手術,要從體內找出那根骨刺,它是慢性病癥或者劇烈疼痛的根源,詩寫成之后,要讓人看,讓人懂得,讓人明白他們的身體里也有同樣的刺,由此證明人也是物以類聚。所以詩應該是能夠自明的,古今中外的名篇都是如此。詩不能靠闡釋,寫了一首詩,讀的人不懂,作者抑或是評論家來解釋,解釋還未完畢,瞌睡已經悄然來臨,厭倦無法產生詩意。一些詩人過于艱澀,別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只有說得很深沉。但他不甘心一個人深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于是出版了給大家看,請專家來解釋。大家或許略微明白,但又有新的疑問:詩與古文有什么區別?這樣,疼痛沒有轉移,還在寫作者那里。時間久了,必要瘋狂。
(《詩歌手記》, 《青海湖》2013年第33期)
●詩人谷川俊太郎在接受田原采訪時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對家人和朋友說的語言和作為詩歌寫出的語言的根源是相同的,但在表現上不得不把它們區分開來。現實生活中的語言盡可能表現出真實,詩的語言基本上是虛構的。一首詩里的第一人稱,不一定指的就是作者本人。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作者完全沒有把自己投射到作品當中。作者的人性隱藏在詩歌的“文體”之中。“文體”是一個很難被定義的詞,它不僅包含著語言的意義,形象、音調、色彩、作者對語言的態度等所有的要素都融為一體。在現實生活里,人與人的交流不只是特定的伙伴之間的語言,他們的動作、表情等非語言的東西也是非常具體地進行著的。至于化為文字、化為聲音的詩,是一個作者與不特定的、復數的讀者或聽眾之間更為抽象的交流。可是,作者本身的現實人際關系也投影到他下意識的領域。雖然“活著與語言的關系”在詩歌里極為復雜,可是,作者無法完全意識到它的復雜性。因為讓詩歌誕生的不只是理性。我想,可以這么說,以不完整的語言把無法完全被語言化的生之全部指示出來的就是詩歌。
(《寫詩是我的天職》,《上海文學》2013年第9期)
蔭梅申友認為安娜·卡明斯卡是一個偏愛清凈和獨處的詩人,生前拒不加入任何詩歌團體,也不追隨任何時髦的寫作時尚。當詩人們熱衷于討論新的詩歌寫法時,她卻沉浸在對古典作品的閱讀當中,并語出驚人:“我不懂什么叫創新。”當有人揚言,“奧斯維辛之后,寫抒情詩是可恥的”,她卻在研讀美妙動人的《雅歌》,認為其自由而又準確的語言,永遠不失為好詩的典范。在她看來,人心不死,詩歌就不會死亡。她給詩歌下過一個簡單的定義:“勤勉的驚詫”。而她寫作的動機,是“為了解惑,而不是為了表現自己”。她的詩歌的特色是語言澄澈、手法簡明。現代派詩人提倡的知性和用典,在她的作品里也很少見到。她反對晦澀蕪雜,主張“直接、溫柔地言說,給事物和概念命名”,要讓詩寫得“像玻璃窗一樣透明/一只迷途的蜜蜂迎頭撞上”。
(《隨信仰而來的智慧》,《世界文學》2013年第4期)
蔭許多余認為在詩與生活愈加遙遠的年代,我們更多的時候所聽到的,只有贊歌與哀歌。底層被碾壓的慘劇時刻上演,情感變得麻木,幾乎令人無悲憫之力——與此同時,無恥而虛空的贊歌卻大行其道,屢唱不爽,經久不衰。一個民族的心靈從未有過如此蒼白。我們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生活就是真實的生活,它們如此荒誕,如同虛構。可它們就是我們的生活!詩人不能適應,又無法拒絕。正如玻璃上反射的天氣,從缽里溢出黑色的嗡響,它們呆板而宿命。
(《詩,模擬宗教般的生活》,《特區文學》2013年第4期)
蔭宇向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寫作和生命、身體、心靈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去寫現實,寫作的人懂得現實不是我們說的那個藝術世界里的“真”。我們忠實的應該是在生存困境中的內心豐富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就寫什么。她認為“真”是寫作的要義,而由“要義”才能達到“奧義”,同時由最基本的生存感受達到那個最終的追問,這同時就有了一個巨大的“張力”,而同時由于源于個體的真實感受,就有了“原創”、“獨創”的意義。
(《宇向訪談:我幾乎看見》,《詩選刊》2013年第8期)
蔭李犁認為上帝用圣靈柔化人和心靈,詩人通過寫詩走向圣靈和神明,圣靈就是一種光芒,就是詩歌要抵達的境地,它讓詩歌棄絕凡塵,讓心靈寧靜,讓人生清澈。神明不等于詩歌的神性,鳴久追求的神明是個人修為,是個人品行要達到的境界,是心靈的方向和根。它讓我們仰望也讓我們甘愿接受煉獄,整個過程就是佛家的修行之路。這是一條通往人的內心最深遠的路,詩歌就是探測人的心靈同時又是引導著心靈走出迷惘走向圣靈的道路。在這個道路的盡頭是一種自由的充滿的超然的明亮和透徹,是完全卸去沉重的肉身和欲望后的輕松安詳平衡和美。這就是詩歌柔化心靈的方式,其結果就是讓身心和詩歌一樣真而純。
(《王鳴久:寫詩就是修行和坐禪》,《海燕》2013年第9期)
蔭陳衛認為很長時間以來,因為國家處在不安定當中,詩歌一直幫襯著主流意識形態,起到準宗教的作用,詩歌因此與嚴肅的生活態度相關,寄托了對終極理想的思考與追求,或者僅限于表現現實生活的真實性,詩歌的主趣特色基本蕩然無存。而顧北的詩則除了遠離崇高的美學,也遠離沉重或高蹈的抒情。文字在他筆下,更像是用來玩的。顧北在作品中呈現玩的態度,既不高調,也不低俗,有時口語調侃,有時又來一下抒情;他關注奧巴馬,也寫一寫佛祖,想一想“隨手拎起來就走的哲學”,也偶爾表示一下纏綿。在顧北的詩里,與生俱來的情感都經過了一定程度的變形、夸張或掩飾,所以讀他的詩會讓人生出在哈哈鏡前才有的怪誕感,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趣味性。
(《在平淡的生活中發掘快意》,《福建文學》2013年第9期)
蔭葉櫓認為一個真正尊重古典詩歌傳統的人,不會因為曾經擁有的輝煌而固步自封。古代詩人們的輝煌成就,不應當成為一種精神包袱,更不能永遠匍匐在這種遺產面前不思進取。洛夫對這些唐詩的“解構”,固然是處于對這些經典詩篇的熱愛和尊重,但他也并不認為這就是永遠不可超越的“珠穆朗瑪峰”。作為后人,超越前人不僅是一種理想和追求,更是應當付諸實踐的創新和創造。我們從洛夫在對經典詩篇的進入之后所另辟蹊徑的創造中,不難看出他在意象的呈現和鋪排上,顯然是具有更為豐富的表現手法的。而在對諸如意境、禪境等的理解和藝術把握上,顯然融入了更多的現代意識。而這,正是我們作為一個現代人所應該和必須具備的清醒意識。如果我們只是沉溺于對古典詩歌成就的崇拜和迷戀之中,不思進取,并進而沉醉其中,那就不僅是有負于那些先輩的祈望,更證明了自己作為不肖子孫的侏儒行徑。真正有出息的現代詩人,必定是那些另辟蹊徑而充分發揮出獨創精神的探求者。
(《回眸中的審視與超越——從〈唐詩解構〉說起》,《揚子江》2013年第5期)
蔭張清華認為某種程度上,一個詩人的意義,正是取決于其語言的符號價值。而這是一個相互發現和選擇的過程,詩人發現了某種最具時代性的符號,而時代則將會選擇這個詩人作為精神的代言象征。鄭小瓊的語言充滿了這種可能。從這部詩集中我感受到,她晚近的寫作正在使這種“符號的力量”得到強化,因為在她的修辭中,幾年前頻繁出現的“鐵”,已被擴展到了更為寬闊的時代的街頭巷尾與垃圾場上,她的界面正日益寬闊,這些詞語以特有的冰涼而堅硬、含混又曖昧的隱喻力、輻射力和穿透力,串連起了我們時代的一切敏感信息。
(《語詞的黑暗,抑或時代的鐵——關于鄭小瓊的詩集〈純粹植物〉》,《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