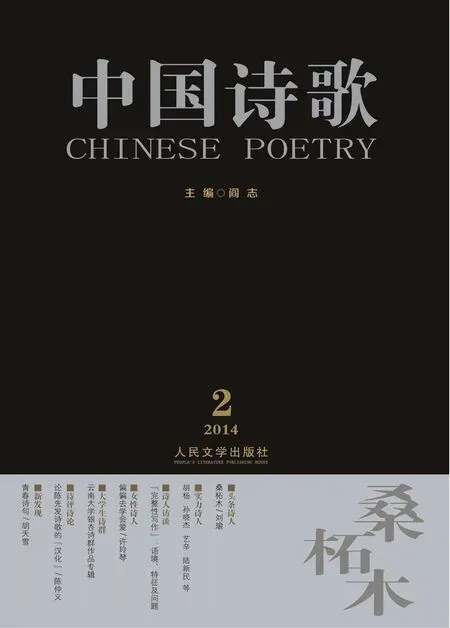痖弦新詩導讀
□鄒惟山 王金黃
臺灣詩人痖弦是當代中國杰出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詩歌評論家,其新詩代表作是詩集《深淵》,其詩論代表作是《中國新詩研究》。一位詩人,只憑一本薄薄的詩集《深淵》,便風行海外,聲名鵲起,奠定了其中國新詩史上杰出詩人的地位,這樣的事件有一點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而之所以如此,要從其神秘的出生地與豐富的人生歷程說起。痖弦出生于河南南陽,那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也是古老中國歷代被稱為“中原腹地”的地方。只就近代以來,就有哲學家馮友蘭、詩人李季、小說家姚雪垠等杰出人才出世。更為重要的是,詩人從青年時代開始不斷地南遷,以至于與國民黨政權一同去到臺灣,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成為了一名著名的編輯家、杰出的詩人與文學活動家,老年而至于遷居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定居。從老家跨過長江,進而跨過海峽,終至于跨越大洋,這就是其最為主要的人生歷史軌跡。最近十年以來,他以一個文壇老者的身份在海峽兩岸,以至于世界各地出席各種文學與學術會議,以自己的力量為世界漢語文學的發展貢獻了巨大的心力。他的文學創作與其人生經歷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說,其文學創作就是其人生經驗的一種呈現與生命感悟的一種記錄。在幼年和青年時期,他曾經經歷了偉大的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風起云涌的社會大變革與時代大變遷,讓他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思想者與記錄者。而時代變動中產生的越來越大的空間距離,也許是其詩情詩思產生的重要原因。1949年,他以一個中學生的年紀,隨國民黨政權退據臺灣,從此在很長時間里隔斷了與祖國大陸的音信,讓他對故鄉的思念之情與日俱增,以至于產生了中國本土式的存在主義思想。這樣的歷史背景與文化語境,既是他詩歌寫作的大背景,也是其許多詩歌產生的根據。痖弦詩歌創作雖然總共只有短短的十幾年時間,數量也不過百首左右,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他不僅是臺灣現代詩界的一座頂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整個中國當代新詩的一面旗幟。他的詩曾經獲得過許多重要獎項,最近還在北京獲得了“中坤國際詩歌獎”,越來越顯出獨立的思想深度與藝術風格。讓許多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在數十年前所創作的詩歌作品,不僅沒有像同時代的許多作品一樣過時,而且常讀常新,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在整個世界文學史上,其詩歌作品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以一部詩集而能獲取這樣的詩史地位,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很少有的。而沒有南陽的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沒有三次大的地理跨越,沒有在臺灣文壇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經歷,沒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想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有機結合,沒有自己在人格上的獨立與藝術上的追求,他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功的。除了寫詩之外,他對中國新詩有系統的研究,《中國新詩研究》中對于自五四開始的各位杰出詩人與著名流派,如劉半農、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詩作,以及中國新詩的發展道路,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流派與詩人,都發表了獨到的藝術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它與其詩作結合起來閱讀,因為它們本來就是相存相生、二位一體的存在。
1
痖弦詩歌之所以獲得這樣的成功,并不是無緣無故的。
首先,與詩人本身情感的豐富性與思想的深刻性,存在密切的關聯性。其許多詩都是以下層視角所進行的人文關懷,表達了對底層人民生命意義的追尋,以及自我的豐富人生的深切感悟。從《坤伶》、《乞丐》、《水夫》等詩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坤伶”、“乞丐”還是“水夫”,都是身居下層的無產者,在詩人的筆下是一種形象、真實而深刻的存在。讓我們讀一讀其《山神》:“……春天,呵春天/我在菩提樹下為一個流浪客喂馬/……/當瘴癘婆拐到雞毛店里兜售她的苦蘋果/生命便從山鼬子的紅眼眶中漏掉/夏天,/我在敲一家病人的銹門環/……/秋天,呵秋天/我在煙雨的小河里幫一個漁漢撒網/樵夫的斧子在深谷里唱著/怯冷的貍花貓躲在荒村老嫗的衣袖間/……/冬天,呵冬天/我在古寺的裂鐘下同一個乞丐烤火”。這里所寫的“流浪客”、“瘴癘婆”、“病人”、“漁漢”、“荒村老嫗”與“乞丐”是多么的可憐,他們生活無著落,貧窮而骯臟,然而,為什么讀起此詩來,卻如此地溫馨動人,看起來像是一幅美麗的油彩畫?詩人將自己濃濃的關懷注入到下層人物身上,讓他們一年四季里不再是孤單的人,因為詩人與他們在一起“喂馬”、“嬉戲”、“撒網”、“烤火”,詩人的自我與下層人民共歡樂、共憂患。這種真實而深刻的力量,來自于詩人寫作時采取的平視敘述。所謂平視敘述,既不同于有的詩人所采取的俯視底層勞動者的高高在上,也迥異于有的詩人所采用的仰視以放大、美化乃至于歌頌,而是以一種平等的、類似于共同生活式的記錄方式,將詩人眼中的真實發現與心靈感覺呈現在讀者面前。詩人正是以此種方式拉近了與荒村老嫗、流浪客、乞丐的心理距離,客觀地展露了乞丐、水夫等人的心理變化。正是因為如此,“春天,春天來了以后將怎樣/雪,知更鳥和狗子們/以及我的棘杖會不會開花/開花以后又怎樣。”(《乞丐》)這樣的詩句才是那樣的讓人感動。雖然對乞丐的心理進行了詩化處理,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無名“乞丐”內心深處的孤獨無依,以及對于未來生活的嚴重無望。在表現底層人物的真實與深刻的同時,對人生命運的無限感嘆和對世事無常的冷靜觀照,也同樣引人入勝,“而地球是圓的/海啊,這一切對你都是愚行”(《水夫》)。詩人所發出的對于“水夫”的美好愿望與現實生活背道而行的一種質問,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漠然的接受;他不僅是在質問自己,也是在質問每一位讀者:誰能不為這位水夫感到傷心呢?聯系到詩人自己所處的時代,誰又能不為這位詩人感到傷心呢?其詩中大量的貧民形象躍然紙上,詩人以同情的方式與他們對話,或者以自我內心獨白方式表達哀憐之情,不僅批判了當時的黑暗社會,并且抒寫了一種人道主義思想。詩人之所以沒有高高在上,是因為他也曾經是流浪者中的一員,是士兵中的一員,是社會底層民眾中的一員。
其次,從自我個體出發對所處時代進行深刻的批判,并且具有一種歷史的深廣度。如果說詩人對下層群體的關懷是點的話,那么對時代的批判就成為了一個面,雖然詩人并沒有對那個社會進行全面的反思與批判,并沒有像小說家與思想家那樣做出價值判斷。請看《上校》:“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自火焰中誕生/在蕎麥田里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而他的一條腿訣別于一九四三年”。這首詩中因打仗負傷而被截肢的退役老兵“上校”,對自我的未來生活已經厭倦,只有“太陽”能夠“俘獲他”,詩人在這里固然有對英雄悲壯的贊頌,也有對昔日戰斗生活的緬懷,但最為根本的卻是對“戰爭”的控訴,對英雄悲壯情懷的一種反思。《紅玉米》、《鹽》都取材于作者幼年時期的大陸生活,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一種深濃的故土之情,久久縈繞于心中。“紅玉米”和“鹽”的兒時記憶已深深印入其心,“二嬤嬤”更是對兒時父老鄉親群像的濃縮。如果說《紅玉米》是低吟的、深沉的,因為其中有這樣的詩句:“它就在屋檐下/掛著/好像整個北方/整個北方的憂郁”,那么《鹽》就是絕望的、嘲弄的,因為其中有這樣的詩句:“托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嬤嬤”。詩人以自我的經歷和反思為起點,通過“紅玉米”和“二嬤嬤”打破了讀者心中的歷史觀念,從中揭示了一種血和淚的真實人生經驗。在長詩《深淵》中,詩人以薩特“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作為引子,接著展開一種混雜奇異的想象、怪誕詞句的拼接、暗無天日的憂愁,以及百無聊賴的自我調侃——“哈里路亞!我仍活著。”成為長詩中反復出現的重要句子。詩人在長詩中特別強調自我的視聽及心理感覺元素,展示了那個時代和大環境的壓抑與扭曲。長詩中之所以對現實進行內心化、個人化的鞭笞,源于詩人本我的真實;當真實與本質結合在一首詩中時,就讓當代讀者產生了一定的距離。從此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刻畫社會人物和描寫社會現實的詩作,因為融入了自我的內心真實,而具有了一種“心史”的維度。其詩歌表現了從清末到當代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從戰爭到災荒,從鄉村到城市,從北方到南方,從東方到西方,從大陸到臺灣,從民間到宮廷,雖然是一種簡要的意象化呈現,其所涉及的社會生活內容與歷史文化面是相當廣的,并且也具有相當的深度,因為其情感是獨特的,思想是深刻的。
再次,濃郁的憂思不僅是自我的,同時也是時代的。流沙河先生曾經詼諧地把痖弦比喻為一只“憂郁的鼠”。其每一首詩中都包含著豐富的情感,并且這種情感總是與事、人、物緊密結合,有著一種與時代相關的深刻憂思。其詩中的憂思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其一,早期詩作里的舒緩的淡淡的憂思。《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我也不凋落,也不結果,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這里所展示的東方式的唯美意境,像中國古典詩歌一樣的“哀而不傷”。《一般之歌》有對時間與場景的恬靜回憶,甚至存在一種讓人享受不盡的味道,正如詩人所說“安安靜靜接受這些不許吵鬧”。其二,惆悵的、反復的憂思,在《傘》、《焚寄T·H——為紀念覃子豪先生而寫》、《瓶》、《秋歌——給暖暖》等詩作中有豐富的表現。《焚寄T·H》和《秋歌》這兩首詩,一個是紀念自己的友人,一個是寫給親人暖暖,詩人對于友情的緬懷和對親情的思念,在詩中化作了一種惆悵的憂思,再加上句式上的反復,就更加的濃郁與深厚。這樣的情感內容,既是詩人自己的,也是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或者說是由于那個時代的感染而產生的:如此大規模的戰爭,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一灣淺淺的海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讓本是血脈相親的人不再來往,音信全無,詩人面對這樣的時代不憂不懼才怪呢。其三,濃烈的、深深的、帶有質疑性的憂思。《如歌的行板》“之必要”句式一貫到底,最后以“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里”結束。詩人以幾近絕望的聲音,質問精神救贖的虛無,表達了一種對現實的漠然,以及對整個時代的無可奈何,讓其憂思深化到了一種極境,讀罷掩卷,不禁讓我們唏噓不已!以上所說的三種憂思,在其詩中并非一種歷史性的發展形態,而是兼而有之,時斷時續。總而言之,深厚的憂思是其詩歌中揮之不去的情感,也是其詩歌的思想情感基調。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社會存在一種飄泊之感,一方面沒有了自己的根,一方面也無法完全融入西方的社會政治體系,詩人作為時代精神的晴雨表,有這樣的深廣憂思是不難理解的。
最后,存在一種深刻的哲理書寫。存在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在它的指導下所產生的痖弦詩作,自然與哲學關系密切。這種哲理書寫,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將深刻的哲理融入詩中,讓其絕大部分詩作在詩行之間或者詩節之間產生一種哲思。這在《如歌的行板》、《瓶》、《C教授》等詩中,均有所體現。《C教授》寫了一位老式而古板、堅毅而執著的人物,兩個詩節之間形成了一種鮮明對比的反諷,豐富且深刻。《如歌的行板》以“……之必要”的句式構成,直到最后以“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里”結束。讀罷這首詩,會不由自主地聯系到廢名名詩《街頭》,它們都具有句式一貫到底、結尾哲理升華的特點。《瓶》更是一首豐富多義、韻味無窮的詩。其二,以某一作家作品里的一句富含哲理或詩意的話作為引子,從而結構全詩。組詩或長詩形式是其詩的主體,并不只是對前人話語的一種闡釋。《巴黎·奈帶奈靄,關于床我將對你說甚么呢?——A·紀德》、《芝加哥·鐵肩的都市他們告訴我你是淫邪的——C·桑德堡》、《從感覺出發·對我來說,活著常常就是想著——W·H·奧登》、《深淵·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薩特》等作品,都是一種現實的存在,也是一種哲學的存在。在這樣的詩作里,從紀德、桑德堡到奧登、薩特的作品片斷都成為了一種必要的存在,也具有了一種獨立的意義,而痖弦之所以選出四位的話語為引子,因為它們能夠在詩作里起到激發靈感與組合詩思的作用,呈現出對人生現狀更為冷靜和嚴肅的態度。“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歐戰,雨,加農炮,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散步之必要/遛狗之必要/薄荷茶之必要/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陽臺、海、微笑之必要/懶洋洋之必要”。正是這樣的詩行,為其詩擴展了縱向深度,為讀者提供了多樣的生命體驗。
痖弦的詩歌數量不多,寫作的時間跨度不大,然而其質量卻相當高,有很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題材與主題也許并不重要,思想的深度與情感的厚度卻是詩藝存在關鍵。從平民視角到時代憂思,從社會批判到哲學思考,他的詩作雖然表面形態簡要,內在形態卻是相當復雜的。童年生活與少年記憶,青年流浪到中年憂思,東方神話到西方傳說,舊的時代與新的人生,全部都糾纏在為數不多的詩作里。它們都是以抒情的方式而存在的,以自我的方式而延續的,以藝術的方式而被閱讀的。時代的、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與個人的東西得到了有機的統一,并且以詩的方式而存在,并將繼續這樣的無限期存在。
2
痖弦詩歌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獨立的追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擁有一種東方民謠式的體式。痖弦曾在1956年提出過“新民族詩型”的觀點,追求意象新穎和意境至上,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傳統。因此,他展現給讀者的正是一種東方民謠式的體式,由三種要素相互組合、縱橫交錯形成一張立體化的感官網。其一,如傾如訴、娓娓道來的抒情方式,與濃郁憂思結合得天衣無縫。這在《秋歌——給暖暖》一詩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現,“落葉完成了最后的顫抖/荻花在湖沼的藍睛里消失/七月的砧聲遠了/暖暖//雁子們也不在遼 的秋空/寫它們美麗的十四行詩了/暖暖//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在南國小小的山徑/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韻/在北方幽幽的寺院//秋天,秋天什么也沒留下/只留下一個暖暖//只留下一個暖暖/一切便都留下了”。肅殺的秋天勁風掃落葉,詩人卻將其從容地放緩,每一句都是對親人的訴說,同時也是對自我的寬慰,在漫步中抒情,讀者感受到的是一種淡淡的憂傷與深深的眷戀。其二,循環往復的藝術結構。《詩經》中那種循環復沓、重章疊句的句式,在其詩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在抒情詩《傘》中,“雨傘和我,和心臟病和秋天”這樣的句子反復重現,相遞組合,抒寫一種無法言說的、百無聊賴的憂悶,將自我的情感映射到幾個物象里,讓全詩渾然一體。其三,仿民歌式的旁白插入。這樣的藝術處理或是疑問句,或是感嘆句,在不同段落的末尾插入,起到了一種間離效果,在《殯儀館》、《乞丐》、《坤伶》等詩中都有具體的表現。在《殯儀館》中,“(媽媽為什么還不來呢?)”作為旁白反復插入,如果把這樣的詩作看作可以詠唱的歌詞作品,那么全詩產生了一種東方歌劇的味道;《乞丐》中的旁白,則是另一種情景,“(依呀嗬!蓮花那個落)”,“(依呀嗬!小調兒那個唱)”,像這樣的中國特有地方小曲的曲目,從一個“乞丐”口中發出來,實在是相當真實而豐富。痖弦的詩歌雖然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然而卻具有東方詩歌的風味,與中國古典詩歌甚至地方文學相接,與西方文學拉開了很大的距離。從其藝術風韻與藝術風格而言,其詩中那樣一種靜美的、典雅的、含蘊的氣質,實在是讓人覺得東方的詩人無論如何西方,也不可能脫離自己固有的文學藝術傳統。
第二,意象上具有鮮明的東方韻味。好的詩歌往往以意象取勝,創造了具有獨立性的意象的詩人,往往成為優秀的詩人。痖弦的詩具有濃郁的詩情,彌漫著深深的憂思,然而意象并不因此而雜亂;相反,其詩中存在多種具有蘊含深刻的意象群。其意象群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底層人物意象群(“乞丐”、“坤伶”、“水夫”等),生活物品意象群(“傘”、“紅玉米”、“鹽”、“麥子”等),東方自然意象群(“秋天”、“秋雨”、“山神”等),現代西式意象群(“機器鳥”、“圣女”、“絲帶”、“廣告牌”等)。在現代西式意象群中,詩人表現出了一種完全拒斥的態度,混雜著種種反諷與嘲弄,像這樣的詩行比比皆是:“穿過廣告牌悲哀的韻律,穿過水門汀骯臟的陰影”(《深淵》),“在芝加哥我們將用按鈕戀愛/乘機器鳥踏青/自廣告牌上采雛菊/在鐵路橋下鋪設凄涼的文化”(《芝加哥》)。對于東方式自然意象群,詩人則表現出一種心靈的歸屬感,“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在南國小小的山徑/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韻/在北方幽幽的寺院”(《秋歌》)。與此同時,詩人把眷戀和深深的回憶留給了生活物品意象群,“宣統那年的風吹著/吹著那串紅玉米//它就在屋檐下/掛著/好像整個北方/整個北方的憂郁/都掛在那兒”(《紅玉米》)。最后,詩人用博大的胸襟緊緊裹住了底層人物,如前述的《山神》。其詩中所有意象群表明的是詩人內心深處的愛憎分明,盡管當時的社會具有強烈的西化傾向,然而東方式的生活才是詩人所向往與贊美的,因為詩人的根在大陸,根在故鄉,根在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傘”、“紅玉米”、“鹽”、“乞丐”等等意象的呈現都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詩人為了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思想而有意為之,表明這樣的意象已經深深地印入詩人自我的生命之中。雖然痖弦的詩中有許多西方意象的出現,希臘、巴黎、芝加哥這樣的西方都市意象也有許多的出現,然而不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意象,它們都出自于一個東方詩人的筆下,具有東方的氣息與風味。一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眼中的西方自然及文化,與西方詩人筆下的西方顯然是不一樣的。就是在那些運用現代主義手法的詩作里,也同樣是如此。
第三,綜合運用西方現代主義手法。痖弦詩里有著明顯的現代主義傾向,與他早年學習里爾克的詩密不可分;痖弦還吸收了意識流、黑色幽默、自由聯想等西方技巧以創作自己的詩歌。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壇,西方各式現代主義思想潮流迅速流入,詩人們也樂于試用各種藝術手法。痖弦之所以能夠從那個時代脫穎而出,與靈活巧妙地運用西方現代文學資源密切相關。在《瓶》中,詩人開始說“瓶”是一種象征,因為“我的熱情已隨著人間的風雪冷掉”,然而詩人筆鋒一轉,“龜裂”卻導致了冬季的“迸破”,就是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將“瓶”與“冰”的裂紋化為一體,象征與自由聯想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在《傘》中,意象單調而反復,思維毫無邏輯可言,然而神經質一般的喃喃自語,卻把詩人心中憂悶情緒完美地展示了出來。“而吃菠菜是無用的/云的那邊早經證實甚么也沒有/當全部黑暗俯下身來搜索一盞燈/他說他有一個巨大的臉/在晚夜,以繁星組成”(《C教授》)。此詩中的“巨大的臉”“以繁星組成”,就是一種意象的變異與拼貼,產生于詩人的一種感覺,在“繁星”中得到了全部的保存與強有力的表達。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藝術技巧上,痖弦的詩歌最大限度地吸收了西方現代派詩歌藝術的營養,像反諷、嘲弄、戲仿、拼貼等,在其詩中是大量的存在,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第四,具有高度音樂性的語言。痖弦采取的是親近百姓日常生活,同時有著中國傳統抒情格調的語言;當其與濃郁的憂思結合時,便產生了一種哀婉的情調。即使是在批判社會與反諷現實的時候,也同樣是如此。在《從感覺出發》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他們昨夕的私語/如妖蛇吃花”,“一株苦梨的呼吸/穿過蒙黑紗的鼓點”,“節骨木依然,叢生著青苔/那莖草依然空搖著夜色”;在《芝加哥》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自廣告牌上采雛菊”,“當秋天所有的美被電解”,“恰如一只昏眩于煤屑中的蝴蝶”。這些富有音樂感的語言,貌似柔弱,實則有一種反抗現實的強大力量,印證了“以柔克剛”的道理。詩人也很注重詞語的選擇,那些重章疊句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誰在遠方哭泣/為什么那么傷心呀!”(《歌》)在詩中的每一節都出現一次,并且貫穿首尾,特定的問句讓讀者更加注意到傷心的原因“那是昔日”、“明日”、“戀”和“死”,哲理意味得到了加強。《深淵》中的句子,也許是其所有詩中最長的,仍然做到了精確而精致,如這樣的詩句:“生存是風,生存是打谷場的聲音,生存是,向她們——愛被人胳肢的——倒出整個夏季的欲望;在夜晚床在各處深深陷落。”詩人用了三個形象化的比喻來闡釋生存是什么,依次擴充、豐滿和立體化,由“風”——“聲音”——“欲望”——“陷落”的線型細化,精到而準確,更是讓讀者回味無窮。音樂性并不只是語言的問題,而是中西詩歌藝術共有的特征,只是表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痖弦的詩顯然是現代詩,因此其語言也就是標準的現代白話語言,而不是古典的文言文,然而它同樣具有古典語言的精致與文氣,也有西式語言的自由與開闊,在音樂性的構成上實現了兩者的統一。比如那樣一種反復的句式,由短句拼成的長句,將長句切成好幾個短句,以及自然的韻腳,大致相等的節奏,都是自有其審美意義的。“去年的雪可曾記得那些粗暴的腳印?上帝/當一個嬰兒用渺茫的凄啼詛咒臍帶/當明年他蒙著臉穿過圣母院/向那并不給他甚么的,猥瑣的,床笫的年代”(《巴黎》)。這里的語言清新而純粹,節奏感與語感都很強,不僅適合于閱讀,并且適合于朗誦,音樂感是其基本的構成要素。
3
臺灣現代詩歌,一開始就走著一條與中國大陸并不一樣的道路。以痖弦、洛夫、余光中為代表的一批現代主義詩人,從自我的人生體驗出發,根據自我的生存環境與發展需要,創造了與同時代的中國大陸政治性過強的完全不同的詩歌作品,開創了中國新詩的新道路。他們的詩歌之所以取得了獨立的詩史地位,在于他們與五四新詩傳統存在重要的關聯,同時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相通,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也是從小就開始了閱讀,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一種天然的聯系。切斷自己與傳統的關系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現代的、古典的,民族的、西方的,都是可以在詩人的自我中統一起來的,因為每一個人都得于像一條河一樣的傳統之中。痖弦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憂國憂民的傳統,并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深深的以憂思為主要內容的思想,這種憂思迥異于同時代中國大陸所流行的“戰歌”與“頌歌”,使中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得以延續;另一方面,詩人又最大限度地吸取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與藝術的營養,并在詩歌創作實踐中靈活多變地綜合運用,使得其詩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詩界獨樹一幟。痖弦的詩在七十年代后期傳入中國大陸,對新詩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學術界對痖弦的研究至今不衰,可見他的詩已超越了時代,獲得詩學史的認可;這種認可,源自其詩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實現一種中西合璧的完美理想。痖弦早已擱筆,對此他笑稱自己是“死火山”,是“失敗的作家”,但他投身于編輯、出版事業之后,為文學界發現了更多的詩人與作家。或許其詩存在著“難于理解”、“過于憂傷”等問題,然而,其中國新詩里程碑的位置似乎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