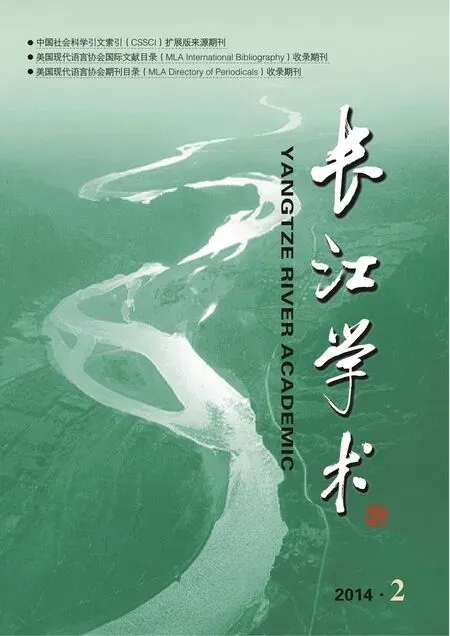《我是你爸爸》的雙重敘述結構
張巖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我是你爸爸》的雙重敘述結構
張巖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在王朔的小說創作中,《我是你爸爸》幾乎是唯一一部沒有引起爭議的作品。究其原因,在于小說透過馬林生這個父親形象的塑造以及他與馬銳父子關系的描寫表現了不同以往的價值意蘊。小說表面延續了自“頑主”系列以來對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否定,實質則是作家在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定文化語境中對傳統、秩序的困境進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凸顯了作家反抗的對象只是出現了問題的秩序。這一雙重敘述結構形成的張力使《我是你爸爸》在王朔小說創作中表現出獨特的風貌。
《我是你爸爸》 雙重敘述結構 馬林生 父子關系
《我是你爸爸》是王朔繼《玩的就是心跳》、《千萬別把我當人》之后創作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刊發在《收獲》1991年第3期上。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單行本,同年收入四卷本《王朔文集》。這部作品既不同于其早期創作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言情小說,也異于《頑主》、《一點正經也沒有》、《玩的就是心跳》等因調侃風格被冠以反文化反傳統之名的爭議性作品。以致參與編寫《我是王朔》的采訪者對王朔坦言,“那個有點看不下去。跟你以前寫的不一樣。我還以為別人寫的發不了,你署名開了個玩笑呢。”當時為數不多的評論文章則給予了正面評價。張新穎認為《我是你爸爸》顯示出王朔創作的明顯變化,“敘述比較嚴謹、講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化思考空間和向度,對于王朔來說,是別樣的人物、場景出現在作品中”。唐小兵頗為認同“小說敘述中所貫徹的一種特性,那就是對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及私人層面的關注,這種關注也許可以說正體現出王朔小說的現代性。”《收獲》編輯程永新在后來的采訪中也強調這部結構、形式都非常簡單的探討父子關系的長篇,“在駕馭和控制方面對作家的考驗比較大”,對王朔“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這部“不像”王朔的作品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爭議,除了以上學者言及的該部作品提供了更為開闊的意義空間,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人物形象和對日常生活經驗的關注從而顯示出新質外,最為關鍵的是王朔在《我是你爸爸》中透過馬林生這個父親形象的塑造以及他與馬銳父子關系的描寫表現了不同以往的價值意蘊。要把握這種改變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小說“審父”、“馴子”這一表層結構,而要深入到小說的深層敘述結構中。
一、父親形象的改寫
父親在文學中從來意義重大。西方學者認為“父親的死亡將使文學失去許多趣味。如果沒有了父親,敘述故事又有什么意義呢?任何故事不都回歸到俄狄浦斯嗎?”中國家國一體文化中,父子關系是建立社會秩序的關鍵環節,所謂“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禮義”,父子在終極意義上打通了“家”和“國”,“忠”和“孝”兩級。中國新文學發展至今,父親形象和父子關系更是成為作家筆下各種隱喻性的價值意義的載體。新時期文學中,眾多父子小說從“審父”視角出發,對父親及其象征的“傳統”、“秩序”、“權威”采取了拒絕、顛覆的立場,其后“弒父”繼而尋找“理想之父”、“精神之父”的變遷都折射出轉型期社會文化語境和作家主體精神的轉變。
但熟悉王朔小說的讀者會發現,很長一段時間父親形象都不是作家關注的對象,或者說王朔筆下的父親很少以主要人物或正面形象出現。即使出現了,也往往成為嘲諷批評的矛頭所向。處女作《等待》中的父親是善良真誠的,在女兒與母親發生沖突時,他向受到“保護性”監視的女兒保證道“你們應該相信爸爸媽媽們,我們會努力使你們——我們的孩子們重新幸福起來的。難道我們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嗎?”《空中小姐》中的父親只是一個少言寡語的普通老人,《頑主》中的父親則是一個穿著摘去領章的軍裝,號召兒子向老山前線的英雄學習的“老頭子”,一個跟不上時代的老人。與《我是你爸爸》同時期發表并引起廣泛影響的《動物兇猛》中的父親雖然是擁有至高權力和強大力量的軍人,但也只是那個年少純情、在對暴力和性的想象與刺激下成長的“我”的叛逆映襯者。對于父子關系的描述也沒有成為王朔小說的重心,父子關系的呈現目的往往是為表現年輕一代受到的壓制及其做出的反抗,調侃嘲諷失去了威嚴的父親。《我是你爸爸》則直面父親形象,著力處理馬氏父子的悲喜劇,呈現了新的變化。
“父親猶如陽光是我們無時不需,有時卻要小心躲避的東西,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母親惟有配偶堪與相提并論,配偶可以選擇而父親則無法選擇。所以,對一個兒子來說父親的問題是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王朔很清楚,對一個成長中的個體來說,作為“他者”的父親的重要性。《我是你爸爸》里,父親走到了前臺,不再隱身于頑主們的背后,既非幽靈般的“潛在的父親”,也不是煥發神圣光彩的“精神之父”、“理想之父”。渴望兒子的馴服之愛而與子發生沖突的馬林生作為中心人物的出現,為我們建立王朔小說中的父親形象譜系提供了參照。
這位父親的失敗似乎又一次佐證了傳統文化的不合時宜,顛覆了傳統倫理價值理念。但與此悖離的是,小說的敘述者沒有像《頑主》中那樣,僅僅站在子輩的視角審視企圖壓制下一代個性成長的父親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也沒有像《動物兇猛》中那樣,將父輩視為子輩自我成長的最大障礙物,以至產生篡弒之心:“我在很長時間內都認為,父親恰逢其時的死亡,可以使我們保持對他的敬意并以最真摯的感情懷念他又不致在擺脫他的影響時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擾,猶如食物的變質可以使我們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強硬撐著吃下去以免擔上了個浪費的罪名。”敘述者采取了靈活的敘述視角,在父親馬林生和兒子馬銳之間交替轉換,將父與子均視作現實生存層面的個體來敘寫,改變了以往父親形象的單一規約性。馬林生雖然懦弱、缺乏行動力量,但不是固守傳統,無恥得以父之名禁錮子輩的父親。對這位“父親”,敘述者給予了更多的憐惜、理解與體諒,呈現出人性的復雜。
二、馬林生的兩重性
《我是你爸爸》的雙重敘述結構集中表現在馬林生這個父親形象的兩重性上。他與之前王朔塑造的父親形象有很大不同。在代際關系上,之前小說中的父親形象是頑主那代人的父輩,馬林生,這位年輕的父親則與王朔筆下的頑主們同屬一代人。他生于50年代中后期,少年時經歷了文革,下鄉插隊返城后先是在街道工廠當工人,后來到書店做售書工作,23歲左右結婚有了兒子馬銳,兒子上小學時,他和妻子離婚,自己帶著孩子生活。但是,馬林生不是頑主,他的父親只是“天橋玩跤兒的”,沒有因家庭出身帶來的社會優越感和日后可以利用的家世背景,他是那個時代北京普通百姓家的兒子和父親,其作為父親的形象及其遭遇因而具有普泛性,賦予小說豐富的文化內涵。
三十來歲的馬林生正是危機四伏:作為書店的售書員,他有著深厚的作家情結,不僅以“老師”自謂,且每晚都會在自己的小天地夜伴孤燈、吞云吐霧,做著文學夢。但是,他從未將最好的文章從自己默默無聞的頭腦輸出付諸筆端。作為離異的單身男士,他有愛慕的女性,她“陽光下飛揚的頭發;明凈如水的眼睛;潔白如貝的牙齒以及清脆、漸漸遠去的笑聲”讓他著迷,這存活于想象中的佳人后來有所依托,具化為少女S,但他不切實際的胡思亂想只是讓他的空虛愈發嚴重。沒有朋友沒有任何寄托的他像抓救命稻草般致力于與兒子的和諧相處,以此填補無聊無趣的人生。父親要做兒子的朋友,建立一種新型的“互相尊重又互相關心同志式”的父子關系。在兒子馬銳的質疑聲中——“會不會亂了套?誰都不管誰了……”——這種中國式的家庭民主實驗開始了。最終,在兒子馬銳理性的主張下——“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兒子,別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實驗以失敗結束。
站在知識精英的立場看,馬林生這個在社會與經濟的重壓下煞費苦心維持形象的知識分子既失去了“獨立的本領和精神”,也缺乏“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對子女根本無法“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面對學校老師的粗暴、自以為是,他嘗試用更加文明人性的方式教育兒子。但當馬銳喊出“我就知道怎么尊重真理……”,權威受到挑戰的馬林生又驚又怕無言以對,面對維護尊嚴的兒子,他像當年自己的父親一樣暴打了馬銳一頓。自以為為兒子好的他試圖讓兒子早點認識社會,把自己理解的人生道理講給他聽:“你傻就傻在不懂得這條做人的基本規則:當權威仍然是權威時,不管他的錯誤多么確鑿,你盡可以腹謗但一定不要千萬不可當面指出。權威出錯猶如重載列車脫軌,除了眼睜睜看著它一頭栽下懸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挽回,所有努力都將是螳臂擋車結果只能是自取滅亡。”這番結論來自于在歷史的荒謬中經受挫折的馬林生的親身體驗,馬林生的真誠,凸顯的只能是傳統對個人的壓制與損毀。這是王朔小說慣有的意旨,但不是馬林生這個人物形象內涵的全部。
猥瑣、自卑、蠻橫、狂暴這些令馬銳痛苦無比的形象只是馬林生的一面。面對新生命帶來的震撼,這位父親曾發下悲壯、決絕的誓言:“我一定要讓這個孩子幸福,哪怕為此我要受盡屈辱,飽嘗痛苦。只要我活著,我就永遠不讓他知道人間有饑餒、苦難和種種不平。我不許,決不讓我曾經受的一切在他身上重演——哪怕為此斷送自己。”王朔讓馬林生在一次酒醉中回憶起了過去,獲得了審視自我的一次機會,認識到那個試圖犧牲自我,對抗現存秩序中的不合理,為孩子營造良好成長環境的父親早已不在。過往只是對其現實人生的否定。“這些年都干嘛了?似乎是一片空白,生活的水流在很遠的過去便停滯、干涸了,延伸過來一直通向今天的記憶只是一條死氣沉沉布滿亂石的河床。”這真切而慘烈的痛感讓他選擇遺忘歷史。失去了連續性的記憶,馬林生也喪失了重建自我的可能。這種逃避無法緩解他的認同危機:馬林生帶上老花鏡,倚靠恍惚曖昧的圖像茍活于世。他努力接受代表著現實生活的齊懷遠之時,象征其“內心深處最隱秘最不為人知的角落”的少女S就幻滅消失了。透過老花鏡模糊的視線,少女S復活了,身邊的一切都變的宜人悅人了。“但每到夜晚,當他摘下眼鏡,躺在被窩里,眼前一團漆黑,他便又跌落回往日的沮喪和無望的深淵,感到一種更大的空虛和不安緊緊攫住了他。在黑暗中白天的一切清楚地浮現,猶如一覺醒來夢境依然縈回,那荒唐的情景、奇特的人物、不合邏輯的擔憂和恐懼一目了然,夢中的輝煌與瑰麗同時也頹然跌得粉碎。”
不乏理想主義色彩的過去滋生著今天的悔恨和對未來的恐懼。馬林生痛苦掙扎存活于兩個分裂的世界,現實世界中清醒的他無法面對自己過去奉行的那套價值標準繼續生活;于是“完全龜縮隱藏在眼鏡后面”虛幻而美好的世界,維系著作父親的尊嚴,也維系著對愛情的最后持守。如何理解生活在20世紀80、90年代之交的馬林生的這種痛苦?他對自己的處境自己的行為有清醒的認知,但無法做出改變,或者試圖改變卻在權衡利弊后選擇了退守。即使行動了,卻因方法觀念的問題而導向必然的失敗。正如前面所言,馬林生的人生遭際具有普泛性,探究造成這種逃避現實的深層原因才能真正理解馬林生的兩重性。
小說巧妙選擇了第11屆亞運會做背景,對了解馬林生人生的關節點或者說那一代人的人生歷程提供了可能。1990年亞運會在北京的成功召開,是以充分調動喚起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參與重大公共事件的慣性為前提的。亞運會準備期間,“對巨大事物的關懷使得人們變得友愛了”。《我是你爸爸》不無調侃地描述了舉國上下在這一時段的同心同德和精神面貌的煥然一新。在國際性的體育運動盛會中,中國人再次體驗了有如革命運動帶來的狂歡化的沖擊,馬林生與馬銳的關系也是在這種氛圍中達到了最大的和諧。一年前,在同樣的城市,曾經發生過一場影響深遠的風波。它與文革后期的理想主義革命教育和激進運動,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全國性的重大思想事件一起積淀生成了馬林生這代人的共同記憶與情緒,促生了馬林生式的中國父親。他們是信仰不斷被打碎重建,無法在當下生活中安置自己的身心和人生意義,最終歸于虛無的一代。信仰從這代人的生命中消逝,被埋藏在意識的深處,再也不能重生。馬林生們的痛苦正是對虛無的高度敏感但無法沖決的絕望造成的。
小說通過塑造馬林生這個生活在當代中國的父親,展現了“父親”這個符號之下父親形象的豐富性。并借助日常性的生活經驗展現了1990年代中國轉型時期理想與現實的尖銳沖突中社會普遍存在的無力感這一景觀,突破了拒絕一切否定一切的價值立場。
三、“民主”實驗的破產
《我是你爸爸》共十八章,就“審父”、“馴子”的表層結構來講,第一章至第五章講述的馬氏父子的日常生活狀態,已經充分實現了對父輩及其代表的秩序的審視與批判。但從小說的深層結構看,故事的真正開始是第六章,即馬林生為改善父子關系,在攜兒子馬銳去公園游玩時提出實行家庭民主這一情節的出現。“民主”實驗的起源可以說是來自兒子馬銳對父親的反抗,這種反抗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父子關系的平衡,從而激發了馬林生對父子關系的重視以至希冀,于是采取另一種“馴子”方式。至此,馬氏父子的關系進入了非常規的“民主”實驗階段。馬林生試圖用朋友之誼取代父子之名,具體生動地用兩國關系和西方父子關系比附他設想的與馬銳的新關系。這種牽強附會的打比方本身就預示了這一實驗失敗的前景。
從第十二章開始,馬林生與馬銳的“和平共處”結束,父子沖突加劇升級。此后,馬林生不僅翻查兒子的衣物、抽屜、日記,而且還聯合不知尊重為何物的老師劉桂珍管教馬銳,致使父子二人爭吵幾乎以武力相見。在第十四章插入馬林生的回憶,搭建了這位父親的自我發現之路,用過去的事件為他的自我實現提供了可能性。隨后的章節講述馬林生無法承受改變的重負決意對兒子放手,馬銳面對父親的缺席被迫加速成熟,以至憑一己之力應對胡同小流氓的堵截,最終住院導致母親許娟訴諸法律爭奪其撫養權。小說以兒子馬銳回到父親身邊結尾,一切似乎歸于平靜。
有學者就該小說的形式提出王朔采用循環結構來強化反傳統主題的觀點,即“《我是你爸爸》重現了這種人生的悲劇,它像是人類代際循環的一則寓言:馬林生飽受父親的粗暴教育(完成了的文化閹割);馬林生發誓讓自己的兒子幸福(反抗),馬林生重復父親原來的教育方式(文化閹割),馬銳像馬林生一樣有了反抗欲望(反抗),馬銳重歸傳統的秩序(完成文化閹割)。”這種認識有其合理之處。馬林生作為一個傳統的踐履者自不必說,馬銳對“父親”角色的權威的認同也隨處可見:對父親要做自己的朋友的恐慌;用父親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來勸導父親做回成人做回“父親”;對馬林生這個父親的內質的失望。由是觀之,馬銳對馬林生的反抗并非對父親權威的徹底反抗,反抗之前他已部分接受了傳統對他的閹割,所以他渴求的不是無父,而是一位值得他尊敬的有權威的父親。但還應該看到:馬銳的反抗中除了對父親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成規的認同以至自我內化的趨勢,還包涵因為對所謂“權威”的虛偽的認識而偏離自我“閹割”軌跡的可能性。而馬林生作為成長中的生命個體的再次覺醒和掙扎也多少顯示了其對“父親”角色的藩籬突圍的嘗試。由此,王朔筆下的“父子”不只是符號化的抽象的“父子”,還是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的“父子”。
所以,作為父親的馬林生可以冷笑著說:“從你記事那天起,我就沒過一天像樣兒的日子,沒一天不勒著自己的,生怕給你留個壞印象。我哪是為自己活著的呀?我凈盡責任了。你沒想到我是這么個人,那是我把自個扭曲了!你大概都沒想到我是個人吧……”“是啊,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呀?不過是一個父親,一個符號。饑了渴了向我伸手,有麻煩有困難我就得替你解決,不管什么問題我都得有求必應。我既是你的寶葫蘆又是你的萬能鑰匙還得寬仁體貼毫無怨言,否則就是禽獸不如,喪失人倫,法律也得制裁?”當父親哭訴為了兒子所做出的犧牲奉獻而兒子卻不知感恩回報時,馬銳會大聲質問父親:“你生我養我不是放長線釣大魚吧?……不是像資本家到咱們國家來投資老百姓到銀行去存錢或者去保險公司投保想著總有一天能撈本再大大賺上一票吧?”
小說不斷通過“民主”實驗中父子的沖突打破讀者對父子角色的慣常認知,王朔關于傳統倫理對人的影響的認識之深可見一斑。“民主”實驗成為馬林生和馬銳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也成為王朔探討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建立新型父子關系的可能。小說對于傳統、文化成規等的批判與反省集中表現于此。但是王朔“民主”實驗的設置同樣說明了等級秩序對家庭的重要作用,這種認識不乏社會學、精神分析學的佐證。
費孝通曾說:“在一個撫育是父母的責任的社會中,父母就得代表社會來征服孩子不合于社會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會的沖突一化而為施教者和被教者之間的沖突,再化而為親子間的沖突。這是我認為家庭三角里親子間第一個可能發生摩擦的根源。”父母與孩子的沖突不單單是個體間的沖突,在精神分析學理論看來,父親象征著法律和家庭的秩序,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起著制約的作用。也就是說,父親與兒子在家庭中處在等級秩序的不同位置,朋友間的平等、民主在父子關系中不具合法性。否則,家庭秩序無以為繼,只會趨于分裂。
所以,小說設置馬林生試圖放棄“父親之名”實現“父子平等”與兒子和諧相處之際作為小說真正的開端是有其深意的。設想馬林生繼續維持之前的父親形象,那么馬銳只可能是新時代中的又一個馬林生,小說在反傳統的同時只可能是一個落入俗套的人類代際悲劇的寓言。馬林生從被動假裝放棄父親的權威到真正從父親的位置上退出,以及相應的馬銳的反應都說明的是父子秩序的重要性,即“父父”、“子子”的合法性。用王朔自己的話說:“放棄了責任的父親并沒能使家庭出現其樂融融、相親相愛的局面,反倒使我們看到了事物更本質更可怕的另一面:那就是一旦在任何人與人的關系中失去制約悲劇的發生便不可避免,哪怕是具有強大親情力量的父子間也同樣如此……垂直關系中只有承認等級才能融洽相處,如同男女關系中只有承認差別才能真正做到平等。”
從這個層面看,“民主”實驗的破產是必然的,這也是王朔不可能在這部小說中建構所謂新的理想型的父子關系的關鍵原因。王朔反抗的只是出現了問題的秩序,他本人依舊是將父與子、男與女設置在二元結構中的兩端,打破了這個結構只能是混亂、無序。
四、結語
簡單來看,《我是你爸爸》講述的是現代社會父子關系的故事。王朔將這對父子的周邊清理的很干凈,單親家庭,馬林生與前妻再無感情糾葛,他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也就是說一位中年男性可能具有的多重身份(兒子、兄弟、丈夫及父親等)在馬林生這里只有一重,父子沖突一旦激化很難再有相關因素可以使之緩和。但隨著父子二人對對方認識的加深,即使面對馬林生這樣一位不合格甚至可以說糟糕的父親,已漸形成獨立個體意識的馬銳,這個14歲的少年,認同“盡孝”是子輩的義務,愿意以裝小孩、服人管來滿足父母。對于這樣一位從精神上反叛父母、老師的權威的少年,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絕不愿意再次讓老師和父親的權威干涉他的思想和行為。所以,從某種角度講,父子沖突的解決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這個代表未來充滿現代意識的孩子的適應能力。
與王朔之前小說中對父子沖突的處理相比較,《我是你爸爸》表現了更多的溫情。無論從父親還是兒子的立場看,傳統倫理都在束縛壓抑著他們的意志和個性的發展。但馬銳的解決方式不是與之決裂徹底打破,而是承認它的合理部分,傳承了“孝道”。也是在這個層面上,《我是你爸爸》一改對傳統文化或社會秩序的極端調侃,著意表現普通人日常瑣碎生活中的煩惱和欲望以及無奈和無助。從表層結構看,馬氏父子家庭民主實驗的失敗在消解、顛覆馬林生的父親身份,否定父輩文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深層結構則是王朔在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定文化語境中對傳統對秩序的困境進行的一次深刻反思:表現與“頑主”一樣被“革命歷史傳統”締造的馬林生這一代人岌岌可危的現實生存狀態和價值存在狀態——潛意識中對傳統、秩序不滿,但又無力打破重建;馬銳這代人的自我成長道路阻力重重,他們需要突破父輩權威的束縛建構獨立自主的個體的能力,需要靈活處理與傳統、秩序的關系的能力。這一雙重敘述結構形成的張力使《我是你爸爸》在王朔小說中表現出獨特的風貌,是作家對其模式化創作的突破。
但王朔對這部小說的態度頗為曖昧。在1992年接受采訪時承認這部作品是他最深沉的一部,是他“用最大的真摯,最大的深情”寫作的開端,自此“為了扳調侃的毛病,哪怕犧牲了那些我招來的讀者也在所不惜。”同時又是唯一一部從概念出發的作品,“純屬的從概念到概念”,不像“《玩的就是心跳》,《頑主》那種,是生活的,是從生活中呱呱割下來的一塊肉,那是真的。”1995年在《王朔文集自序》中他再次否定了《我是你爸爸》,“所有細節:行為動作、人物對話統統是為了最終的揭示,如修萬里長城。”
可以見出,《我是你爸爸》的出現確實與王朔創作策略的調整有關,王朔所認為的“深沉”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深度”,即作品的思想性。這也是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其作品備受指責的一點。《我是你爸爸》無疑是有深度的,突出表現在小說雙重敘述結構取得的效果上。但“最大的真摯”與“最大的深情”有夸張之嫌,小說中某些太過的對話確實造成了沉悶之感,以至有人“感覺還是要硬著頭皮才能讀下去”。《我是你爸爸》可以看作王朔對評論界批評的一個回應,自我褒貶之間顯示的是那時作者的創作狀態以及不同的創作追求,這與后來的創作危機并無直接關聯。
TheStructureofDoubleNarrationinIAmYourFather
ZhangYan
(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mongWangShuo’swritings,IAmYourFatherisalmosttheonlyoneworkwithoutcontroversy.Thereasonlies inthevalueofdifferentimplicationsinthenovelthroughcharacterizationofthefather,馬林生(MaLinsheng),anddescriptionoffather-childrelationship.Onthesurface,thenovelcontinuesdenyingtraditionalcultureandsocialorderasWangShuo usedtodoinhisseriesofTheTroubleShooters.Inessence,thewritermakesdeepintrospectiononthedilemmaoftradition andorderinaspecificculturalcontextoftheChinesesocialtransformationinthe1990s,whichhighlightsthatwhatthewriter opposesisjusttheorderwithproblems.Thistensionformedbystructureofdoublenarrationmakestheworkstylistically unique.
IAmYourFather;StructureofDoubleNarration;MaLinsheng;Father-childRelationship
責任編輯:蕭映
張巖(1978—),女,山東即墨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