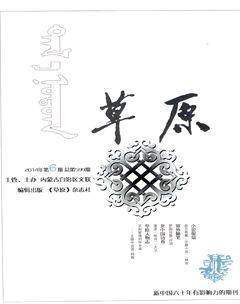不知疲倦的懷鄉者
訪談人物:王建中,男,漢族,1967年出生于內蒙古準格爾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內蒙古準格爾旗政協科教文史委員會主任。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其小說曾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散文選刊》、《新華文摘》等選刊轉載,并入選年度選本。其中在《草原》刊發的短篇小說《準格爾女人》被《小說月報》轉載,《四牌樓》被《小說選刊》轉載。電影劇本有《舂米的女人》、《遍地清泉》等。著有小說集《風中歌謠》、《往米年》、《最后一個漢奸》、《第三十七計》,散文集《漫瀚長歌》、《賀勒德蘇默秘事》、《蒙情第一案》、《你死我活》等。短篇小說《遍地風情》獲第十屆內蒙古“索龍嘎”文學獎。
由于深厚的故土情結,對原鄉文化與精神基因的執著探尋與挖掘,王建中被譽為“準格爾的歌者”。
阿霞:在進行這次訪談之前,我從其他途徑了解過你的一些情況。大約是1994年你曾經參加過《草原》舉辦的一個寫作培訓班,后來看資料,你好像正是從那個時期走上文壇的。
王建中:是的,1994年《草原》舉辦了一期培訓班,都是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我有幸成為這個班上的學員。后來和這個班上的老師和學員都成為了好朋友。在這個班上,我完成了兩篇自己認為很重要的小說,一篇是《走月亮》,另一篇是《一林雪》。后來,《草原》都以頭條的位置隆重推出,并配發了評論,由此可以看到《草原》不遺余力推出新人的力度。以后好多年再也沒有遇到類似的培訓班。現在還很懷念那段日子,懷念那種氛圍,懷念朋友。
阿霞:具體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是什么促發了你的寫作興趣?
王建中:最早發表作品是在1986年。這個小說是高中時在不喜歡的數學課堂上寫的。題目叫《遠方的風》,寫了一匹馬在新時期的際遇,編輯在編發這篇小說時,覺得它的寫法比較特殊,把它編在一個名叫“怪味豆”的欄目下。至今,這篇小說在我的創作中也是一個異數。不知道當時為什么會這么寫。小說發表后,好多人問我,這是什么寫法?你想表達什么意思?
促使一個人寫作的理由和動機可能很多,對我來說,可能是寂寞與孤獨。當時讀了一些文學作品,有寫作的沖動,對當時的一些作品也不敢茍同,經常和朋友們在一起對一些作品說長道短,于是有人就說,你說人家的不好,那你寫一個出來看看。于是就偷偷寫了起來,題目叫《小河彎彎》,是以故鄉的一條河為背景,寫了一對青年男女沖破阻力,艱難戀愛,又無奈分手的酸楚愛情。完成后草草抄寫出來,有兩萬多字。然后又修改了一遍,謄寫清晰后,好長一段時間不知往哪里寄,也不敢拿出來。于是就放在學校的抽屜里。稿子是我的一個女同學幫我謄寫的,她的字好。于是,就先在一些同學中傳看,好多同學都傳是以“誰誰”為原型寫的,于是就引起了同學的好奇,紛紛傳看。后來,另一個班的同學拿去看。在課堂上看時被老師發現給沒收了,以后就找不見了,至今都覺得很可惜,但當時不敢去和老師要。參加工作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當時沒收我“作品”的那位老師提起,她根本不記得這回事兒,這使我有一種莫名的難過。當時同學們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動力,于是就又寫了《遠方的風》,發表后給了我極大的信心。
阿霞: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記得你的短篇小說《準格爾女人》在《草原》發表后,很快被《小說月報》轉載,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你開始受到關注。
王建中:1994年第6期的《草原》發了我兩個短篇小說,題為《準格爾女人》,路遠先生為這兩篇小說寫了精彩的評論。當時是作為《草原》的頭條小說推出的,小說一發表,就獲得一些好評。《小說月報》很快予以轉載。后來小說被多個選本收入。《小說選刊》復刊后,將它評為1994年的重要作品。雷達、白燁主編的《世紀末中國短篇小說精粹》一書收入了它,產生了一些影響。
《準格爾女人》被轉載后,有一些刊物開始約稿。但一些刊物收到稿子后,總是期望寫一個像準格爾女人那樣的故事,甚至可以寫些“葷”故事。這時我才發現,寫作中,總是有各種各樣世俗的力量想左右你,這個力量很強大,也很有誘惑力。有時它是和利益、榮譽裹挾著一起向你襲來。是白雪林先生及時提醒了我。于是我開始思考自己該寫什么的問題。我覺得不僅要看一個作家寫什么而更要看他不寫什么。這個很能看出一個作家的水準、性情和品格。
這里有兩個故事:一是《準格爾女人》發表后,有一天,領導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大發雷霆,好一頓訓斥后我才知道,有一個女人找到我們單位來,跑到領導那里,說我的小說侵犯了她的隱私,要領導教育教育我。領導告訴我以后不要惹這些麻煩了,否則的話你以后還怎么進步!另一個是小說《鄰居》發表后,一個有和小說類似經歷的女人來我們單位偷偷看我。說實在話,我的這個小說借用了她的故事。看完后,她大概覺得我還是可以信任的,就找了個下班的時間,在我們單位門口等我,然后告訴我哪句話她沒有說過,哪件事她沒有做過。把我的同事都說得哈哈大笑起來。后來,刊載這篇小說的雜志,她一個人就問我要過19本。有一回我偶然從她家門前經過,她正在喂豬,于是她就大聲喚她的新丈夫出來,很高興地把我介紹給她的丈夫。這是我寫小說的兩個有趣的插曲。
《一林雪》發表后,一位安徽讀者黃玉坤給我來信,說我的作品“充滿水汽,濕漉漉的,有江南小鎮的柔美與恬淡,人物與故事又具有傳奇性,語言頗有話本遺風。”最后,他猜我可能是“從江南移居北方的,至少祖上應該有南人血脈,而且年歲不輕了,因為作品是有風霜感的……”這時我想這可能就是人們所說的受到關注了罷。
阿霞:“準格爾”似乎是你的一個系列題材,很多年來,你一直在寫。從什么時候開始著眼于這個系列題材的?以后還會繼續這一題材的創作嗎?
王建中:準格爾是我的故鄉,有人稱我為“準格爾的歌者”。在所有的稱贊中,我最樂意接受這個稱謂。
其實每一個作家在寫作時,總有一個故鄉的背景與影子。這個系列是在1994年開始的,最初是一種自省,現在是一種自覺,不是偶然的。這個創作始于《準格爾女人》,先后寫了10個人物,是對故鄉女性的一種敬意與愛意激發了我的寫作熱情。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娶一個準格爾女人做老婆,是準格爾男人的福,天下男人的夢。現在,我依然持這個觀點。endprint
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塊產生偉大故事的土地。隨便舉幾個歷史片段,比如說胡服騎射、單于爭位、匈奴漢國、孟姜女哭長城、昭君出塞、文姬歸漢、木蘭從軍等等都與這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新秦中就是以準格爾為中心的歷史地理所在,秦直道的修建與廢棄也與準格爾有呼應;中國歷史上有兩個著名的誠信故事,都發生在這塊土地上;勝州城是隋唐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州城之一,隋朝建制的設立,大唐的繁盛,都在這片土地上演繹過精彩紛呈的故事,隋煬帝、康熙的安邦治國之策也與這片土地有行動上的大呼應;便是唐詩的吐納在這里也綿延不絕,中國歷史上頂級的大詩人不僅把詩作留在了這片土地上,而且把人生的沉浮也與這片土地緊密地聯系起來;榆關是邊塞詩的象征,也是文化地理上的重要關隘,重要的歷史人物你方唱罷他又登場……各個歷史時期,這里是著名的榷場。許多民族在這片土地此消彼長,風云際會;便是在地理上,她也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位置上。早在秦漢時期,這里森林茂密、湖泊遍地、阡陌縱橫,到處生長著茂密的竹林……這里還是“河套人”的故居,參與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性設計與積累;依傍著黃河草原,農耕與游牧文化進行著大碰撞、大融合、大奔涌,不斷塑造和改寫著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文明幾個重要的精神意象,比如黃河、黃土、長城都集中到了這片土地上,甚至出現了意象的交叉與重疊,足以大書特書。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眾多的文化描述中,準格爾會呈現出另外一種樣子。這里有可能成為我們共同的精神故鄉,也極有可能被我們塑造成心上鄉土……
一個寫作者,要想把自己的“鄉土”延展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地理坐標,我覺得還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足夠的精神成長的高度,二是有廣闊的靈魂生長的寬度,三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積累的人文深度。準格爾為我提供了足夠飛翔的天空與大地,所缺少的是一顆足夠強健的心靈去感知她,捕捉她,描摹她,提升她,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為此,我會不懈地努力,并且一如既往地表達我對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
阿霞:其實不用細究,就可以發現你的小說寫的都是鄉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作家在從事寫作后,大都會選擇離開故土到一個更大的城市去,比如各省的首府或北京、廣州之類的大城市,而你一直生活在準格爾。你是一個有鄉村情結的作家嗎?
王建中:我們常常感嘆生活在遠鄉、遠地。作家到什么地方生活很重要,這個被古今中外的許多作家的創作所證實。我個人認為,學者居住在小城市最好,因為大城市的繁雜會無端地消耗他的創造力。但這個理由經不住時間的淘洗。迄今為止,文明的最大創造和成果依然還誕生在大城市。這可能是個悖論,但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至于作家,遠離有時候是一種意外的審美觀照與審視。關于這個現象有很多論著,好像并無定論,不同的作家也有不同的選擇。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文化與哲學現象。記得幾年前有過一個地域與作家創作的討論,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你說的這個意思。
地理上,準格爾確實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我認為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文化的支點。有了這個點,也就擁有了無限廣闊的精神的疆域。這個疆域,足夠我鋪展開有限的情智,去完成一次次遠足。
鄉村情結是一個哲學命題,許多生活在都市的作家也有這個情結。這在創作上屬于一種情感歸宿,甚至是一種精神歸宿。這個情感歸宿不僅僅屬于作家、藝術家,也屬于哲學家、科學家以及很多領域的專家學者,還屬于普通人。
我是鄉村情結很重的人,但這和生活在城市或鄉村沒有太大的關聯。這個情結可以生發出許多人文、哲學的命題。而且在各個時代、各個生活層面始終都生生不息。鄉土和城市都可以是情感和精神的歸宿,也可以是現實選擇。作家始終以作品說話,關鍵不是你在哪里生活,而是你發出了什么聲音。當然,在哪里生活一定會與你的作品產生某種深刻的聯系,這個聯系是你與社會之間的大通道。不同的選擇,最終會引導你走向一個不同的結果。這是相輔相成的。所有這一切,都不足以成為我生活在準格爾的理由。
一個人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說選擇在什么地方生活,有很多因素。特別是有很多非愿望和人力所能左右的因素在主導著你,那么,創作與生活孰重孰輕,哪個影響了哪個,這是不言而喻的。這里我想說明一個觀點,曾經一個時期,中國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出身與出生地的不公平。它幾乎可以限定、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你一出生,仿佛你的命運就被左右了,安排了,要想擺脫這個命運,真是難上加難!路遙《人生》的悲劇意味就是由此生發的。
一個人和廣闊的鄉土能深入接觸,時間久了,就可以獲得一種大寧靜,可以使你從容不迫、天馬行空,但因為限制,也容易使人沉淪,小農意識有所泛化。
阿霞:很多人評價你的小說集《往米年》像一幅唯美的晉陜蒙風情畫卷。這部小說集收錄的十幾篇小說,每個故事每個人物都充滿了濃郁的晉陜蒙的世態情狀。為什么給小說集起這樣一個奇怪的書名?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你說《往米年》是送給你的祖母的,這是什么意思?
王建中:《往米年》出版后帶給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它居然印了兩版,并且發到了國外。原先我以為這樣的小說可能讀者會很少。而且我在寫作時是有讀者對象的預設的,但它超出了我的預設與認識。
“往米年”是故鄉對遠年的一種稱謂。書出來后,很多朋友對此不理解。有一位澳大利亞的學者把它理解為“沒有余糧的歲月”。還有很多朋友給它正名:“往彌年”、“往覓年”、“往每年”不一而足,都沒有“往米年”傳達的字意好。這是對地域方言的一次規范整理和超越。在書前我曾寫了一段話來闡釋“往米年”,我覺得這是一種情結,這個情結在這里可以解讀為舊鄉與遠年。往米年也是一首詩,是我和故鄉共同完成的。
“給祖母”,是我寫在扉頁上的一句話,因為我發現,祖母是對我寫作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她幫我建立了一個想象的世界,也給了我一個幻想的童年。童年的很多往事后來都進入了我的文字。祖母在幫我建立想象的世界時,也潛移默化影響了我待人接物的方式,確立了我與社會相處的關系,形成了我的性格,甚至確立了我的道德觀。祖母應該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許多年后,我才認識到祖母是個具有非凡想象力與虛構力的人。也是后來我才明白,祖母給我描摹的那個她生活的年代與世界,已然經過了她的“藝術”過濾,這個過濾是清水漂洗的過程,漂洗后的這個世界是純凈的、樸素的,但又充滿了精神的向往與自由,是個生長故事和童謠的世界。那些被水洗過的日子,只要祖母愿意,就會隨時開出燦爛的花朵來。這確立了我的世界觀和文學觀。祖母的內心是溫暖與寂寞并存的,這也成了我小說的基調。隨著閱歷的增長,我開始體會祖母在生活重壓下,始終葆有的那顆被善良包裹的柔軟的心。有時,我覺得她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她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祖母始終對生活保持著積極的態度。現實世界對她的擠壓,始終沒有奪去她樸素的生活信仰。由此我也悟到,祖母在給我講述這些故事時,其實她是在創作,我只是她的聽眾,她一直徜徉在她的世界里,那時的祖母一定是幸福的。但她沒想到,我的想象力也會在她的講述中慢慢成長起來。祖母雖然沒有文化,但她敬重文化。我日后留下的只言片語的紙張,她都精心保存起來。她的這個習慣,意外地為我保存下我少年時代寫的一部短劇,這是祖母留給我的最珍貴的禮物。而《往米年》是我送給祖母的一份禮物,一份遲到的禮物。endprint
阿霞:原《人民文學》主編、著名詩人韓作榮對你的小說有很高的評價,這是怎么回事?你和文壇還有什么樣的交往?
王建中:韓作榮先生我不認識,而且至今也未謀過面。韓先生是當代重量級的詩人。我的小說他是在一次研討會上讀到的,韓先生撰文給予熱情的肯定。同時參加研討的評論家朱秉龍先生也給了很高的評價。先后有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的讀者和評論家給了這些文字熱情的肯定,這使我倍感溫暖。我始終相信,文壇是寬闊、包容、豁達的。有一次偶然和梁曉聲先生相遇,他說過一句話——“面向文學,背向文壇”,這句話影響了我,也無形中為我確立了我與文壇的關系。
阿霞:有一年你好像去了魯迅文學院學習。那一段經歷對你來說有什么特別的體驗或收獲嗎?
王建中:1994年,《準格爾女人》發表后引起了爭議。當時《草原》的主編丁茂先生、副主編白雪林、編輯路遠,都以不同的方式鼓勵和支持了我。正好魯迅文學院給了內蒙古兩個進修名額,丁老師便建議我去魯院學習。于是在文聯和宣傳部的推薦下我就去了。那段生活很新奇,魯院獨特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形式至今記憶猶新。
知識改變命運,學習改變性格。在到魯迅文學院學習前,我一直生活在鄉鎮。奇怪的是,到魯迅文學院前,我幾乎沒有很好地寫過鄉鎮,這從我的創作經歷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到魯迅文學院后,我寫了一系列關于鄉鎮的作品,似乎也是在魯迅文學院,完成了文學觀念上的一次遠足。很多同學都說魯迅文學院是個大熔爐,在這個熔爐里,有的人脫胎換骨了,有的人卻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我到魯迅文學院是接受教育的。教育不僅僅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陶冶人格、人性、仁心的必由之路。毫不諱言,我是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開始的,在本意上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也有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品行端正的文化人的愿望。我很慶幸,在人格、文學存廢之間的十字路口,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行。魯迅文學院富有彈性的教學方式營造出一種醉人心脾的學習氣氛,這種氣氛,比書本和課程本身更能熏陶人、感染人、啟發人、鼓勵人,這是其他教學所不能給予你的。為此,我要感謝文學,感謝魯迅文學院。
阿霞:在具體寫作活動中,你對自己會有什么樣的要求嗎?題材與手法或者說“寫什么與怎么寫”,哪一個對你更重要?
王建中:創作和做人一樣,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脫離低級趣味。創作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挖掘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你會覺得有很多領域你還沒有開發,因此你會珍惜。
題材與手法是相輔相成的,藝術與人生也是相輔相成的,寫什么其實決定了怎么寫,這也是相輔相成的。內容決定形式。創作中我更多的是在選擇語言,尋找語感,一旦找到了這些也就找到了突破口。其實在寫下第一個字的時候,你的目標已經確定了,你只是不斷地去接近這個目標。
對一個成熟的寫作者來說,寫什么幾乎是注定的,而怎么寫并不是作家真正的用功點與著力點。我覺得怎么寫是技巧,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寫什么是原則,是方向,是生活的饋贈。重要的是提煉生活、表現思想的能力與達到的高度。
阿霞:你是否也認為寫作是一種體力活?你覺得作家的精神活動在寫作與生活中會有矛盾或沖突嗎?
王建中:寫作肯定是一種體力活兒。這種漫長的精神積累,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用心與用力同樣重要。
愈是優秀的作家,在生活中與社會的矛盾愈是激烈、尖銳,甚至對立,只不過方式與形式不同,但也不是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內心的矛盾與沖突幾乎伴隨著創作的整個過程。這種沖突與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作家的作品風格與精神走向。對立愈是深刻,沖突愈是尖銳,精神體驗也就愈強烈。這個體驗愈是獨特,與眾不同的表達方式也就在這個體驗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找到了、完成了,因為你的體驗是你自己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甚至不能超越。
精神活動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幾乎就是他的行動使命。一個負有使命感的寫作者,在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更多地表現為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之間的落差。這個落差有時候會給創作帶來一種意外的張力。
阿霞:從技術層面講,一個作家應該怎樣處理小說故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虛構是否可以完全脫離現實世界或獨立解決文本的目的?
王建中:作家與生活的關系,是魚與水的關系。小說與現實則是流水與河道的關系。河道決定了流水的走向,但是如果洪水泛濫了,河道就會被沖毀。這樣的失衡我們常常看到,問題是我們既不能降低水流的高度,也不能無節制地增高河道的防護堤。
作家如果只靠生活中的真實去寫作,我覺得也就不成其為作家了。作家應該是一個特別有想象力的人,也是一個特別會虛構的人,還應該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人。沒有智慧的人是成不了小說家的。但小說肯定是虛構的,但這個虛構里的一切都有生活真實的一面,而真實的程度,取決于作家加工生活的本領。
你說的技術,我更愿意理解為駕馭生活的能力和對某種藝術形式的熟練應用。好的作品幾乎看不到技術的痕跡,因為這個技術在創作的過程中被你的心靈其實已經濾掉了。這個技術的最高程度,就是情感與思想的最大程度的釋放。但我們既不能把寫作當作一種技術去修煉,也不能蔑視任何寫作的技術。這個技術幾乎是不可學的,否則我們就可以一批一批地培養出作家和詩人了。
我認為藝術表現中的技術與道德是聯系在一起的,一個道德感很強的寫作者,幾乎不假思索,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表現手段和表現形式,有時候簡直就是信手拈來,而且天衣無縫。這幾乎就是一種先知先覺的能力,仿佛就是與生俱來的。可以說,藝術的技術就是道德的外顯。如果說一個作家寫小說的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那么他的精神道德也一定遙遙領先,非同尋常了。
文本是反映生活的載體,也是藝術創造的形式。文本可能還是生活的鏡子。文本的意義不會低于生活的意義,但也永遠不會大于生活的意義,這是一個作家立言的基本能力。好的文本就是一個鮮活的生命,獨立存在是與生俱來的。endprint
阿霞:你心目中理想的小說應該什么樣的?是否存在好小說與壞小說這樣的說法?
王建中:這個很難說。但好小說肯定有獨特的精神氣息。比如說,寫頌歌卻能把它寫成淡淡的挽歌,寫苦難反而把它寫成了溫婉的人生故事,這也是小說的一種境界。
我心目中的好小說,都有寓言性質。好小說寫到最后都有寓言性。好多小說都能把握它,描述它,再現它,但就是找不到一條通道。這條通道不是直觀的,而是造了一個境、一個場,是一種氣,是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核”連接成一個整體,與這里那里相通。像地氣與脈絡一樣,使小說周身通暢,渾然天成。在這個整體中,個人與人類相通,村莊與世界互換,所謂“環球同此涼熱”就是這個意思。當小說一旦獲得了寓言的品性,它就是詩,是哲學,也是生命。另外,我覺得小說的氣味與氣息也是一個好小說必需的。而這個氣和味是作家通過文字的經營,把作品的意蘊很好地傳達出來的同時,還使小說獲得了一種多義的審美體驗。這還是作家獨特的精神氣質的呈現。這樣的小說,想想都是迷人的。因此說,小說的好與壞,就像生活中的好人和壞人,其實都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阿霞:就目前來說,你對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或小說是哪一部?
王建中:就現在的作品來說,在藝術上都還沒有達到理想的高度和深度。曾經寫過一個劇本,名字叫《山河謠》,這是我迄今為止整個創作過程中最讓人滿意的一次寫作,但它依然距離心目中的好作品有很長一段路。
阿霞:換一個話題,我知道你也寫過很多影視作品,寫影視劇本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考慮?在你看來,影視和小說寫作有什么不同?影視劇本寫作能給你帶來小說寫作的快感嗎?談談你從事影視編劇工作的一些情況和感受。
王建中:其實在寫小說之前,我一直喜歡電影文學,寫了兩部電影劇本,兩個舞臺劇。其中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沒有突破的防線》寄給了北京電影制片廠,意外地得到了編輯回信,編輯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劇作才能,這使我驚喜若狂。當時在學校中這還是個不大不小的事件。教導主任很熱情地把我叫到辦公室,把編輯給我的信看了好幾遍,連我先前的調皮搗蛋也既往不咎了,他鏡片后和藹的目光現在想來還令我動容。另一部舞臺劇叫《楓林渡》,是一部九場的“大戲”,寄給了內蒙古文化廳辦的《北國影劇》,時任編輯吳新秦老師坐客車專程從呼和浩特顛簸一天到準格爾來見我。現在還記得吳老師約我到準格爾賓館見面時的情景。吳老師是個熱情似火、激情洋溢的人,給我做了劇作輔導,晚上又請我吃飯,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吳老師請的。臨走,吳老師還專門見了我父親,向我父親介紹了我的“成就”,希望我父親支持我成為一名劇作家。同年10月,在吳老師的熱情推薦下,我參加了內蒙古戲劇筆會。這次筆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我特別感念吳新秦老師,是他,給了我一次最深情的引導。現在看來,這兩件事對我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來,吳老師知道我寫小說去了,十分可惜,曾經托人帶給我一句話:好好寫,你有這個才能!之后,每當我在寫作遇到困境時,我總是想起吳老師的這句話。借此機會,我想問候一句吳老:你好!
任何一種藝術,都有其遵循的原則與規律。影視文學的繁榮與發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業的繁榮。這為影視藝術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保證。
電視劇在生產過程中,劇本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但它與小說不同,它更多的是一個流程,這決定了它的特性。如果說文學是用來欣賞的,由語言、氣息、情節、故事共同營造了一個場或一種境,那么影視劇本提供的則是藍圖,像施工時的設計圖一樣,是用來構筑樓體的藍本。影視文學劇本與小說最大的不同,我認為是用途上的不同,這種不同也是藝術分野的界限。
小說的藝術手段更豐富,而影視文學則相對單一,但不是簡單。小說在語言的基礎上可以無限自由地想象,而影視受到的限制則很明顯,我把它稱為戴著腳鐐的舞蹈。
影視文學的創作也有快感,這個快感和小說寫作的快感沒有區別。有區別的是這種快感的產生不像小說那么來得率性與優雅。這是我的經驗,任何經驗其實對別人不產生激勵作用,它只是對自己產生效果。
影視在表現生活時,有自己的藝術積累與創造。這種藝術形式更多的是一種綜合手段下的集體創作,以導演為創作核心。我認為它表達生活的手段與深度與其他藝術形式沒有高下之分,只有藝術創造動力之分。
喜歡一種形式,并應用這個形式的技巧去表達自己的發現與思想,這和自己的藝術素養與藝術積累有關,也與表現力有關。形式在任何藝術家手中,最高的境界是所表達的人類情感與智慧所達到的深度與高度。真正配談經驗的那些人,應該是那些開拓并豐富了各類藝術形式的大師,我們只是聒噪而已。
前前后后寫下了十幾部影視劇本。這些作品有些是在很嚴肅的狀態下完成的,有些僅僅是作為一個“任務”完成的,因而看不到鮮活的靈魂,也缺少豐富的內涵,更沒有生動的個性。真正有血肉、有靈魂、有正義、有感情、有冷暖的作品大家都是可以分辨出來的。但這個世界也有很多瞎子,對他們,就只當“讀圖”罷。
影視藝術講究的也是深度與高度的完美融合,我的幾部作品沒有達到這個要求,非常遺憾。
阿霞: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很多作家主要是小說家或多或少的都介入了影視編劇這個行當。但也有很多人對影視劇本的文學性存有質疑,一些嚴肅的作家拒絕寫影視劇本。對此,你怎么看?
王建中:作家用什么樣的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發現與思想,這不僅是創作的自由,其實也是由內容決定的,不完全是一種形式。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很多話題就沒法展開。另外,也跟題材與藝術表現力相關。
影視劇本由藍圖到成品,這個過程是一個豐富的藝術再創作的過程。前面說過,影視劇本是講究用途的,簡潔與繁復是由藝術表現和藝術要求決定的。一張設計藍圖并不需要很多修飾性的細節與華麗的色彩和筆觸,影視劇本的文學性,我理解應該是塑造人物、結構故事、推進情節、營造場景和描摹世態人情的綜合能力。與文學本質上沒有高下之分。對此,大家可能有誤讀。這里的文學性更多的是一種優化的手段與方法,在規定的場景中,用最有效的手段表達最豐富的情節,展現人性、人情。endprint
優秀的作家不一定能寫出優秀的劇本,但一個蹩腳的作家肯定寫不出優秀的劇作。作家的嚴肅與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和思想。
任何一種形式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其中都應該有詩性的流動。那么,這個詩性就是真正的文學性。
影視是一門綜合藝術的匯集與融合。所謂綜合不應簡單地理解為工匠式的拼接與堆砌,盡管有時候也可以操作得很精巧,卻沒有詩意。影視是各門類藝術家極其和諧的藝術創造和獨特貢獻的總和,是一種詩性的重塑與匯合,有了這種詩性的重塑與匯合,影視才會調動音響、詩畫、色彩、造型等等藝術手段,并把各自的手段發揮到極致。這種種極致里當然也包括編劇的生命體驗、人格精神、知識底蘊、藝術感覺、營造語境以及種種藝術積累與修養的呈現。而詩性往往是劇作所散發出來的渾然天成的天籟。我這樣說,誰還能說劇作缺乏文學性?
阿霞:有很長一段時間,寫小說的王建中在大家的視野中消失了。是這樣嗎,干什么去了?
王建中:有一回,我到文研班去看一個朋友,在走廊上聽到兩個學員在談一個作品,最后一句是“這個人不寫小說可惜了!這個人到哪去了?”他們說的是我的小說《一林雪》和《鄰居》。他們對《鄰居》的評價讓我汗顏。他們認為《鄰居》可以和汪曾祺先生的《陳小手》媲美。他們顯然不認識我,我也沒敢說什么,像個賊一樣悄悄溜走了,連朋友也沒敢看。在生活中,一旦獲得了一種身份符號,并且大家認為你是很善此道的,那么大家就會以此來歸攏你,你的不作為可能就會換成別人對你的指責和失望。但生活其實沒有空白,總會有一些東西來填充,對我,這個填充就是換了一種形式。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形式。因為熱愛,也因為你的根扎在這塊土地里,我以為我就有了義務也有了責任,這是你的性格決定的,你的命運也就形成了。這完全是你自己的選擇,不管結果如何,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
2001年12期《草原》以專輯的形式隆重推出了我的一組小說,《小說選刊》很快予以轉載,并入選當年的年度選本。也是在這一年,我的散文創作也開始引起關注,約稿很快多了起來,但也就是這次專輯之后,我幾乎停止了小說創作。可以說,我是在創作狀態最好的時候,離開創作的。很多朋友大惑不解。而且十年來幾乎和文壇斷絕了聯系。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工作發生了變動,直接或間接對創作產生了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工作性質的轉變,我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史整理和出版上;二是在創作形式上發生了轉變,從2002年起我開始介入影視,先后完成了十余部劇作。這個過程大約持續了十年,我覺得這十年來繁雜的事務性的工作,無端地消耗掉了許多時間。它們像一地亂石與雜草,清理它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當然這里也有我自己人生的失誤與選擇的誤區。但這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也是你自己走過的路,理清這一切,也要靠自己,這可能還需要時日,但好在現在可以重新選擇一個起點了。感謝大家對我的關注。
阿霞:談談你的關于漫瀚調和漫翰文化的散文吧。據我所知,這是一個系列散文,你寫了很久,而且篇幅都很長。
王建中:漫瀚調是一種音樂形式,是故鄉的一個地域民間藝術的總稱。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漫瀚調與漫瀚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寫的這組散文總題為《漫瀚長歌》,這組散文是一種文化大散文的構建格局。
漫瀚文化是一個很寬泛的理論概念,在這里,我把它概括為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工業文化的一種總稱。歷史上,中華文化是由幾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構成的,費孝通先生把它稱為“一體多元”的大文化格局。歷史上也有多種文化交融發展,彼此匯聚的事件發生。
比如,秦漢時期的匈奴,我在敘述匈奴文化時,有一篇名為《遠去的兄弟》的文章,匈奴文化對中華文化有特殊貢獻,它在中華文化中的歷史地位有待于進一步強化。再比如,北魏時期,鮮卑政權在取得全國統治地位后,主動放棄自己的文化而尊崇漢文化,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文化融合的繁盛時期,文化上的多元與交融,為北魏王朝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統治動力,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文化多元發展的大格局,促使北魏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盛一時的統一的超級帝國。北魏王朝對中華文化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其實,由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尊崇漢文化的王朝,都是中國歷史上極盛一時的帝國,不一而足。
準格爾是一個特殊的地域,為我們觀察中國歷史文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歷史視角。站在這塊土地上,面向中原,你會感到二十四史所給你的滋養與灌溉。但站在黃河邊的長城線上,向草原瞭望,你又感到二十四史有轟然倒塌的威脅,歷史是以另外一種面貌存在的。每當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甚至停滯不前的時候,北方游牧民族的馬蹄就呼嘯著越過長城線,給農耕文化以強勁的啟迪。從商代到清末,中國文化經歷了一次次血與火的洗禮,文明間的固守與侵入,多民族的融合與統一,構成了整個中華文化演進的主旋律。北方民族文化強悍的草莽之氣,使農耕文化血脈噴張。也可以說是“胡羯之血”一次次的注入,激活了中華文化的勃發之態。
漫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血脈之書。這樣一種構建,應該說是調動了思想與文化積累的一次激情抒寫。為此,準備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它充滿期待。這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內心與氣質。而且,我相信這組文章會產生一種力量。我想這是一種溪水四溢、跌宕漫涌的狀態,一定會有碎裂的飛雪產生。它力求新的觀念和審美取向,我希望它既可以感悟人生,又富有智慧與靈性,同時又具有歷史和文化的批判意識。我希望它具有歷史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有助于再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曲強勁的多民族共同演進的歷史頌歌,它縈繞于山河之間,不絕于耳,讓歷史連同大地一起飛翔。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努力。
阿霞:你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因為很多人和我提到王建中時都會說“他太能折騰了”,我想他們指的是你除了寫作、還搞攝影,拍電影電視、搞旅游項目什么的。
王建中:一個對生活期待相對較高的人,都可能是精力旺盛的。他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多個可能與方向,因為不滿足或者緣于一種責任與熱愛。矯情一點說,是你的血緣決定了你的性格。是你循著你激情的地圖,一路走下來,而這些事物通常又是極其美好的一些東西,至少在你看來,他們是以歌聲和陽光的方式向你靠攏,那么,這幾乎注定了你的命運。我發現,一個有想法、有創意,心中充滿了對家鄉與大地熱愛的人,又有些理想與抱負,那么你不會無動于衷,也就是所謂的折騰吧。endprint
小說是表達發現的一種方式,影視作品也一樣。搞攝影、搞旅游開發,并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想把自己的發現告訴別人。發現的快樂是最大的快樂。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有一種升華,這個升華不去做永遠不會有。這個升華也是相互滋養的,彼此都可能會成長。沉淀后你會發現,你義無反顧,你為它千辛萬苦,甚至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幾乎是你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它和你的認識、你的性格、你的愿望,你對人與社會的理解,糾結在一起,相互滲透,而你的價值可能就隱藏在這其間。因此“折騰”是不由自主,也是不自覺的,回過頭,它是你的歷程,你的人生方式。那么,我相信,其實這種“折騰”幾乎就是你與社會的綜合關系,你在這個關系里獲得了勇氣、信心與力量。
艾青先生有一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無論是蕭紅、沈從文還是汪曾祺,在他們的作品中你總能看到一種血濃于水的感情,對故鄉我也有這種熱愛。因此,很多的“折騰”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是荒煙蔓草還是一地亂石,一切都有待于時間的沉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你的靈魂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你的行為包括你的一切愿望,都可能是你行為的起點,也可能是你行為的終點,那么,這個過程或者說這個結果,你還會在意嗎?
阿霞:接下來會有什么寫作計劃?主要精力放在影視劇創作還是小說寫作上?
王建中:對一個人來說,青年時期是一個發酵期。這個時期,你與什么東西發生反應,這個決定了你的氣質。整個青年時代,我是屬于文學的。感謝文學給予我的滋養,在很多個人生的路口上,它很像燈盞,不僅照亮了我的內心,也照亮了我的生活道路。很多時候,是靠著它取暖,也是以它除去了內心的雜草,搬走了心上的巨石,給你一種向善的力量。
以后會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但會在散文寫作上完成一個系列,這個系列可能大家會覺得陌生。但我相信,這里有泉水,希望它能有一次噴涌。
阿霞:你如何評價今天的內蒙古文學創作?你認為今天的內蒙古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層面上處于怎樣的位置?有哪些你認為優秀的作家或作品?
王建中:內蒙古是一個蘊藏著多種文化與文學資源的大地。這塊土地也是產生文化大師與大作家的地方。我們有很多學者與作家已體現出了這種特質,可是一閃即逝,這是十分可惜的。是什么沒能形成持續的光亮,使其足以照亮自身,也照亮天地?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內蒙古是個多元文化薈萃的地方,這片深厚的土壤適宜參天大樹的成長。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倡導草原文學,也涌現出了很多作家和作品,我個人認為,還沒有出現真正體現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作品。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比如成吉思汗,是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富礦,可我們開拓挖掘得不夠,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表現成吉思汗的作品,還沒有產生一座與成吉思汗遼闊的疆域相媲美的精神高峰。我想,這個現象,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在文學層面上所處的位置有點相似。
盡管我們現在暫時還沒有看到這個高峰,但我相信,一些優秀的種子已經開始發芽,我的前輩們,朋友們,好好捕捉這些發芽的聲音,收集起來,這是我們未來的洪流。我期待這種洪流的雷霆之勢,因為這是內蒙古固有的文化優勢。內蒙古廣闊的山川、河流、草原、沙漠已蘊藉起足夠寬廣的精神疆域,千里縱馬,誰主沉浮,只是個時日了。那么,每一個寫作者都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華與能力。
內蒙古的文學藝術創作相對滯后,我們還沒有產生與內蒙古文化藝術深厚積累相匹配的作品。說到作家與作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高度和尺度在那里。但怎么說,都難免掛一漏萬。在這里我不想面面俱到,同樣也不想閃爍其詞。我覺得冉平先生的《蒙古往事》是內蒙古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收獲,即使放在整個當代文學作品中衡量也不遜色,薩娜是目前內蒙古作家中最勤奮、最多產的敘述者;但我也會永遠記住馮苓植、烏熱爾圖、白雪林、路遠、肖亦農、鄧九剛為代表的作家,是他們使內蒙古的文學創作有了飛翔之態。
阿霞:最后,祝賀你獲得去年的“索龍嘎”文學獎,獲獎的感覺怎么樣?如果讓你對更年輕的一代寫作者給出一些建議,你想說些什么?
王建中:獲獎是一個意外。獲獎可能會使作品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關注,對作品的傳播會起到一個推動作用。對于作者,可能是一種鼓勵與支持。獲獎使自己對創作可能有了一種新的期待,也忽然有了緊迫感。
更年輕的寫作者與我們的文學觀念、文學選擇會有很大不同,他們的表達可能更自由更直接,但不論這個自由與直接有多大,有一點我想是很重要的,讓你的文字變得有意義,有責任,有義務,就一定要有所擔當。不管是對文學還是對社會,勇敢擔當起來,只有擔當起來了,你才會有重量,有內涵,有深度。
我覺得,川端康成先生的一句話說得非常好:明知道寫不好,為什么還要寫呢?因為一切藝術不過是走向成熟的過程。
時間會使一切花朵都燦然綻放。那么這個過程一定是迷人的,否則就不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寫作者前仆后繼地跋涉在這個進程中。
文學的高度與深度和生活密切相關。一切文學藝術形式,最終都是一次精神遠足。我想對年輕的寫作者說:讀書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訓練。
〔責任編輯 楊 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