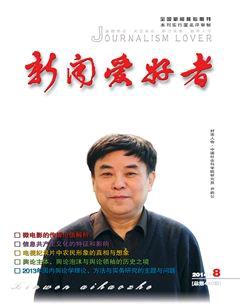史家之絕唱,記者之先聲
李彬
記得叔本華的《論讀書(shū)》有個(gè)觀點(diǎn):20年之內(nèi)的書(shū)最好不讀,因?yàn)榇蠖酂o(wú)非過(guò)眼云煙。回想自己20年來(lái)過(guò)目的書(shū),也許只有小部分能入叔本華心儀的正典,可謂“不讀白不讀”,其余大部分恐怕真成為過(guò)眼云煙了。而后者又分為兩類,一是“讀了也白讀”,一是“白讀也要讀”。“讀了也白讀”的代表是五花八門(mén)的熱銷書(shū),今天大多連書(shū)名及作者都想不起來(lái)了;“白讀也要讀”則有種種不得不讀的書(shū),如實(shí)際所需、情勢(shì)所迫等。另外,還有一時(shí)雖然難以歸入經(jīng)典,但又確屬精神文化或?qū)W術(shù)思想的用心力作,如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阿來(lái)的《瞻對(duì)》、梁衡的《人杰鬼雄》等。現(xiàn)代人的時(shí)間既緊張又寶貴,所謂“時(shí)間就是金錢(qián)”成為當(dāng)代中國(guó)最響亮的口號(hào)之一,而一曲《時(shí)間都去哪兒了》也讓人感慨噓唏,讀書(shū)時(shí)間更是稀缺。而在寸陰寸金的時(shí)間里,除了應(yīng)對(duì)“讀了也白讀”和“白讀也要讀”的東西——且不說(shuō)微博微信什么的,如何盡可能浸淫于古典、陶冶于經(jīng)典,委實(shí)是個(gè)十分突出的矛盾。對(duì)此,前人已有各自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魯迅先生把他人喝咖啡的時(shí)間都用來(lái)讀書(shū),這里借花獻(xiàn)佛再貢獻(xiàn)一點(diǎn)——化整為零,螞蟻搬家。首屆范長(zhǎng)江新聞獎(jiǎng)9位獲獎(jiǎng)?wù)咧弧⑿氯A社原總編輯南振中,2008年為新華社年輕記者作了一場(chǎng)關(guān)于讀書(shū)的報(bào)告,題為《把“閱讀”培養(yǎng)成為一種愛(ài)好》,其中談到自己通讀《列寧選集》的經(jīng)驗(yàn)即為一例:
《列寧選集》第1卷858頁(yè),第2卷1005頁(yè),第3卷933頁(yè),第4卷765頁(yè),4卷合計(jì)3561頁(yè)。由于采訪報(bào)道任務(wù)繁重,要在短期內(nèi)讀完這4大本書(shū),的確有一定困難。為了解決讀書(shū)同時(shí)間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擬定了一個(gè)總體學(xué)習(xí)計(jì)劃:按照每小時(shí)平均10頁(yè)的閱讀速度,將《列寧選集》1-4卷通讀一遍需要356個(gè)小時(shí)。如果每天擠出1小時(shí),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寧選集》1-4卷通讀一遍。有了這個(gè)總體規(guī)劃,零碎時(shí)間就像珍珠一樣被串了起來(lái)。實(shí)踐的結(jié)果是只用了6個(gè)月,就把《列寧選集》通讀了一遍。(《中國(guó)記者》,2008年第5期)
他的經(jīng)驗(yàn)也給了我啟發(fā)。于是,除了20年目睹之雜碎書(shū),這些年還用此法啃讀經(jīng)典、溫習(xí)古典,頗見(jiàn)成效,《魯迅全集》《資治通鑒》等就是這樣零打碎敲,用一年時(shí)間讀完的。拿中華書(shū)局的點(diǎn)校本《資治通鑒》來(lái)說(shuō),共有20本約1萬(wàn)頁(yè),平均下來(lái),每天約30頁(yè),由于多為有聲有色的人物以及一波三折的故事,讀來(lái)有滋有味,不亞坊間八卦。2013年,經(jīng)方家數(shù)十年辛勤勞作,新版《史記》出版發(fā)行,接著《毛澤東年譜(1949-1976)》也在偉人誕辰120周年之際問(wèn)世。《史記》10本,《毛澤東年譜(1949-1976)》6本,于是決定2014年化整為零的攻堅(jiān)目標(biāo)就是這兩套大書(shū)。結(jié)果表明,同南振中讀《列寧選集》的情形相似,不到半年就基本完成了。
當(dāng)然,《史記》的“表”“書(shū)”等專精內(nèi)容匆匆翻過(guò),重點(diǎn)是感興趣的史記故事,如“本紀(jì)”“世家”“列傳”等。關(guān)于《史記》,魯迅先生的評(píng)語(yǔ)向稱不刊之論:“史家之絕唱,無(wú)韻之離騷。”放在人類文明長(zhǎng)河,也許只有古希臘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及其《歷史》庶幾近之。另外,司馬遷及其《史記》既是不可超越的史家之絕唱,又是當(dāng)之無(wú)愧的記者之先聲。無(wú)論司馬遷的讀萬(wàn)卷書(shū),行萬(wàn)里路,深入現(xiàn)場(chǎng),調(diào)查研究的良史之才,還是《史記》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shí)錄記載,都不能不讓新聞?dòng)浾叻钪疄楣磐駚?lái)第一人。只消讀讀《太史公自序》,一位風(fēng)塵仆仆的記者形象不就躍然紙上了嗎:
遷生龍門(mén),耕牧河山之陽(yáng)。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huì)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fēng),鄉(xiāng)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guò)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bào)命。
這位行者與記者——記述事實(shí)之人,使人不由想起新聞史上的名家名作,如范長(zhǎng)江的《中國(guó)的西北角》、薩空了的《從香港到新疆》,想起當(dāng)代中國(guó)那些“褲腿上永遠(yuǎn)沾著泥巴”的人民記者,如《告別饑餓》一書(shū)的四位新華社記者之一馮東書(shū):
在從事新聞工作的40余年間,馮東書(shū)的足跡踏遍祖國(guó)東西南北的山山水水:東到黑龍江省撫遠(yuǎn)縣,南到海南省三亞市,西到新疆帕米爾高原腳下的烏恰縣,北到黑龍江省漠河縣,并對(duì)全國(guó)多數(shù)貧困地區(qū)進(jìn)行過(guò)調(diào)查。
馮東書(shū)的名字也儼然成為深入調(diào)研的代名詞……一位老記者在博客中寫(xiě)道:“當(dāng)年新華社記者馮東書(shū)坐拖拉機(jī)下鄉(xiāng),我也在太行山上用腳板‘量路;那收獲,絕對(duì)比如今坐小車下去采訪大得多,也豐富得多。”這句話并不是虛言。在被譽(yù)為“新西行漫記”的《告別饑餓1978》一書(shū)中,我們可以領(lǐng)略到馮東書(shū)“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調(diào)研所結(jié)出的碩果。
馮東書(shū)到農(nóng)村調(diào)研的故事流傳很廣,至今還能從新華人的口中聽(tīng)到一些趣聞?shì)W事。如他出差調(diào)研到某分社,分社門(mén)衛(wèi)看他頭發(fā)凌亂、衣衫襤褸,不像新華社記者,倒像是個(gè)叫花子或者上訪者。[1]
如今,新聞行當(dāng)大都意識(shí)到講故事的重要性,懂得新聞固然得講政治,因?yàn)樾侣劦谋举|(zhì)是政治,核心在政治,即使“新聞自由”也屬政治話語(yǔ)與范疇,但新聞之為新聞,首先在于故事,沒(méi)有故事,新聞就成為評(píng)論或文章,哪怕是重要的評(píng)論,縱然是精彩的文章,也算不上新聞,更夠不上好新聞。于是,講故事成為新聞?dòng)浾叩墓沧R(shí)。那么,什么是故事,怎么講故事,又怎么講好中國(guó)故事呢?這些問(wèn)題,也可在古今記者第一人即司馬遷及其《史記》中得到鮮活的答案,尤其是中國(guó)氣派、中國(guó)風(fēng)格的答案。有位博士生也是高校青年教師,一次同我探討學(xué)位論文的選題,提到中國(guó)的新聞敘事與西方專業(yè)主義的“嫁接”問(wèn)題。我說(shuō),與其如此張冠李戴,還不如探討中國(guó)的新聞報(bào)道與《史記》一類文本文體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呢。《人民日?qǐng)?bào)》的一則《編輯札記》,也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
古人寫(xiě)文章,一到描寫(xiě)一個(gè)人,常用至妙至簡(jiǎn)之筆,而令其形神風(fēng)度皆躍然紙上。
印象最深的,是韓愈寫(xiě)南霽云,前后只用三句話。第一句是求援之時(shí),賀蘭賞其酒食,霽云慷慨道:我突圍出來(lái)的時(shí)候,睢陽(yáng)城里已經(jīng)一個(gè)多月沒(méi)開(kāi)鍋了,我現(xiàn)在獨(dú)享美食,實(shí)在吃不下去。然后“拔其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第二句是遭拒之后,霽云縱馬離去,將出城時(shí),返身一箭,射在佛寺浮圖上,立志說(shuō):等我破了賊兵,一定回來(lái)滅你賀蘭,這支箭便是見(jiàn)證。最后一句是被俘之際,面對(duì)敵人勸降,霽云默然不語(yǔ),老首長(zhǎng)張巡以為他要降敵,對(duì)他說(shuō):大丈夫不可為不義屈!霽云聽(tīng)了笑道:我本來(lái)是想保存實(shí)力,以圖再起,既然您這么說(shuō)了,我哪敢不死!于是與張巡一起就義。endprint
只此三句話,一個(gè)忠肝義膽、胸有丘壑的剛烈男兒、赳赳武將,便永遠(yuǎn)立在了文史之中。此后但說(shuō)南霽云,永遠(yuǎn)也繞不開(kāi)拔刀斷指、箭射浮圖的那個(gè)經(jīng)典形象。
這種例子很多。司馬遷寫(xiě)項(xiàng)羽,也是寥寥幾筆,便見(jiàn)項(xiàng)羽一生。“項(xiàng)籍少時(shí),學(xué)書(shū)不成,去。學(xué)劍,又不成。”他叔父于是教他兵法,項(xiàng)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xué)”。此后見(jiàn)始皇帝游會(huì)稽,渡浙江,項(xiàng)籍又說(shuō):“彼可取而代也。”學(xué)書(shū)學(xué)劍半途而廢,雄圖霸業(yè)自然也難有全終。一個(gè)性情浮躁、志大才疏的梟雄形象,便在太史公幾句話里,展露無(wú)遺。
古人寫(xiě)人,運(yùn)筆精妙,惜字如金,卻見(jiàn)神見(jiàn)骨,風(fēng)姿卓絕,余味難以窮盡;今人寫(xiě)人,洋洋灑灑,長(zhǎng)篇高論,卻千章一律,寫(xiě)到最后仍讓人感覺(jué)面目模糊。古今之異,其何大哉。[2]
倘若說(shuō)世界三大宗教無(wú)不關(guān)注人與超驗(yàn)世界的問(wèn)題,那么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中華文明則始終操心人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關(guān)系。所以,人世、人生、人倫、人情構(gòu)成了中國(guó)歷史連綿不絕的主線,對(duì)現(xiàn)世生活的熱望熔鑄為千萬(wàn)年中華文明的底色,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地勢(shì)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如“舌尖上的中國(guó)”。無(wú)論是先秦諸子深入淺出的寓言哲理,還是《左傳》《戰(zhàn)國(guó)策》《呂氏春秋》等引人入勝的歷史敘事,無(wú)不散發(fā)著濃郁的、溫暖的、可親可近的人間煙火氣。司馬遷的《史記》也處于這一脈文化源流之中。于是,讀《史記》,仿佛在讀人生的喜怒哀樂(lè)與悲歡離合,一觴一詠無(wú)不浸透人世情懷,真切,自然,生動(dòng),樸實(shí),猶如儷生對(duì)漢王劉邦進(jìn)言:“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儷生陸賈列傳》)遺憾的是,下面不得不用列舉法說(shuō)明一二,而對(duì)于如此渾然一體的偉大作品,列舉法實(shí)屬焚琴煮鶴的無(wú)奈之舉。
凡是故事,自然離不開(kāi)人,核心都在人的活動(dòng)、行為、言語(yǔ)、心理等。史記故事特別是最有故事性的列傳,都是圍繞一個(gè)個(gè)活生生的人而展開(kāi)的。比如,著名的《刺客列傳》,就寫(xiě)了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幾位義薄云天的俠士、壯士、烈士。這些動(dòng)人心魄的故事經(jīng)過(guò)司馬遷的娓娓講述,千百年來(lái)代代傳揚(yáng),家喻戶曉,已經(jīng)積淀為集體無(wú)意識(shí)中的文化原型,從而激勵(lì)著一代代生為人杰死為鬼雄的中華兒女。魯迅先生《故事新編》的眉間尺(《鑄劍》),以及郭沫若的《聶縈》《高漸離》《棠棣之花》等劇作人物,就繼續(xù)演繹著這些傳奇故事,而《趙氏孤兒》更在民間廣為流傳。以《刺客列傳》中的豫讓為例,就是那么有血有肉、有聲有色: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wú)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shuō)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bào)讎而死,以報(bào)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涂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dòng),執(zhí)問(wèn)涂廁之刑人,則豫讓,內(nèi)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bào)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jǐn)避之耳。且智伯亡無(wú)后,而其臣欲為報(bào)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醳去之。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豫讓以一己之生命詮釋著這一中華文明的精神,抒寫(xiě)著《蘭亭集序》所謂“人之相與,俯仰一世”的情懷。后來(lái),豫讓不依不饒,繼續(xù)行刺趙襄子,結(jié)果同樣失利。當(dāng)他又被趙襄子捕獲時(shí),趙不解,說(shuō)你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智伯消滅他們后,你不為他們報(bào)仇,反而委身智伯,今天智伯已死,為什么偏偏沒(méi)完沒(méi)了地為他復(fù)仇呢?豫讓回答說(shuō):“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bào)之。至于智伯,國(guó)士遇我,我故國(guó)士報(bào)之。”這同《大公報(bào)》的張季鸞頗為相似,當(dāng)年蔣介石曾以國(guó)士相待,故而他也是國(guó)士相報(bào),遂有世人詬病的“小罵大幫忙”。聽(tīng)了豫讓的回答,趙襄子喟然嘆息,流淚說(shuō)了一番話,然后配合豫讓共同上演了一幕長(zhǎng)歌當(dāng)哭的悲劇:
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jì),寡人不復(fù)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愿請(qǐng)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bào)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bào)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guó)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fù)還!豫讓故事同荊軻及其刎頸之交高漸離前赴后繼刺秦王的壯舉一樣,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血?dú)夥絼偟那啻簜チΓw現(xiàn)了“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高貴精神。今天,知識(shí)分子及其話語(yǔ)儼然一枝獨(dú)秀,有人將其同先秦的“士”聯(lián)系起來(lái)。不過(guò),通觀古典時(shí)代,無(wú)論是司馬遷筆下的《刺客列傳》,還是禮賢下士的戰(zhàn)國(guó)四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士”與其說(shuō)是一種社會(huì)階層,不如說(shuō)是一種生命境界,如士可殺而不可辱,或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yuǎn)。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yuǎn)乎?”這從《管晏列傳》的一個(gè)故事里,也可略見(jiàn)一斑。故事說(shuō)的是,齊國(guó)賢相晏子有一次出門(mén),他的車夫駕著高車大馬,意氣洋洋,其妻從門(mén)縫看到這一幕,覺(jué)得不勝羞愧,等車夫回家后,就提出分手。車夫不解,詢問(wèn)原因,于是這位無(wú)名無(wú)姓的女子說(shuō)了一通話,既讓車夫汗顏,也足令后人自省: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mén)閑而窺其夫。其夫?yàn)橄嘤瑩泶笊w,策駟馬,意氣揚(yáng)揚(yáng)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qǐng)去。夫問(wèn)其故。妻曰:“晏子長(zhǎng)不滿六尺,身相齊國(guó),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zhǎng)八尺,乃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wèn)之,御以實(shí)對(duì)。晏子薦以為大夫。
司馬遷不僅善于講故事,而且長(zhǎng)于寫(xiě)細(xì)節(jié),往往白描式的幾筆,就把人物神態(tài)與特定場(chǎng)景勾畫(huà)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xiàn)。下面再看一例。由于秦漢以后的郡縣制奠定了中國(guó)大一統(tǒng)的社會(huì)政治制度,漢代高官也就包括京師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守,其標(biāo)志即為兩千石及其以上的俸祿,正如過(guò)去十三級(jí)是高干門(mén)檻。漢文帝時(shí)有位朝廷元老,姓萬(wàn)名奮,由于本人以及四個(gè)兒子都是省部級(jí)以上高官,于是皇帝戲稱他為“萬(wàn)石君”,也就是說(shuō)父子五人的俸祿總計(jì)一萬(wàn)石。這位萬(wàn)石君及其兒子都憨厚實(shí)誠(chéng),下面這段《史記》花絮還被司馬光用于《資治通鑒》,看后如在目前,令人忍俊不禁:endprint
萬(wàn)石君少子慶為太仆,御出,上問(wèn)車中幾馬,慶以策數(shù)馬畢,舉手曰:“六馬。”
武帝看來(lái)是逗他玩兒的,因?yàn)榛始矣{的馬匹都有定數(shù),而且一目了然。沒(méi)想到,這位可愛(ài)的萬(wàn)太仆居然舉著馬鞭,點(diǎn)著御馬,一匹一匹數(shù)將過(guò)來(lái)。這樣令人過(guò)目不忘的細(xì)節(jié),《史記》中比比皆是。再如《孔子世家》末尾,寫(xiě)到孔子垂暮時(shí),就有一段情景交融的細(xì)節(jié):
孔子病,子貢請(qǐng)見(jiàn)。孔子方負(fù)杖逍遙于門(mén),曰:“賜,汝來(lái)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至于許多常被教科書(shū)選錄的名篇,如《項(xiàng)羽本紀(jì)》《留侯世家》《孟嘗君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等,更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與細(xì)節(jié),就像流播人口的霸王別姬、雞鳴狗盜、負(fù)荊請(qǐng)罪等。下面不妨再看幾例《李將軍列傳》的細(xì)節(jié):
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guān)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shí)!如令子當(dāng)高帝時(shí),萬(wàn)戶侯豈足道哉!”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hào)曰“漢之飛將軍”,避之?dāng)?shù)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jiàn)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méi)鏃,視之石也。因復(fù)更射之,終不能復(fù)入石矣。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jiàn)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ài)樂(lè)為用。
……
眾所周知,司馬遷曾因“李陵案”遭受慘毒的腐刑,從他撰寫(xiě)的《李將軍列傳》中,也能體味一種悲涼慷慨的沉郁之情,宛若李陵《答蘇武書(shū)》:“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cè)耳遠(yuǎn)聽(tīng)。胡笳互動(dòng),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tīng)之,不覺(jué)淚下……”所以,每讀《李將軍列傳》,心頭都禁不住陣陣泛起后人那些悵惘低徊的深長(zhǎng)歌吟,包括張承志《荒蕪英雄路》中的《杭蓋懷李陵》:“兩唐書(shū)中記載了大量黠戛斯(柯?tīng)柨俗危┤俗苑Q李陵苗裔的族源傳說(shuō);日本突厥學(xué)家護(hù)雅夫認(rèn)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發(fā)黑須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這一傳說(shuō),已經(jīng)成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而詩(shī)壇千古流傳的名篇佳作,更是后世之人對(duì)李廣李陵祖孫兩代英雄末路的無(wú)盡追懷:
秦時(shí)明月漢時(shí)關(guān),萬(wàn)里長(zhǎng)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
林暗草驚風(fēng),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méi)在石棱中。(盧綸)
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wàn)戶侯何足道哉。(劉克莊)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云翔。良友遠(yuǎn)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zhǎng)。嘉會(huì)難兩遇,歡樂(lè)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隨時(shí)愛(ài)景光。
嘉會(huì)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zhǎng)纓,念子悵悠悠。遠(yuǎn)望悲風(fēng)至,對(duì)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dú)有盈觴酒,與子結(jié)綢繆。(《蘇李詩(shī)》
……
作為新聞的先聲,司馬遷的《史記》既講故事,狀細(xì)節(jié),又以“太史公曰”成為新聞評(píng)論的典范。這些評(píng)論文字,寥寥幾筆,畫(huà)龍點(diǎn)睛,頓使全篇故事形神兼?zhèn)洌櫯紊恕J聦?shí)上,“太史公曰”已經(jīng)成為史記故事不可分割的有機(jī)構(gòu)成。范敬宜在清華大學(xué)開(kāi)設(shè)新聞評(píng)論課時(shí),常常以此傳道授業(yè),《李將軍列傳》結(jié)尾的“太史公曰”,更是他的經(jīng)典教學(xué)案例: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shí)心誠(chéng)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其實(shí),這段文字何嘗不是范敬宜的寫(xiě)照呢?“其身正,不令而行”“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也像這位“將軍一去,大樹(shù)飄零”的一代報(bào)人嗎?再如《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同樣堪稱精辟、深刻而貼切:
詩(shī)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xiāng)往之。余讀孔氏書(shū),想見(jiàn)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shí)習(xí)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dāng)時(shí)則榮,沒(méi)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xué)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guó)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拿破侖臨終時(shí),回顧自己曾經(jīng)指揮千軍萬(wàn)馬而如今淪為孤家寡人,耶穌孑然一身而后世向心歸化,于是不由感嘆真正強(qiáng)大的不是利劍而是精神,這同司馬遷的上述評(píng)論可謂英雄所見(jiàn)略同。除直抒胸臆的評(píng)論,司馬遷還在看似不經(jīng)意的敘事中,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傳達(dá)種種就事論事的評(píng)說(shuō)。如《樂(lè)毅列傳》記述了樂(lè)毅一封《報(bào)燕惠王書(shū)》,其中有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習(xí)近平系列講話中不時(shí)提到“善始善終,善作善成”,即由此點(diǎn)化而來(lái)。再如,《商君列傳》中商鞅變法的一段陳詞,也為治國(guó)理政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啟發(fā):
孝公既用衛(wèi)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wèi)鞅曰:“疑行無(wú)名,疑事無(wú)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jiàn)非於世;有獨(dú)知之慮者,必見(jiàn)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jiàn)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lè)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圣人茍可以彊國(guó),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綜上所言,除了文化以及文字的血肉關(guān)聯(lián),司馬遷及其《史記》與現(xiàn)代新聞至少有三點(diǎn)可謂一脈相通:一是實(shí)事求是,調(diào)查研究;二是講故事,重細(xì)節(jié);三是字里行間的高遠(yuǎn)境界與高貴情懷。最后一點(diǎn)尤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因?yàn)檠巯乱恍┬侣劰适拢跣踹哆叮u零狗碎,仿佛淪為稗官野史,既沒(méi)有政治意識(shí),也沒(méi)有什么精神價(jià)值。要之,《史記》既當(dāng)?shù)闷痿斞钢ㄔu(píng),也無(wú)愧于記者之先聲。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對(duì)《離騷》的一段經(jīng)典評(píng)論也完全適用于《史記》:“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jiàn)義遠(yuǎn)。”
在千萬(wàn)年中華文明進(jìn)程中,司馬遷與《史記》如一座豐碑為人尊崇,自來(lái)著述也如萬(wàn)斛泉涌,不擇地而出。河南大學(xué)教授王立群為《百家講壇》欄目開(kāi)講《史記》,就是最新一例。在學(xué)術(shù)界,李長(zhǎng)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fēng)格》(1946)廣為人知,備受推崇。李長(zhǎng)之是“清華四劍客”之一,與吳組緗、林庚、季羨林相提并論。作為第一部全面評(píng)議司馬遷與《史記》的專著,李長(zhǎng)之在這部名山之作的自序中,將其人格與風(fēng)格歸結(jié)為一個(gè)共同點(diǎn)——“浪漫的自然主義”。所謂自然主義,乃指極端客觀寫(xiě)實(shí);而浪漫主義,則又極端主觀,注重內(nèi)心世界,抒發(fā)自我情感。兩者看似完全對(duì)立,卻相輔相成地有機(jī)統(tǒng)一于司馬遷及其《史記》,形成魯迅先生的定評(píng):史家之絕唱(如實(shí)),無(wú)韻之離騷(抒情)。實(shí)際上,古今中外的一流記者及其作品,也無(wú)一不是主客觀的完美融合,絕對(duì)客觀與絕對(duì)主觀都不可能鑄就好新聞,也不可能成就大記者。正如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方面如此真切地記錄了事實(shí),達(dá)到古今良史與實(shí)錄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浸透著一位有良知記者的深摯情感,特別是對(duì)中國(guó)的熱愛(ài)以及對(duì)中國(guó)人民與中國(guó)革命的深切同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