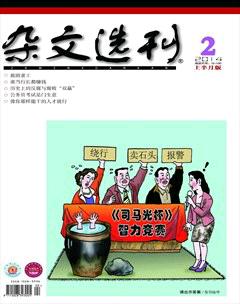李庚辰雜文特色
李志遠
收到庚辰同志寄來的這本集子,一氣讀罷,反復回味,不由心為所動。作為他的老讀者、老作者、老文友,很想發點感慨。庚辰曾長期供職于解放軍報社,又長期編寫雜文,見多識廣,躬行體驗多多,所以,選入本集的雜文,幾乎篇篇上乘。具體說,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主要特色:
濃郁的憂患情愫。多年的軍旅生涯,鍛鑄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為其雜文的思想品格奠定了基礎。他在其最近發表的《雜談雜文》一文中說:雜文“它胸懷天下,心憂家國”,“它顧念草根,情愫悲憫,憐貧惜苦,為民鼓呼”。此為心聲,也是其雜文的真實寫照。本集雜文,無論對官員貪腐、“四風”問題、用人之弊,還是社會不正風氣等等的針砭,字里行間,都透映著對國家民族的憂心,對真善美的呼喚,對弱勢者的同情。《打錯了比方》一文,針對封建遺風說,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真不知怎么能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合拍”。他擔心“君子”斗不過小人,在《也說“君子要與小人斗”》一文中,為“君子”出主意說,“一是‘君子慎與小人斗,二是‘君子善與小人斗”。憂患是“公知”的特性,也是雜文家的應有素質。沒有憂患,雜文家和好雜文就無從談起。
深透的批判力度。庚辰說:“雜文主司批評,是戰斗性文體”,對“不是東西者流”,不僅“義正詞嚴,器大聲洪,霹靂閃電,振聾發聵”,而且“一針見血,一擊致命”。他的雜文,驗證了他的雜文觀,常常是不留情面,層層深入論證批判,直至捅到要害。報載有位巴西醫生認為,貪官易得絕癥,因“當違反自己的倫理道德準則時,在精神和肉體上就會受到自體的攻擊”。而《“貪官短命”說質疑》一文則說,貪官“膽子特大,心理承受能力特強,簡直可上九天撈錢,可下五洋淘金。國家的金庫他敢挖,百姓的腰包他敢掏,哪里的地皮都敢刮”。因他們的所謂“道德準則”,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所以,貪官不會“受到自體的攻擊”。事實上,“有幾個不是吃得腦滿腸肥、紅光滿面”?要說他們中會有人“受到自體攻擊”的話,“那也絕非在他們貪贓得利之時,必定在東窗事發之后”。借駁一種歪理,將貪官批得落花流水。《說“受騙”》,講了“官僚主義頭頭兒”受騙的種種情況之后,指出:“‘受騙云云,實在與騙人分不開”,因為,下級騙了他,他用假成績來騙自己的上級,取信上級,作為固位升官的資本,“受騙者受益也”。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知人善任”一說》,說“當事者說:這叫‘知人善任;而局外人卻以為這不過是‘善任知人”。可謂一針見血。其雜文批判,以理服人,邏輯性強,深刻而中肯,即使被批對象也不得不誠服,只有舉手投降的份兒。由此足見雜文效力之高和作者功力之深。
自如的引經據典。庚辰雜文善于用典,古今中外,經史子集,順手拈來,“為我所用”。“借石攻玉,托物論理”,增添了文章的厚重感、知識性和書卷氣,令人喜聞樂見。《假話的實效》,圍繞假話典例,從美國說到中國,從隋朝說到清朝,從“大躍進”說到“文革”,論危害談根源,末了語重心長道:“切不可讓假話腐蝕了人們的靈魂和黨風民氣,切不可為了騙取虛假的‘榮譽而敗壞了實事求是的作風。”讓人折服而受益。不少用典,并非大段生搬,而是舉其要義,點到為止,輕松自然而靈動,使文章渾然一體無斧痕,又給讀者以回想余地。《說“度”》說:“人,誰能不笑?但打敗了金兀術,牛皋笑過了頭,竟笑得斷了氣兒!人,誰又會永遠不生氣?而周公瑾氣起來不要命,架不住諸葛亮三折騰,竟氣得伸了腿兒!”等等。“腹有詩書氣自華。”善于用典,自是緣于作者的博覽群書。
洗練的文學語言。庚辰的不少雜文,從標題到行文,都是形象化語言。《狗的故事》、《“錢”字兩支戈》,標題就引人入勝。“撲哧哧到處打雞血”、“咕嘟嘟許多人又喝起涼水來”、“呼啦啦家家又培植起紅茶菌”,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同時,還多用四六句和排比句。如“概而言之,所謂有德,最起碼的一條,恐怕得有公心”;“此人遠見卓識,大智大勇,才武絕人”。再如“‘好人受氣,壞人神氣,壓制了正氣,助長了邪氣,單位搞得烏煙瘴氣”;“李白斗過高力士沒有?岳飛斗過秦檜沒有?楊漣斗過魏忠賢沒有?”等等。文學語言,讀來朗朗上口,明快而有節奏,形象而有韻味,無疑為雜文的文學屬性增了色,添了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