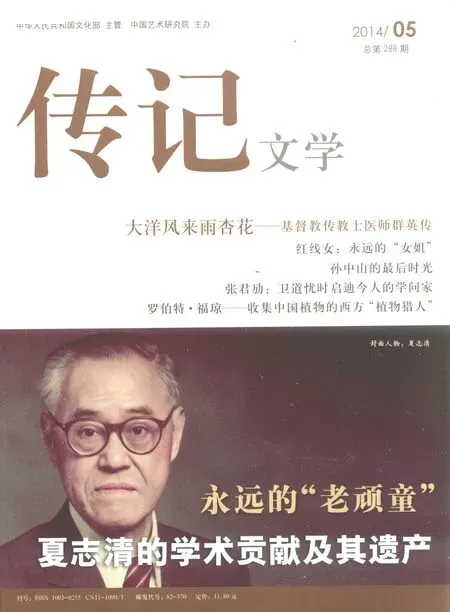熔古鑄今,書寫傳奇
——讀張緒平先生新作《夢囈》
李 雷
熔古鑄今,書寫傳奇——讀張緒平先生新作《夢囈》
李 雷
《夢囈》是張緒平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新作,起初是以“忠武公傳奇”一名逐章逐節(jié)地發(fā)布于起點中文網(wǎng)、榕樹下等知名網(wǎng)絡(luò)文學網(wǎng)站,頗有些影響,后來結(jié)集成書在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應(yīng)該說,與“忠武公傳奇”的中規(guī)平實相比,“夢囈”更能貼合小說奇譎瑰麗且略帶魔幻的敘事風格,亦更富文學意味。
整篇小說圍繞主人公“忠武公”來展開敘事,以類似于電影《阿甘正傳》的敘事方式記述了“忠武公”的傳奇一生,只不過“忠武公”生活的年代被放大至兩千年的中國歷史,顯然這并非一般的人物傳記,因為人物傳記的首要原則便是符合史實,真實可信,而“忠武公”和“阿甘”一樣,則完全是虛構(gòu)的人物形象。“忠武公”,原名余最,出生在公元元年的漢代國都長安,早年混跡于長安市井,機緣巧合得以結(jié)識之后的光武帝劉秀,其后屢立奇功并因輔佐光武帝實現(xiàn)“光武中興”,得以敕封“忠武公”。后來,歷經(jīng)中國歷史近乎兩千年的時代變遷與命運浮沉,參與了諸多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并幫助成就了“太康之治”、“開元盛世”和“咸平之治”等盛世景觀。總之,在作者筆下,“忠武公”是一位前無古人后乏來者的傳奇人物,他橫貫煌煌兩千年中國歷史,歷史變遷,朝代更迭,世事無常,但始終以其生命與實踐來闡釋著忠君愛國,憂國憂民,公平正義,除邪鏟惡的“忠武”本義。
顯然,“忠武公”的形象雖是虛構(gòu),但我們又分明能從中國歷朝歷代的名臣賢士身上尋覓到他的影子,冒死進諫的魏征,不事權(quán)貴的李白,忠君報國的岳飛,剛直不屈的方孝孺等等,皆或多或少與“忠武公”存有重合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