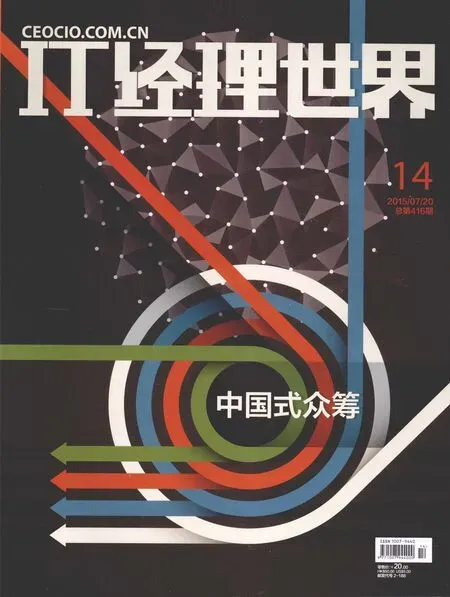“網絡造星”生態的中外差異
艾博·索瓦爾

美國知名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不久前披露了幾組YouTube上一線草根明星的收入數據,雖然推估的結果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這份參考價值足以在被貼了“商業機密”的匣子上刻出一道裂痕,透出的微光中映現出令人咋舌的廣告主投放力度和“網絡造”明星的吸金能力。
且看:PewDiePie是一名24歲的來自瑞典的游戲玩家,這位YouTube上的超級巨星真名為Felix Kjellberg, 他通過上傳分享自己玩游戲的視頻而吸引了2770多萬粉絲,點擊量超過47億,在2013年一年間就創造了400萬美元的廣告收入(注:此為《華爾街日報》報道數據);
BluCollection Disney Toys!是由一個玩具極客開設的專題,乍看之下該賬號的粉絲數僅77萬有余(他們都熱衷于拆解、組裝和評論各種玩具),但16億的瀏覽量卻為賬號主帶來介于66萬美元和640萬美元之間的年收入;
網絡明星又何止于出鏡達人們,Robby Ayala就是這樣的例子——當還是一名法律系大學生時,他通過在6秒短視頻分享應用Vine平臺上每日更新搞笑短片而在頃刻間就為自己贏得了260多萬名粉絲……現在Robby已從法學院退學,全力追逐一個全職的Vine短視頻金牌制作人的職業生涯夢想。
筆者了解到,中國也有不少“網絡造”明星,鑒于中國網民數量更巨大、黏合性更強、以及到達家喻戶曉之境界的曲線更陡直等等因素,中國“網絡造”明星的吸金能力同樣不可小覷。不過,如果視“網絡造星”為一門新興產業的話,那么不難發現,無論是造星機制、還是整個配套體系的生態圈,均有不少有意思的“中外差異”,不能不說這些差異本身也將對產業發展方向形成較長遠的影響。
一是運營商在網絡造星中所擔產業角色的相對透明化vs不透明化。眾所周知,YouTube與視頻內容生產方(也是產生草根明星的直接源泉方)之間可簽署“合作伙伴計劃”。該項目始于2007年中,初期實行邀約制,但后來開放性顯著提高,來自各個國家的用戶都可提出加入。與此同時,YouTube與進駐谷歌AdSense計劃的用戶分享廣告收入也是完全公開的,一旦表演者的視頻內容走俏,吸引大量觀眾之后,其廣告分成收入自然就會水漲船高。
另外,YouTube作為運營商在主導觀眾瀏覽習慣(從而長遠來說為草根明星贏得回頭客粉絲創造一個有利環境)方面也不遺余力。比方說,僅2012年,YouTube就斥資1億美元投入用于100個視頻頻道的扶持,努力引導用戶從觀看單獨視頻轉向習慣于觀看頻道,形成長久黏性。
在中國,我們發現運營商們在制造話題明星的過程中角色是相對不透明的,富于想象空間,這可能與文化淵源相關。但是,人們又何嘗會篤信——在徐靜蕾當年成為博客女王、在姚晨如今坐擁7000余萬微博粉絲背后,運營商是沒有任何作為的?運營商僅僅是因她們而集聚了人氣、帶火了博客/微博這兩個產品,而沒有更多的合作伙伴深耕計劃嗎?在一切機制變得透明化之前,答案可能永遠不為人知。
第二,美國對廣告業的監管更嚴格,因此才有了像“原生廣告”這樣的新物種留給微電影、微廣告的燎原機會;相對而言,在中國,什么都可以是廣告,所以由“輕”監管地帶而燎原新生的商機反而不突出。
在美國,根據監管要求,所有付費而獲的媒體曝光(也就是廣告的經典定義!)必須有醒目的識別標示,無論是贊助式廣告、付費搜索結果,還是宣傳性質的故事與報道,都需讓消費者有效地識別出與中立性媒體報道的區隔。
而原生廣告作為一個新事物,因為其“保持了在信息流中高度的原生性”,可謂是規避了上述監管地帶,(至少在目前而言)并不受制于聯邦監管方關于廣告標示的約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原生廣告成為美國當前增長最快的廣告類型之一,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尤其如此。不少廣告主積極開啟與Vine(Twitter旗下短視頻分享應用)風格一脈相承的官方賬號,意圖通過個性鮮明的微廣告片卡位社交媒體,率先招攬大量的粉絲;更多的廣告主則不斷加大預算投入原生廣告的制作與傳播,這也促成了像Niche公司這樣的自詡為“原生廣告工坊”的新型廣告代理商的方興未艾。
Niche公司本身也是一個社交媒體達人的“伯樂”工坊,與其合作的社交媒體達人多達3000個,覆蓋粉絲數量達到5億人。如今,不少廣告主視“移動互聯一代”的年輕群體為目標消費者,因此他們非常樂意與Niche公司合作,在后者的服務支持下,眾多的社交達人可以讓自己的原創內容——如Instagram上的圖片、Facebook上的故事、或Vine上的短視頻——與相關品類的產品(如嬰兒衣服、運動飲料等)建立聯系,并分享到粉絲群、引領出“轉、評、贊”等新一輪用戶互動。
Niche聯合創始人羅博·費什曼表示,目前公司已與約70個品牌客戶建立合作關系,其中包括家得寶(Home Depot)、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Gap童裝(Gap Kids)等。“我們的作品絕不是簡單的內容定制,而是形式與平臺信息流保持高度一致的原生廣告,”他表示。當然,或許意識到留給原生廣告輕監管的時間窗口畢竟有限,所以公司也會建議用戶在推廣內容中加一個#(標示出相應的企業或品牌),或者使用“我與......進行合作”等特定詞條,體現長遠合規考量。
相對而言,原生廣告在中國網絡媒體環境中并無獨有的廣告主青睞力,原由上文已述。也因此,“網絡造”明星或達人的廣告價值更多依附于其人格化體現,而不僅僅以他們本身作為傳播介質體現。
第三,眾多歐美網絡明星與經紀公司等生態圈伙伴一道以“Co-Creation”的運營模式進行合作,而在中國卻強調互聯網的“脫媒”屬性、網絡明星最終走上“去經紀化”之道似乎成為一條不歸路。
今年5月,中國著名的視頻自媒體品牌“羅輯思維”(由資深媒體人羅振宇創辦)確認與其經紀人申音友好分手;當雙方還處在蜜月期時,兩人攜手將“羅輯思維”這個全新“網絡造”明星節目品牌收獲了一年半200萬微信用戶、視頻過億人次觀看的不俗佳績。而就在這對黃金搭檔分道揚鑣之前不久,申音的經紀公司還失去了另一視頻節目新貴《凱子曰》的出品人王凱......而這僅是冰山一角:中國多少網絡明星紅人在起家時的經紀公司真正能一起走得很遠的?事實上,利益讓渡機制的缺失或不成熟,是無法被諸如“互聯網擁有脫媒屬性”這樣的蒼白鼓吹所掩飾得了的。
而本文開頭提到的瑞典人PewDiePie,其與經紀公司(Maker Studios)一直保持雙贏合作,后者亦在今年春季以超過9.5億美元的高價被迪斯尼公司收購,由此Maker Studios將有機會近身接觸到迪斯尼旗下所有品牌資源,包括皮克斯、漫威(Marvel)、ESPN、美國廣播公司(ABC)等。據測,Maker Studios與迪斯尼公司合并后所能觸達的全球互聯網用戶群將僅次于谷歌和Facebook。
經紀公司的附加值當然不止于接入商業與品牌生態圈。它們還為網絡明星積極創造線下的巡演機會、聚集各路業內牛人來一道Co-Create新作品......例如,YouTube上的明星本身大多沒有現實世界的演藝經驗,他們作為“在地下室、車庫或者自家后院悄悄發光的一群人”是沒有什么機會面對成千上萬名觀眾獻藝的;而經驗老道的演藝公司顯然從這一點捕捉到了機會——有不少公司專門為YouTube明星組織線下巡演,從納什維爾到圣地亞哥,再到西雅圖、新澤西......今年8月在加州的一場演出中,組織方預計將有1.8萬名粉絲到實地捧場,他們將排隊數小時以獲得自己偶像的親筆簽名。并且,全球巡演的日程表也緊跟其上:今年春季一場名為YouTube Fanfest的演出在新加坡熱售(入場門票從62美元起),之后還到悉尼和孟買進行了巡演。
就連CBS熱劇《犯罪現場調查》(CSI)的出品人Anthony Zuicker這樣的娛樂產業資深人士也經由經紀公司被引進了“網絡造星”的生態圈。原創的恐怖/科幻片BlackBoxTV系列不僅由YouTube獨家播放,劇中卡斯陣容相信也頗具網造明星時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