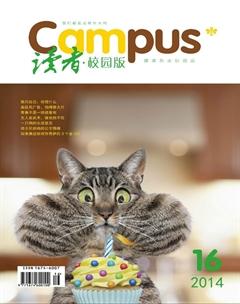我要大聲說話
黃翠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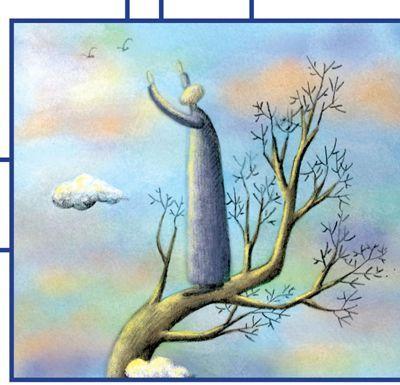
“不準大聲說話。”“不許吹口哨。”“吃飯不許吧嗒嘴。”“要文明,懂不懂?”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經常看到這樣的提醒,尤其一些人上升到整個民族的高度,說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大聲說話很不文明。
是的,我曾經很贊同這些觀點。
可是,慢慢地,我發現不是這樣的。我記得小時候在田間地頭干活,喊一個人過來抬玉米,必須大聲喊,尤其在山上,不僅要大聲還要把聲音拖長了喊,這樣才能傳播到較遠的地方,能讓別人聽到。當我們拾好了柴火,相約一塊下山時,你必須放開喉嚨,把伙伴們喊答應為止,急促的喊聲在風中停留的時間過短,是不行的。你得把手做成喇叭狀放在嘴邊,朝著一個方向喊開去:“李——小——秀——”“黃——名——花——”就像夏天在枝頭鳴叫的蟬一樣,只要聲音在空氣中待的時間足夠長,那靜靜的山林里回環曲折的就全是你的動靜了。那些正在忙忙碌碌的伙伴在把柴火一捆一捆捆好后,就可以知道集合的時間了。怎么可能小聲嘀咕呢?若有人嘟嘟囔囔,我們就說她那是在說給自己的腳尖聽。
大聲說話,那是必須的。
至于吹口哨,那是最美好的事情了。到了麥假,所有孩子都到坡里干活,正好上面一塊地,下面一塊地,兩個孩子就可以用口哨對話,先是打著口哨喊名字,然后問口渴嗎?喝水嗎?全是用口哨,問明白了,就一同循著溪流,到上面找個水清的地方喝個飽,喝完水當然還可以把河里的石頭翻一下,找幾只小螃蟹。
高興的時候用口哨唱支歌,最經常唱的是《甜蜜的事業》,后來還有《蝸牛與黃鸝》,輕松歡快極了。
最調皮的是,用口哨和女孩打招呼。口哨剛開始幾聲短而急促,好像說:“你好!”然后拖得很長很長,好像說:“美女,你好啊!”這時候女孩就加快腳步匆匆跑了。我呢,當然學會了口哨,也沖女孩吹,等她們回頭發現是我時,每次都紅著臉驚訝地問:“原來是你呀,丫頭!”哈哈!
至于吃飯,誰說不能吧嗒嘴的?發出聲音那是對好飯菜極高的贊揚。母親只要做了平常吃不到的菜,一定會問:“這菜香不香?”我們姐弟仨一定非常配合地咂咂嘴,搖頭晃腦地說:“嗯,香!真香!”嘴吧唧吧唧地直出聲。隨著這聲音,脖子成弓狀彎曲,即使菜從嘴巴滑到肚子里了,好像香味還在肆意漫延一般。這時候,母親一定把笑容從嘴角堆滿眼角,有很多時候,我們把菜吃得一干二凈,都忘了給母親留一份,母親卻總是高高興興地說:“今天的菜就是香,你看看,都吃干凈了。”
后來,在長期的讀書生涯中,我漸漸養成了安靜的習慣,說笑不再肆意流淌。我漸漸注意做到笑聲的克制,走路的輕盈,還有看人的臉色,調整漲落的心態。我以為自己高雅了,褪去了那層“山村皮”,換上了“城里人”的樣子。可是,我錯了。
去年在北京待了一周,到處玩,每天坐擁擠的地鐵。人群擠得要爆裂了卻常常靜悄悄的,沒有一個大聲說話的人。有一個母親剛大聲說了一句,就馬上被旁邊的兒子用食指豎起在嘴唇上制止住了。大家的耳朵里全是耳麥,手里全是手機,誰也不理誰。
太恐怖了,我竟覺得自己身處荒原,周圍根本沒有人群!
直到進了一個候車廳里。一個老人,一個穿著是農民模樣的人,他大聲地跟另一個人打招呼,那人明顯是他的老鄉。兩個人激動地大聲說話,用他們的方言,熱烈而親切。那才是人的聲音啊,我的可親可愛的首都!
后來,回到老家,母親告訴我:“說話當然要大聲。那話說出來就是讓人聽清楚的,你像個蚊子,在嗓子眼里哼哼,誰聽得見?說話大聲,那叫理直氣壯;低聲下氣那是以前做奴才的人干的事。咱吃得飽穿得暖,現在老百姓過得比過去的地主還要好,說話還能不大聲?那是高興,那是從心里淌出來的。”
至于我那留學回來的同學,更是一語道破了天機:“英語發音大都是雙唇音與唇齒音,只需要嘴皮動就行,不需要大聲,更不費多少力氣。我們的漢語可不行,要說話那就要底氣足,很多發音簡直是從丹田發出來,所以我們說話有‘字正腔圓之說,有‘抑揚頓挫之感。”
哦,原來說話不大聲都對不起發明漢字的老祖宗啊!
我——要——大——聲——說——話!讓那些為之側目的人哂笑去吧。
我自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自豪,我要大聲說中國話!
(本文作者系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六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