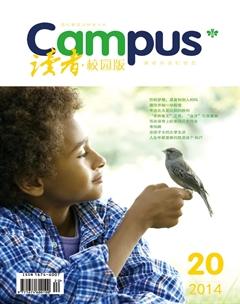丹·布朗:科學和宗教講的是同一個故事
于青

丹·布朗在宗教環境里長大。他說:“我母親是當地圣公會教堂的風琴手和唱詩班領隊,所以小時候我基本可以算是個基督教徒。同時,我又生活在一個由來自全世界的學生和機構所組成的校園里,他們帶來了十分廣闊而豐富的宗教類型。”對一個孩子來說,在學校里長大顯然會有很強烈的學術情結,正是這種環境,讓丹·布朗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對知識感興趣。他到現在都記得,自小學習對他而言就是件好玩的事。他父母也鼓勵他探索各個宗教理念之間的不同,并提出尖銳的問題。
和他筆下的羅伯特·蘭登教授一樣,丹·布朗很小就對符號和密碼著迷。從第一次在本地的共濟會會堂里看到那些神秘符號開始,他就迷上了這些東西。之后,他的興趣就被邏輯學占領了,因為它使用的是一種高度抽象的語言。升到八九年級開始學習天文學、宇宙論以及宇宙起源的時候,他問了牧師這么一個問題:“我搞不懂了。書本告訴我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但是宗教卻告訴我是上帝在七天里創造了一切。究竟哪一個才是對的?”他得到了這樣的回答:“好孩子不問這種問題。”一束光熄滅了,丹·布朗覺得《圣經》一點道理都沒有,還是科學更可信,就此離開了宗教。
在大學里,丹·布朗選修了不少科學科目,比如天文、物理、宇宙學、心理學。在轉去英文系之前,他在地質系待了兩年。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的科學知識越多,他就越發現物理像玄學,數學像虛數。越往科學里鉆,就越覺得世界深不見底。他的感受是:“哦,原來科學也同樣有其秩序和精神層面。”現在,他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科學和宗教只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它們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
有音樂底子,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作者
讀英文系的時候,丹·布朗的時間只夠用來讀指定書目,主要是古典文學。他最喜歡的是莎士比亞、約翰·斯坦貝克,以及博爾赫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現在,他基本只看非虛構類書籍——既為研究,也為樂趣。小說類中,他比較喜歡看驚悚小說,而且它們必須在開篇就能牢牢吸引他。他曾經以為自己會喜歡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但努力嘗試后,結果還是不喜歡。
在學生時代,他寫了一些短小的故事,但要說寫一部完整的小說,他想都沒想過。畢業后,丹·布朗成為一個音樂人,因為他那時候覺得,比起寫作,音樂更便于社交,也更好玩。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更享受獨處的時光,更愿意成為一名作家。
“從音樂人到小說家的轉變,這么說吧,挺搞笑。那會兒剛剛感覺到可能音樂和洛杉磯都不太適合自個兒——我住在好萊塢林蔭大道,鄰居都是搞重金屬音樂的。我就像一條離了水的魚——作為一個在學校里長大的人,我連一條藍色牛仔褲都沒有。于是我給《艾克賽特校友》雜志寫了個故事,主角是一個住在音樂產業中心地帶的極客書呆子,故事的名字叫《日落大道的常識與優點》。”
他寫這個故事純粹是為了好玩。故事發表后,丹·布朗接到了來自紐約的一通電話。有一個家伙在電話里說:“我很喜歡你的觀點,也喜歡你的寫作風格。你來紐約的時候記得打電話給我,我請你吃午飯。”
下一回去紐約的時候,丹·布朗給那人打了電話,那人果真請他吃飯。丹·布朗給那人講故事,他就跟丹·布朗說:“你應該寫小說。”丹·布朗回答說沒法想象自己能寫小說,那家伙從桌子那頭看著他說:“聽著,我在這個行業里做了很久,你是個會講故事的人,我能分辨得出。將來總會有那么一天,你找到了你想寫的東西,然后你會寫出一本小說來。”丹·布朗那時還將信將疑,他回答:“好,好的。見到你很高興——瘋狂的老家伙。”然后就回了家。
在丹·布朗看來,音樂就像液態的數學——一種流動的結構。它那藝術性的美感,來自藝術家如何運用那些最基本的規律。他覺得其實作曲和寫作非常相似,其核心都由情緒的積累和最終的釋放構成。另外,音樂和文學都非常看重節奏、調性和結構。他說:“我確信,有音樂底子,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作者。后來,我出了一張名為《天使與魔鬼》的CD,又寫了一本名為《天使與魔鬼》的小說——我所有的‘天使與魔鬼項目,都源自我想在自己的生命中平衡科學和宗教的欲望。我總是糾結于理解科學與宗教之間看似存在的矛盾與對立。”
我對權力著迷,特別是隱藏在暗處的權力
寫第一本小說的契機,是因為丹·布朗讀到了西德尼·謝爾頓的《末日追殺》。這本不厚的書給了他從未有過的閱讀體驗。在大學時他是上過創意寫作課程的,“但他們總想讓你寫點兒你知道的東西,而且我從來沒有將情節展開,再加點角色”。
那時,丹·布朗已經成為艾克賽特學院的老師。他的一名學生惹了個大麻煩:寫了一封威脅總統的電子郵件,就被特勤局盯上了。這讓丹·布朗震驚:他們是怎么看到這封電郵的?難道這不屬于個人隱私嗎?于是,丹·布朗對美國國家安全局做了點研究,對此著了迷,同時告訴自己:我會就此寫一本小說。
得知他要寫小說,他妻子的反應是:“開寫吧,這主意不賴。祝你玩得開心。”從此丹·布朗有了兩份工作:每天凌晨4點起床,寫到8點;騎12英里的自行車,去一所學校的初中教西班牙語;再騎12英里回家,沖澡,跑步,去艾克賽特學院完成下午的課程;接著在第二天凌晨4點醒來。一年之后,他寫出了處女作《數字城堡》。
他是在寫《失落的秘符》時意識到《達·芬奇密碼》將會大賣的。他說自己跟任何一個踏入成功之門的作家一樣,變得相當自我警惕。“你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單純地寫下故事情節,而是先去想:‘等一下,會有幾百萬人看到這個故事。就像一個對下一個擊球思考過多的網球運動員似的,你感覺自己的腿瘸了。”
不過這股瘋狂勁兒很快就過去了。他認識到,紅不紅跟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沒關系。“我只是個寫故事的人,僅此而已。對,是多了點兒錢,以及戲劇化的生活轉變。大部分變化都很美妙,但絕非全部。”
他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有連貫性。每次寫新故事,他都會回到那個屬于符號、密會和歷史的世界。“我對權力著迷,特別是隱藏在暗處的權力。國安局,國家偵察局,天主事工會。那種凡事背后必有因的感覺,讓我想起宗教。宗教會讓你覺得,這世上沒有偶然,如果我生命中出現了悲劇,那么一定是上帝在考驗我,或者在給我發信號。而這也是陰謀論者的想法。他們說:‘經濟形勢變壞?哦,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那是布拉格的一幫富人在密謀……”
他解釋自己為何在《達·芬奇密碼》中寫到神圣女性主義:一方面是他那位很強壯的母親,她很樂意看到自己所背負的“原罪”的定義能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他當時正在熱戀,對所謂異教、母系大地的概念分外著迷。還有一個理由,是基于他多年目睹的那些來自男人的破壞欲:“看看我們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我們能把用來殺戮的智慧和金錢的一半,用在解決問題上,那該是件多么好的事啊。”他基本上把這歸咎于睪丸素。如果上帝是個女性呢?如果我們能夠更多地接受我們女性化的那一面——我們會不會變得更有創造力、更有接受力,也更加有愛?
當這個世界有壞事發生時,我們總會自我安慰地認為,這背后一定隱藏著某個原因
丹·布朗覺得,自己并不是一個陰謀論者,而更像個懷疑論者。“我并不相信UFO,也不相信世界會在2012年毀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歡看我的書,是因為我的寫作是從懷疑論的角度出發的。”羅伯特·蘭登教授正是不相信任何現有觀點的人。他表示,如果自己的工作到位,那么讀者跟隨故事而產生的想法就會是:“我的神啊!可能是這樣,可能真是這樣。”
《達·芬奇密碼》被改編成電影,蘭登教授的忠實粉絲覺得改編得太爛。丹·布朗并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親自參加改編工作。“寫作是需要單獨完成的事,拍電影則要掌控成千上萬的場面和人員。每一個決定都是妥協。寫小說時,如果不太喜歡筆下人物的相貌和對話,那你用筆桿子修改就好;但在電影里,如果有什么部分你不太喜歡,改起來就麻煩了。”
他相信人類總在渴望一個有秩序的宇宙,人們會對“生命無常”“生無意義”這樣的觀點感到害怕。當這個世界有壞事發生時,我們總會自我安慰地認為,這背后一定隱藏著某個原因——可能是上帝的意志,可能是某個黑暗的陰謀,或者只是來自外星的某種影響。“我對于陰謀論、古老符號、秘密代碼非常著迷。我將它們視為對人性最為直接的反映:人們總是需要相信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存在一些神秘力量,它們在不停地制造謊言。”
至于蘭登教授和自己有沒有共同點,他的回答是:“蘭登教授和我同樣對歷史、符號和密碼著迷,但我們的共同之處僅此而已。蘭登教授擁有更加冒險而刺激的生活,從許多方面來說,他都是我想成為的英雄。”
對他來說,即便成為全球著名的暢銷書作家,生活還和從前一樣。他依然在凌晨4點醒來,坐在新打開的空白文檔的電腦前。他說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并不關心這些書賣出去多少冊,他們與以前一樣,更需要關心和動力。“雖然寫作并未變化,但我的生活卻不可避免地變化了。當然,它們之中的大部分是美妙的。我享受著那些能接觸到私人研究和專家材料的新渠道,那些令人興奮的旅行和探索,以及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慈善活動。說到底呢,我失去的也不過是自己的隱私而已——你失掉了自己甚至是家人的隱私權,這又怎么會是件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