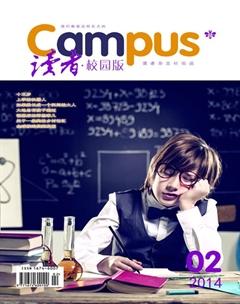大丙出頭記
劉墉

編者按:青春是葳蕤絢爛的夏花,青春是悠揚動人的歡歌。盡管時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個人都有過不一樣的流金歲月。近期,我們約請了一些知名學者、媒體人、專欄作家,撰文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和廣大讀者朋友們一道分享他們的青春之歌。我們從2013年第14期開始,連續刊發,敬請大家關注。
去年秋天,我回母校成功高中演講,場面挺熱鬧。演講前校長先請我去他的辦公室休息,并贈我紀念品一份,是個精美的大夾子,打開來赫然出現一排排數字,竟然是我高中三年的成績單,我定睛一看,差點鉆到桌子底下。因為我高一的平均成績是“丙”,高二、高三也差不多。
我把成績單接過,向校長及在座的主任們致謝,心想:你們可真會送禮!干脆把我的成績單裱褙裝框,掛起來好了!對那些成績差的學生一定有廉頑立懦之效。
我的成績很爛,妙的是,我在學校從來都很神氣。老師可以一邊罵我不上課,一邊對我豎起大拇指,那是因為我課外活動表現好。
才進高中,我就代表學校參加全臺學生美展,拿了第二名,這打破歷年紀錄,因為當時是大學和高中一起比賽,第一和第三都是師大美術系的,就我這個小蘿卜頭位列前三,而且學畫不過幾個月。美術老師說得有理:“你雖然畫齡很短,但是很敢畫,噼里啪啦,大筆揮幾下,把評審唬住了。”
他的話一點也沒錯!我天生少根筋,也可能多根筋,很大膽!
學校有個池子,水干了,別人都不敢下去,說有青苔,危險!我不怕,縱身一躍,發覺自己躺在那兒,才不到半秒,怎么躺著了?離后腦勺一寸,正有一塊尖尖的大石頭。
督學來校考察,我前一天探聽到,就去買了十幾根蠟燭,后排的同學每人點燃一根,以“秉燭日讀”表示抗議。因為學校的電費分賬,日間部除了黑板上面一排燈,后面全黑,只有夜間部才能用。碰上烏云蔽日,教室后面很暗。
當天只見校長笑吟吟地跟著督學走過,看見我們,突然每個人都睜大眼睛,校長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全不見了。督學才走,訓導主任就怒氣沖沖地跑來問是誰干的好事。聽說是我,又轉身走了,偷偷把我叫去,說有話好說嘛!
隔天后面的燈就亮了,而且從此全校皆亮,這次“舉義”使我除了頭上有光,連走路都生風。
有人說訓導主任怕我。他不是怕我,是怕我去外面亂說話。因為我當時編校刊,常往“救國團”跑。主任不怕“教育部”,卻怕“救國團”,據說他能不能升為校長,全看團里的意思。所以當我對團里講因為主任支持,這期校刊的厚度將加倍,主任聽說后,就會想盡辦法增加校刊的預算。
編校刊影響了我一生。因為我除了征稿、審稿、校對、畫插圖,還得“補天窗”。每次主任說某篇東西有“早戀暗示”或政治批評,不能用,我就得立刻把那空下來的地方補上。寫論文太累,寫散文太慢,最快的就是寫“詩”。一個字加個嘆號,也算一行,所以我開始寫現代詩。后來還把作品拿給一位曾經帶頭打美國“領事館”、被留校察看的老師看。
那老師就是名聞中外、今年以百歲高齡過世的現代詩元老紀弦先生。
紀老扶著他的煙斗,瞇著眼看我寫的“紅樓夢里有個探春,我才是真正的探春,我是最早的探春者,我探最早的春”。啪!把煙斗一拔,往桌子上一磕,說:“好!有味道!”
我又拿給國文老師看,他也瞇著眼,看半天,斜著臉說:“惜春吧!惜比探有意思。”
我寫詩,除了“補天窗”,還有個原因,是有一回代表學校參加民辦的演講比賽,有位私立高中的代表,由“演講老師”擬稿。看到他的演出時,我眼睛一亮,他不但音調抑揚,連手勢都如行云流水,美極了!比賽結果,他拿第一,我拿第二。
我四處打聽那是何種流派,有人說叫朗誦詩。從此我就四處找朗誦詩的題材學習,也試著自己寫。沒多久,我參加官辦的全省演講比賽,便發揮所學,“硬把式”加“朗誦詩”,剛柔并濟,拿回第一名。這還不夠,后來我編寫并導演的朗誦詩,4次拿下全臺競賽冠軍。而且大學沒畢業,就應聘在大學教詩。
我對詩有心得,還有個重要的原因:高二上學期,有一天半夜我覺得胸悶咳嗽,咳著咳著,咳出一口血,接著一口又一口,吐了小半盆,進醫院看急診,已經是肺結核中期。醫生把我娘罵了一頓,讓我立刻辦休學手續回家靜養,否則活不長!
我沒靜養,反而得其所哉,畫我的畫、寫我的詩、讀我的書。我后來的好多強項,都是那年“閉關”練出來的,大有打通任督二脈,功力增加一甲子之感。所以,我后來常說只讀課本不夠,因為你會的別人也會,反而課外涉獵的東西能讓你出頭。而且人生最浪漫的時候,是青少年時期,中國孩子多半的創意被埋葬在教科書里,等到年長有暇,卻時不我與,失去了少年情懷。我有幸因病休學,沒了功課壓力,正好海闊天空地進行創作。
我的海闊天空也得感謝高中的國文老師和美術老師。有一回上國文課,我站起來讀課文,把一個字念錯了(那要怪我娘,是她一直都念錯)。結果一整堂課,老師都避過那個字,下課鈴一響,就跑回辦公室查字典,下一堂課一進門便糾正我,還很坦白地說害她以為她自己念錯了。
美術老師更棒,她叫我不用上課,去教員休息室自己愛做什么做什么(免得在班上搗蛋)。我每次“移駕”,老師們都去教課,辦公室空空,只有個16歲的女校工,挺漂亮,陪我聊天。我去年回校,她還沒退休,特地跑來校長室跟我敘舊。
我也感謝軍訓教官對我的容忍,有一回教官說美國B-52轟炸機有4個螺旋槳。我在下面插嘴:“5個!”教官馬上改口:“對對對!是5個。”我又笑說:“哈哈!騙你的!”全班都大笑了起來。教官也好像沒生氣,臉紅紅地指指我:“頑皮鬼!”
當時學校嚴禁交女友,抓到就記過。我在外面搞活動,認識不少女生。有一個女生把她在家事課上做的點心拿到學校給我,教官居然非但沒找麻煩,還代為轉交。可惜因為從小我娘就警告:不可吃女生的東西,里面有蒙汗藥。那盒點心我半塊也沒碰,全分給了同學和那位教官。
我雖然自認為很神,常寫文章諷刺功課好的同學,但高考前一個半月還是屈服了,昏天黑地地看書。畢業考成績出來后,我沒上補考名單,高二的學弟之前一個個拍我的肩膀:“老哥兒終于跟我們同班了。”還有人唱:“總有一天等到你。”卻沒想到我過關了。
高考我只填了師大美術系、文大美術系、藝專美術科、藝專美工科和某校國文系。報名表送上去,訓導主任和導師都跳了起來,說:“人家填100多個,最少你也得寫臺大政大的外交系和法律系吧!”我心想:可真瞧得起我!你們不是知道我年年兩科都不及格嗎?我是“大丙”耶!能考得上嗎?我口才雖然不爛,贏了一堆獎杯,可我真愛的還是畫畫和寫作啊!
高考放榜那天,我姨父是記者,早就告訴我考上了第一志愿,但我還是去母校看門口貼出的榜單。問題是在師大美術系下面,左看右看硬是沒看到我的名字,敢情姨父搞錯了?我大駭,擠到榜單前細看,才發現上面有個被原子筆捅出的洞,我的名字就躲在那洞里面。連我的導師見到我都露出詭異的笑:“考那么高分,原來不用功是假的!”
我雖沒在成功中學留過級,卻足足待了8年。3年高中課程、1年休學,大二開始回校教“演辯社”。大學畢業那年,成功中學校長對我說:“如果你分配不到成功中學來,我搶也要把你搶來。”所以我又回校任教了一年。
多妙啊!我這個“大丙”學生。每個老師同學都知道我成績爛,但沒人瞧不起我,沒人否定我的潛能。所以雖然我的作文總拿乙,卻能編校刊;功課總吊車尾,卻能代表學校四處參加活動;搗過一堆蛋,卻半個小過也沒有被罰(全饒了我)。而且我回校任教那年,辦公桌不是在導師辦公室,而是在訓導處主任旁邊。有人說我是“地下主任”,因為主任有事時總征求我的意見,我說他總是栽培我、愛護我,從起初到現在。
去年我回母校的那天,除了演講還帶了6000多本著作,送給每位同學和教職員,又運了幾百本我的藏書捐給圖書館,最近則寫了一幅字給母校。那字掛在校長室,寫的是李白的詩: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