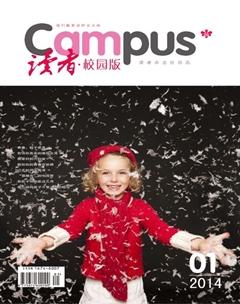來自遙遠星球的孩子
安心

自閉癥(孤獨癥)患兒又被稱為“來自遙遠星球的孩子”。他們降臨地球,靜靜地旁觀著這個世界,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因為長期在盲童學校的自閉癥中心做義工,這些遙遠星球的孩子拉近了我和這個星球的距離。因為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基本的東西并非是人人都需要的。比如一塊手表,對于我來說是用來清楚地告知我時間的;對這里的盲童來說,卻并非必需品,只要吃飯鈴聲一響起,他們就會興奮地從地上爬起來,相互牽引著走向飯堂。
只是,現在的人不僅需要認識時間,更需要知道認識時間的這個載體是不是出自百達翡麗、歐米茄、江詩丹頓、卡地亞等家族。這真是人類在不斷進化過程中的偉大發明——分類標志。
我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基本的概念,也并非普遍、簡單地適用于每個人。
一個盲童問我:“老師,什么是藍色?”我說:“藍色是大海的聲音,藍色是我心情低落時的感受,藍色是薄荷糖入口時的清涼感覺。”“但是老師,什么是顏色?什么又是藍色的鉛筆?”
這就是他們的世界,很多在我們眼里看似重要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卻微不足道;而很多在我們眼里不值一提的事情,對他們來說則神秘無比。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泰國恒久不變的烈日高掛在天空,空氣里黏人的氣息讓我渾身不適。我提著一些甜點像往常一樣走進了盲校。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自閉癥中心教室里的那個男孩。
推門而入,大約20個孩子在教室里的空地上各自活動著。掃視了屋內一圈,我注意到了那天在我旁邊歡喜地聽我唱歌的男孩,于是徑直向他走了過去。
他的名字叫Sonti,15歲,雙目完全失明,并伴有自閉癥。我平時見他時,他要么是一個人低頭獨自坐著,要么是自我陶醉般晃著腦袋。
我蹲下身,坐在他身旁唱起歌,顯然Sonti聽出了我的聲音,往我這邊挪了挪,我順勢握住了他的手。他驀地抬起頭,我又看見了他的微笑。
我遞給Sonti一塊餅干,示意他這是可以吃的。我看到他先是將餅干放在鼻尖聞了聞,然后將一小部分送到了嘴里。
因為失明,所以對眼前的事物會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性,總是以試探的姿態去接觸、去感受,這是大多數失明孩子的共性。
想到這一點,我便主動扶Sonti站立起來,示意他走動走動,他低著頭害羞地笑了笑。
我的左臂伸過去扶著他的左臂,右臂摟著他的右肩,我們就這樣慢慢地前行著。下意識地,我忽然覺得他雖然長期不說話,但聽見我唱小曲時他會有微笑的反應,這是否說明他有認知或者交流的意愿呢?只是長期以來,沒有人真正給過他細微的關懷罷了。
于是我將他帶到道路旁邊的樹叢,慢慢地讓他去觸摸并感知垂落的樹葉,并用泰語問他:“這是什么?喜歡嗎?”
Sonti先是小心翼翼,然后一把抓住。忽地,他說:“喜歡。”而他也一直低著頭,這儼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現。
在Sonti開口說話的那一瞬間,我莫名地激動、欣慰,還有歡喜。這至少證明我的直覺沒錯,這個孩子之所以封閉自己,大部分原因是在早期失明階段缺乏關愛,缺乏指引。
我和Sonti繼續在盲童學校繞圈子轉悠著。我見有些盲童在學校的游泳池里游泳,便主動帶Sonti走近了游泳池。
我讓他先坐在岸邊,將兩只腳淺淺地伸入水里。我靜靜地蹲在他身旁,仔細地觀察著他的一舉一動。我想知道他對水的反應,因為在法國,水療也是一種治療自閉癥的方式。不到3分鐘,我便看見Sonti的面部有些許反應,那是一絲淡淡的微笑,其中摻雜著驚喜、膽怯與好奇。我低下頭,問他:“喜歡嗎?”他答:“喜歡。”我再問:“想游泳嗎?”他答:“想。”總是很簡短的表達,但對他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望望四周,向一個美國義工問,是否可以讓Sonti換上救生衣下水。他點點頭。
就這樣,我看著Sonti換上救生衣下到水里,像在做水中冥想,一聲不吭,一動也不動地浮在水面上。后來幾次,Sonti都是這般在水里一漂就是一個小時。他是對在水里的這種特殊感覺緊張戒備,還是依托于水面找到安全感后有些許放松?我終究無從得知。
最后一天,我離開盲童學校時,坐在車上,遠遠地就看見了Sonti獨自走在道路上。“砰”的一聲,他的頭就這么毫無防備地重重撞上了停靠在道路邊的汽車的尾部。
坐在我身旁的一個英國義工不禁感嘆道,上次她在盲校門口,看見一個盲人自己摸索著過馬路,路邊沒有任何按鈴式的紅綠燈。
另一個丹麥義工也插話,在她的國家,盲道隨處可見,十字路口還專門設有為盲人辨向的音響設施。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我反倒有些說不出話來了,只能靜靜地聽他們講西方國家是如何為身體障礙者提供無障礙環境的。
什么是無障礙環境?我不禁感嘆花巨額的資金去打造地標、樹立城市的國際形象,有時可能還比不上將這些細節做到位。
讓我們看一看,那些公共建筑物的入口臺階處是否有相應的坡道,用旋轉門的建筑是否有專門的盲人通道,公共廁所里是否有帶扶手式的坐便器……
這些都是公益的細節,如果不是親身經歷,親眼見到這些孩子,我是不會注意到他們的需求的。義工旅行,因為經歷,所以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