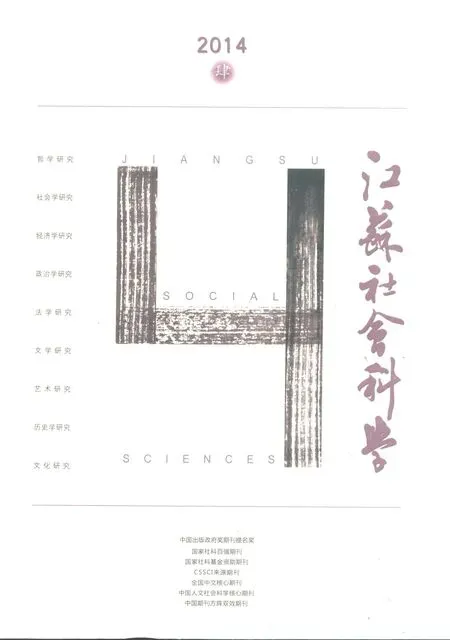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錦標賽”增長模式的來源與演變:一個經濟史分析
王劍鋒 顧標 鄧宏圖 雷鳴
“錦標賽”增長模式的來源與演變:一個經濟史分析
王劍鋒 顧標 鄧宏圖 雷鳴
本文首先對建國以來中共歷次黨代會報告、黨章、五年計劃和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考察,而后分析了改革開放前后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一致性及其經濟擴張模式演變。主要觀點有:第一,地方政府行為內生于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以及中國垂直的行政體制。第二,為了同時涵蓋改革開放前后分別側重精神激勵與晉升激勵的兩類實踐,我們更傾向于采用“錦標賽”增長模式的稱謂。第三,在1979年前后兩個時期中,地方政府所面對的激勵體系及其影響下的基本行為邏輯,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錦標賽增長模式 經濟趕超戰略 歷史來源 比較制度分析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實際執行者,其直接推動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楊瑞龍,1998;林毅夫等,1999;張軍,2005)。然而,隨著地方競爭的不斷加劇,地方政府在產業結構升級、國民收入分配等方面負作用也開始顯現,并逐漸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桎梏(吳敬璉,2008)。
針對上述問題,學界和實務部門主要有兩方面建議。第一類側重于宏觀層面的觀察,比如,李揚(2012)認為,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和產業結構調整應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轉移。江小涓(2008)則提出,應該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水平獲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條件。第二類主要集中于地方層面,認為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是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削弱其粗放型的投資擴張沖動(郭慶旺、賈俊雪,2006)。應該說,以上分析指出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方向,但還存在不足。比如,有關地方政府權力過大的問題我們很早就注意到了,但卻為什么遲遲沒有實現大的調整呢?上述現象暗示,基于某種邏輯的考量,此類地方政府行為或許有其“合理性”。為了切實推進有關體制改革,還應進一步廓清地方政府增長激勵的歷史和制度成因。
在有關地方政府行為的研究中,以“晉升激勵”的稱謂提出但實則兼具“財政激勵”與“晉升激勵”的觀點,得到了較多認可。然而,當前其面臨的一個理論邏輯挑戰是,有研究指出(陶然等,2010),干部考核條例中沒有明確列出經濟增長指標,因而無法滿足錦標賽理論要求的“必需具備明確規則”這一必備條件。但在我們看來,在所謂正式干部考核內容之外,中央政府完全有可能通過其它渠道,以非正式規則的形式,替代所謂的正式規則。具體來說,就是中央主導制定的五年計劃、黨代會報告以及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其中的經濟數量指標,就起到了一種昭示作用。另外,已經實現年度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在無時無刻的向地方官員暗示,中央更關心的是經濟增長。在一個政治集權的體制下,很難想象一個拒絕執行上述文件有關經濟任務的官員能夠獲得很高的政治回報。
二、“錦標賽”增長模式的歷史來源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選擇都會受到資源稟賦因素的制約,但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發展意志”及其政治動員能力,同樣會對經濟發展戰略選擇構成重要影響。下面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通過分析中央政府趕超意識以及垂直行政管理體制的形成背景,來考察錦標賽增長模式的歷史來源。
1.“錦標賽”激勵模式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政治動員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并結合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與制度環境情況,對地方官員實施差別化的激勵模式。在計劃時期,中央政府主要采用的是集體利益宣教式的干部管理方式。在該階段,有兩個因素使其官員激勵模式在具體表現形式上有別于改革開放后。首先,在集體利益至上的氛圍下,實現中央的經濟目標,并不完全為了實現晉升,而是為了完成政治任務,獲得組織認可等精神層面的回報。其次,官員與普通職工間的綜合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官階職位在物質刺激方面的吸引力比較弱。為此,我們可將該階段稱為“為集體利益而增長”的精神激勵模式。應該說,這一階段的激勵保持了相當大的強度,就實際表現而言,既包括以“大寨精神”為代表的一大批真典型,也包括在氣力用盡、力所不逮情況下為求上級認可的“爭放衛星”行為。在市場化階段,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得到承認,激勵模式逐步轉向“為個人晉升而增長”。但無論如何,垂直管理的政治組織以及上級動員為主的激勵模式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建筑其上的“錦標賽”增長模式也保持了穩定。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晉升錦標賽”理論僅僅將職務升降作為博弈支付的假設,并不能涵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治實踐。為此,我們將地方官員的支付進一步拓展為政治收益。這種政治收益在計劃時期主要表現為精神方面的獎勵,而在改革開放后,隨著意識形態和制度環境的變化,作為博弈支付的政治收益則進一步變形為職務晉升。
2.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及垂直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來源
新中國成立后,主要有三類因素促使中國政府確立了趕超型發展戰略:一是冷戰格局形成后的國際軍事威脅,逼迫中國必須盡快提高經濟軍事實力;二是自1840年以來持續百年“挨打受屈”的歷史,使得中國社會積蓄了謀求富強的強大能量,并進一步轉變為作為執政合法性基礎的“統治績效”要求;三是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功經驗的示范效應。應該說,盡管不同時期出現了一定的起伏,但總的來看,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線。具體來說,從1949-1978年期間,國際軍事威脅具有重要影響,這就逼迫中央政府必需設法在短期中建立相對完整的國防重工業體系。而隨著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改善,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則更多的來源于執政績效的需要。
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系方面,中國是一個有著濃厚集權歷史的國家。張明庚和張明聚(1996)的研究發現,中央集權在中國始自秦始皇“廢除分封推行郡縣制”的改革。自此之后,各朝各代在地方行政區劃上雖然有所變動,但其目的都是為了加強中央政治權力的集中度。而自清末開始,因農民起義而出現的湘軍和淮軍團練制度,使得中國的分離主義抬頭,并逐步演變成軍閥勢力(鄧宏圖等,2013)。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手段重新實現了政治統一,中國再次進入到一個集權化周期。具體來看,自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開始,在各個版本的憲法中,無論其它部分如何修改,有關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論述都始終沒有變化。基于這一前提,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領導權,就具備了法統上的合理性。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政治關系以此為依托,并進一步通過黨章中有關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地方委員會之間權力安排的規定體現出來。我們通過查閱從一大到十八大之間的黨章發現,各個版本的時間維度與其中“中央與地方權限安排的明確化程度”基本契合,并可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一大到八大,這一期間的黨章明確了兩點:一是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二是在有關“紀律”部分明確指出,下級必須服從上級指示[1]六大雖然將中共明確共產國際支部,并未改變中共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安排。。其次,從九大到十一大所對應的黨章中則進一步指出,地方和軍隊各級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黨委會的人選,都必須經上級黨委批準。第三,從十二大到十八大,黨章明確規定“在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并一直延續至今。
盡管在以上三個階段的黨章中,有關中央與地方委員會間的權屬關系安排,在表述的精確程度上有所不同,但總的來看,中央都對地方委員會具有明確的指導管理權。最近的黨章規定則更為清晰的展現了上述關系。考慮到地方委員會往往五年才召開一次,每次僅約一個星期左右。因此,面對絕大部分時間處于閉會狀態的地方委員會,中央能夠指派其負責人的制度設計,使得中央對地方黨委人事安排事實上具有了直接管理權。在此基礎上,中央委員會和地方黨委又進一步通過對同級人代會的組織領導,獲取了對行政機構施加重要影響的權力。這一機制從中央到省再到市、縣、鄉的延續,就構成了所謂“垂直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架構。
3.中央政府的經濟趕超意識及其傳導機制
經濟增長任務未必體現在官員考核條例中,但完全可能通過其它途徑以非正式規則的形式表現出來。歷次的中共黨代會報告、五年計劃以及國務院工作報告,事實上都是傳達“中央意志”的重要渠道。中共一大到七屆二中全會,主要側重于自身組織建設以及政治軍事斗爭,較少提及全國性經濟戰略規劃方面的內容。因而,本文主要考察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代會報告。
表1顯示,只有中共九大報告基本沒有提及經濟建設任務,其他報告則大都明確列舉了數量化的目標。另外,在九大召開的前后幾年中,雖然文革等政治事件對經濟戰略帶來了沖擊,但至少從經濟總量增長情況看,這些事件并未改變中國的趕超戰略。20世紀50年代制定的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在整個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前期沒有被廢棄。
在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方面,由于受到政局動蕩、自然災害等影響,在1954至2012年間,有13個年度沒有召開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因而其對應的政府工作報告缺失[2]這13個年份是:1961、1964、1966-1974、1976、1977。,其它年份則均有正式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同時,并非每年都設定總產值或GDP的增速,有些年份或以同期五年計劃中年均增速代替,或以農業和工業重要產品的產量指標增速代替。明確提出當年總產值或GNP和GDP增速的有26個年份。
從黨代會工作報告中涉及經濟的主要內容,以及歷次五年計劃和歷年的國務院工作報告這三方面材料看,它們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特征,即都是圍繞著各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共同發揮著中央昭示經濟增長任務的作用。而各個五年計劃中對于經濟增長指標的設定,又是受到了中央政府“趕超意識”的影響。在這一背景下,具有趕超意識的中央政府,通過垂直行政管理體制,促進經濟增長的“錦標賽”增長模式由此形成。與此同時,中央對經濟建設任務的要求在一定時期內也一度明顯升級。具體來說,中央政府不但要求“在二五期間,在全國建立強大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還強調“各協作區都應當建立起比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點的工業體系,各省、市、自治區也都應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以便發揮地方參與經濟建設的主動性(武力,2010)。上述安排不僅導致重復建設,更是增強了地方政府經濟增長任務的剛性,并最終加劇經濟短缺。

表1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中涉及經濟增長任務的內容

表2 中央政府工作報告

表3 各個五年計劃的增長目標
事實上,中央政府甚至對經濟增長任務的下放及其放大機制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指導。比如,在1958年1月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除了在第二條中明確將工業數量指標置于工作首位外,還通過第十一條“各地工業產值爭取在五年、七年或者十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的規定,明確了工業優先的地位。第五條“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每年看前冬”、第六條“一年至少檢查四次”,以及第七條“省和省比,市和市比,縣和縣比,社和社比,廠和廠比,礦和礦比,工地和工地比”的規定,則明確了中央監督指導下的競爭機制。另外,第九條要求在生產計劃中要建立所謂的“三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如此的三本賬制度,更是打開了層層加碼、追求高指標的渠道。
三、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一致性及其經濟擴張模式演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有四方面因素影響著地方政府行為:一是國際環境和意識形態因素,二是行政(財政)分權因素,三是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四是中央對地方官員的垂直管理及考核制度。其中,后兩個因素具有中心和樞紐作用,也是導致地方政府行為邏輯在改革前后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關鍵。在垂直的政治管理體制下,中央政府無疑會利用其對地方官員的影響力,通過提高地方政府的增長激勵促進有關發展戰略的實施。這一邏輯與計劃或市場的體制背景無關。
1.計劃和市場兩種體制下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一致性
從表1、表2和表3中提供的資料看,盡管在一些時期中央政府曾因經濟過熱而采取了壓低增長指標、限制地方權力的措施,但就總體而言,中央政府選擇了一條以高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在經濟任務制定中采用了“防冷為主、防熱為輔”的原則。在體現上述意圖的各類報告和文件影響下,地方政府自然會傾向于采取高增長的措施,同時由于不需承擔主要的宏觀經濟穩定責任,地方政府更“偏好防冷而忽視防熱”。為了調控中央與地方間經濟行為不一致性帶來的問題,中央政府會不斷交錯采取“放權”與“收權”措施,并帶來所謂“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象。雖然在計劃和市場兩種體制下,由于市場化程度存在巨大差異,中央地方間分權安排的宏觀經濟影響會有所不同,但地方政府偏好擴張的基本邏輯并沒有改變。
從新中國成立后60年多歷史的整體看,后三十余年中對市場放權的力度獲得了空前提高,然而,中央與地方間的放權與收權循環依然在延續。為了更為集中的對比獲得權力情況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行為邏輯,在前三十年中,我們特別選擇了1958-1960年以及1969-1972年這兩個權力下放時期;在后三十年中,我們選擇1998-2003年以及2008-2010年作為分析地方政府行為一致性的典型案例予以分析。
在計劃時期,生產經營行為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因而這一時期中央對地方的放權,主要是圍繞對國有企業生產和投資計劃等方面的管轄權而展開。1957年底,為了解決中央集權過多制約地方靈活性和主動性的問題,國務院頒布了一系列向地方放權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下放計劃權力。第二,下放企業管轄權。第三,下放財政和稅收權以增加地方的收入。第四,下放投資和信貸的審批權。第五,下放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和勞動管理權。1969-1972年是中央政府在計劃時期的第二次大規模放權。除了試圖改變中央統得過多、過死狀況的原有動機外,戰備形勢是另一個重要因素。1970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把全國劃為10個大協作區,各自建立工業體系,自己武裝自己。為此,中央把曾因經濟整頓而回收到中央的經濟管理權力再次下放給地方,具體包括:對地方實行三個“大包干”、計劃體制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給地方以較大的管理權限。上述放權安排對國民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就其積極的方面來說,除了大幅促進了總量指標提高外,在工業結構領域主要有四點:一是重工業部門在這個時期得到了明顯加強。二是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有了加強,技術水平有了提高。三是除了明顯促進了國防軍事工業的發展以外,地方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都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武力,2010)。四是農村工業第一次有了迅猛發展[1]雖然這些企業大部分在調整時期下馬,但畢竟為后來的社隊企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善,中央對地方放權的具體形式出現了一定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國有企業的管理權不再是中央對地方權力收、放的主要內容。但在投資審批與融資的控制方面,雖然也有所變形,但基本延續了計劃時代的特征。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在通過對地方報送項目施加“審批標準與審批速度”的控制,來影響地方政府行為;另一方面,雖然信貸審批權不再成為權力收放的主要內容,但卻在“改頭換面”后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對地方融資平臺放松或控制的選擇。就1998-2003年期間來說,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央政府果斷采取措施,在投資管理方面,由當時的國家計委牽頭專門成立了“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領導小組”,采取集中辦公、聯合評審的辦法,加快審批進度(劉國光,2006)。而在融資方面,中央政府在1998年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中,明確將500億元轉借地方,這與另外500億中的中央補助地方投資的建設項目,重新賦予了地方較大的財力。不僅如此,中央政府還要求銀行為國債項目提供配套貸款。由于國債資金領域投向為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這就通過鼓勵“地方融資平臺”變相下放了信貸管理權,從而為地方的投資與經濟增長沖動提供了資金支持。而對2008-2010年這一期間來說,在項目審批方面,雖然并未再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加快項目審批的決定,但無論是從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擴大內需十大舉措中“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鐵公機’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來看,還是根據“發改委門前車水馬龍”的媒體報道判斷,當時中國再次出現了審批標準放松和審批周期的提速[2]吳婷,發改委門前人頭攢動4萬億投資吸引眾企業,上海證券報2008年11月12日。。與此同時,中央也再次放松了對地方融資平臺的控制,2009年3月央行和銀監會聯合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3]當然,2010年初經濟在大規模經濟刺激下重現過熱苗頭時,中央政府又于當年6月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開始從商業銀行發放貸款以及有關平臺成立兩個方面,限制融資平臺的發展。。
2.地方政府經濟擴張模式的演變
中國整體的工業化模式選擇受到資源稟賦、國際環境、中央政府意志的共同影響,而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經濟增長的放大機制方面。在1949-1978年期間,基于國際軍事威脅和相對封閉的國際經濟環境等條件,中央政府選擇“以內部循環為特征”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有其合理性。在垂直管理體制與計劃體制預算軟約束的共同影響下,地方政府增長激勵就具體表現為對各類商品和物資的“獎入限出”上,紛紛通過爭投資、搶項目,在建立本地獨立工業體系的同時實現對重工業優先模式的進一步擴張。周飛舟(2009)曾指出,大躍進時期是一個短暫的舉國錦標賽時期。這場錦標賽無論在涉及的范圍、競賽的程度、配置的資源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各方面都空前絕后。
從70年代末開始,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對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認識也開始獲得突破,在經歷了改革初期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驗不成功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開始轉而實行增量改革戰略,把主要精力放在非國有經濟方面。但受左的思想影響,中國政府在改革之初對外資實施了較為“苛刻”的條件。在上述背景下,我國在增量改革中的所有制類型的選擇上首先側重了集體經濟。所有制變化與放權讓利后居民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補償性增長相結合,共同催生了以輕工業為產業重點的鄉鎮企業發展。而到80年末后,隨著國內改革的體制效應發揮殆盡以及信貸分配中結構性問題的日益突出,鄉鎮企業在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方面逐漸顯露出了一些不足。因而,依托發達國家對外轉移一般制造業的背景引進加工貿易型外商投資,便成為接續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選擇。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給予加工貿易類外資企業的優惠力度顯著提高。基于上述環境變化,地方政府的外需依賴度及對外資的偏好明顯升級,對“資本要素獎入限出”而對“一般商品則獎出限入”的政策力度不斷提高,進一步放大了工業化模式的出口導向型程度。
四、“錦標賽”增長模式的持久性及其變遷路徑的比較制度分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盡管經歷了幾次集權與放權的循環往復,但錦標賽增長模式在中國表現出了持久性,并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格雷夫(2008)的說法,要想讓制度持續存在,就必須能夠自我再生。而且,只有當那些促使、引導和激勵個人行為的規則和信念,與觀察到的行為或結果不相矛盾時,制度才能真正實現自我再生。格雷夫(2008)和青木昌彥(2001)均堅持系統化的制度觀,也都將博弈論引入到制度分析當中。只不過,青木昌彥認為制度是博弈均衡,并通過所謂的關聯博弈將社區規范解釋為一種內生性的結果。而格雷夫則在綜合“制度演化視角”與“有目的創建視角”的基礎上,認為制度不是博弈均衡,并在對“核心交易”與“輔助交易”進行區分后,通過分析交易間關聯,強調了輔助交易在強化核心交易參與方共同信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從錦標賽增長模式所處的制度體系的實際構成看,其核心交易是地方政府履行中央政府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要求,輔助交易則是中央對地方官員的獎懲制度。而支撐上述關聯交易的組織則是中國共產黨垂直的政治管理體制。六十余年來,作為核心交易的地方增長動力之所以始終存在,則主要是因為用以支撐輔助交易的組織基礎,即中央地方間垂直的政治管理體系并未伴隨國際條件及經濟水平的變化而進行大的調整。具體來說,主要有兩個因素保證了該垂直體系的自我實施性。首先,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了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其內部組織結構也保持了相對穩定。其次,中央政府始終保持了強大的財政汲取能力,這使得中央政府能夠保持對地方政府較強的財政控制能力。在計劃時期,中央政府可以籍由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汲取到其所需要的經濟資源。改革開放政府實施放權讓利改革后,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雖然有所下降,但中央政府卻通過對國有銀行體系的控制,獲得了因私人部門收入增長而出現的金融剩余,并作為財政汲取能力的一種變形使得受到各種沖擊的情況下中央地方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仍能保持穩定。
中央地方間的垂直政治關系之所以能保持穩定,一方面來源于所謂“整頓治理的運動型機制,延綿不斷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動”(周雪光,2011);另一方面則來源于中共發展史上的特殊實踐,比如,中共始終堅持了“對前一代最高領導人主要給予正面評價”的傳統,而并未像蘇共那樣因頻繁上演“現任否定前任”的黨內斗爭使其在民眾當中的威望損失殆盡[1]比如,斯大林有其專斷的一面,但也在衛國戰爭中建立了卓越功勛。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徹底否定,雖然解決了大量歷史冤案,但如此過激的做法在客觀上也削弱了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同時,文革讓很多老干部通過含冤受屈、深入思考改革、帶頭支持改革,以及文革促進了社會各階層交流與融合的角度(劉國光,2006)。這在客觀上起到了使得社會階層扁平化的作用,并使中共及中國的改革具有較少的阻力。上述歷史過程無疑會強化和維持地方官員“遵從中央政府意圖”的信念,也可以認為是導致中國的“錦標賽”增長模式相對成功的特殊因素。從國際比較來看,后進國家在經濟趕超過程中,為了克服所謂的“后發展癥候群”(任曉,1995),必須要有一個強政府來主導,這與采用何種政治制度無干。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因國情不同,具體發展路徑和結果也有所差別,并引致不同的結果。其中有日本、韓國這樣的成功案例,也有拉美等國家相對失敗的情況。曾被黃亞生(2011)用來證明中國模式不可持久的巴西發展模式,雖然采取了“軍方+專家”組合模式的威權體制,但由于巴西軍政府并不具備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動員能力和自我調適能力,才使其干預下的經濟奇跡僅僅持續了十幾年。
在轉型路徑的選擇方面,格雷夫(2008)在吸收舊制度主義的演化視角以及新制度主義有目的創建視角的基礎上認為,內生的作用過程、外生沖擊或者兩者的共同作用,可以引起制度變遷。上述判斷意味著,中國的制度轉型除了應遵循制度自我演化的規律外,發揮關鍵人物在特殊歷史時刻的能動作用也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目前積聚起來的“改革共識”,并將其作為降低改革阻力的基礎,推出若干能夠帶來“當前制度自我削弱”過程的改革。考慮到地方政府是各項政府工作的直接實施者,因而上述改革的核心,應該是改變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參數集。在我們看來,參數集中的要素或維度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錦標賽增長模式運行的制度環境;二是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偏好的共同信念;三是“鼓勵生產而不是消費”的稅收制度以及地方政府擁有過大自由裁量權的土地管理制度。但也要注意到,為了降低改革難度,應首先著力推動那些影響當前制度的準參數的變化。在我們看來,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家庭比重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隨著居民收入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才能為一系列制度改革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縮小原有制度自我實施的參數集范圍,并最終觸發“制度自我削弱”的過程。盡管提高中等收入居民比重同樣需要克服一些困難,但以此為階段性目標的調整過程,總比動輒劍指所謂遠景目標的改革在難度上要小一些。
五、結語
本文首先對建國以來中共歷次黨代會報告、黨章、五年計劃和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考察,而后分析了改革開放前后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一致性及其經濟擴張模式演變。本文的主要觀點有三個:第一,地方政府行為內生于中央政府的趕超意識以及中國垂直的行政體制。第二,為了同時涵蓋改革開放前后分別側重精神激勵與晉升激勵的兩類實踐,我們更傾向于采用“錦標賽”增長模式的稱謂。第三,在1979年前后兩個時期中,地方政府所面對的激勵體系及其影響下的基本行為邏輯,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不過,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國際條件下,地方政府經濟擴張的模式選擇會出現變化。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運用比較制度研究方法,分析了“錦標賽”體制的穩定性及轉型問題。
總的來看,要糾正地方政府的不良增長激勵,首先應從削弱中央的趕超意識做起。為此,中央政府在“五年規劃”、“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黨代會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應果斷降低甚至取消經濟增速目標,并通過“加強民生及社會公正建設”緩解政府體系的執政績效壓力。此外,還要通過相關體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當然,對相關改革方略的討論,仍需慎而又慎。盲目推出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不僅不能包治百病,還可能事倍功半。無論是一些亞非拉國家推行“嫁接式”政改后曾被預期的“社會正義”并未實現的事實,還是日本明治維新取得成功而中國戊戌變法卻走向失敗的近代歷史都表明,無論何種改革方案,為了切實推動經濟與社會的轉型與進步,保持中央政府強大的政治組織動員能力與財政汲取能力都是必需的。
自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共領導集體已經確立了強力推進改革的總基調,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是,如何找到改革的抓手,通過實施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措施,倒逼出能夠帶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改革。我們認為,除了在長期中應著力促進中等收入居民比重提高這一“準參數”的變化以外,在短期中則主要有兩個改革抓手:一是預算的透明化,不僅公布類、款級科目,還要公布項、目級科目。不僅要公布經常項目預算、基金預算,還要公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甚至社會保障預算。在已推出預算支出的功能分類科目體系上,要盡快推行財政支出的經濟分類科目,讓公眾能夠看到某筆支出履行了何種功能、購買了什么物品或服務。通過輿論和社會壓力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讓群眾知情,讓普通民眾更多的參與到經濟目標中“又快又好”之間的權衡當中來。二是對《土地管理法》與《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進行適當修改,限制地方政府對土地征收成本和基價設定方面過大的自由裁量權。
參考文獻
[1]格雷夫:《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8頁。
[2]郭慶旺、賈俊雪:《地方政府行為、投資沖動與宏觀經濟穩定》,〔北京〕《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3]黃亞生:《“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頁。
[4]江小涓:《中國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5]李揚:《經濟轉型有很多誤區》,〔北京〕《財經國家周刊》2012年第13期。
[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2頁。
[7]劉國光:《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頁。
[8]錢穎一、許成鋼:《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M型的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北京〕《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3年第11期。
[9]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54頁。
[10]陶然等:《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北京〕《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11]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頁。
[12]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卷)》,〔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534頁。
[13]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兼論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行為》,〔北京〕《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14]張軍:《為增長而競爭:中國之謎的一個解讀》,〔濟南〕《東岳論叢》2005年第4期。
[15]張明庚、張明聚:《中國歷代行政區劃(公元前221年-公元1991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4頁。
[16]周飛舟:《錦標賽體制》,〔北京〕《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
[17]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北京〕《經濟研究》2004年第6期。
[18]周雪光:《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廣州〕《開放時代》2011年第10期。
[19]任曉:《韓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責任編輯:天則〕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ampionship Mode of Economy Expansion: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History
Wang JianfengGu BiaoDeng HongtuLei Ming
Based on collecting the data of the previous five-year plan and reports of NC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paper studied the consistency on the economic expansion mode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logic and its ev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ree main ideas as follows:firstly,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comes out of the catch-up consciousnes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features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econdly,in order to cover two class of practice focused on spiritual incentives and promotion incentiv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we tend to use the title of championship mode of economy expansion.Thirdly,before and after 1979,the basic logic of behavior-incentive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did not change fundamentally.
championship mode of economy expansion;economic catch-up strategy;historical causes;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王劍鋒,對外經貿大學應用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100029
顧標,上海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200433
鄧宏圖,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300071
雷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300071
本文系對外經貿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CXTD4-04)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