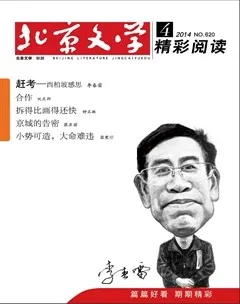小勢可造,大命難違
一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是之在《龍須溝》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程瘋子。他當時只是一個23歲的青年人,可是演出卻“一炮打響”,演絕了,譽滿全國,被北京市文聯正式嘉獎,獎品是一套灰色布質的中山裝。他的表演還被評價為:“這出戲是奠定了北京人藝的基礎,也奠定了于是之的基礎。”顯然,這里是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道路的藝術基礎。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那時,是之不但跑到龍須溝邊上老街坊們那里深入生活,還要天天都寫一篇有心得感受的“演員日記”。由于他非常熟悉城市的平民生活,在排練開始以前就充分發揮了想象力,勇敢地、創造性地寫出了6000多字的“程瘋子自傳”,把程瘋子的家庭、地位、經歷、文化、性格、思想、感情……一一細致入微地道來,而且交代出這個有錢人“外家”生養的兒子,以及自己母親的悲慘命運。最后他們又是怎樣完全破落下來,他萬般無奈地淪落在天橋撂地賣藝,過著屈辱、貧困的日子。因此,真實可信地寫出了程瘋子整天“瘋瘋癲癲”的個人原因、家庭原因和社會原因。這個自傳完全可以當作優秀的短篇小說來讀,不但受到了導演焦菊隱的充分肯定,更受到了劇作者老舍的高度贊揚。大約,從這個戲演出起,是之就已經算是“成名成家”了吧?
二
然而,好景不長,道路坎坷曲折。僅僅三年以后,是之在《雷雨》中扮演大少爺周萍,由于對生活不夠熟悉,難以展開想象力,而碰到了“鬼打墻”。如他所說:“‘程瘋子’成功了;后頭就是《雷雨》的周萍,慘敗。足見演員是驕傲不得的。《龍須溝》里的人物幾乎都是我童年時的街坊四鄰,《雷雨》里的就不行了,特別是周家的人,他們從未在我的生活里露過面。為了排戲,也找了一家名門望族去看了幾次,談了談,只覺得聽著新鮮,引不起我任何舉一反三的想象來。戲組里的同志們也用他們所記得的生活啟發我,同樣無效。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就像一塊濕劈柴,怎么也燃不起火苗來。”后來,戲組的工會小組在每周“工會日”里,都要拿是之當作重點,幫助突破表演創作上的難關,這種“隔靴搔癢”式的幫忙,只能越幫越忙,最后到了無路可走的可怕又可悲的地步。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是之竟然對導演苦苦哀求說:“干脆你教我吧,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最為嚴重的時候,他排起戲來由于緊張而站位不對,導演硬是上場用手大力掰動著演員的雙腳,而且根本沒有掰動。于是,是之羞愧難當,面紅耳赤,連連搖頭,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想想看,是之是一個要求自己很嚴格,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如何受得了如此的對待啊?在這種情況下,是之完全喪失了排戲、演戲的信心,他甚至出現了要馬上辭職,改行去做共青團工作的念頭,認為自己“根本就不是塊能演戲的材料”。甚至,是之還極為難過地認為“自己這么年輕就成了浮名過實的沒有出息的人……”他實在是不肯也不敢再想下去了。此刻,是之在表演創作的道路上,已經跌入了慘不忍睹的低谷。人生莫測,風云突變,確乎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三
有人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很可惜,是之是經過了長長的“六年半”之“冬天”,才迎來了“春天”的。那是1957年,在梅阡根據老舍小說改編的劇本《駱駝祥子》完成以后。是之看了劇本,就熱血沸騰,忍不住地躍躍欲試了。他并沒有申請扮演主要角色駱駝祥子,而是立即寫了申請扮演次要角色人力車夫老馬的報告。同時,申請報告的字數并不比老馬在戲里的臺詞字數少,其中已經包括了他對人物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豐富想象和全面理解。是之經過藝術創作上的迂回徘徊以后,終于欣喜若狂地再一次找到了“大海里游泳”的美妙感覺,再一次找到了當年扮演程瘋子以前的那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和激情。是之早在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住在北京城的—個大雜院貧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院子里就有一位拉人力車的車夫,胡同的附近就有—個專門租給車夫人力車用的車廠子。是之正是和鄰居拉人力車的車夫們朝夕相處,共同生活,知己知彼,非常熟悉的。那些車夫們有個“請會”組織(一種民間自發形成的經濟互助形式,大家把血汗錢集中起來,以解決窮哥兒們一時的急需之用),一當要發個通知,記記賬本的時候,就都要找是之——大雜院里少有的“知識分子”,過去幫忙抄抄寫寫。為此,是之又一次在深厚生活積累的啟發、激勵下,全身涌動著飽滿的、熱烈的、不可多得的創作熱情與靈感。他甚至覺得如果不扮演老馬,不把這個自己熟悉的人物送上舞臺扮演好,那就會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痛苦感覺折磨自己,也愧對當年的那些老鄰居們、那些同甘共苦的窮人們。是之所以看中了小角色老馬,大約有這樣兩個重要原因:首先,是對這樣的人物有著熟透了的生活積累,可以充分展開想象力的翅膀高飛遠行;其次,看中了人物身上那些難能可貴的哲理性,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完全可以塑造成能夠入詩、能夠入畫的藝術形象。是之在創造老馬形象的時候,真有一種得心應手的感覺,從外部形象,到內部形象都是如此;從一舉手,一投足,到一個表情,一句臺詞,無不引發出觀眾的豐富聯想和深刻感悟。這個只有兩場戲,二三十句臺詞的小角色,最后在舞臺上呈現出來的藝術容量,是能夠寫出一篇出色的短篇或中篇小說來的。戲劇評論家稱贊為:“難能可貴的是,這里于是之從生活走到生活,而不是從后臺走到前臺。他的身后,有著一片可以引人充分聯想的生活空間啊。”是之也說過這樣十分動情的話:“老街坊車夫老郝叔早已作古。他無碑,無墓,所有辛勞都化為烏有。他奔波一世,卻仿佛從未存活在人間。說也怪,人過中年,閱人遇事也算不少,但對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記,總覺得再能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一次,評論家問:“比較而言,你更喜歡自己創造的哪個角色呢?”是之想了想回答:“《駱駝祥子》中的老馬還好一點吧。”
四
是之乘扮演老馬的東風,接著又迎來了一個嶄新的局面。1958年的春節,北京人藝上演了老舍的新作《茶館》,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從《茶館》剛剛交稿的時候起,是之就深深愛上了這部戲,并且積極申請扮演主人公王利發掌柜。他說:“我特別喜歡《茶館》。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還有,它美。”“我覺得在還能演戲的時候,演上《茶館》這樣的劇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別的事,我都知足了。”他繼而更十分坦率地表明:“我狹隘地不喜歡高貴的、情節太多的作品;喜歡以性格為主的作品,覺得后者更真實些;不喜歡浪漫主義而喜歡現實主義。因此,在戲劇上,喜歡《龍須溝》《茶館》。不是不想更開闊些,但始終未能突破。這大約與身世有關。或者可以說,從《龍須溝》到《茶館》塑造了我。”是之扮演的王掌柜是繼扮演程瘋子、老馬之后,又一次獲得了可喜的成功。如果說《茶館》是一曲人生的交響樂的話,是之扮演的王掌柜就是這交響樂的靈魂。在《茶館》首演的當天夜里,老舍看完戲以后興奮不已,回到家中夜不能寐,坐到寫字臺前大筆一揮,為是之留下了這樣的墨寶——“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幾乎?”然而,更令人沒有料到的是,是之收到這條幅以后,竟然一聲不吭地鎖進抽屜里,既沒有向旁人顯露,更沒有裱起來掛在墻上,連平時接觸比較多的朋友也一無所知。而且,這一鎖就是30個春夏秋冬,如同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同時,是之卻是這樣談到了《茶館》的藝術魅力之所在:“這個劇本寫得‘真’,就像老舍先生為人那樣‘真’。老舍先生是結交三教九流的,他是精通世故的,他不精通世故寫不了《茶館》。但老舍先生對人對事又是非常真摯的,我覺得缺少了這種真摯也寫不成《茶館》。一個老人,精通世故而不世故,返璞歸真,待人特別真誠,我覺得這種品格,就決定了他寫東西不撒謊,不浮夸,不說假話。我們看過老舍先生《出口成章》中的那些文章,他有時不惜用比較刻薄的話反對那些充滿生造的新名詞、華而不實的文章。由于老舍先生有那么一種品格,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頭,就沒有故作多情的東西,沒有矯飾,沒有文字上的做作和雕琢。而且對那種文學現象,老舍簡直是深惡痛絕。但評價他的真實,我不愿用‘提高’‘加工’這樣的詞,倒情愿用提煉或篩選這樣的詞。他的《茶館》,真像沙里淘金一樣,排除了大量沙子之后,找出了本身就有光的那點東西,他既沒有拔高,也沒有夸張。……在第一幕戲里,寫了清末帝、后兩黨的斗爭,結果慈禧勝利了,殺了譚嗣同。這個‘勝利’,是一個多么殘酷、多么腐敗的勢力的‘勝利’。這是一個黑暗的勝利,腐敗的勝利,殘酷的勝利。到底用什么表現這個‘勝利’最合適、最形象呢?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都聽說過什么太監娶媳婦呀,什么某太監真的傳了代呀等等傳說。老舍先生就用了流傳在民間的這些傳說來表現這個‘勝利’。一個太監要買一個15歲的女孩做媳婦,我覺得再也沒有什么比這個最形象地說明慈禧的勝利是多么黑暗,多么殘酷,多么愚昧。老舍先生把這個作為表現后黨‘勝利’的情節,這個情節帶有象征性。它是現實生活,但看著真有些荒唐。它是荒唐的,但又是真實的。看了之后,那種難過不是一般的。老舍有自己的真實,而這個真實不是一般化的。”顯然,是之把《茶館》輝煌創作成就的首功,如實地奉獻給了劇作者。
五
一聲霹靂,“文化大革命”似乎從天而降,人們還沒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就已經來到了身邊。是之剛剛從國外出訪回來,下了飛機,就被關進“牛棚”里,行動失去了自由。理由是他屬于“公安六條”(當時中央規定的有歷史問題的人員)上的“罪名”。人藝過去演出的《茶館》更是成為特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草”,被軍、工宣隊領導人逢會就加以嚴厲批判,甚至破口大罵。是之后來說:“對《茶館》的批判,批判中也點了我的名。我惶恐,我要求自己要‘態度老實’,于是我批判了自己,也批判了《茶館》。假如老舍先生還在,我會坦率地告訴他這些事的。他將怎么對待我呢?大約是寬容,但我更希望受到他的責備,這于我能夠心安。”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之連演戲的資格也根本給取消了。后來,是之自嘲地在葉淺予給他扮演的角色畫像上加以說明,三幅畫——1948年《大團圓》里拉提琴人;1958年《茶館》里王掌柜;1978年《丹心譜》里丁文中。“正好十年一幅畫,很可惜,1968年由于‘文革’中喪失了創作的權利,沒有扮演角色,也沒有可畫之對象。”更加讓人動容的是,是之十分悲傷地說:“‘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我才39歲,就讓人家從舞臺上給轟下來了……當時那種難受勁兒,比讓我去死好受不了多少……”
六
1989年,是之已經63歲的高齡,深感過去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必須抓緊一切機會再多演幾個戲。于是,他毅然主動地申請在我寫的《新居》中,扮演主要角色澹臺文新——一位經歷坎坷的老翻譯家。澹臺文新被打過“右派”,還因為冤假錯案坐過牢,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他不顧年老體衰,依然拼命地把中國湯顯祖的古典名著《牡丹亭》翻譯成英文,準備推向英語國家作專門的介紹,而且堅持要高標準、高質量、高水平,與同年代英國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一比高低。這個為改革開放時代唱贊歌的劇本,就是在是之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寫出來的,他功不可沒。然而,萬萬想不到的是,這個受到觀眾歡迎的戲,剛演出了8場就被上級命令停演了。理由竟然是“劇作者為有問題的知識分子說話,打抱不平”。劇場已經賣出去的票,也讓全部把錢退還給觀眾。是之對此十分不解,我也十分不解,但無奈地只好去執行。事后,上級又改了說法:“這個戲修改以后,還可以演出,并不是大毒草!”是之反問對方:“請你們查查發下來的文件,看看到底是怎么寫的?”為了這場演戲風波,是之已經被折騰得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場。他激動地對我說:“他們真不知道,輕易‘槍斃’一個戲,給創作人員帶來的傷害會有多么的大!”何謂惆悵?大約就是一種面對美好事物的流失的無奈、一種面對痛苦又不得不接受的無奈。是之再次深深地感受到惆悵。
七
老天爺真是不公平,是之這時已經發現自己的身上出現了老年癡呆病(也就是彌漫性腦血栓病)之先兆。具體地說,就是記憶力明顯減弱,伴之以越來越口齒不清的毛病。在北京人藝建院40周年,1992年7月16日的時候,老版《茶館》于首都劇場進行告別演出。應該說,這既是《茶館》的絕唱,也是是之扮演王掌柜的絕唱。那天,不但觀眾席里坐滿了人,就連劇場兩邊靠墻的通道上也都站滿了人。然而,是之幾度忘掉了臺詞。是之說:“兩三年前,我就有了在臺上偶爾忘臺詞的毛病,這逐漸使我上臺就有了負擔。再演《茶館》,久不登臺,我這負擔就更覺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場的熟戲,在舞臺上偏偏屢屢出毛病。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爺那段臺詞,它必須流利干脆,前兩場就已經出了些小毛病了,那一天就自覺要壞。開幕前,后臺特別熱鬧,院內、院外的朋友們紛紛要簽字留念,我就特別緊張。我跟天野同志說:‘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戲,你注意點兒,看我不成了,你就設法隔過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說他‘隨時可以接過去’。幸虧他有了準備,屆時我真就忘了詞,他也就幫我彌補,勉強使我能夠繼續演下去。這以后,不只一處,每幕戲都出漏洞,我在臺上痛苦極了。好容易勉強支撐著把戲演完,我得帶著滿腹歉意的心情向觀眾去謝幕。我愧不敢當,觀眾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熱烈,而且有觀眾送花束和花籃,還有不少觀眾走到臺上來叫我們簽字,我只得難過地簽。有一位觀眾叫我在簽字時寫點什么話,我不假思索地寫了一句話——‘感謝觀眾的寬容。’我由衷地感謝那位觀眾,他賜給我一個機會,叫我表達了我的慚愧。當聽到一位觀眾在臺下喊著我的名字說‘再見啦’時,我感動得不能應答,一時說不出話來……我演戲以來只知道觀眾對演員的愛和嚴格,從來沒想到觀眾對演員有這樣的寬容。”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是之說過一句自我調侃又充滿悲憤的話——“也許我在舞臺上說得太多,老天爺懲罰我不讓我再說話了!”
八
在1995年秋天,是之又有一次模仿毛澤東講話的嚴重失語。同行者是這樣回憶的:“這天晚上賓館組織了一個聯歡會。觀眾是住在賓館里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旅客。一些旅客聽說大名鼎鼎的于是之在場,十分希望他能即興表演一個節目。主持人走到于是之面前說:‘是之老師,您行嗎?’于是之答:‘行!行!我今兒行!’于是主持人向觀眾介紹——‘著名表演藝術家、全國人大代表于是之先生也來到了咱們這個聯歡會場,接下來,請是之老師為大家表演節目!’人們歡迎的掌聲是非常熱烈的。于是之拿著一個寫好的紙片走上小舞臺。所謂于是之的表演,仍然是保留節目,用湖南口音模仿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上)的那段講話。會場上安靜下來以后,于是之開始表演——‘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毛澤東的講話只念了半句,便卡在那里。停了半分鐘之后,他靜了靜心,重新端起紙片,開始第二次試著往下念,但第二次又卡在那里。于是開始第三次念,而第三次只念了四五個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紙片從眼前挪開,雙手垂了下來,十分沮喪地說——‘念不了了……’在場的觀眾一驚,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復了一句——‘念不了了!’主辦方的人見狀,匆匆走上前把他攙扶了下來。于是之嘴里嘟囔著——‘這兒燈太暗,紙片上這字兒看不清楚……’后來,我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于是之癱坐在椅子上。幾個小時之間,他好像老了十歲,他嘴里自言自語地嘟囔著——‘完了!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多少年來,我從沒看到過于是之的神色那樣惶恐。不管我怎么勸慰,他嘴里喃喃著的只是幾個字——‘完了!真完了……’夜已經很深了,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突然,他坐起身,眼睛盯著我跟我說——‘看來,我是絕對不能再回到舞臺上去了,我完了!’說到此處,于是之熱淚盈眶,接著就輕聲啜泣起來。”在片刻以后,于是之竟然又說出了這樣的話來:“我這條魚(于)算是他媽的背透了!一輩子走到哪兒趕上的盡是開水!”
九
雖然,是之在堅持表演當中,一再努力失敗,又一再不肯服輸。表面上看似平靜,內心里卻從來沒有罷休。他與舞臺確實有著難舍難分的不解之緣。1996年秋天,是之的戲劇生涯已經有半個世紀之久,怎么能夠輕而易舉地走下獻出了青春,又獻出了終身的藝術“圣壇”呢?這時,是之竟然爽快地同意了在我執筆的《冰糖葫蘆》里,客串扮演一個只有兩次短暫出場的、只有幾句臺詞的群眾角色。我們選擇了和他一起主演過《雷雨》《虎符》和《洋麻將》的老演員朱琳大姐做搭檔。他們扮演一對知識分子老夫妻,每天早晨都要出來散步,而且幾乎每天都要互相提醒不要忘記帶上家里防盜門的鑰匙。這天,老先生發現自己的鑰匙不見了,很著急,一再埋怨是老伴兒拿錯了鑰匙;老太太根本就沒有丟鑰匙,堅持認為是老先生把鑰匙胡亂放在什么地方,自己忘記了。經過認真的、風趣的爭論以后,在老先生衣服的口袋里找到了鑰匙……我和是之商量好:“這段戲的情節比較簡單。同時,我只給你寫10句左右的臺詞,而且每句臺詞都不超過4個字。”他連連點頭,表示:“只要這次沒有問題,咱們以后還可以接著來!”仿佛眼前出現了能夠繼續演戲的曙光。那天排練場上的氣氛是嚴肅而熱烈的,大家非常關心地來看是之排戲。導演陳颙也格外地耐心,告訴是之不要著急慢慢來,戲不多,很快就會完成。朱琳對是之說:“我已經把兩個人的臺詞都背下來了,萬一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一定會很順利的。”是之更是笑著點頭,表示感激。他們坐在那里對臺詞的時候還好,基本上可以丟掉劇本了;站起來走位也沒有遇到什么大問題。出人預料的是在休息以后,導演進行細致的排練時出現了麻煩——有幾句臺詞是之總是說不出來,特別是“鑰匙”兩個字老卡住殼。只有四五分鐘的戲,硬是排了將近一個小時也不能完整地串下來。可以看得出,別人都沒有任何不耐煩的表現,但是是之的臉色漸漸泛紅起來,顯然是有些著急。排練場上變得安靜極了,大家都有所擔心但又不肯吭聲,期盼著情況能夠有所好轉。是之不時皺著眉頭,連連地搖頭,樣子顯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尷尬。越是心急就越是說不上臺詞來;越是說不上臺詞來就越是心急。導演想緩和一下氣氛,讓大家休息一會兒。在休息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終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是之突然有些激動,手在發抖,站起來用很不連貫的語言,對自己,又對導演說:“我是有病……不然……這點兒戲早就排完了……你們著急,我更著急……我耽誤了時間,實在對不起大家!……可是沒有辦法……怎么辦呢?……到底該怎么辦呢?……”導演趕忙解釋:“你的情況大家都知道,千萬不要著急,今天排得基本上差不多了,再從頭兒順一順就可以過了嘛。”吃午飯的時候,鄭榕和我以及陪同來排戲的是之夫人李曼宜,把包子和稀粥端到是之的面前,勸他吃點兒飯,先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是之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不肯吃飯,也不吭聲。他的臉色蒼白,眼睛直瞪瞪地望著樓窗以外很遠很遠的地方,心潮翻滾,痛苦已極……這時,我想起了是之不久以前,在他樓上書房窗子前邊說的話:“我好幾回都想順著這兒走下去!”
十
如今,是之和林連昆都已經辭世,這里是他們生前的一個“鏡頭”——
在是之住醫院期間,一天,他在電梯間里意外地看到了同樣來住醫院的林連昆。兩個人相對無言,很久很久,一個是說不出話來,一個是不知說什么話才好。四只眼睛互相凝視著,心里都有說不出,又說不盡的話……大家都知道,他們兩位的表演風格是很相似的,又是取得巨大藝術成就的好演員。是之曾說:“我的表演,只有林連昆能夠說得清楚。”醫院里這最后的一幕,沒有任何語言的一幕,實在是太耐人尋味了。
是之很喜歡表演,一生的最大愧疚就是沒有把戲演到底。他也很喜歡書法,在晚年曾經寫過兩幅墨寶——一幅是“落花無言,人淡如菊”;一幅是“留得清白在人間”。或許,這就是他當時的心聲吧。
只有能夠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也許才能懂得什么是生命。
是之說:“人的性子就是命,咱們不能和命爭。”
人有命運嗎?有時候,命運是很不公平的。人們在命運的隨意擺弄面前,常常是無能為力的,很無奈的。真是——小勢可造,大命難違啊。
人生的許多道理是在你經過以后方才知道,那已經為時很晚。大約,這就是我們永恒的惆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