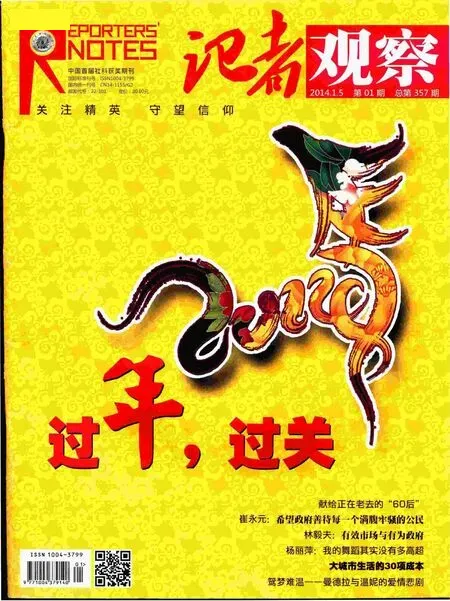民國女作家自述洞房經歷:不愿把處女貞操輕擲
王開林
謝冰瑩決不肯嫁給一個連信都寫不通的男人,她可不愿意把處女的貞操輕于一擲。后來,她在《女兵自傳》中寫道:“處女的貞操,不能為一個與她毫無愛情的男人而犧牲,我寧可和他拼命,決不能屈服!”5歲時成為包辦婚姻的準犧牲品
謝冰瑩5歲時,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將她許給了本地一位比她大5歲、名叫蕭明的男孩。家里放鞭炮慶賀兩家聯姻時,這個懵懂無知的女孩還興高采烈地跑過去。與別的孩子爭搶那些引線未燃的鞭炮。殊不知,這一刻她已成為包辦婚姻的準犧牲品。
“未婚夫”蕭明家倒也富裕,是新化的一戶土財主,蕭明的三伯父做過省議會的議員。逢年過節,他都會周全地給岳父家送來豐厚的禮物。女孩子懂事早,再加上姐妹們不斷提醒,謝冰瑩明白這是怎么回事,心里便漸漸地生出了反感和抵觸情緒。每逢蕭明來時。她就躲在閨房里,一門心思讀書寫字,縱然母親千呼萬喚,她也充耳不聞,家人只好解釋她這是害羞,不好意思見人。身受這般冷遇。“未婚夫”蕭明顯然感到很尷尬,他的性格倒也隨和。完成了禮節性的拜訪,便起身告辭,并不磨蹭。
十年彈指一揮間,昔日懵懵懂懂的黃毛丫頭已出落為亭亭玉立的少女,最根本的變化則來自于謝冰瑩的內心,她從文學中汲取了足量的精神養分,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見。像她那樣的倔脾氣,一旦認定了什么目標,就注定是九牛不回頭。九死而不悔。她入了軍校,上了戰場,寫了《從軍日記》,那幾年的生活真是風生水起。多彩多姿。但她始終有一個心結未解,還得回到家鄉去解開它。
北伐戰爭虎頭蛇尾,軍校解散后,女生隊的女兵各奔東西。當初,謝冰瑩是瞞著母親去當兵的,她這一出格之舉在家鄉引發不少流言和謠諑,有的說她中彈身亡了,有的說她做了俘虜,有的說她鼻子、乳頭被割掉了,有的說她肚破腸流赴了陰曹,這些流言和謠言嚇得她母親日夜驚悸,寢食不安,常常求神拜佛。
老天保佑,女兒總算回了家,母親心中滿是喜氣,臉上則滿是怒氣,劈頭蓋臉一頓數落:“一個女人怎么好去當兵,和那些講自由的男人在一塊,還成什么話?你破壞了我們的家聲,也有損于婆家的名譽。現在我要趕快把你嫁了……”
3次逃婚被捉洞房花燭夜與新郎講道理
做母親的不知道,女兒已經有了心上人,這段愛情是在北伐戰爭的血與火中鍛造出來的,對方名叫符號。符號的信追到了新化,被謝冰瑩的母親攔截了,原來如此!真是女大不中留,再不將她嫁到蕭家,眼看就會鬧出丑聞。母親知道女兒的脾氣,求她沒用,講道理——謝家是有名望的人家。不能失信毀約——也沒用,只有以死相脅,興許奏效。謝冰瑩真就服了母親這一狠招,但她口服心不服。3次逃跑都被捉了回來,真有點孫大圣跳不出如來佛掌心的感覺。
謝冰瑩決不肯嫁給一個連信都寫不通的男人。她可不愿意把處女的貞操輕于一擲。后來,她在《女兵自傳》中寫道:“處女的貞操,不能為一個與她毫無愛情的男人而犧牲,我寧可和他拼命,決不能屈服!”洞房花燭夜,在保衛自由與愛情的戰斗中,謝冰瑩與新郎講道理(“愛情不能施舍,更不能欺騙”),直折騰得新郎眼皮打架,沒奈何點了頭。這段經歷,謝冰瑩在自傳中寫得分明:
我5歲被“指腹為婚”式地許配給一個叫蕭明的未婚夫,那時他10歲。我參加北伐回來,家里就逼我結婚。我反對這門親事,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他,哪里談得上感情?媽媽個性強,她一點也不通融,說我若不從她就死;我個性也強,也不通融,認定了的理,誰也改不了。爸爸說,為了媽媽你犧牲一下吧。我說,你殺了我,我也不從!爸爸說,你先去,然后跑。我帶著無限的委屈依從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種設想和準備。
婚,只能成假,不能變真。我對蕭明說,我是奉父母之命來你家的,我們結婚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只有痛苦;我們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談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過,只好睡覺;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著不停地在火爐旁寫日記。蕭明人很好,通情達理,終于放了我……
與符號志趣相投生死相許
婚后,謝冰瑩在蕭家待了一段日子,她一直在尋機逃脫,湊巧她的母校大同女校聘請她為六年級級任教師,她便征得蕭明父母的同意,前往就聘。她從大同鎮逃到長沙,寫信給蕭明解除婚約,然后經人介紹,去省立五中附小(校址在衡陽)短期任教。她受人排擠,便乘“洞庭丸”去了漢口,再由漢口乘船至上海,受到編輯家孫伏園的熱烈歡迎。
在北伐戰爭后期。謝冰瑩所在軍校的學生兵隸屬葉挺領導的獨立團,謝冰瑩在宣傳隊,符號在特務連。兩人志趣相投,筆桿子里出詩文,孫伏園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和茅盾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都發表過符號的詩歌和謝冰瑩的小說,是戰爭和文學令他們心心相印。生死相許。
上海雖大,好飯碗卻難尋,賣文為生,談何容易,三餐不繼是常有的事情。更有一宗,她不慎租住在一個綁匪家中,被警察抓去關了幾天黑牢,餓個半死,幸得孫伏園多方設法營救,她方才脫身。為了生存,謝冰瑩輾轉奔波,身心交瘁,她去了北平,編輯《民國日報》的副刊,然而好景不長,她編的副刊觸犯了政治禁條,受到當局的打壓,她再度失業。
女兒小號兵出生符號卻被捕入獄
不遲不早,就在這時,她和符號的女兒——小號兵出生了,謝冰瑩產后虛弱,營養不足,沒奶吃的嬰兒整天哇哇大哭,再加上符號猜疑謝冰瑩心中另愛他人,情緒波動極大,寧肯出去打牌也不肯照料可憐的妻女,夫妻矛盾因此升級。劫難往往喜歡追逐窮人的腳踵,符號去天津找差事,受到朋友的牽連,沾上共產嫌疑,被捕入獄。
可想而知。謝冰瑩抱著骨瘦如柴、饑腸轆轆的小號兵去天津探監,一路上心情何等凄惶悲苦!夫妻相見于囚牢,仿佛相逢于異度空間,絕望變成了一串串咸澀的淚水。
謝冰瑩帶著小號兵回到武漢的婆家。與符號的母親住在一起。符母守寡多年,兒子坐牢,生死難卜,小號兵就成了她的命根子。為了養家糊口,謝冰瑩以拼命的勁頭碼字,但收益極其微薄,全家仍處在饑寒交迫之中。這時,她想到了慈父嚴母,想到了家鄉的親人,只有他們才是最后的依靠。謝冰瑩帶著小號兵走后不久,符母便起了疑心,她帶著四鄰街坊去把媳婦攔住,硬是強行從謝冰瑩懷里奪走了小號兵。謝冰瑩心碎了,但善良的她不忍傷害同樣善良的婆婆,畢竟婆婆對小號兵的愛并不比自己少。
符號在天津遭受了5年牢獄之災,出獄后,在武漢的家中只見到白發老母和怯怯認生的小號兵。謝冰瑩走了。他們的緣分盡了。是謝冰瑩絕情嗎?多年后謝冰瑩拿出了自己的說法:“往事如煙,我與符號溫馨的一切,都已過去,我們當時相親相愛。是歷史和命運將我們分開。”
在美國得悉女兒去世噩耗
1942年。謝冰瑩在桂林見到了魂牽夢縈多年的女兒小號兵。她試圖說服小號兵跟媽媽一起生活,從此接受她的監護。然而由于母女長期疏離,感情基礎薄弱,盡管血濃于水,但咫尺如隔天涯,小號兵不肯跟隨謝冰瑩,不愿遠離孤苦伶仃的祖母,也不樂意融入一個陌生的家庭。母女唯有抱頭痛哭,合影留念。
小號兵既漂亮又聰明,遺傳了父母的文學天賦。南社詩人柳亞子曾稱贊她有“乃母之風”,特贈七律一首,開頭兩句是:“可憐天小十三齡,雛鳳清于老鳳聲。”建國后。小號兵執教于北京中央戲劇學院,但她沒能逃過“文革”浩劫,由于海外關系,她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一百多萬字的日記也被付之一炬。
上個世紀80年代。謝冰瑩在美國得悉這一遲來的噩耗,痛絕肝肺,情緒極其低落,她用顫抖的雙手捧著她與小號兵在桂林的合影,不禁老淚縱橫,因此她一直不肯原諒符號,認為符號根本就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謝冰瑩曾作《愛的清算》一文。其中有這樣的奇句:“奇(符號原名符業奇)之于我,一百條恩愛。一百零一條罪狀……”上個世紀80年代,符號得知謝冰瑩定居美國,依然健在,想邀她回大陸探親訪友。但她以腿傷為由婉言謝絕了。
1986年,符號讀到大陸出版的《謝冰瑩作品選》,其中有一篇《焚稿記》。謝冰瑩以傷感的筆調記敘了她與符號之間的悲歡離合,為了了斷前塵往事。將字字深情的作品一火而焚之。他還聽說,謝冰瑩晚年虔信佛諦,絕智無我,一時間萬千感慨齊攢心頭,遂賦七絕二首:
苦心孤詣稱鳴妹。訴罷離情訴愛情。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門聽取斷暢聲。
知君焚稿了前緣。中夜椎心懺舊愆。
勞燕分飛天海闊,沈園柳老不吹綿。
人生中有許多說不清,謝冰瑩怪罪符號未能在大劫難中保全女兒的生命,只因她不曾領教那場風暴的迅猛和殘酷。俱往矣,一切幽怨哀愁的堅冰都注定要在時間的大鍋中融化為水,最終變成蒸汽,隨風散盡,不肯輕易褪色的唯有一把鉛字。
第三段婚姻:婚禮現場寫血書立誓終生不渝
謝冰瑩的第三段婚姻,是在抗戰期間與賈伊箴的結合。賈伊箴畢業于燕京大學,相貌堂堂,文質彬彬。婚禮上,有一個特殊儀式,新郎新娘當場咬破指尖,用鮮血在白布上寫下自己的姓名和生日,立誓終生不渝,白頭偕老。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誓只是一紙空文,謝冰瑩與賈伊箴的婚誓則字字落實。他們相濡以沫,親密無間,共同生活了51年。
有趣的是,謝冰瑩稱呼賈伊箴為“維特”,喊得既親密又甜蜜。當年,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是浪漫青年熱讀的小說,“維特”一名可謂眾所周知。據新聞界名人嚴怪愚回憶,他曾為此調侃好友謝冰瑩:“你的維特長得這么帥,你不怕別的女孩將他從你的身邊奪走啊!”謝冰瑩望著身邊的維特,問:“會嗎?”維特點點頭:“會的。”謝冰瑩吃了一驚:“啊?”維特笑了:“這個女孩不就在我身邊嗎?”“你這滑頭鬼,真壞!”謝冰瑩給了身邊的維特一拳……
謝冰瑩與賈伊箴的婚姻體現出來的是性格的互補,其中融合了不少孩子氣的成分。謝冰瑩是剛的,賈伊箴則是柔的;謝冰瑩急躁,賈伊箴舒緩;謝冰瑩豪放,賈伊箴溫和;謝冰瑩粗獷,賈伊箴細致;謝冰瑩善于出擊,賈伊箴善于防守。總而言之,他們的關系是婦唱夫隨。
賈伊箴廚藝高超,做得一手好菜,謝冰瑩便樂得做清閑太太;賈伊箴愛護妻子,抗戰期間,謝冰瑩組織“婦女戰地服務團”奔赴抗日前線,他爭取當上“編外團員”,與妻子寸步不離,遇著敵機轟炸,他便用整個身體屏蔽妻子,謝冰瑩一邊感動,一邊嗔怪:“你呀,是個天造地設的大傻瓜,你又不是鋼筋水泥,你這把瘦骨頭,能護得住我嗎!”賈伊箴只是呵呵一樂。下次照舊故伎重演。他們這樣形影相伴,被人戲稱為“鴛鴦”。
1948年,謝冰瑩應聘臺灣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賈伊箴說:“冰瑩,你真是個名副其實的‘謝百天呀,在哪兒也待不了一百天!剛到北平,干得好好的嘛!咱們還是別到臺灣去了吧。”謝冰瑩說:“臺灣是祖國的寶島呀。我還沒去過呢!就這么定了,去!”賈伊箴在這么大的決定上依然是唯謝冰瑩的馬首是瞻,后來定居美國舊金山,仍是謝冰瑩拿的主意。
摘自《百年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