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姓什么
余健
最高決策層剛剛通過的《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在企業界引起陣陣波瀾:有人忐忑不安,有人幸災樂禍,還有人憤憤不平。60萬工資帽背后的邏輯正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猜測:是央企負責人“配不上”當前的薪資水平,還是為了促進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抑或是黨內“八項規定”已正式延伸至經濟領域?若一定要厘清是否“配得上”,可以分析不同類型央企對企業家能力的依賴程度。涵蓋國資委113家工商企業及大型商業銀行、煙草等中管企業,“央企”的盈利內核其實大相徑庭:自然資源或營業牌照(能源、通信、煙草)、勞動力規模經濟(建筑)、傳統研發與制造(軍工、機械)、計劃定價差額(電網、銀行)等。橫向比較下,不同類型央企對企業家個人的依存度迥異,這一現象同樣存在于非國有企業。“工資帽”應該能緩解部分行政壟斷企業對基尼指數的推高,但也難免會“委屈”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央企。
至于央企負責人收入是否“過高”或“不合理”,在于參照對象如何選取。央企負責人薪資究竟應該比照高級政府官員,還是同行業民企甚至外企CEO?這一長期困惑反映出決策層對央企屬性的猶豫和搖擺,以及現代企業制度在央企生根之艱難,畢竟各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在2008年至今的央企業績波動中顯得太過沉默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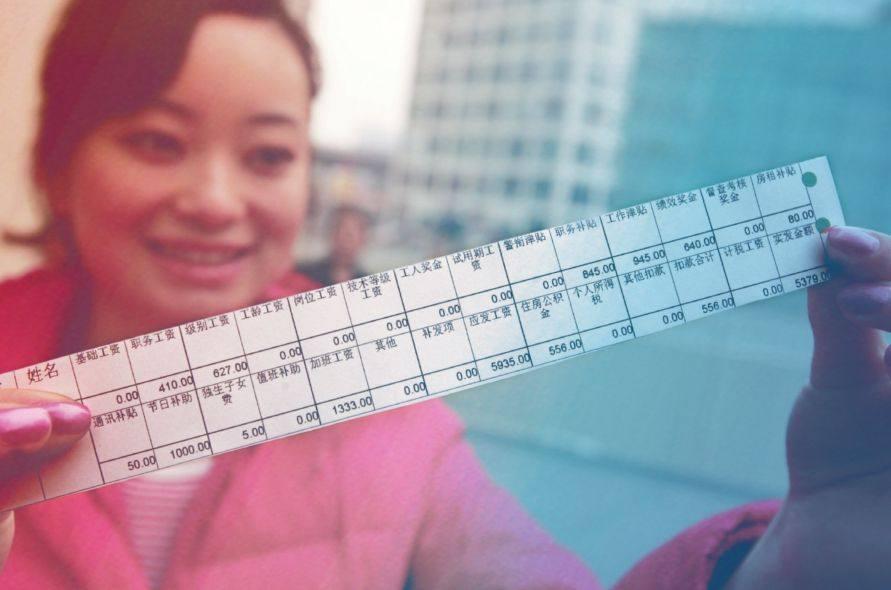
令人遺憾的是,《方案》僅涉及國有獨資或控股央企,示范意味十足但長遠效應有限。2010年職工收入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國有單位與民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相差不足兩倍,但金融業與農林牧漁業人員平均工資相差4倍多,可見行業收入差距(而非國資民資之分)已成為國內薪酬差距的頭號影響因子。2014年的上市公司數據仍舊支持這一趨勢:年薪排在前10位的董事長中有8位集中在金融和房地產行業;上市銀行董事長平均薪酬是上市央企負責人平均薪酬的3倍有余。故“國資還是民營”成為此次薪酬改革的標尺委實不妥,減小行業間收入差距才是最徹底的方案。
由于此番薪酬改革著眼于資本屬性而非行業屬性,收入分配體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催化作用仍然缺失。反觀建國初期,重工業和高科技的快速進步與當年物質待遇的傾斜不無關系,即當重要國民經濟領域急需改善的時候,持續低于社會平均水平的行業薪酬絕不是好兆頭。根據清華大學發布的2013年就業統計,該校畢業生境內雇主前十名中已有七家是軍工集團。學子報國之心固然可嘉,但若“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之景延續至今,上述就業統計如何也很難講。類似地,若要改變國內軸承、基礎電子元器件、精密鍛鑄等行業的孱弱,刺激性的薪酬指導政策對這類行業中的國企和民企同樣必不可少,這與是姓“國”還是姓“民”無太大關系。
有預測稱,限薪后的國有金融機構將會面臨人員流失潮。他們忽視了央企“去行政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及相應的“旋轉門”機遇),且國企內外巨大文化差異將會削弱薪酬因素的沖擊。如2010年張紅力作為德意志銀行高管加入工商銀行,彼時工行董事長僅為德銀CEO的1/12;但德銀會以“給公司造成損失”為由向張紅力提起訴訟并索賠632萬美元,而這樣的事情對包括工行在內的央企是難以想象的。
過高的工資收入大多來源于過于輕松的盈利模式,在高利潤率行業強制維持相對較低工資水平不啻于用結果來糾正原因。若要突破權益之計,終須打破準入壁壘并放開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管制,使各行業盈利水平向國民經濟總體利潤率趨近。此外還須提防經濟政策的政治化,畢竟工資收入與“八項規定”力戒的特殊收入有本質區別,通過薪酬改革調整勞動力價格是為了讓企業界更健康,追求符號化的公平則會傷害企業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