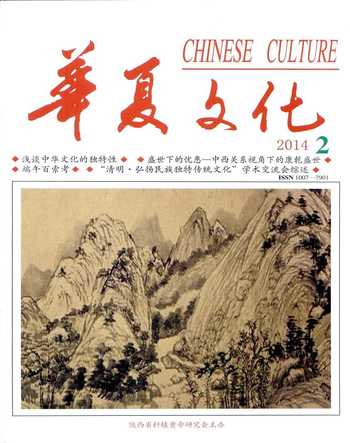蒙學讀物與黃帝文化
高強
中國人素有記史、傳史、治史、重史的優良傳統,史學在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每當談及史學作用時,國人必說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蒙學讀物。
所謂蒙學,指的是學業的啟蒙階段,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學讀物就是學業初始階段學童們使用的課本。中國的蒙學讀物是從字書發端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學童識字、習字用的字書。據《漢書·藝文志》載:“《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顏師古注《史籀》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史籀篇》是著錄于史冊的最早的蒙學課本。
秦統一后,曾分別由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母敬用小篆編寫了《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漢書·藝文志》)。漢代,有人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合稱《蒼頡篇》。宋代以后,《蒼頡篇》亡佚。1977年,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漢簡中,發現《蒼頡篇》殘簡541個字。2009年發現的北京大學西漢竹書中有《蒼頡篇》1200多個字,其中多數為首次發現。《蒼頡篇》采用隸書,為四言韻語,常將同義、近義或反義詞編排在一起,此種編法對后世蒙學字書影響很大。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不少蒙學字書,僅《漢書·藝文志》“小學”類著錄的即有10家45篇。其中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揚雄的《訓纂篇》,還有不知著者的《別字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的蒙學字書有賈魴的《滂喜篇》,張揖的《埤蒼》,蔡邕的《勸學》、《圣皇篇》、《黃初篇》、《女史篇》,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飛龍篇》,朱育的《幼學》,樊恭的《廣蒼》,陸機的《吳章》,周興嗣的《千字文》,束皙的《發蒙記》,顧愷之的《啟蒙記》等,其中《滂喜》與《蒼頡》、《訓纂》合稱“三蒼”。這些蒙書多已亡佚,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由西漢黃門令史游編撰。今本《急就篇》共2144字。《急就篇》篇首云:“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意。”“分部別居”和“泛施日用”是這本書的兩大特點,它把當時的常用字,按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分類,編纂成三言、四言、七言韻語,既便于記誦,又切合實用,是漢魏至唐代通用的蒙學字書。
顏師古稱《急就篇》“如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乘稟,猶竟習之”(《急就篇》注序),可見《急就篇》在漢唐時期影響之大。《急就篇》沒有敘述黃帝,倒是顏師古在為其作注時兩次提及黃帝。“橋竇陽”注曰:“黃帝葬于橋山,群臣追慕守冢不去者,因為橋氏。”“公孫都”注曰:“黃帝姓公孫氏,支庶遂以為姓也。”另有多處與黃帝有關,如“顏文章”注曰:“顏氏本出顓項之后。”“慈仁他”注曰:“慈氏本高陽氏才子之后也。”又如注釋童姓曰:“顓頊之子號老童者,其后因以為姓。”顏師古的注釋源于《世本》、《史記》、《風俗通義》等典籍,與漢魏以來族譜及墓志銘中祖述黃帝的風氣相一致。
蒙學讀物以宋代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宋代以前的蒙學讀物以識字為主,流傳下來的很少,只有《蒼頡篇》、《急就篇》和《千字文》等寥寥幾種。宋代及其以后的蒙學讀物,流傳至今的較多,除了識字這一基本功用外,突顯了儒家思想和倫理教化的功能,這是后期蒙學讀物的主要特點。之所以如此,或與宋明時期理學的興盛密不可分。宋代及其以后蒙學讀物的另一個特點是越來越細化,出現了專門的歷史讀物。正因為蒙學讀物到后期發生了變化,涉及黃帝文化的內容明顯增加。
《三字經》相傳為宋代著名學者王應麟編著,從論述教育的重要性開始,依次敘述三綱五常十義、五谷六畜七情、四書六經子書、歷史朝代史事,最后以歷史上苦讀不輟、光宗耀祖的事例作結語。《三字經》“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章太炎:《重訂三字經》序,《三字經》,岳麓書社,2005年,第141頁),開三言韻語蒙書的先例,把識字、歷史知識和倫理訓誡熔為一爐,家喻戶曉,膾炙人口,是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蒙學讀物。《三字經》曾被譯為滿文、蒙古文等少數民族文字及英文、法文等外文,被譽為“千古一奇書”、“袖里通鑒綱目”。《三字經》的注釋版本甚多,以王相的《三字經訓詁》、賀興思的《三字經注解備要》、章太炎的《重訂三字經》最具代表性(均見《三字經》,岳麓書社2005年版)。
明末清初學者王相對蒙學讀物情有獨鐘,曾經為《千家詩》、《三字經》、《女四書》等作注。王相稱贊《三字經》“言簡義長,詞明理晰,淹貫三才,出入經史,誠蒙求之津逮,大學之濫觴也”。《三字經》正文共計1128字,有306字敘述中國歷史。其書云:“自羲農,至黃帝,號三皇,居上世。”王相注曰:“黃帝有熊氏制衣裳,定禮儀,文明大備,品物咸亨,作萬國具瞻之表。”(王相:《三字經訓詁》)賀興思注曰:“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又姓姬,名曰軒轅。諸侯尊為天子,以土德王,建都涿鹿。作甲子,造律呂、耕田、貨幣、宮室。畫野分州。”(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章太炎的《重訂三字經》云:“自羲農,至黃帝,并頊嚳,在上世。”將“號三皇”改成“并頊嚳”。章氏注曰:“黃帝,軒轅氏,亦稱有熊氏,姓公孫。”(章太炎:《重訂三字經》)
如果說姓譜書籍推崇的是作為血緣之祖的黃帝的話,那么蒙學讀物頌揚的則是作為“人文初祖”的黃帝。據說由明代大學士李廷機編寫的《五字鑒》(通行的本子稱《鑒略妥注》),用五言韻句敘述了從上古到明代的歷史,是濃縮了紀傳體的通俗歷史讀本,是清代至民國時期學習歷史的啟蒙讀物之一,流行于書院與私塾之中。其書對黃帝的功德作了全面的概括總結,勾勒出一位開創文明的英雄形象。
清順治年間,進士王仕云編了本四字一句的《四字鑒略》,約3000字,成為與《五字鑒》齊名的歷史啟蒙讀物。《四字鑒略》較之《五字鑒》更為簡潔,偏重于記述與王朝更替、國家興亡有關的大事,其他則略而不書。其書言“軒轅黃帝,生而圣明。擒戮蚩尤,神化宜民。六相分治,律呂調平。五幣九棘,泉貨流行。麟鳳顯瑞,屈軼指佞。在位百年,文明漸興。”(王仕云:《四字鑒略》,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頁)
明人程登吉編著、清人鄒圣脈增補的《幼學瓊林》曾經風行全國,經久不衰。
時人常言:“讀了《增廣》會講話,讀了《幼學》走天下。”《幼學瓊林》打破了一般蒙學讀物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限制,當長則長,當短則短,用駢儷句式編寫,并按照內容分類編排而成。其書言:“黃帝畫野,始分都邑”;“甲胄舟車,系軒轅之創始;權量衡度,亦軒轅之立規”;“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始備;桑麻蠶績,自元妃而始興。”(程登吉編著、鄒圣脈增補:《幼學瓊林》,岳麓書社,2002年,第174頁)瑯瑯上口,通俗易懂。
蒙學讀物里的黃帝文化源于《史記》等史書。借助蒙學讀物,黃帝形象更加深人人心。蒙學讀物是傳播黃帝文化的重要載體,其貢獻不亞于二十四史之類的官修正史。周谷城先生在論及蒙學讀物時指出:“我們研究文化史,應當著眼全民族和各階層人民文化的演進,著眼以往各時各地社會上多數人的文化狀況。……當時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通過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觀、神道觀、倫理觀、價值觀、歷史觀,在這類書中,確實要比在專屬文人學士的書中,有著更加充分而鮮明的反映。”(周谷城:《傳統蒙學叢書》序,岳麓書社,2002年,第4頁),透過蒙學讀物,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中國人對黃帝的認識,對黃帝的感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黃帝文化在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蒙學讀物其實就是通俗讀物和普及讀物,雖說難登大雅之堂,也算不上什么科研成果,但卻不可或缺,不容小覷。試看今日中國,有幾人通讀過《史記》、《資治通鑒》?又有幾本像《三字經》、《幼學瓊林》那樣家喻戶曉的蒙學讀物?
蒙學讀物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的重要載體,批判地繼承和利用蒙學讀物,不僅對于傳承黃帝文化、弘揚黃帝精神有益,而且對于傳播中華文明、復興中華民族有益。
(作者:陜西省寶雞市寶雞文理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系,郵編7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