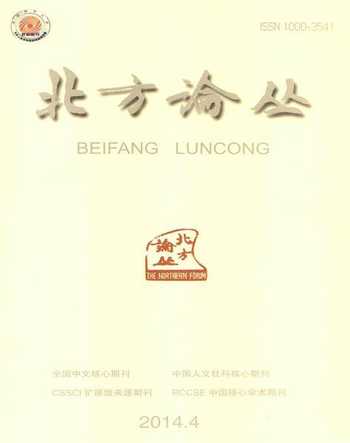20世紀30年代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及其空間表征
逄增玉 孫曉平
[摘 要]20世紀30年代文學受制于當時中國的京海社會結構和時代動蕩,一方面以五四時期啟蒙主義、反現代性的浪漫主義和革命意識形態等視角,繪寫同一時空中國鄉村世界的不同政治與文化、文學與審美的地理空間,塑造了不同的鄉村和中國形象;另一方面,對北京與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國,從政治、革命、性別和文化視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國的文化地理空間及其色調,使摩登的上海與古都北京既呈現出現代與傳統的不同內涵,又使不同政治與審美立場的作家筆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復雜多態的空間意義及其表征符號。文學敘事中的20世紀30年代中國其實呈現和蘊含非同一性的多個中國的形象及價值空間特征。
[關鍵詞]20世紀30年代;中國形象;空間表征;京海結構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5-0001-07
[收稿日期]2014-06-25
中國新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受制于民族救亡、啟蒙、革命、戰爭和解放等語境,開始不斷地描寫和敘述有關中國、都市和地區的文學形象和空間意象。這些形象和意象既構成與客觀環境緊密相關的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和國家文學特有的母題和形象系列,也再造了現代中國的國家和地域的政治、文化、社會、道德與性別地理,成為賦予各種意義的符號化表征空間,以至于一提起現代中國的某個地方和地域時,許多人首先浮現于腦海的是文學作品、特別是經典作家作品對其的描繪和“形象定位”,而非從政治、經濟和地理類書籍獲得感知與知識。文學作品不是簡單地“視為是對某些地區和地點的描述,許多時候是文學作品幫助創造了這些地方”[1](p.40),而是以文學手法和形式創造了一個文化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及其表征空間,并構成了一套文學的、文化學的、有關中國的、地理空間的知識系統,其中摻雜著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的多種價值取向和功能意義,并由此使中國現代文學具有鮮明的空間地域與文化地理的多重意義。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從不同的角度塑造和描繪了一個復雜的、具有政治與文化地理學意義的中國。
一
近代以來,中國出現的少數經濟與文化發達的都市與內地廣大農村并存的二元社會結構,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政治革命、民族危機等時代激變的刺激而導致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愈發突出,作為時代產物并對之予以反映的文學,由是出現了與社會結構同步的文學型構,即都市文學和鄉村文學成為現代文學最突出的兩大文學題材和類型。如果說這兩類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還沒有出現雙峰并立的局面,那么,到了20世紀30年代,則已成為最顯著的文學題材與主題內容。而鄉村世界、鄉土中國的描繪,在20世紀20年代鄉土文學的基礎上,有了更為廣大和豐富的視域與風景。多元豐富的內地和邊地鄉村世界的描繪與敘事,構成了文學化的空間中國的形象化表征,一言以蔽之,寫鄉村和地方,都是為了說中國,說出同一時空里的不同性狀的多個中國形象。魯迅曾經認為,同一個時空里的中國,其實是具有不同內部時空與景觀的,“幾乎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2](p.344),20世紀30年代鄉村文學描述的就是在社會發展階段和思想狀態上呈現出多元景觀的中國。
“魯迅風”式的以現代性目光透視和描寫鄉村世界的啟蒙主義敘事,在20世紀30年代農村題材文學中仍然是普遍性現象。吳組緗的《菉竹山房》和《X字金銀花》等小說,作者的立場和態度是啟蒙主義的現代性,并由此轉化為小說的敘事者的目光和態度,敘事模式仍然是游子回鄉,即讓在都市謀生的現代知識分子擔任敘事者回鄉省親,從現代都市進入和回到內地鄉村,通過這個敘事者的觀察與接觸,看到和感受到鄉村世界并進行具有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意味的文學描述。在小說敘事者的視野中,故鄉皖南的自然風景和地理依然秀美,但社會與文化構成的人文地理環境依然是前現代的和中世紀性的,傳統的封建性綱常名教依然依托于司馬第府宅等陳舊空間和事物,繼續壓抑和束縛婦女并“吃人”,換言之,魯迅在五四時期啟蒙主義小說中揭示的那種“吃人”特別是吃婦女的“陳年流水簿子”和“老中國”的禮教道德,依然作為傳統和現實的力量繼續“造惡”,由此小說描寫和揭示的鄉村中國的社會結構、關系和現狀,呈現出“停滯性、壓抑性和封建性”空間的特征,其中“道德壓抑”和“性別壓抑”是這個空間的主要內涵和色調。這種歷史停滯和道德壓抑的鄉村世界,與作為小說背景的敘事者來自的有柏油馬路、電車、電影院、跑馬場和霓虹燈的外部世界,二者在自然物理時間上是“同時”的,但在社會發展階段、文明道德范疇等構成的價值時間上卻是異質的,即同一個中國呈現時空分延、多元多態的形象和性狀。
這種停滯和壓抑性的內地與鄉村中國的描寫和敘事,在沙汀、周文等人的描寫四川和川康地區的小說中,得到更多樣化的揭示。沙汀小說對川西北地域則著眼和定位于階級與社會性的極度黑暗和暴戾的——一種中世紀性的政治、經濟、軍閥、黑道等社會結構和關系構成的地獄性質的社會空間。他的小說很少描寫那里的自然風景,其著眼點都是社會視域下的社會景觀,而這社會景觀的意義,沙汀小說主要是從統治階級的思想行為的方面予以揭示的,在這些揭示和描寫的視野里存在和隱含的,是敘事者代表的作者的左翼化的政治和階級壓迫的視角與立場。《堪察加小景》《獸道》等小說描寫的四川地方軍閥官吏、黑道縉紳構成的關系結構和壓迫環境,不僅將“出格越軌”的婦女予以駭人聽聞的“點牌牌”(輪奸),而且將全體百姓乃至壓迫勢力內部都作為殘害和傾軋的對象,甚至連災荒年月外出逃荒的災民都要巧立名目予以盤剝敲詐。這個地方社會仿佛根本沒有進入現代而一直停滯和倒退,仿佛是與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明、更與現代文明脫節的被拋離正常社會軌道的“人間地獄”,只有社會性的黑惡勢力和混世魔王在這個世界如魚得水,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20世紀40年代,沙汀小說一直如此冷峻冷嘲地掃描和定位四川形象、特別是川西北的社會構成和整體形象,也是沙汀小說在敘述和表達中,努力揭示和制造出那個令人恐怖和作嘔的地方社會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定型”。另一位以描寫四川與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區見長的左翼作家周文,其小說敘事背后的思想視野和立場也是左翼的“階級”意識,與沙汀一樣,致力于描寫川康地域和社會的“無道”與魔獸狀態,為揭示這一狀態的視野聚焦仍然放在地方統治階層和軍閥,但不同的是,更著重揭示這一由統治階級行為構成的黑暗無道地域的“荒唐”與可笑,其中蘊含著強烈的反諷意味。亂世怪異、荒唐可笑、民不聊生成為地方性社會的主色調和特色,是一種左翼作家視野中的四川內地的“區域文化”和“地方社會”,這種被描繪出來的地方社會的“特色”,幾乎成為當時得到中國社會共識的四川景觀和“共相”,以至于改編于四川作家馬識途小說的當代電影《讓子彈飛》,也強化和強調這一地方特色。
與此相似,20世紀30年代云南作家馬子華在小說《他的子民們》里,也以這樣的筆調描寫大西南邊陲內地世界,不過描寫的是一個更為特異的邊地世界——云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及其統治地域。這是一種更具特色的地方社會和地域文化,小說在自然景觀與社會景觀的交錯中,描寫和揭示的焦點和視點是這一云南邊陲土司統治的地方社會和區域的原始性與中世紀性,在這種地方社會景觀的特色和“意義”描寫與揭示的背后,依然是身在上海都市的作家,以現代性目光對地方邊陲社會“落后性”的聚焦和思想透視,一種異于現代的邊陲文化地理和由原始性的社會關系與結構組成的地域性社會空間及表征。這類對西南內地邊陲腐朽或落后情形的描繪,不僅制造了有關地方社會和區域的知識與景觀,也表達了作家們對地方社會描寫與譏諷中的立場態度:對故鄉的強烈的反思與批判,而沒有對故鄉與地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表達出社會批判性之下秉承五四和魯迅傳統的精神潛流。
另一位四川作家艾蕪,卻以對西南邊陲社會的地方性特色的描寫,而給20世紀30年代以寫實為主調的左翼地域鄉村小說帶來一股奇異的、不乏浪漫色調的敘述。艾蕪小說運用的是另類的“游子回鄉”的模式,以一個受過五四教育、具有現代意識、自愿到邊陲考察和歷練人生經歷的知識分子擔任敘事者和小說主人公,通過他在云南和中緬交界地區的漂泊流浪,凝視、考察和探究那個奇異的地方世界。由是,艾蕪小說將流浪漢小說與文化地理探險模式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呈現了與“魯迅風”的啟蒙主義和沙汀等人的內地黑暗世界寫實迥異的邊地風情。在小說流浪兼探險的敘事者的視域中,提供了西南邊陲亞熱帶雨林地區的自然與社會的奇特景觀與結構:自然風景多姿多彩又險峻猙獰,社會風景則是與內地世界脫節的死角和夾縫,它收留和包容了那些在內地因自然災害、社會情仇、特別是殘酷階級性壓迫而無法謀生的農民以及反抗復仇鋌而走險的所謂罪犯們,讓他們可以在統治者鞭長莫及的邊陲有生存的機遇和空間,演化為形形色色的趕馬幫人、私煙販子、煙土種植者和盜賊匪寇,成為社會的邊緣階層。同時這里自然的險峻和社會的叢林法則,也使得這塊社會裂縫和邊緣地帶的謀生者的生存充滿艱險磨難和暴力殘酷。但盡管如此,險峻邊陲的自然與人生也是浪漫而瀟灑的,艱難求生的各色邊緣人和流浪者在苦難煎熬中,卻依然保持底層勞動者和游俠者的無私、勇敢、正義和豪俠,與西方流浪漢文學表現出的精神氣質具有相類性。正是他們身上的這種流浪漢的仗義豪俠,使得他們可以在邊地艱險中生存下去,也不斷幫助和教育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生考察和探險者,使其知曉和懂得人生的苦難中依然有高貴和正義。艾蕪小說的如此有意凝視和意義發現的描寫,使得奇異的西南邊陲世界的自然風景和人生社會景觀,都充滿了獨特的文學、文化地理學的價值和蘊含。
對邊陲地方社會和特色的描寫更具有浪漫主義成分的,是小說家沈從文。早在20世紀20年代對“鄉村中國”予以描繪的鄉土文學中,與魯迅代表的揭示中國鄉村落后和衰敗,“荒村”世界的現代性缺失為指歸的寫實批判的敘事異質,廢名的抒情浪漫主義的鄉村描繪,則充滿了前現代的禮俗鄉村世界的自然與風俗、道德與人心的美善和溫情,是“唐詩絕句”里的鄉村,也是文化中國、價值中國的文學化表征。這樣的鄉村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的以邊地湘西為背景的鄉村敘事中,有了更廣泛和集中的展示與描繪。以《邊城》和諸多湘西系列的小說為代表,沈從文是以所謂最后的浪漫主義的“造希臘小廟”、在其中供奉真善美人性的追求,在宗法制鄉村邊地與都市現代性文明對峙、贊美前者而批判后者的“質疑現代性”的視角和視域中,展示和揭示邊城世界所代表的少數民族生活與文化、地方文化的價值及其價值,邊城苗鄉、地方生活與文化第一次以如此積極正面的形象和價值出現于文學中,再造了浪漫主義和烏托邦的田園詩世界——它們不僅沒有被離棄,反而具有強大的歸屬感和感召力,應當倍加珍惜,永世長存。為了揭示這一主題,作者或者如《湘西散記》那樣,采取直接的游子回鄉模式記錄見聞,或者如《鳳子》那樣,讓城市人、工程師到苗鄉采礦被鄉野生活折服的模式,或者像《邊城》那樣,作為精神的還鄉者和敘事者敘說邊城的幾乎純凈如水的真善美世界。在近代以來被強行嵌入的社會現代化進程把中國撕裂為城鄉二元對立結構、五四以來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文學大多賦予都市和現代文明以正面價值之際,沈從文的文學則表現出質疑都市世界和現代文明、禮贊乃至美化邊地鄉村和傳統中國的浪漫主義傾向和美學,與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文學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但這正是沈從文文學的價值:描繪和塑造了與現代性背道而馳的邊地鄉村暨地方區域的自然與文化的地理景觀,一個人性完美和道德至善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空間形象,一個未曾坍塌的田園詩世界。這個地域空間蘊含和透射出的是作者的立場態度賦予其中的關于地方邊地、關于鄉土中國和傳統中國及其文化的永恒價值意義及其認同感與歸屬感。
與沈從文等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作家的烏托邦邊地敘事大異其趣,也與艾蕪的邊地人性禮贊和沙汀等左翼作家的內地黑暗寫實構成差異的,是20世紀30年代另外一批左翼作家的鄉村階級搏斗與反抗革命的敘事。像茅盾的《春蠶》還只是描寫浙江農村豐收成災的一般性社會批判主題,到了《秋收》和《殘冬》卻演變成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江浙鄉村農民起義革命的內容,全不管與上海臨近的江浙鄉村在中國鄉村中相對富裕、革命資源缺乏的基本現實。葉紫的《豐收》和丁玲的《水》等鄉村題材小說,與茅盾的農村三部曲一樣,都不僅把鄉村敘事為自然災害、社會災害造成的苦難之地,更把鄉村敘事為革命戰地。其實,20世紀30年代,中國地域廣大的鄉村的自然地理、社會結構和地方文化都是非均質的空間,存在諸多不同,但是,在這些左翼小說中,他們對地域性自然風景的關注和描寫不感興趣,感興趣和關注投入的是社會景觀,并把這些存在差異的、非均質的地方社會結構和景觀描敘為均質空間,即它們都是均質和等值的由自然災害與社會壓迫的苦難之地變為革命的熱土和階級斗爭的戰場。鄉村不再是五四啟蒙主義鄉土文學表現田園生活潰敗主題的社會地理空間,不再是社會批判性左翼文學表達憎恨和厭惡等情感結構的黑暗王國,也不再是浪漫主義文學表達地方文化特色及其價值歸屬感的世外桃源,而是由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主觀性”投射其中、使之具有和產生新的社會關系、情感道德關系和行為結構,成為文學作品所創造的產生新的“革命”意義的鄉村地方社會的形象和空間,是階級斗爭的戰地。東北流亡作家蕭紅則通過《生死場》,展現了一個被帝國主義侵略強行撕裂的中國形象,蕭紅自己設計的小說封面插圖就包含這樣的意蘊。與此同時,她的小說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等以東北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一樣,也通過對苦難中奮起抗敵的農民群像的描繪,展現民族浴血抗戰中的東北地區的形象和戰地中國的形象,一個像黃河一樣古老的民族終于崛起并發出怒吼的中國形象。這樣一個在階級斗爭與民族抗敵的戰地中活躍的中國鄉村與中國形象,不僅是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的普遍視域和主題,也是呈現給世界的中國形象。這樣的形象自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光,美國作家斯諾編選和英譯的《活的中國——中國現代短篇選》,魯迅、茅盾受美國作家之托編選的《草鞋腳——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都展現和形塑了一個在階級與民族矛盾中的苦難、動蕩和斗爭中生死掙扎的倔強的中國農民與國家的形象,即階級與民族革命和斗爭中的中國形象。用魯迅的話說,是“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3](p.296)。把活的中國形象傳達給世界,是斯諾和魯迅等人編選20世紀30年代中國小說的用意所在,而斯諾英譯的中國小說集1936年在英國出版后,也的確引起不小的震動,穿著草鞋跋涉的、苦難中戰斗的中國形象和人民形象,烙印在異域世界讀者心中。
二
京海構造是中國近代踏上“被現代化”之路后出現的社會現象與結構,殖民化與現代化集于一身的摩登上海與皇城帝都的北京,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城市與城市文化最獨特的第三世界文化景觀。對城市的認識與書寫,對城市的物質與精神空間及其相應的城市文化地理景觀的描寫與制造,成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都市文學的熱點與風景,幾乎所有流派的作家都在對城市的書寫中展露或挑戰著自己的才華,嘗試著自己文學成就的高度。
上海作為中國最大最繁華的都市,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都市文學聚焦和描寫最多,也是城市形象和色調最繁復的多維空間。不論是20世紀30年代海派文學代表的“新感覺派”,還是政治化的左翼文學,在上海都市敘事中,最鮮明描寫和呈現的,是上海的集現代(摩登)性與殖民性于一身的都市景觀。新感覺派作家劉納鷗把自己的一部小說集命名為《都市風景線》,在這個都市風景線里,最有代表性和特征的,不是自然風景,而是社會景觀。幾乎所有聚焦上海的文學,都形象地描繪出一種與上海近代城市化進程吻合的、都市存在本身揭示的殖民主義地理學特征和空間景觀,即殖民者按照殖民政治和美學要求對城市的規劃與設計:租界,碼頭,洋場,洋行,跑馬場,公園,舞廳,咖啡館,百貨公司,電影院,貧民區,殖民者對于城市的知識和控制統治的意愿具體表現于都市的景觀和功能的安排設計中,并具體外化于區域、街道、房屋、建筑。這些殖民風、歐洲風的地理空間,同時又是摩登和現代的,連接城市的道路上跑著現代的電車和“1930年福特轎車”或“1932年別克車”,電車駛過外白渡橋摩擦出的電火花和南京路商業區霓虹燈廣告渲染著消費的繁華,夜總會和咖啡館、舞廳和酒吧流溢著欲望的喧鬧和綺靡,電影院、書店、百貨公司里的人流把都市的物質與文化既分流又捆綁在一起,摩天大廈怪獸般排山倒海地壓來,撕裂著都市的空間與天空。新感覺派和左翼作家不約而同地把這座城市客觀具有的、也是自己主觀的知識與認識形成的“現代性和殖民性”兼而有之的社會文化景觀——一種新的都市風景線,書寫和制造于自己的文本。
這個城市空間同時也是聚焦有關階級壓迫與斗爭和政治革命的空間。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小說《上海的狐步舞》,旋風般展現了夜上海賭場、舞廳、酒店房間里富人的紙醉金迷和荒淫亂倫,卻又通過貧窮老婦人拉著兒媳婦賣淫的“夜景”,將“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的兩極空間特征,不斷進行對比性重復與揭示。如果說本身就是都市浪子的穆時英對上海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描寫,更主要的還是來自一般性的貧富對立的文人意識——中國文人自古及今一向具有這種認識,那么,左翼作家則從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化的階級意識出發,描摹大上海社會景觀的另一個方面:階級斗爭和政治革命的空間。左聯詩人殷夫紀念五卅運動的詩歌《血字》,就曾經把上海的街頭道路描繪為革命與反革命、殖民與反殖民勢力斗爭的戰場,丁玲從革命加戀愛小說走向政治小說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把上海寫成革命者自我完成、錘煉革命性的革命戰場和圣化空間,殖民地都市的殖民與現代性之外,又顯示出政治性與“革命性”的空間色素。到茅盾以上海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說《子夜》,對這種殖民性與階級斗爭壓迫性空間的揭示,就更為充分和成熟。通過吳老太爺到上海的視覺、聽覺和心理感受,小說入木三分地描寫了大上海的那種迥異于鄉村中國的現代與摩登,通過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的斗法及后者的失敗,又把殖民性上海的猙獰面目刻畫得淋漓盡致。而通過民族企業家吳蓀甫與企業工人的壓迫與斗爭,通過工廠工人的形象與群像和革命者領導的罷工斗爭,《子夜》不僅給人們展現了現代文學中前所未有的新鮮的上海都市的工廠、車間、汽笛、紡織機器、工人住宅等構成的工業風景,而且在這種新的風景中描繪了深入工廠的革命者的密謀與策劃、資本家走狗和企業管理者的收買與破壞、工人為反抗資本剝削進行的沖廠和總同盟罷工等階級性斗爭場景。一種左翼文學提供的摻雜于殖民性和現代性都市上海空間的新的空間景觀——階級斗爭與政治革命使其具有了革命性的色素和內涵,成為階級革命的戰地、戰場和殺場。在19世紀波德萊爾的詩歌和歐洲文學中,巴黎和都市酒館、咖啡館和各種場所出現的密謀者、波西米亞人、藝術家、流浪者兼城市觀察者,是都市景觀的不可或缺的組成[4](pp.1-230)。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如丁玲和茅盾等人的小說,那些活動于工廠、工人夜校、學校、影院、咖啡館等公共場所的都市地下革命者,實質也具有密謀者與波西米亞人的色彩,他們的活動不僅描畫了城市的政治與文化地理構成,也是上海都市具有的革命性空間的構成要素,是都市社會與政治地理和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者的出沒與活動、工人群眾的罷工、來往于租界與華界的洋人西崽、印度巡捕和各色華人,他們的存在和活動本身都構成和說明著上海都市之殖民、現代與革命的多重性狀,構成著上海都市的景觀表征。
文學中的上海還具有性別意識形態空間的意蘊。這種性別意識形態空間對于女性而言具有互相矛盾和對立的兩種意義:第一種是具有提升和解放婦女,使之“成人”的積極意義。在茅盾長篇小說《虹》和其他左翼作家作品里,內地特別是四川等地方與上海一樣,都受五四影響追求自我與婚姻解放的知識女性,當她們在內地和地方時,自我和個性的天空是狹小的,人生和命運只能在婚姻、家庭、相夫教子甚至做小為妾的軌跡中輪回。閉塞的內地與女性命運的傳統化和牢籠化密不可分,這是左翼也是現代文學的四川和內地敘事常見的主題和空間表征。只有離開故鄉和地方來到上海,她們婚姻和自我解放的追求、自我的人生價值才能得以實現。不僅如此,都市還為她們提供了從婚姻自我解放的追求到更廣大的政治與革命人生轉變和完成的空間,是真正的個性愛情得以實現的情場和更大的人生價值——政治與革命的追求——實現和馳騁的戰場。女性命運的轉變與都市上海構成了一種場域的內在聯系,內地和上海也成為女性不同命運的空間符號象征。都市的性別和道德空間第二種意義則是消極的,它不僅是知識女性從個人小家庭走向社會大家庭的性愛與革命追求和轉換的舞臺,也是女性在資本和商品邏輯下被物化、欲望化、異化的魔界。在丁玲、茅盾等人的左翼小說和穆時英、劉吶鷗的現代派小說里,似乎都有這樣的意蘊:鄉村內地固然落后保守,卻也保守了女性的貞操和道德,女性被傳統倫理道德壓抑、使其依附于家庭和舊式婚姻、窄化了她們的人生世界,卻還未被商品化與物質化、欲望化與玩物化,只是封建倫理道德的犧牲品卻還不是商品——鄉村內地在這樣的意義上與女性構成了聯系、顯示了其社會空間的特征。但都市空間卻使她們被商品化、非人化和玩物化了,她們徹底打破封建傳統的貞操觀家庭觀而追求的自由、時髦和解放,不過是以身體換取商品、物質和金錢。如茅盾《子夜》里民族企業家吳蓀甫的妹妹四小姐,在鄉下足不出戶,讀《太上感應篇》而恪守傳統閨訓婦德,雖然精神閉塞卻也是金童玉女的身心。到上海后被種種光怪陸離紙醉金迷的“摩登”刺激,內心已經失衡,口誦《太上感應篇》卻心旌搖曳魂不守舍,表明都市生活對傳統道德和婦德的強大沖擊與瓦解力量。另一位因避農村動蕩和農民運動而逃到大上海做“寓公”的鄉下大地主馮云卿,其女兒在鄉下還是懵懂少女,到大上海后卻很快適應“墮落并快樂”的都市商品和金錢邏輯,學會以身體和貞操向金融買辦大鱷換取物質金錢,傳統倫理道德和婦德在資本聚集的都市幾乎不堪一擊。在茅盾和新感覺派小說里,都描寫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女性、都市麗人、交際花和闊太太在魔獸般的物欲驅使下或被迫沉淪、或自甘墮落、或主動求歡,資本、殖民、市場和消費的邏輯造就了商場、艷窟、大飯店、包房、咖啡館、夜總會、跑馬場、豪華游輪等物欲橫流的都市場域,也造就了大批依附于此的馬路天使(妓女)、交際花等物欲的“女奴”。物化和欲望化的女性與這些都市空間密不可分,她們本身也是摩登都市、資本和商業邏輯構成的都市空間風景,揭示著都市空間的性別意識形態特征。對都市這種使婦女由傳統道德的壓抑對象到資本邏輯的欲望對象、對五四文學中追求自我解放的“女神”到成為低級或高級的物化“神女”、由人到妖的過程和現象,茅盾等左翼作家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予以揭示和批判的,《子夜》里的交際花徐曼麗、劉玉英和鄉下地主馮云卿的主動賣身的女兒,并沒有感到自己的異化和玩偶化而是樂在其中,而她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資本的強大邏輯已經完全將她們同化了。非左翼的劇作家曹禺,在《日出》里把都市知識女性的墮落和下層婦女的賣身,歸罪于社會的整體不良,社會不良的背后依然清晰可見都市資本“惡”的勢力。而新感覺派作家一方面炫耀都市的摩登、奢華和紙醉金迷,如都市浪子一樣穿行和享樂于其中,所有的新感覺派文學,不論作家是誰,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敘事者和浪子的視角,浪跡和游歷于都市的所有空間場景和角落;另一方面,又從底層流氓無產者和傳統文人未泯的道德角度,而非政治經濟和階級角度,對城市之罪與惡進行了道德化的批判性描寫,展示和揭示了都市無恥無德的非道德空間的本質、狀態和形象,特別是形形色色的女性在都市的被沉淪與自我沉淪。華麗摩登的都市在消費物質的同時也消費女性,她們出沒依賴的商場歡場和“艷窟”,也是吞噬她們的 “人肉廚房”,新感覺派小說在這樣的意義上表達了都市與女性“被吃”的關系和意象。
充滿復雜性的上海都市又是撕裂和碎片化空間,它不僅制造了對立的多樣化的階級與階層,更使得被拋進都市旋渦的個體都是痛苦、孤獨和渺小的。由是,將中產白領階層、都市浪子和下層貧民立場一勺燴的新感覺派小說,那種天堂與地獄比鄰共存的上海都市印象和空間表征,其實內里表達的,是上海都市空間的撕裂化與碎片化,是被看不見的巨手攪進殖民與現代雜交的現代都市、急于想適應又難以適應、急于想跟上都市快節奏而又跟不上所產生的心理焦慮……這種復合交集的心理折射出的,就是碎片化與絕望化,而絕望后的反應自然就是對都市空間種種現象與存在的惡魔化——它是妖魔和魔窟。那些在夜總會和舞廳里跳著上海狐步舞的人,那些煙酒肉欲和黑人侍應,其實在深層里具有一種狐貍妖魔的隱喻。焦慮和妖魔化的下一個反應,就是逃離。所以,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黑旋風》表達的都是對碎片化妖魔化的都市絕望焦慮后的想象性出走——到水泊梁山避難與造反。這樣的離開都市上山落草造反的抗拒都市的模式,是城市貧民也是流氓無產者和小資產階級在都市焦慮下的自然的、千古不絕的俠客夢和大王夢,與真正的階級斗爭意識毫不沾邊。而這樣的心理反應,又恰恰是與都市空間對應的都市精神世界之一種,是都市空間碎片化的精神表征。
三
與客觀存在的和文學敘事中上海都市形象與空間的多維不同,京海構造另一極的都市北京,就像它自身具有的內涵面貌、文化地理和空間景觀一樣,它是中國另一種都市和都市文化的代表,呈現出自己獨有的風姿。對都市北京及其人生視景,林徽因、老舍和林語堂的小說都有出色的描繪,其中老舍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最地道的京味小說的集大成者。老舍的文學寫作及成就與北京相輔相成,離開北京,老舍的小說成就大打折扣,離開老舍,北京的城市與人生社會景觀不會這樣的顯著和有特色。老舍與大多數五四后寫作的作家一樣,骨子里有與改造國民性、改造國家的啟蒙主義相通的精神追求,有強烈的愛國情與故土情構成的家國關懷。早在寫中國人老馬父子的異國生活并構成文化對比的小說《二馬》中,老舍就處處拿半殖民地又歷史悠久的老中國和中國人,與殖民地強國的英國和英國人,其實也是與整個西方世界進行文化與民族性的對比,對“出窩老”的中國人的中庸、保守、愚昧、羸弱和由這樣的國民構成的“貓國”,發出了既幽默又痛心的指責。沿著這樣的思路,老舍在其后的一系列以北京的城與人為表現對象的小說里,借著對北京和北京人的敘事,指事和言說中國——中國人和中國的形象、中國的歷史與現狀及未來、中國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的生死存亡,幽默的北京味里依然暗含著感時憂國的傳統。
老舍的京味小說無與倫比地形塑了北京和北京人(主要是北京市民)的形象,是北京的自然、歷史與文化社會地理的形象表征。從《駱駝祥子》到《四世同堂》,老舍小說對北京的自然環境、建筑街道、天候物產等,做了出色的具有自然地理意味的描繪。北京的自然環境與城市空間,無不顯示揭示著北京的古老與內斂、知足與保守、等級與秩序,一個古老帝都代表的老中國的氣派與停滯。北京城自然和物質空間的古老性與保守性,對象化于它的子民和市民中,換言之,是中國的老文化“物化于”北京都市的物質空間,而這物質空間凝聚的傳統與文化又作用于北京人的精神空間與世界。在老舍的小說里,北京的城與人構成緊密聯系,北京的城市形象更多地被北京人的精神行為所代表和表征。如果說在海派文學中,上海市民盡管依賴于都市環境而生存和作為,但又與都市環境是隔膜和疏離的,骨子里是都市的匆匆過客。而老舍筆下的北京市民則過于依托、依賴皇城都市的物質與精神的“皇城根”,千年不變的帝都及流溢于其中的精神文化、最有中國味的物質與精神文化把他們同化了,他們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如果上海是殖民的、摩登的、過于追求現代和變化的、碎片化的,北京則是拒絕前進的、退守的、活在過去的古墓般的寧靜而僵化地方。這構成了北京的特征,并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的隱喻。
這樣的北京城及其文化,好處是保留了若干傳統里的好東西,使北京城成為一座文化城,這文化不僅表現在那些故宮里的古文物和大學的眾多,也表現在它造就了一批守持文化傳統的文化人,如《四世同堂》里不食周粟、殺身成仁的錢先生一家,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傳統里最有價值的那份氣節、高貴和正能量。但就總體而言,老舍小說里,的北京城及其文化的負面價值遠大于正面價值,是消極傳統而非積極傳統,其對依賴于皇城蔭庇的北京人的精神世界的影響,也大多是負面的。最明顯的,是導致老北京人的守舊閉塞和空間意識的狹窄:世界的全部就是北京城和自家庭院與胡同,只知有家而國家意識淡薄甚至懵懂,特別是像《四世同堂》里祁老太爺那些老北京市民而言,世界與中國就是小羊圈胡同和自家屋院。同時,這老北京城也造成他們時間意識、時代意識的淡薄與短視,就如祁老太爺在日本人進城后的所作所為:把大門頂住不外出,北京再大的災難也不出三個月。一場曠古未有的巨大民族災難被他們的時間意識給短暫化和窄化了,他們是時間的“不感癥”者,沒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長時段意識而總想停滯在時間的某一點上。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小說《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寫的是都市人與事的無常與快變,講的是適應快變及時行樂的必要性和追不上善變的時間與生活的悲劇性,是對時間的麻木中表達出殖民地都市紙醉金迷生活的模式化和均質化,是時間與空間內容的對立——時間是流逝的動態的,而空間里的都市社會生活內容卻是不變的和同一的,是模式化的。與此相反,老北京人的時間不感癥追求的是時間的停滯與不變,是由于“古已有之”的歷史與生活的同質化、少變化造成的時間與時代感缺失。時空固化和窄化及生活與歷史的循環造成的社會與人生的同質性,不僅造就了老北京人的善良而無用、中庸而平庸的精神弱點,也造就了一批單純追求物質享受而沒有精神操守的痞子與京油子,和平歲月他們是行尸走肉,亂世來臨他們就是漢奸無賴,如《駱駝祥子》里的車廠主和偵探特務,《四世同堂》里的冠曉荷、大赤包、李東陽、胖菊子等一干流氓——北京城也是藏污納垢和生長膚淺的“壞蛋”惡人之地。在這樣的意義上,北京城縱然在時間上是停滯和不變的,其形象和內涵卻也是復雜的。
老舍小說里,北京城的這種正傳統與負傳統、好與壞、善與惡兼而有之的社會存在和景觀,使得北京代表的都市文明顯示出復雜性乃至腐蝕性,特別是對下層人民和鄉村而言,它更顯示出腐蝕性和歷史與道德的“惡”的面目。因此,老舍筆下的北京城也具有了道德空間的色彩,承載著作者來自市民意識形態和啟蒙意識交融形成的都市文明批判的價值觀。這種都市文明和道德批判的訴求,在《駱駝祥子》里得到集中的體現。如小說所揭示的,淳樸憨厚的鄉下農民祥子到北京城謀生,遭遇了一連串來自社會總體黑暗的磨難與打擊:軍閥混戰、特務橫行和從夏太太到虎妞的一連串都市魔女的“色誘”與吞噬。如此的城市不僅是鄉下人和底層貧民的地獄,也是腐蝕人性的魔窟。可悲的是進了城的鄉下農民卻再也無法回到鄉村,惡魔般的都市有惡也有魔力:祥子在被虎妞“色誘”之后,一度打算跑回鄉下,可最終覺得這有北海白塔、軒屋美服之地,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死也不回鄉下”,不回去的結果只能是墮落到如活死人,城市徹底消滅了來自鄉村文明的一切人性美好。都市無所不在的黑惡、人性難逃腐蝕敗壞、是苦難之地也是誘人魔窟(存在從虎妞到夏太太等各種吞人精血的“妖精”)的形象,是老舍對都市文明與道德批判的濃墨重彩之處,也是老舍描繪的北京的文化地理和社會景觀。而在這一切描寫的背后,老舍小說顯示出他受狄更斯和福爾摩斯小說影響的色調:社會轉型期造成的都市苦難與罪惡,無約束的權利和統治者對都市的控制與造惡,底層人民在都市的沉淪或犯罪,善與惡在都市的交織和彌漫。只不過狄更斯等人在對都市苦難與罪惡、監禁與懲罰的背后指向了資本的魔力和權利,而老舍筆下的城市形象反映出的更多的是社會轉型與失范時代皇城帝都背后整體權利與統治的失控、道德與文明的潰敗,是類似于田園潰敗主題的都市翻版。
與老舍同屬于自由主義的作家沈從文,在以詩情畫意描繪老遠的湘西遍地的世外桃源風情、表現他的桃花源情結,并給世人臆造出一個希臘小廟式的想象的烏托邦的同時,也以稍顯笨拙的筆墨刻畫著他身在其中又倍感難受的都市。但區別在于,海派和左翼作家描寫的上海,是殖民性與革命性充斥的都市,殖民性帶來了現代與摩登,現代化的工廠也成為工人革命、政治革命的策源地,是殖民化現代化的天堂,也是貧民的地域,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被動現代化過程中復合現象的交集;而老舍筆下的北京是典型的古都皇城文化,市民與官場文化是主流,時間與空間的停滯造成舊中國都市的特色。而沈從文描繪的都市,是他以一個遍地鄉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表達對都市厭惡的文學反映,這個都市沒有現代與傳統結構中的任何特點,既非殖民現代的,也非古老傳統的,只是一個模糊的都市輪廓。當然,也對湘西宗法原始世界自然與人事皆美的鄉土中國夢的描繪相反,沈從文對都市是整體否定的,特別是都市上流社會——官場、官員、闊人、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紳士家庭、都市婦女等“都市中人”,既從性格身體上揭示他們的“閹寺”性——普遍的性無能,也從道德上揭示他們的虛偽自私和毫無人性。都市是人性——從身體到精神到道德的毀滅之地,是基督教里的索多瑪城,應該被毀滅。這是沈從文的都市描寫的特點,是從他對兩個中國——鄉土中國的浪漫主義美化和對都市中國的現代主義厭惡的思想和價值觀,派生出來的文學想象和世界。兩個對立的中國形象就這樣出現于沈從文小說的全部敘事中,當然,他的鄉村敘事更為成功和具有魅力。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是復雜的,存在幾個或多個中國的聲音與形象。上述文學對都市中國與鄉村中國的描繪,既有真實中國的底子和影像,又有出自不同政治和美學訴求的作家的想象和臆造。有意味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還有大量的出自中外作家的紀實類文學關注和描繪著中國,捷克作家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左翼作家發起的“中國的一日”征文及最終由茅盾主編的同名報告文學,美國作家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都是對廣大中國的真實紀錄。除了斯諾的報告文學,整體而言,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鄉土與都市中國的描寫,反而更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也更具有文學藝術的和文化地理的蘊含。在這個意義上,20世紀30年代文學的確承擔和完成了一個出色的使命:形塑和創造了一個媒體文字中的多種元素、多地域組成的動亂中國的形象及其表征。
[參 考 文 獻]
[1]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M].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魯迅.隨感錄·五十四[C]//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魯迅.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且介亭雜文二集[C]//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德]瓦爾特·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張旭東,魏文生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
(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孫曉平:中國傳媒大學副編審)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