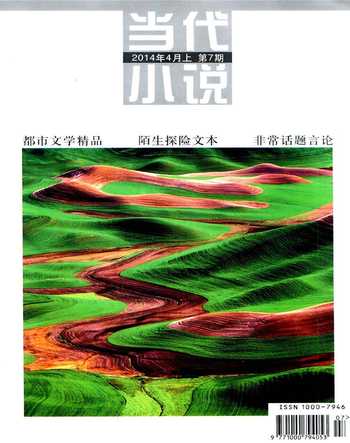清真寺案件
徐巖
1
進紅磚拱門,左首有幾棵古柏樹,正午的時候能投下來很多陰涼,每天招的人多,走來走去,上香的,扎堆看下棋的,買賣物品的,一直不斷,寺院臨街,街不寬卻車水馬龍,有路牌標明是道外頭十四道街。路燈白天也亮著,有胳膊上戴紅袖標的年輕男人在寺廟的門前巡邏,走過來,再走過去,過路般悠閑。
廟門的一側是各種吃食的所在,有兩家燒烤鋪子,破了洞的窗玻璃中往外冒著黑煙,鋪子里烤的都是素食,有韭菜串、饅頭片和插滿了竹扦子的大蒜瓣,實在想吃葷腥了就來串雞脖子,上面抹了辣椒粉和色拉油,進店里邊去吃或拿草紙裹了走。旁邊還有一家面館,格子窗,玻璃上貼了彩色的紙,里面是十幾張黑色的木桌椅,同樣黑色的烤漆桌面,干凈亮堂,灶房售貨的窗口擺著剛出鍋的花卷饅頭,大桶的羊下水湯,極其刺激食欲。
這應該是清真寺廣場早些年的情景,可自打小鎮經歷了一次地震之后就變了樣,地震發生在這個春天的一個夜晚,一場大雨將這場震級為3.5的地震給遮蔽了,人們只是感覺自己家棚頂的燈泡晃了一下,地震便完成了,就是在這個雨夜,清真寺廣場的門前發生了一起案件,離案發現場最近的建筑派出所民警老胡帶著小警察齊玉亮騎自行車來勘查現場,下午四點一刻,天要黑還沒黑的光景,街巷里都亮起了燈,民警老胡正在派出所的院子里給自行車鏈子上抹黃油,副所長陳海峰喊他出警,老胡扎煞著手問哪里又響雷?響雷是民警們的辦案用語,意思指那塊又發生案件了,陳副所啞著嗓子罵咧咧地說清真寺廣場跟前一家酒鋪子不知什么玩意兒爆炸崩著人了,你快帶人去吧,別磨磨蹭蹭的。陳副所長剛一說完話,天上就響了個雷,雨水緊接著瓢潑似的噴灑下來,剛剛還晴朗的天頓時間烏云密布,陳副所氣得仰起臉又罵道:這也不知咋了,昨個地震,今天又響雷,這是老天爺發怒啊,把各方的妖魔鬼怪都給放了出來。
民警老胡趕緊拿起地上的抹布胡亂地擦去手上的黃油,喊上新分來的民警小范推車子出警。
2
兩個人來到清真寺廣場欲進正門時,被一個矮胖的中年男人給擋了,中年男人穿了件紅色的汗衫,腰上扎了條油漬麻花的圍裙,男人說你們是派出所來破案的警官吧?民警老胡邊點頭邊問他是哪一個?矮胖的男人說報案電話他打的,他是燒烤鋪的老板,剛剛有一伙人在店里打架斗毆,出人命了都。
矮胖男人故作驚恐狀地拿手指了指旁邊的一間店鋪說,都是這家燒烤鋪子惹的禍,你們自己進去瞧吧。鋪子面積不大,不過兩間臨街的磚房而已,里面挨排擺放了十幾張學生用的課桌,凳子都是有顏色的塑料椅,用餐區跟廚房之間用一塊透明玻璃隔著,往里頭張望,能看見兩個中年婦女正動作嫻熟地圍一張案板串肉串,烤箱更不設在屋里,是擺在屋外的窗戶底下,此時看到的是已經翻倒在地的盛著火炭的鐵箱子和油鹽作料瓶,民警老胡問矮胖男人是誰出了人命?男人幾步走到廚房門口,進去手腳麻利地從里面拽出一個腰上扎了圍裙的婦女說,是她家老六,拿刀把一位吃飯的客人給殺了,你說平時老實巴交的,上真張就來虎勁了。扎圍裙的婦女插話說,還不是被那喝多了酒的家伙給逼的嘛,他灌點貓尿罵俺家老王是頭蠢驢,你說這樣歹毒的話他都能夠說出口,還能怪俺家老王不動刀子宰他?矮胖男人說我看你家老王平時的老實巴交都是裝的,真就是如那人所說,是頭蠢驢,挨幾句罵算個球,又不能掉幾斤肉,至于動刀子殺人嗎,就好像殺人不償命似的,我看他確實是一頭蠢驢,哪頭輕哪頭重都不曉得。看兩人的樣子大有打起來的架勢,民警老胡擺手將兩人的爭吵及時的制止住,問婦女殺人的人和被殺的人都去了哪里?矮胖男人搶先說,被殺的讓救護車拉走了,宰人的老王跑了。民警老胡聽后有些怒氣地說,跑了,跑哪去了?矮胖男人自己嘀咕說,還能跑哪,也就火車站唄。民警老胡轉身望了一眼自己左側火車站的方向命令跟他一起來的那個新民警,抓住立在旁邊的自行車騎上便往派出所回。
3
回所里后民警老胡把出警的情況跟副所長陳鵬作了簡單匯報,陳副所長一拍桌子說,趕緊帶幾個人去火車站抓人,這個案子牽扯到民族團結問題,應該盡快破案才對。民警老胡又拉響警鈴,集合了在家的十幾個民警,整裝直奔火車站。
十幾個民警擠在派出所惟一的那輛面包車上,一路警笛呼嘯著奔城南的火車站方向疾馳,車出派出所大院沒幾分鐘,老胡突然想到個問題,他趕緊掏出手機給陳副所長撥了過去,電話里老胡說有一點忘了提醒領導了,那個被殺的食客被救護車拉醫院去了,應該安排人去看看是死是活。陳副所長扯著公鴨嗓子告訴他這件事他會安排人去辦,你老胡的任務便是趕緊到火車站布控抓人,咱丑話說在前頭,要是因為你們貽誤了戰機,讓殺人犯跑了,組織上饒不了你。民警老胡聽著陳副所長的聲音嗡嗡的在電話里響心情突然煩躁起來,心里想所長外出學習不在家,你就是個副的,臨時負責而已,喊什么喊,說殺人那是要有證據的,你又沒有去現場,我和新來的小民警去了,沒抓住人不說,連受害人也沒見著,你怎么就斷定是殺人案呢,老胡腦袋里亂亂的像一鍋粥,就在他使勁理著頭緒時,面包車吱嘎一聲來了個急剎車,哐當一下停住了,順車窗玻璃往外看,老胡發現已經到了火車站廣場的入口處,老胡把剛剛復印好的犯罪嫌疑人照片每人發一張吩咐大家快點下車分頭去找,有人接了照片復印件問找到了怎么辦?老胡說先帶回去再說,那抓人的理由呢?又有人說,這句話倒是把老胡給問住了,他低下頭想了想說,就說有案子需要他回去配合調查,總之不管你想個啥理由也得把人給我帶回去,千萬不能放跑了人。
看著車上的民警都下車涌入了火車站廣場鬧哄哄的人流中,老胡也下了車跟上去。
民警老胡他們搜遍了整個火車站廣場,包括候車室,也沒有發現那個從清真寺廣場逃跑的殺人犯的身影,老胡親自去問了那個設在候車室門口的問事處,從早晨八點到現在這三個多小時時間里,總共有八列客車離開這座城市,奔西而去,老胡之所以查西行的客車是有原因的,他在清真寺廣場發案的那個小飯館里勘查現場時悄悄地問了那個知情的矮胖男人,打聽到所謂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小飯館的燒烤師傅王大志是新疆籍,老家是位于南疆庫車北部一個叫木塔里普的小鎮子,真要是他殺了人的話,那他只能選擇坐火車逃回老家去這一條路。
老胡安排民警管幸福帶兩個人繼續到車站廣場附近的飯館旅店等一些消費場所去查找,自己給陳副所長掛電話請示用不用乘車去王的老家追捕,陳副所長斬釘截鐵的告訴他可以去,就由他帶隊去一個小組。
半小時后,民警老胡跟兩個伙伴趙警官及省刑偵學校畢業剛分來的民警小范登上了西行的列車,三人在車廂里找到座位后車就開動了。上午的時候老胡問了在車門口驗票的列車員車到終點站烏魯木齊需要運行兩天一夜的時間,這一時間概念將意味著三個人的旅行將極其的漫長和枯燥,比老胡小幾歲的趙警官埋怨民警小范應該在買票時給老胡買一張臥鋪票,畢竟旅途遙遠,老胡年紀又大,老胡則擺擺手說用不著,他身板硬朗得很,硬座也挺好,三個人坐一塊兒能聊天不說,還能看車窗外面的風景,干了大半輩子警察,新疆他還是頭一回去,趙警官坐在一旁插話說喀納斯湖很美,得閑要去看一下。
兩天后的下午,三個人下了火車,又乘機動三輪車輾轉兩次到了新疆的邊境城市庫車。按照陳副所長發給他們的犯罪嫌疑人王大志的原籍地址,三人又坐驢吉普連夜趕到了庫車河西岸塔里木湖一側的草湖鄉,在當地派出所的檔案室里查到了工大志的真名叫吐尼亞孜,老胡斷定王大志是他到內地打工時辦的假身份證的名字,既然查到了這個人,三人心里懸著的一塊石頭暫時落了地。三人又趕到王的居住地阿格洛村,于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的房子里見到了他的父母,王的母親是一位蒙面的維吾爾族婦女,端坐在一把老式的木椅上,她的褐色面紗一直垂到膝蓋,眼神黯淡,好像我們幾位陌生人的來訪跟她沒有一點關系。陪我們一同前往的那位黑臉警官小聲地用我們聽不懂的維語跟老人交談,幾分鐘后他才回轉身來告訴我們,吐尼亞孜到東北打工賺錢,走了三年,一直沒有回來過。黑臉警官的話讓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在老胡的眼神的指揮下,趙警官跟民警小范兩人快速地走進隔壁的屋子,仔細地搜查了一遍,確認沒有他們要找的人后才會同老胡一起往大門外面走。回到庫車后,三個人尋了坐落在庫車河岸邊的一家維吾爾族小飯館吃飯,隔窗就能夠看見穿城而過的庫車河,龜茲古渡,遠處的清真寺和滿街的毛驢車,老胡等三個人不認識寫在菜譜上的維文,只好拿手指著鄰桌兩個人吃的食物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要三份,他們指的是新疆的美食抓飯,每人適應著吃了一大盤抓飯后,都有了精神,便決定回小旅館休息,睡好覺明早再到當地派出所查找線索。回到小旅館后,老胡打電話把情況跟陳副所長做了簡單的匯報,問人沒回來怎么辦?陳副所長明確指示他們,要蹲守幾天,爭取抓到人,別白跑了那么遠的路。
夜里睡下時感覺房間里很冷,外面似乎起風了,有東西不停地擊打窗玻璃,趙警官說一定是下雨了,他說完就披衣服起身推門出去看,回來告訴老胡他們外面刮的是沙塵暴。趙警官隨后還說了一句:這鬼地方。
三個人一直在這個鬼地方呆了七天,也就是第二天的早晨,老胡給幾個人分派了任務,趙警官帶民警小范繼續去王大志家附近蹲守,自己則去了庫車城北的那個西街派出所。他先是調取了王大志,也就是吐尼亞孜的檔案,其中有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在他青年時期曾經在本地做過鐵匠爐的學徒,有了這一發現后,老胡從西街派出所出來就一個人去了城南一條叫沙依巴克的街上去轉了轉,他是從一個到西街派出所辦理戶口的當地人嘴里得知那條街的巷子里有幾間鐵匠鋪的,老胡進巷子后一間鋪子一間鋪子地找,到第四家爐的時候終于問到了吐尼亞孜曾經當過學徒的鋪子,里面的一個爐燒著通紅的火,鐵錘叮叮當當,兩個男人腰上都扎著帆布圍裙,守在爐火邊打鐮刀,這種鐮刀呈拋物形,初被捶打時還能夠看出是一彎扁鐵,打著打著就有了雛形,如一個幼芽剛從土里長出來。鐵匠師傅知道它會長成怎樣的一把大彎鐮,他們手里的錘從那一刻起,變得干脆而有力。
民警老胡給暫時歇息的鐵匠師傅和他現在的徒弟每人點了根煙卷,閑聊中知道現在的鐵匠師傅叫吐迪·艾則孜,也是吐尼亞孜曾經的師傅,他用幾句生硬的漢語告訴老胡吐尼亞孜早就不學打鐵了,他要出去賣苦力掙錢回來蓋新房子結婚娶媳婦。打鐵太累人,又掙不上錢,像他這個當師傅的都打了幾十年鐵了,還住在破爛的房子里。
晚上回到小旅館里后,趙警官說他們又是白守了一個整天,也不見吐尼亞孜的人影,是不是陳副所長搞錯了,那家伙根本就沒跑回來,或者逃到別的地方躲了起來,老胡說咱再堅持幾天,守到這個月末就往回返,這樣沒頭沒腦的案子沒法搞,這陣子弄得腦瓜仁子都疼。陳副所倒成了甩手掌柜,把咱們派出來他連個主意也不幫著拿。
坐床沿上捧茶缸子喝開水的民警小范說陳副所現在沒時間顧咱們,他正接受分局考核,等著提職呢。老胡說沒影的事情別亂講啊小兄弟,說的跟真的一般,趙警官插話說是真的,中午我倆去郵電所給家里掛了個長途,李民,常超,于關勝他們正忙著畫票呢,分局政治部來工作組搞民主測評,所長正式調走了,得有人補缺的。老胡說他們愿意測評就測評,咱哥幾個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安心干好活就得了,不許操那個心。
4
三天后,民警老胡他們等到了吐尼亞孜家里人的報告,聲稱人回來了,來報告的人是吐尼亞孜的母親,說人正在家里睡覺,老胡他們趕緊跑步過去,將人控制住并帶回了小旅館,令人不解的是吐尼亞孜沒有絲毫的反抗,很老實很乖順的就跟他們回了旅館,老胡讓事先找好的維語翻譯,小旅館旁邊一所中學的老師古麗告訴他是因為他在東北殺了人而被抓之后,吐尼亞孜竟然點了頭表示承認。
按照陳副所長的意見,民警老胡他們拘押了王大志后就地進行了突審,王大志承認他是在哈爾濱道外的清真寺廣場那家燒烤店里做燒烤師傅時跟一位客人發生口角而動手傷了人,那人是喝多了酒而用言語挑逗謾罵他方把他激怒的,坐在桌子前執筆記錄的趙警官問他那人說了什么話來激怒他?王大志操著生硬的漢話說那個可惡的家伙竟然讓他給烤兩只豬蹄子用來下酒,王說完這句話又改用了他流利的維語,老胡他們請來的翻譯告訴他們吐尼亞孜十分生氣,他強調跟他打架的那個人不尊重他,在回族的燒烤店里提及豬肉食品那就是侮辱他們的人格,是讓人無法容忍的,他不得已才動了腰刀的。王跟老胡幾乎同齡,有四十歲的樣子,正是人生中精力旺盛的時候,難免會血氣方剛,老胡問他傷人的那把刀子在哪里?吐尼亞孜搖頭說當時就丟掉了。老胡逼問他究竟丟在了哪里,是現場還是其他別的地方,問了好幾遍,吐尼亞孜都沒有說清楚。最終案件只能算有了眉目,罪犯抓獲了也有了口供,但終究是沒有人證和物證,這樣結案有些牽強和草率,老胡把電話打給陳副所長,陳說人抓住了,又交待了那還不算結案算什么,你們把審訊筆錄傳真回所里任務就算完成,就抓緊打道回府吧,一定要把人看好了,別途中逃跑就行,回來給你們請功。老胡對著電話說真的嗎陳副所?陳說那還能有假,你陳哥咱已經被任命為大所長了,跟上級領導說句話還是有分量的。
5
掛斷電話后老胡的心里多少有點喜悅,陳副所畢竟有那么一句暖心窩的話,請功事小,有那份心意足矣,領導下令讓他們返回了,這意味著哥三個這次的苦差事算是完成了,老胡想的是這來去的一折騰已經有幾天的時間了,餐風露宿不說,飲食習慣太成問題了,到庫車后幾個人天天手抓飯或者羊湯泡馕,吃的沒一個不反胃的,他已經暗中問好了那個翻譯女老師,城東有一家漢人開的面館,很地道的,他決定晚上便帶兩個兄弟去改善一下伙食,適當的也可以喝一壺酒,權當慶祝一下這次辦案之旅。老胡還想怎么也得多留兩天,帶他們去幾十公里處的喀納斯湖景區看一眼,從黑龍江到新疆行程之遠,來一趟著實不容易的。
晚上到城東那家面館聚餐時老胡特意邀請了西街派出所的兩個同行,警長韓富貴和外勤民警庫爾班買買提,所有的人都吃喝得興高采烈,到最后,趙警官和小范還隨著買買提跳起了民間舞蹈買西來甫。
不是有句老話說嘛,樂極生悲。這話有時候是很靈驗的,就在老胡他們聚餐的第二天下午,在西街派出所的小會議室里喝茶聊天的老胡他們三人趕上了派出所的維族兄弟出警,看著幾個人慌張地套警服掛警械的樣子老胡問已經熟識了的韓警長發生了什么事情?韓說有人舉報城郊客運站有人販子出沒,被拐賣的據說還是你們東北的婦女。老胡一聽氣得拳頭立馬攥了起來,他望著韓警長說,我們也去協助你們抓捕如何?正是他這一句話導致了后來一起事故的發生,隨后的抓捕行動中,民警小范由于缺乏經驗,被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用刀刺中胸部,因流血過多而犧牲。事后韓警長說導致拒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那名販賣團伙的骨干分子察覺抓他的小范是漢人才被激怒的,老胡他們去的那段時間,庫車在內的所有新疆南部地區正鬧民族分裂,一些有劣跡的維族不法分子情緒異常激動。老胡徹底傻了眼,本來這趟任務完成得很好,沒想到中途又發生了變故,因為自己的逞能而損兵折將,小范是個多么好的小伙子啊,昨天還生龍活虎的,轉眼間人就沒了。在庫車西街派出所弟兄的幫助下幾個人把小范的遺體做了火化處理,于當天晚上,老胡跟趙警官兩人抱著小范的骨灰盒,押著王大志登上了返回東北的列車。在火車站刮著寒風的站臺上,韓警長跟庫爾班·買買提來送他們,韓警長朝著趙警官懷里的骨灰盒鞠躬后真誠地說對不起了,是他們的責任,沒有履行好地主的職責呀。老胡抓著韓警長的手說不怪你們的,是他這個組長不小心。列車啟動的時候,老胡跟警官趙京站在車門口,從窗玻璃處望出去,模糊的西部邊城庫車起風了,有成片的沙塵在天空中飛舞著,那些沙塵一瞬間就彌漫了老胡仍舊紅腫的眼睛。老胡小聲地在心里邊說了一句:亮子,胡哥帶你回家了。亮子是民警小范的小名,小范去年才從省人民警察學校畢業分到他們所在的派出所,可以說是出征伊始,卻因為自己的失職,把魂留在了西北邊疆。老胡感覺到自己的淚水刀子般割疼了他的眼眸,老胡趕緊轉過身來,低下了頭。
6
回到派出所的下午,民警老胡便被叫到分局法制處問責,老胡以為是小范犧牲的事情,進了門卻知道不是,法制處的劉德偉處長告訴他新疆庫車之行他們完全抓錯了人。老胡拿手摸了摸長得有些過長的頭發說,難道抓回來的人不是王大志?劉處長說是王大志,但錯在王并沒有殺人。劉處長的話無疑像一顆炸彈,一下子就把老胡給炸暈了,老胡好半天才結結巴巴地問到底是咋樣的一回事情,劉處長告訴他王大志在清真寺廣場的那家餐館里跟人打架動了刀子沒錯,但是只是皮外傷,受害人根本就沒死。在場的分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李衛東說,胡福海你是名老警察了,怎么出現場都不認真呢,一起普通案件愣是被你們搞成了殺人案,從即日起你就留在分局接受法制處的調查,聽候處理。民警老胡的腦袋有點發蒙,他的第一反應是案子辦錯了,隨即他想,怎么就錯了呢?犯罪嫌疑人已經被他們抓回來了呀,而且還對自己所犯罪的事實供認不諱,在他低著頭吸煙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分局刑偵大隊的老管推門進來告訴他案子確實是辦錯了,因為受害人根本就沒有死,這是開玩笑,而且這玩笑還讓他們給開大了,分明就是冤假錯案。老胡拿手使勁摸了摸自己的后腦勺想,自己怎么就那么笨呢,當了十多年的警察,辦殺人案哪有不查實受害人的情況的呢,真是老糊涂了。
7
老胡在分局法制處呆了兩天后,問題弄清楚了,這確確實實是一起假案,始作俑者是他們派出所的副所長陳海峰,分局紀檢部門已經介入調查,回派出所一周的時間,分局政治部主任帶工作組來所里宣布命令,撤銷所長陳海峰黨內外一切職務,停止工作反省,一道被停止工作的還有民警老胡和趙警官。老胡知道他們是吃了陳副所長的鍋烙,事情弄清楚了,副所長陳海峰為了給自己的升職創造有利條件,親自謀劃并設計了道外區清真寺廣場燒烤店的那起殺人案,他先通過找那家燒烤店老板,一個姓張的自己的親戚做好了新疆籍燒烤師傅王大志的工作,由王扮演這起案件的主角,也就是那個殺人犯,設計如此,實質上并不是真殺人,而是假裝打架時動刀子制造血案之后逃跑,跟他講好即便抓捕他那也是做樣子,不會量刑入獄的。陳這么做其意圖就是說明他們短時間內破獲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騙取上級的信任并借此邀功,因為此前王大志有事情正求助派出所幫忙,他在清真寺廣場的那家燒烤店做燒烤師傅干了五年沒有拿到工錢,陳副所長答應事后幫他討回所欠工錢,算是作為回報。案子結案后,陳海峰憑借這一假成果受到了分局的表揚,并在提職考核時受到影響,順利晉升為所長。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幾天里,清真寺廣場的燒烤店里發生了一起真正的殺人案,那個被殺的食客又一次跟同屋喝酒的一個醉酒男人發生口角,被其用彈簧刀刺中心臟不治而亡。分局治安隊出現場時發現被害人的情況跟不久前分局下發的清網行動的戰報中一起已破獲案件相似,經過比對發現問題,兩個被害人竟然是同一個人,這意味著這名受害人一個月的時間里被殺了兩次。如此滑稽奇怪的情形讓他們有所警醒,立即報告了分局法制處的領導同志,經由法制處領導核查弄清了其中的緣由,進而查實了這起假案。民警老胡了解了整件事情的原委之后真是有些哭笑不得,老胡頓覺他的兩只手有些癢,他苦于副所長陳海峰那廝沒在身邊,如果在的話,他一定會掄起胳膊狠勁抽他幾個耳光不可,絕不手軟,也絕不含糊。
8
三天后的一個下午,民警老胡收拾了自己的東西,跟派出所的同事們告別,他剛接到上級領導通知,鑒于前不久的那起假殺人案,分局政治部門下發了對他跟趙警官的后續處理意見,兩人均降一級警銜,從城里的派出所發配到郊區看守所當管教。老胡很愉快的便接受了組織的決定,他以極快的速度跟所里的新民警交接了工作,打算下午就去郊區監獄報到,新任的所長想留他和趙警官晚上一起吃頓飯,畢竟是兩個老民警,即便是犯錯誤調離也應該送行一下,被老胡擺著手拒絕了,他想好了自己真是沒有臉吃那個送行的飯,他怕想起那個叫范玉亮的小兄弟來心里難受。
9
到郊區看守所的第二周的一天,在監獄大門口值班室里值班的民警老胡在快下班的時候接待了一個自稱犯人家屬的矮胖男人,老胡看此人有些眼熟,便問他來接誰?矮胖男人說他是道外清真寺廣場紅旗燒烤店的老板,咱們見過的。老胡便想起了是辦那起臭名昭著的假案時見過此人的,心里猜想他要接的不會是那個被冤枉的王大志吧。正想著的當口,監獄的大門打開了,那個被他們親手從新疆庫車城抓回來的維族人吐尼亞孜提著行李卷從里面出來了,那被剃光了的短寸頭在陽光下閃了一下,竟是極其的刺眼。民警老胡趕緊將身子隱藏在了值班室的門后邊,低下頭不吭聲了。
吐尼亞孜隨著矮胖男人走后,老胡翻看了下桌上的日歷,季節已經進入深秋,他清楚地記得他們的那次新疆之旅是六月十一號,那時還是夏季,王大志被抓回來后送進看守所關了四個半月,這一百多天對于王的家人來說,他一定是下落不明,這樣的下落不明將一種強烈的罪惡感塞進了老胡的胸腔,使老胡幾乎透不過氣來。
責任編輯:劉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