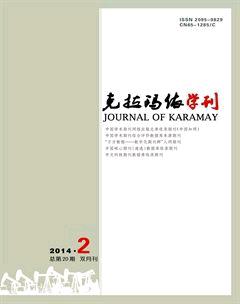儒學:大一統權力無害化處理的歷史智慧
苗永泉 張銘
摘 要: 大一統政治的建立有其歷史合理性,但高度集中的權力也有自我異化的極大風險。秦王朝快速覆亡之鑒為漢以后大一統政治與儒家形成一種“共生型”結合提供了契機。儒學提供的意義世界、精神家園、文化網絡、治道原則與理想政治制度,形成了對權力的“儒化”與精英階層集體無意識的塑造,而科舉制的采納更使儒學精神向整個社會擴散滲透。所有這些都使得大一統王權治統難以長期逾越儒學道統,從而構成一個成功文明不可或缺的對國家權力的有效制約。
關鍵詞: 大一統政治;儒學;共生關系;權力的儒化
中圖分類號:D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829(2014)02-0028-05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后,儒學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被定位為專制主義的幫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氣候,也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價值。但“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及其釀成的亂局,還是引起不少學者的反思。海外學者林毓生首先質疑了“五四”時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做法。90年代以后大陸學界也開始對此作出較為深刻的反思。盡管如此,由于種種原因,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的傾向在今天的大陸政治思想界仍有較大的影響。
如何看待自己的傳統與歷史文化,是一件直接關系到我們當前道路選擇的大事。本文力圖表明,“儒學中國”在歷史上的成功,是以建立對大一統權力進行有效約束為基礎的。而儒學之生命力也正體現在它能對高度一統的王權作出“無害化”處理。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對我們而言不是包袱,而是一種歷史智慧。
一、大一統政治的結構性要求:儒學制約一統王權的時代背景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經由周秦之際發生的劇變而形成的大一統政治架構幾經變遷,一直延續到帝制時代末期。其間雖有分裂動蕩局面的穿插,但最后都復歸于大一統秩序。而作為這一政治架構開創者的秦王朝能從列國爭雄中勝出,受到歷史之垂青,自有其道理。正是秦王朝經改革而形成的“嚴密的行政結構”與“高度現代主義的政府”,[1]168以“編戶齊民”的方式下沉到了社會基層,體現出了高度組織性與無與倫比的效率。可以說,這是歷史在那“爭于力氣”時代所選擇出來的“獨門武功”,并由此形成華夏文明在國家制度領域中的一次創新。
今人多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參照系,對具有“帝國體制”或“專制主義”特點的大一統政治架構不以為然。這樣的認識在當下雖說是可以理解的,但卻缺乏一種必要的“歷史感”,沒能看到帝國體制在前現代社會具有它的普遍性,[2]3沒能看到大一統政治架構的出現,既是當時的一種制度創新,同時也顯現出歷史選擇一向較為偏愛的比較優勢。
這里所說的比較優勢大體上指的是一個文明所具有的超強組織動員能力、超強汲取和分配資源的能力,以及進行大規模、大范圍的統一指揮、統一協調與統一行動的能力等。具體一點就華夏文明來說,這種能力的獲取使得高度集權的中央權力能在與周邊游牧文明長期的抗爭中占有先機,保持農耕文明內在的穩定發展環境;能使得那些對農耕文明深入發展至關重要的大型水利工程與防御工程修建成為可能;還能為整個社會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分工、協作向縱深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規模平臺,從而為農耕文明的進一步升華創造有利條件。可以說,華夏文明之所以后來能登上世界農業文明發展的巔峰,與大一統政治架構所具有的這些比較優勢是密不可分的。
大一統文明具有自己功能上的比較優勢無可懷疑,而歷史的垂青與選擇應該說,也是以這些比較優勢的存在為前提的。然而,大一統政治架構在提升自己公共權力的集中度與強度、提升自己應對內外挑戰能力的同時,也面臨著集中起來并得到全面強化的公共權力走向濫用與自我異化的不可避免的風險。而這種風險一旦釋放,又一定會使一個國家在治理文明與治理藝術領域里全面倒退,進而遭遇全面的治理危機。因此,國家在運用高度集中并得到強化的公共權力成功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內外挑戰的同時,似乎又為自己制造了一個更難對付的挑戰,使高度集中并得到強化的公共權力接受有效的制約而不致走向自我異化。可以說,人類文明在產生國家之后的每一步長足發展,都與能否成功地應對這個挑戰有關。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開創了大一統政治架構的秦王朝正是在這方面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令后人“哀之”而“復哀之”的反面教材。一部華夏大一統文明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成為對這段歷史經驗教訓不斷進行總結與汲取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強大的、似乎不可戰勝的秦王朝以“馬上”得天下,并以“馬上”治之所招致的“二世而斬”之結局,促成了后世對大一統政治中國家應該如何治理這一問題的深思。
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儒學在漢代應運而生,漢代統治者也在認真汲取前朝“失鹿”教訓的基礎上將之“定于一尊”。儒學的這一興起從根本上來講,與其說是儒家抓住了機遇、漢武帝謀略深遠,還不如說是一種時代的呼喚,其中蘊含著某種歷史的必然。因為,大一統政治架構與儒學的結合,接受儒學道統、治統對于大一統王朝政治的約束,是當時條件下這一政治架構自身、這一國家制度上的創新能得以存續下去唯一正確的選擇。
儒學經過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大家的努力,對“過秦”、“暴秦”的教訓進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總結。世人也由此悟得,秦政之失不在其他地方,而在于過度崇尚“有為”,過度倚仗與迷信“霸道”政治。待“霸道”政治破產,儒家所倡導的“王道”政治具有的內在價值也得之彰顯。儒家在春秋戰國這個動蕩年代所提出與堅持的、但一直得不到統治者呼應的“道統”與“治統”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說對于天命歸屬與人心向背的強調、對文治禮教與治理藝術的重視、對精英的人格培養和權力自我約束的直面,對“逆取順守”、“選賢任能”、“愛民恤民”、“無為而治”等治道原則的堅持,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因應了大一統政治架構進行自新以克服自身痼疾這樣一個時代要求。
儒學在新時期中所具有的內在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大一統王朝接受它堅持的“道統”與“治統”,與之形成一種相得益彰的“共生關系”,已成一種“大趨勢”。在順昌逆亡的壓力下,對儒學的接受實際上成為大一統政治能否有自己明天的關鍵。而從新王朝統治者這些具體當事人來說,他們面對宗廟陵寢、江山社稷、子孫后代福祉時,責任意識與憂患意識的沉重,對懸掛在自己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的警醒,都驅策著他們對儒學的接納與支持。而大一統政治權力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不斷地受到“儒化”,自覺不自覺地被“自我規訓”。
歷史在這里讓我們看到,政治秩序的演進既有人們的參與,但也不是哪個人精心設計之結果。失敗者以自己的失敗標志出歧途,令后來者有機會以此為鑒嘗試其他的可能,而歷史則在人們嘗試的基礎上把那些現實的可能優選出來。那種認定儒學不過是大一統王權手中可加利用的工具的看法,無疑沒有看到歷史形成的復雜性,沒有看到社會整體秩序并不是一種完全以人們理性動機為轉移的對象。
二、儒學對大一統王權的約束與馴化
儒學與大一統政治基于“互利”而形成一種“共生”關系,是我們理解華夏大一統文明中后期演進的一個基本觀點。可以說,大一統王權的政治架構若沒有來自儒學的功能性支撐,秦王朝在國家制度上的創新便沒有得以傳承的可能,而后續的王朝也難以避免重蹈秦王朝暴亡的覆轍。
用當今政治學的眼光來看,儒學在這里所發揮的最積極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對于大一統王權獨斷權力的有效約束上,而大一統王權在尊奉儒學的基礎上不斷被“儒化”,便是這種約束成就的一種體現形式。具體來說,儒學對大一統王權獨斷權力的約束表現在如下這些方面:
首先,儒家在與大一統政治“共生”的基礎上,成為“顯學”,獲得了一種詮釋“道統”、“天命”的“至圣”地位,而正是這種詮釋權的掌控,“使儒家和儒學在與現實政治的對話與互動時,借助于對孔學和經義詮釋的文化優勢地位而能夠保持自身一定的相對獨立性”。[3]118我們知道,在東方大一統政治架構中,君權雖然至尊,但它并不至圣,對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道統、天命的詮釋權完全是由儒家來把握的。這也就是旅美學者張灝所謂的“帝”、“師”之分離。這樣一種安排雖然與西方社會的“政教分離”在形式上不盡相同,但從功能上來說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在這兩種不同的架構中,世俗權力雖然難以撼動,但其自身的合法性來源、制度架構的原則、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精神文化的掌控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儒學對道統、天命的詮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世俗權力合法活動的范圍,并通過“以禮入法”[4]345的路徑,使制度、法律與政府本身走向“儒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馴化了在秦制下幾乎無所不能的國家“硬權力”。
其次,儒家對于道統與天命的詮釋,對于文教禮治的強調體現在“治道”上,便使得“王道”、“仁政”、“民本”等治道原則成為國家治理中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而從這樣一些原則出發,國家努力與窮奢極欲的奢靡之風,與橫征暴斂勢猛如虎的苛政,與好大喜功、膜拜硬權力的霸道政治徹底分道揚鑣,將像輕徭薄賦、使民以時、富民恤民、與民休息這樣的政策落實到具體的治理行動之中,便成為必然。而具有至尊地位的一統王權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治道”的轉變過程中,在對天命無常的敬畏中,在對前朝暴亡的歷史教訓汲取中,逐步設立權力的邊界,收斂自己的行為,審慎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權力。
再次,儒學在取得顯學地位的情況下,手中還掌管了教化與儀禮的規制權。
儒學典籍、祖宗法度、經世之道與人格之規范,不僅是社會上的士人與儒生需要身體力行、率身垂范,而且也是上至儲君,下到平民子弟自發蒙之始就要接觸與學習、歷練的內容,而孔夫子更是天下學子必須敬拜的“大成至圣先師”。顯然,儒家通過“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漢書·董仲舒傳》)之方法,讓人們從小浸潤在這種無形而綿密的文教禮治中,讓儒學道統與治統進入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從而將包括權勢者在內的社會精英籠罩在一種文化軟約束中,讓普通民眾能生活在良風美俗之中,使得整個社會上層對硬權力的使用不再成為一種偏好性選擇。
復次,由儒家士大夫組成的社會精英在儒學道統與治統精神滋養下,形成一種有著強烈道義感支撐的公共輿論——“清議”,這種清議所具有的巨大正能量,能令至尊的大一統王權也不能不有所忌憚。正是這種大象無形而又無遠弗屆的清議,使得儒家堅持的以史載道的傳統代代傳承,使得它對人、對事的裁斷、糾正、評判、界分、褒貶成為一種強大無比、左右輿論、塑造人格的力量。顯然,儒學與大一統政治的“共生互利”,使得儒家成為一種名教,它培育起來的士林清議,打造了一個雖然不具剛性,但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規約一統王權的“籠子”。以為儒學不過是一統王權手上的玩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最后,儒學對于大一統王權的約束還表現在代表大一統王權的君主與其臣子間的互動關系上。這種互動關系一方面表現在君權與相權的分工上。理論上,君主擁有治理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但按照儒家的理想,君主對于國家的治理,以“無為”為要,以愛民如子、選賢任能、清心寡欲、不妄作、不擾民、真正成為萬民道德上的楷模為責任基準。這就是《論語·為政篇》所謂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照此辦理,君主便不再是“有為”之君主,其手中權力自然就“有限”了。而在另一方面,作為華夏大一統文明治理主體的整個行政官僚系統,自漢、唐以后,“儒化”日深,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從作為臣下的士大夫來說,他們既是皇權為首的官僚集團一分子,但又是儒學道統的捍衛者與儒家精神的踐行者,從整體上講,有著很強的儒學性格。正常情況下,皇帝的決策與裁斷會得到全力的執行。但當這種決策與裁斷有違士大夫心中的儒學道統時,則常常會遇到后者的抗爭,這是所謂“從道不從君”的儒家傳統使然。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講,本身就已“儒化”的皇帝還處于史官、諫議大夫和“帝師”們不易脫逃的“道義包圍”之中,真正敢于放膽一心孤行的無道之君畢竟十分罕見。顯然,在這樣一種君臣間互動的狀況下,君權的“就范”是個大概率事件。
三、科舉制、吏治與權力儒化的加固
約束權力當然不只是約束王權,還需要約束直接行使權力的官僚集團,而儒學在這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漢武帝儒學確立自己的獨尊地位,儒學在教化領域大展身手,官吏的選拔也逐步向接受過儒學教化的士人傾斜,官吏的儒化開始提速。其效果在漢代中后期已經顯現出來,史傳的循吏們在社會治理方面不斷嶄露頭角。[5]103這些循吏或儒臣的共同特點是身體力行儒家的治道原則,側重率身垂范、教化民眾、移風易俗這類文化軟權力的打造與治理藝術的提升。不過,就整個官僚集團儒化程度而言,漢代做的還較為有限。漢代大量的官吏是刀筆吏出身,儒學精神還沒有在整個統治集團與社會文化心理層面得到有效擴散。漢以后大一統局面又不甚鞏固,直到唐,儒學與大一統王權的“共生”關系才算重新有了一個較為穩固的制度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