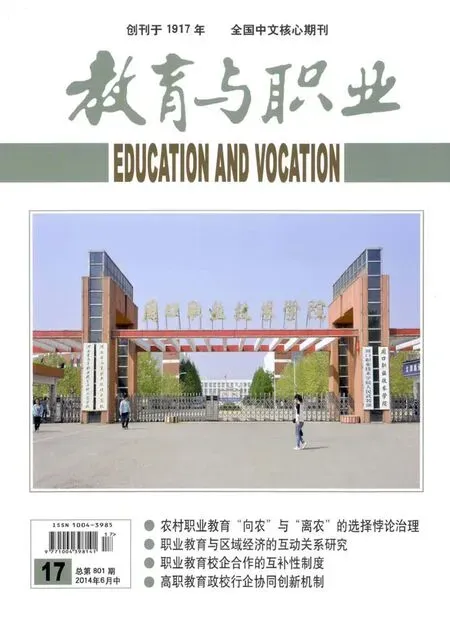農村職業教育“向農”與“離農”的選擇悖論治理
金軍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向農”與“離農”的選擇悖論,時至今日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業已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熱點話題。“向農”論者針對當前農村職業教育“離農”的發展趨勢做出了批判,認為農村職業教育應以服務農村為己任,培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人才;“離農”論者則認為農村職業教育應幫助農民子弟跳出“農門”,以城鎮化建設為紐帶,加速轉移農村人口,為城鎮化發展提供技能與智力支撐。總之,關于農村職業教育“向農”與“離農”的價值選擇悖論,各界莫衷一是,能否妥善解決對于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農村職業教育陷入“向農”與“離農”的兩難境遇
(一)“向農”是農村職業教育對浪漫主義烏托邦的向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日漸明晰,在“工具論”價值取向的推動下,百般重視農村社會進步的教育政策與舉措中涌動著“向農”的暗流。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后教育政策的脈絡梳理,不難發現農村職業教育總體上走的是“向農”軌跡。第一階段,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1958~1966年),我國開始探索性地試辦農業中學。由于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1963年黨中央發出了《全黨動手,大辦農業》的指示,農村職業中學的數量由1963年的3757所提高到1965年的54332所,三年內學校數增加了近15倍,同時在校生人數由25萬人增加到317萬人,增長了近13倍①,該階段農村職業教育辦學緊緊圍繞“向農”方向發展。第二階段,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農村職業教育處于曲折發展階段,仍以“向農”教育為主,期間農業部頒布了《中高等農業院校遷往農村辦學》的通知,指出:“中高等農業院校應當面向農村、面向農業生產,有計劃地遷往農村辦學。”②第三階段,1980~1989年,農村職業教育的恢復與發展,在此階段堅守“為農”教育。第四階段主要是農村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時期(1990~2001年),農村職業教育也逐步由“向農”教育轉向“離農”教育,在該階段國家教委(現教育部)在《深入推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意見》中提出了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農村教育結構,出臺了“三教統籌”與“農科教結合”的政策,從國家政策上出現了“離農”的傾向。第五階段,農村職業教育的高速發展階段(2002~2009年),主要以“離農”教育為主。隨著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率大幅度提升,由此農村集聚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教育部適時頒布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提出大力開展農村職業培訓,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業。第六階段是發展面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職業教育(2010年至今),農村職業教育重新走上了“向農”服務的新征程,這也是在新農村建設與勞動力轉移達到一定規模的背景下提出的。
從我國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歷程來看,總體上是朝著“向農”方向發展的,農村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就是為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然而城鄉教育發展方向的定位各異,于是便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村職業教育就是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培養技能型人才,由此針對農村職業的辦學方向就會出現兩種趨向:一方面,要求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業生產勞動服務,要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使農村地區的學生具備農業生產與經營的相關技能;另一方面,還要在精神層面能夠留得住學生,培養農村學習者熱愛農村、扎根農村、服務農村的奉獻精神。以上關于農村職業教育的服務定位,愿景可謂十分美好,能夠糾正農村教育遠離鄉土生活、脫離農村實際等方面的偏頗,但卻不自覺地陷入了過于“向農”的陷阱。諸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厄迪爾在其著作《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所言:“教育作為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工具,具有維護社會不平等關系的重要功能。”③一味地將農村職業教育偏執于“向農”教育,以“社會本位論”定位農村教育,從農村的發展實際來看,這也僅僅是一種對浪漫主義烏托邦的向往。如果將農村職業教育單一面向“農村劣勢文化圈”,那么將會導致農村學生的劣勢地位,從事劣勢的農業生產工作,農民也將無法擺脫悲慘的命運。④
(二)“離農”是農村職業教育對淳樸鄉土的逃離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城鄉統籌發展不斷推進,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離農”教育在開放的城鄉社會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容否認的是,農村職業教育目的異化較為嚴重。長期以來,我國教育帶有很強的“功利性”與“工具性”色彩,提高受教育水平以逃離農村成為大部分農村學生的希望和寄托。為了迎合農村居民對于教育的希冀,農村職業教育也不例外地走上了“脫農”的道路,大辦“離農”教育,向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力。這種典型的“社會本位”的教育取向與價值追求,僅僅重視社會發展而排斥了個人發展的差異性,從深層次來看,忽視了每一個受教育者的個性培養。早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就曾對我國鄉土教育城市化傾向的問題進行了痛斥:“中國鄉村教育完全是走錯了路,它教人逃離鄉村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糧、做房子不植樹、行走不造路;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農民……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更弱;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更窮。”⑤因此,這種忽視學生個人差異的職業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是無法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盡管在某一層面上為農村學習者脫離“農門”提供了很好的范式,但長期來看也不是有效的、可持續的。
(三)“向農”與“離農”——農村職業教育面臨的價值選擇悖論
首先,發展取向上存在“向農”“離農”悖論。⑥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要面向廣大農村學生,要求其扎根于農村,服務于農村,為農村發展奉獻力量。盡管某種程度上能夠增加農村發展的后勁,但長期來看阻礙了農村學生向上層社會流動,也違背了教育公平與社會發展公平。另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村學生“跳出農門、流向城市”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導致農村職業教育疏遠于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個人理性層面,選擇“離農”教育有利于跳出“農門”,實現個人由農村向城市發展的轉型,不失為明智之舉。然而在社會理性層面,“離農”教育不利于農村社會發展,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城鄉二元對立。反之,“向農”教育亦然。由此可見,農村職業教育在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其次,功能導向上存在“向農”“離農”悖論。在農村職業教育的功能導向上人們還存在二元對立的思維,認為農村職業教育抑或“向農”,抑或“離農”。⑦一方面,“向農”教育倡導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村發展提供直接服務,滿足農業生產與經營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離農”教育要求農村職業教育為城市發展服務,滿足其對勞動力人才的需求,培養能夠脫離農村與農業而且能夠適應城市主流文化的人才。
最后,主體意愿上存在“向農”“離農”悖論。一方面,“向農”教育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價值選擇,從新中國成立后實施的一系列教育政策能夠看出,“農村職業教育定位于培養思想上和技能上都能為農村發展服務的人才”;另一方面,作為受教育主體的廣大農村居民,則偏向于“離農”教育,并且一直為跳出“農門”、改變農民身份而努力。總之,農村職業教育的“向農”與“離農”的價值選擇悖論反映出政府與民間兩大主體間的意愿沖突。
二、農村職業教育“向農”與“離農”的選擇悖論歸因
(一)城鄉對立的二元社會結構⑧的阻隔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由來已久,是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所致。⑨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曾指出:“二元社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普遍現象,主要源于兩種不同經濟性質的國家經濟結構。一是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農業經濟,二是以現代化工業生產為首的城市經濟。中國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是由于實施了錯位的城鄉發展戰略(先城市,后農村),以至于形成了失衡發展的城鄉二元社會”。⑩總體來看,我國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外顯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城鄉分化較為嚴重。以現代工業為先導的城市,集聚了優秀的產業、人才與資源,不管在生產資料,還是居民收入水平都遠遠超過以農業為主導經濟的農村。以經濟為傳導體,城鄉之間的二元形態還表現在教育、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最終形成了對比鮮明的城鄉二元社會體系。另一方面,城鄉二元對立還表現在城鄉之間的封閉與分割。具體來看,城鄉之間形成了一個斷層,各自成為一個較獨立的社會系統,分別在各自的系統內部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代換,形成一個封閉的發展怪圈,致使城鄉資源交流分化與缺失。
城鄉對立的二元社會結構導致農村職業教育在價值選擇上陷入了困境。首先,城鄉之間的封閉與分化導致農村職業教育在功能上陷入“向農”和“離農”的悖論。在城鄉各自較為封閉的狀態下,使得農村職業教育的功能變得非常單一,農村職業教育要么向著“離農”的城市化發展靠攏,要么堅持“向農”取向。總之,在長期的博弈中,陷入了城鄉二元取舍中非此即彼的困境。其次,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市的“優勢文化圈”與農村的“劣勢文化圈”的對立。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人、財、物等資源,具有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代表著社會的優勢文化,農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遠遠低于城市,獨守劣勢文化一端的農村居民難免會對城市生活產生向往,隨之出現大量的農村人才和資源單一地流向城市,導致農村職業教育在價值選擇上出現了個人發展與農村發展的對立。
(二)城鄉分化的二元思維模式的束縛
城鄉的二元結構形態制約著我國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這是農村職業教育陷入“向農”與“離農”選擇悖論的表層原因,而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思維才是農村職業教育價值取向在城鄉二元取舍上非此即彼的深層原因。[11]二元思維割裂了城鄉之間的聯系,將農村職業教育劃歸為絕對的“向農”或“離農”,完全將兩者的中間地帶割裂開來。從近代西方哲學發展的特征來看,主要以“主客、靈肉、心物、有無”等二元對立的視角共同構筑形而上學的內外體系。[12]以城鄉分化的二元思維看待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是一種唯心的簡單還原論,該論調主張將紛繁復雜的事物臆斷地劃歸為簡單的節點,以單個的節點特征把握事物的本源,這種簡單的還原違背了事物發展的本來面貌。由此可見,我國農村職業教育在長期的二元思維指引下,其價值選擇簡單化為“向農”與“離農”,粗暴地將服務城市與農村分割開來,直接否定了城鄉共處一個社會整體,將城市與農村異化為兩個“世界”。同時,該思維模式遮蔽了城鄉之間的聯系與發展,將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逼入單一化,不僅造成“向農”和“離農”的悖論,也導致農村職業教育在社會與個人、城市與農村等不同主體間的無所適從。
(三)設計主體與實施主體價值取向相背離
“實際上,農村職業教育‘向農’和‘離農’教育分別是政府與民間兩種不同教育意愿間的沖突,這種沖突在對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框架內是難以消解的。”[13]政府作為教育政策的設計主體,而廣大人民群眾作為教育受眾,即實施主體,兩者的意愿分歧主要表現在對農村職業教育目的、教育內容理解以及所處的城鄉立場上的差異,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向農”“離農”也表現出不同的偏好。在對教育功能的理解上,政府與個人也表現出兩類相異的價值取向,政府以“工具主義”為支撐,更多強調農村職業教育的社會功能,學校理所應當地擔負起培養社會發展所需人才的工作;而教育受眾秉持的是“本體主義”,將個人生存與發展作為教育的發展目標,更多強調教育的個人發展功能。
農村職業教育“向農”和“離農”的矛盾焦點在于社會與個人的價值導向相背離。“向農”是基于農村社會的視角,關注的是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離農”是建立在城市化發展的立場,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適時提出的,強調提升農村學生工作技能,服務于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不管是“向農”教育還是“離農”教育,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向農”教育阻礙了農村人群向上流動,違背了農村居民的個人發展意愿;“離農”教育偏執于為城市發展服務,卻忽視了農村發展的實際需要,違背了政府城鄉統籌發展意愿。“個人與社會理應以共同的發展為目標,而不是犧牲一方利益為代價去實現另一方的發展。”[14]詹棟梁曾指出,“人不僅是具有智慧的人即‘智慧人’,同時也是能夠工作的人即‘工匠人’。‘智慧人’的特性賦予了人能夠利用智慧而改善個人的生活,而‘工匠人’的特性使人能夠制造并使用工具。”[15]因此,從教育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農村職業教育在對人的培養過程中應該兼備智慧人和工匠人的特點,既要使學生掌握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又要使其具有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至此,主體間的價值選擇相悖也使得農村職業教育在“向農”與“離農”間搖擺。
三、消解農村職業教育選擇悖論的路徑探索
(一)突破局限思維,科學理解農村職業教育的“向農”與“離農”取向
思維是行動的先導。要想改變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現狀,必須突破對其發展思維的局限,系統科學地理解“向農”與“離農”教育。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指出,對立是事物發展中所顯現出的一種自然狀態,這種狀態并不是絕對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關系,而是一種開放、并存的關系,而且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換,從對立走向協調。因此,從一定程度上看,“向農”與“離農”是一種對立思維抽象出來的結果,并不完全是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使然。尋找消解農村職業教育價值悖論的具體思路,首先要樹立系統化的思維,正確看待農村職業教育的“向農”與“離農”問題。[16]
近年來,國家大力倡導農村職業教育堅持走“三農”服務的路線,為新農村建設服務,這也成了農村職業教育辦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但是在具體路線實施層面,如何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各個專家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將農村職業教育的服務定位于農業,應以農業生產為根本,這種倡導貌似正確,但不經意間陷入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背離了農村發展的實際,特別是在我國新型城鎮化蓬勃發展的今天,將農村職業教育僅僅局限于農業生產,是典型的農業中心取向的思維,不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當然,也有些學者將城市中心取向的價值觀賦予在農村職業教育上,認為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希望不在于服務農村,更重要的是服務城市,服務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17]不管是“為農”還是“為城”,都不能人為地割裂城鄉之間的聯系,城鄉共處于一個大的社會系統中,農村職業教育辦學過程中應樹立系統化的思維,要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而變化,在價值選擇應該定位于為城鄉共同發展服務。
(二)將人的發展作為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基點
“向農”與“離農”之爭實質上是工具論的一種外在反映,是將教育作為完成社會義務或責任的手段,但其中忽視了“人”的存在。[18]總的來說,教育的首要使命和功能就是育人,促進受教育者的全面發展,而教育的其他功能都要以此為先導。農村職業教育的外顯性功能主要體現在教育的“工具性”,更多地傾向于“社會功能”,而忽略了應有的“本體功能”。不管是以“城市中心主義”取向的“離農”教育,還是以“農村中心主義”取向的“向農”教育,如果僅僅強調教育內容的多寡、實訓方式的差異,那么不管是何種教育,其局限性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出來。對此,要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改革力度,將“工具性”教育轉變為“主體性”教育,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基點,通過合乎農村居民的發展規律的個性化教育活動來促進受教育者的成長。
在我國整個教育系統內,職業教育是最應該以多樣化的教育形式和教學內容開展教學活動的,公民對其也應有充分的選擇權。但是從我國當前農村職業教育辦學中存在的問題來看,辦學的類型、模式等過于單一,要么“向農”,要么“離農”,沒有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選擇權,忽視了人的教育意愿與個性發展需要。對此,農村職業院校應提供多元化、適切性的教育服務,建立既能滿足城市建設的人才需求,又不以犧牲農村未來的發展利益為代價;既能保障那些能夠升學的農村學生向上流動的公平機會,又不會讓無法以此為途徑進入城市的農村學生成為脫軌者的教育模式。
(三)基于整體觀視角多元動態地調整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思路
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受外部諸多因素的限制,農村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影響著其辦學質量和水平。但是長期以來受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村發展的平衡關系被打破,城市以“剪刀差”的形式長期對農村進行盤剝。受此影響,農村職業教育為了尋求自身發展,只能以城市標準進行自我改造,并且不斷在農村地區選拔優秀人才向城市輸入,因而農村職業教育為受教育者提供向上流動平臺與維護農村發展利益似乎成為非此即彼的選擇。在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框架之下,約束性教育體制使得農村職業教育在“向農”與“離農”間搖擺不定。之所以“向農”與“離農”間的矛盾很難調和,是由于人們潛在地將“向農”教育理解為“務農”教育,將“離農”教育劃歸為“惡農”教育,以極端化的視角看待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19]從理論上看,如果將“向農”與“離農”看作農村職業教育的兩端,那么在其中間也就出現無數種可供選擇的發展方向,這種整體化的視角看待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選擇,將有助于實現價值悖論的消解。眾所周知,中國的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有所不同,表現出多樣性、多元化的特點。因此,根據不同區域間的發展現狀,選擇“向農”還是選擇“離農”相對應的適合點也是不同的。在我國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態勢下,如果仍堅守以往固守農村或過于強調城市的單一取向的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戰略,不僅不利于農村學生的成長進步,也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除了應該以整體、多元的視角看待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之外,還應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動態來調整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思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艾立克·沃爾夫曾經對農民社會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都是依托于農村社會基礎之上,鄉村并不能直接從‘傳統’跳躍至‘現代’,必須經歷一系列持續、變遷的過程。”[20]以往關于農村職業教育“向農”與“離農”的價值選擇悖論的探討,很大程度上是偏于靜止橫斷面的角度,未能立足于我國農村發展史與快速的城鄉建設背景。新農村建設將會改變農村的發展面貌,步入現代化的發展階段,農民身份與職業結構也將逐漸轉變,至此城鄉二元結構也將逐步瓦解,農村職業教育必須隨之進行重新定位。
(四)“強農”教育——農村職業教育價值的應然選擇
“強農”教育是農村職業教育價值的本源所在,其基本思路是通過開展農村職業教育,促進“三農”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使農村、農業與農民由弱變強。[21]“強農”教育將促進農村人口素質提升作為首要目標,以提升農村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價值為根本,全面服務于“三農”,這也是我國農村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現實要求。與此同時,“強農”教育也是基于我國“三農”發展的現實需要對“為農”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可以說,“強農”教育與“為農”教育在價值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具體到目標指向上,與“為農”教育相比而言,“強農”教育更為具體,可操作性更強,也更為強調農村受教育者的主體性覺醒與提升,這也是“為農”教育所不具備的。
與“離農”教育相比,“強農”教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體性權利,這也是兩者的一致性所在,同時還更為積極關注農村居民的“離農”需要與發展愿望,創造條件和平臺以實現農村學習者的“離農”愿望。而“強農”教育與“離農”教育之間也存在一些差異,“強農”教育不僅關注社會發展需求,也關注個人成長需要,并不是將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對立看待,而是追求兩者和諧統一。除此之外,“強農”教育還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它不僅強調城鄉統籌發展,也注重受教育者的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
農村職業教育選擇“強農”價值理念,并不意味著將“向農”與“離農”對立起來,相反,是將“離農”教育作為為農服務的一種重要途徑,這樣也就實現“離農”與“向農”價值觀的有效嫁接。相關研究表明,職業層次的高低對從業者的社會階層演變具有較為顯著的影響。[22]通過實施“強農”教育,能夠有效提升受教育者的人力資本,為農村學習者提供多種發展選擇,也使農村居民向更高層次的職業流動成為可能。在“強農”教育價值理念指引下,“向農”與“離農”都是受教育者的自主選擇,相應地,農村職業教育應致力于培養農村學子的自力更生、自尊自強,使他們在教育的幫助下獲得更好的發展。
[注釋]
①《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181.
②曹曄.農村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離農”還是“為農”——基于歷史變遷視角的考察[J].職教通訊,2012(1):32.
③(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88:125.
④余秀蘭.中國城鄉教育差異——一種文化再生產現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34.
⑤陶行知.中國教育改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8.
⑥鄔志輝,楊衛安.“離農”抑或“為農”——農村教育價值選擇的悖論及消解[J].教育發展研究,2008(Z1):57.
⑦孫揚,朱成科.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基礎教育價值取向研究綜述[J].教育學術月刊,2011(12):36.
⑧張濤,熊愛玲,彭尚平.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2(18):13.
⑨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不同于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需要經歷的階段。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是城鄉二元結構的極端化,其實質是一個社會中以經濟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結構的斷層和分化,它不僅僅是一個發展差距的概念,而是現代與傳統并存于一個社會之中所產生的現代性結構與傳統性結構的分裂。
⑩(美)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施煒,謝兵,蘇玉宏,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35.
[11]劉月紅.論城鄉一體化背景下我國農村教育價值的迷失與重塑[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22):23.
[12](美)米歇爾·沃爾德羅普.復雜:誕生于秩序與混沌邊緣的科學[M].陳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72.
[13]周曄.從“二元割裂”走向“一體化”——再論農村基礎教育的培養目標[J].教育學報,2009(2):20.
[14]莊孔韶,王媛.評議“離農”“為農”爭論——教育人類學視角的農村教育[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83.
[15]詹棟梁.教育人類學[M].臺北:五臺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9:23.
[16]皮江紅.農村社會“非農化”轉型與農村職業教育應對——以浙江省為分析對象[J].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308.
[17]胡俊生.農村教育城鎮化:動因、目標及策略探討[J].教育研究,2010(2):89.
[18]馬啟鵬.農村學校教育如何擺脫“向農”、“離農”之爭[J].教育發展研究,2010(9):66.
[19]張濤,鄧治春,彭尚平.統籌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及機制創新[J].教育與職業,2013(3):8.
[20] Eric R.Wolf.Peasant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66:225.
[21]洪俊.強農:農村教育應然的價值取向[J].中國農村教育,2013(10):10.
[22]陳浩,陳雪春,謝勇.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職業分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