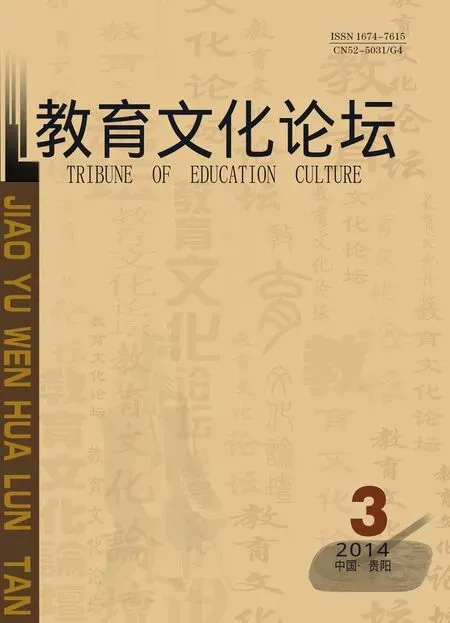近代教育期刊主編與近代教育的發(fā)展
——以《中華教育界》主編陳啟天為例
喻永慶
(中南民族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期刊主編作為期刊的精神核心與輿論的領導者,他們大到期刊的選題規(guī)劃、欄目設置、專號組織,小到稿件的征集、取舍與字句的修改,都能層層把關,對期刊的辦刊理念與發(fā)展方向起著關鍵作用。在交通不便、信息相對閉塞的近代中國,眾多的期刊成為推動文化繁榮與社會發(fā)展的強有力工具。而其中,期刊的主編無一不是社會的精神領袖與時代潮流的引導者,就像陳獨秀之于《新青年》、胡適之于《獨立評論》、鄒韜奮之于《生活》,他們借助自己的才識與社會關系網(wǎng)絡,在文化的傳播、知識的傳承、思潮的推進等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于他們的辦刊思想與編輯理念,當前文學界、史學界、新聞傳播學界等領域的學者進行了廣泛探討。相比之下,近代教育中影響較大的期刊,如《教育雜志》、《中華教育界》、《新教育》、《教育與職業(yè)》等雜志,它們在不同時期的國外先進教育的引入、教育制度的變遷、教育思潮的傳播等方面都影響甚巨。在這一過程中,主編的積極引導同樣不可小覷,但當前教育界對此卻鮮有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鑒于此,本文以《中華教育界》主編陳啟天為例,通過對該時期《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構成及特征研究,系統(tǒng)探討陳啟天在辦刊過程中撰稿人的聚合途徑,藉此全面展示教育期刊中主編辦刊的實況,豐富近代教育期刊研究。
一、《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構成與特征
《中華教育界》創(chuàng)刊于1912年3月,上海中華書局編輯發(fā)行,1937年8月因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出版至25卷第2期后停刊,1947年1月復刊,1950年12月因中華書局業(yè)務方向轉移,出版至復刊第4卷第12期后終刊。《中華教育界》刊行近30年,共出版發(fā)行29卷312期,幾乎橫跨整個民國時期,是近代中國教育期刊中刊行時間長、影響較大的刊物之一,在教育的各個領域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陳啟天自東南大學教育科畢業(yè)后擔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陳啟天(1893-1984),湖北黃陂人,又名翊林,字修平,號寄園。早期就讀于武昌高等農務學堂附小、附中。1912年入武昌中華大學政治經濟別科,1915年畢業(yè)后,先后任教中華大學中學部、文華大學、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9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后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并開始接受國家主義學說,與余家菊、李璜等人力倡“國家主義教育”,并使之成為當時極有影響的一種教育思潮。1924年畢業(yè)后,入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主編《中華教育界》,同年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創(chuàng)辦《醒獅周報》,組織國家教育協(xié)會,將“教育是一種國家主權、國家事業(yè)、國家工具、國家制度”為其奮斗目標,號召并發(fā)起收回教育權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青年黨,后由于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轉赴四川成都大學講授中國教育史、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課程。后從教育轉向政治,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國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部長、中國青年黨黨主席,1984年病逝于臺灣。著有《國家主義論》、《中國國家主義運動史》、《近代中國教育史》、《寄園回憶錄》等著作。在1924年7月到1926年11月主編《中華教育界》期間,他對該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教育改造國家為辦刊宗旨,不斷調整欄目設置,加強期刊與現(xiàn)實教育的聯(lián)系,使得《中華教育界》的面貌煥然一新,在教育界及社會上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同時,他也有計劃地刊發(fā)了10期專號,如“收回教育權運動號”、“國家主義的教育研究號”、“留學問題號”、“師范教育號”、“小學愛國教材號”、“公民教育號”等,聚集了一大批宣傳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先進人士。
根據(jù)筆者對《中華教育界》主要撰稿人的考察,*根據(jù)陳啟天時期的《中華教育界》的署名作者(共176人),制作了“撰稿人及刊文數(shù)統(tǒng)計表”,因篇幅限制,本文略去此表。本文后面的分析,凡依據(jù)該表的資料,不再一一注出。陳啟天時期《中華教育界》撰稿人主要由下列四類人群構成:
第一,大學教師。雖然統(tǒng)計表中多數(shù)人都有過大學從教的經歷,但在陳啟天擔任《中華教育界》主編的時間段內,僅有俞子夷、李璜、廖世承、穆濟波、楊廉、程湘帆、汪懋祖、夏承楓、陳鶴琴、鄭宗海、朱君毅、余家菊、程宗潮、舒新城、邱椿等人在大學擔任教職。其中,除李璜曾先后任教于國立武昌大學和北京大學,舒新城執(zhí)教于成都高等師范學校,邱椿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擔任教員外,其他人則先后擔任東南大學教育科的教職。如此眾多的東南大學教師擔任撰稿人,主要是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伴隨著國際上新的教育思潮與教育理論的掀起與大量引進,東南大學教育科漸漸成為新教育運動的主要陣地,在全國影響頗大。與此同時,《中華教育界》為適應教育發(fā)展的新形式,毅然進行了革新,廣泛地向東南大學教育科師生征稿。正如其所提倡:“我們這本月刊從第十卷第一期起,徹底改革,擔任撰述的人以南北兩高師和各處有經驗有研究的青年占大多數(shù)”,[1]雖然提到南北高師,但此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竟無一人,這與主編陳啟天是東南大學教育科的畢業(yè)生有很大關系。可以說,東南大學教育科這些撰稿人,多為新教育的積極倡導者與推動者,在當時的教育改革中居于領導地位,影響著當時教育的發(fā)展。
第二,中小學教師。《中華教育界》自1912年3月創(chuàng)刊以來,一直以“研究教育,促進文化”為其辦刊宗旨,在十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始終堅持以中小學教育研究為主導的辦刊理念,積極參入中小學的教學和改革活動。這一傳統(tǒng)在陳啟天任主編之時也得到相應的繼承,他在改革之初就申明:“至于本志取材的分量以關于小學的為多,則照舊不變”。[2]并在實際中踐行著這一方針,從撰稿人當時所屬單位,以及撰稿人人數(shù)上我們可以得到印證。從統(tǒng)計數(shù)量上看,當時任中小學教師的有52人,占表格中統(tǒng)計人數(shù)的55%,如胡叔異、沈子善、羅廷光、顧克彬、沈百英、楊效春、張宗麟、鄭朝熙、祝其樂、王克仁、張錫昌、曹芻、蔣息岑、葛承訓、唐瑴、周邦道、李琯卿、馬客談、吳俊升、王崇植、周調陽、盛朗西、施仁夫、古楳等人,他們此時或為一線的教員,或為教育管理人員,根據(jù)自己的教學經驗與體會,發(fā)表著他們對教育、教學的真實感受。
第三,雜志編輯。這部分人在《中華教育界》撰稿人隊伍中所占比例不大,共8人,如陸費逵、朱文叔、沈百英、李步青、余家菊、范壽康、鄒恩潤(韜奮)、常乃德等人,其中陸費逵、朱文叔、李步青(廉方)、余家菊為中華書局編輯,且陸費逵是中華書局的總經理;范壽康、沈百英、常乃德三人為商務印書館編輯;鄒恩潤(韜奮)則為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所辦刊物《教育與職業(yè)》的主編。除去鄒恩潤(韜奮),其他都為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工作人員。這主要由于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都有教科書編輯、出版業(yè)務,他們需要一些從事過教育,對教育有追求的編輯人員。從李步青(廉方)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余夙治教育學,專究國民教育,尤致力于教材研究”。[3]另外,從這些編輯人員服務的時間上看,他們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如余家菊在任職中華書局編輯之前作為武昌師范大學教授,而在中華書局工作不到半年又任東南大學教授,常乃德、李步青、范壽康等人也是如此。可見,雜志編輯大多數(shù)只是一個跳板,或者說是從一個職業(yè)到另一個職業(yè)的中轉站,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教育的熱情,他們從不同學科與角度研究教育與教科書問題。
第四,在校學生。《中華教育界》創(chuàng)刊之初,其撰稿人主要以中華書局編輯與廣大一線中小學教師為主。自第10卷起,該雜志進行了革新,將一些在校學生納入撰稿人范圍,這種情形在陳啟天任主編之時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這些學生既包括國外留學生,也包括國內大學的學生,如周太玄、常道直、王光祈等人此時為國外留學生,其中周太玄留學法國,常道直留學美國、王光祈留學德國,他們加入到撰稿人行列,對歐美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進行了引進。而羅廷光、胡家健、沈子善、衛(wèi)士生等人同為東南大學的學生,相對于上述第一類新教育的倡導者來說,這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新一代青年,最初他們作為新教育的追隨者,后來也加入到倡導者行列,日后并成為中國教育發(fā)展過程中的活躍分子或領軍人物。
二、《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年齡結構與教育背景
在教育背景上,《中華教育界》撰稿人所接受的教育也存在差別,為方便說明,筆者進行了分類。一類是留學日本。1870年代與1880年代出生的屬于這一類,如范源廉、鄭朝熙、李步青(廉方)、俞子夷等人,其中范源廉1901年留學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李步青與鄭朝熙分別于1902年與1908年考入日本仙臺弘文學院;俞子夷也于1903年東渡日本學習,之后又受江蘇教育會的選派,考察日本教育。這類撰稿人中,他們少年時代接受的是傳統(tǒng)的私塾與書院教育,為了改變落后的教育現(xiàn)狀,東渡日本,以速成的方式,學習或考察日本先進的教育方法與教育實驗,并于回國后在教育領域進行著改革活動,給當時沉悶的教育帶來一些新的氣象。
一類是留學歐美,這類撰稿人主要集中在1890年代,如鄭宗海、汪懋祖、廖世承、陳鶴琴、程其保、朱君毅、陶行知、常道直、邱椿、杜佐周等人留學美國,并且都畢業(yè)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周太玄、李璜、王光祈等人留學法國;余家菊留學英國。這一群體出生于1890-1900年間,伴隨1901年的清末新政中新式學堂的大量興辦,他們的中小學教育大多就讀于此類學堂,傳統(tǒng)書院教育相對較少,一些人在結束國內高等教育或預科培訓后直接留學國外,選擇歐美為其學習目的地。在統(tǒng)計中,這一年齡段只有范守康留學日本,但他同上一年齡段最大的區(qū)別是就讀于日本正規(guī)的大學,并獲得了學位。另外,該年齡段人多數(shù)選擇教育為自己的專業(yè),并回國后在大學教育科中任教。這在中國教育學科專業(yè)化的起步年代,為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貢獻頗多。
一類是就讀于國內大學,以1890年代與1900年代兩個年齡段為多,他們集中于1920年前后進入大學學習,在陳啟天擔任主編之時,一些人已經畢業(yè),并在中小學從事教學與管理工作;另一些人則正享受著大學生活。在這類群體中,除周調陽、常乃德畢業(yè)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穆濟波畢業(yè)于成都高等師范學校,魯繼曾畢業(yè)于之江大學,李儒勉畢業(yè)于金陵大學,鄒恩潤(韜奮)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外,大多數(shù)人畢業(yè)或正就讀于東南大學,如陳啟天、羅廷光、沈子善、古楳、胡叔異、夏承楓、程宗潮、吳俊升、祝其樂、邰爽秋、張宗麟、曹芻、李清悚、錢希乃、衛(wèi)士生、胡家健等人,他們作為南京高師或東南大學教育科不同年級的學生。這群人可以說都系統(tǒng)地接受了小學、中學(師范學校)、大學的教育,并且在入大學之前有過從事教育的經歷,對當時中國教育與教學的現(xiàn)狀了如指掌。進入大學后,他們受教于他們的導師,普遍接受了歐美最新的教育理念與方法,成為中國本土培養(yǎng)的最早教育學專業(yè)人才。從整體上看,這一群體都具有較豐富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經驗,作為新教育運動的積極響應者和擁護者,對教育改革賦予了極大的熱情。而當時的重要教育改革與實驗,因這一代人的加入和支持而取得驕人的成績。
最后一類是畢業(yè)于中學或師范學校,如沈百英、馬客談、李琯卿等人,他們大多畢業(yè)于中等學校或師范學校,長期在中小學擔任教職,這類群體在《中華教育界》撰稿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原因主要同該刊關注中小學教育的宗旨是分不開的。另外,一些出版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屬于這類群體,如陸費逵中學畢業(yè),他作為中華書局總經理,堅信以出版輔助教育的理念,并在實際行動中大力宣傳“出版救國”、“教育救國”,發(fā)表大量的教育改革文章。這些出版人、編輯人在《中華教育界》上擔任撰稿人,與近代出版機構教科書的編輯與發(fā)行緊密相連。
三、《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聚合途徑
前面我們探討了陳啟天時期《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構成、年齡結構與教育背景,從中可以了解到,此時期《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構成特征、教育背景兩個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仍能夠在《中華教育界》上形成聚合之勢,同主編陳啟天的個人能力與社會關系密切相關。此時的《中華教育界》,形成了以陳啟天為中心,以革新教育與教育救國為奮斗目標,依靠師友、同學、同道、同鄉(xiāng)、同事等關系的大力支援,逐漸成為宣傳國家主義教育思潮的重要陣地。
1.師友:厚愛與援引
陳啟天曾兩次報考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東南大學教育科的前身),對此他曾有過這樣的回憶:“自五年秋教書至今年(1918年,筆者注),漸覺未學教育而當教師,未免自誤誤人,因有專攻教育之志。惜予無力留學外國,乃于暑假中往考南京高等師范教育專修科,以取入國文史地部,未入學”。[4]18第二年夏他再次報考,被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錄取,但應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之聘,又未入學。后因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政治運動、學校罷課,復課無期,于是函詢“南高教務主任兼教育專修科主任陶行知先生,可否準我再入學,陶行知回信說,‘可以破例照準’”,[4]85于是陳啟天在其他同學入學半年之后成為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甲子級一員。此時,陳啟天已經29歲,之前已經是武昌中華大學政治經濟別科畢業(yè)生,并先后在漢口民新學校、中華大學中學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擔任教職,又經過兩次入學考試并得到教育專修科主任陶行知的親自同意。這些情況在他的同班中可能是少有的情況,也因此會增添了他的一些知名度。對此,陳啟天這樣說道:“我既曾在大學畢業(yè),又曾在小學、中學以及大學教了四年半的書,現(xiàn)在又來入高師,自然容易引起師友的注意。加之甲子級應于民國九年秋入學,而我一個人遲了半年才入學,更容易引起師友的注意。”[4]85就這樣,1921年春至1924年夏,陳啟天就讀于南京高師及后來的東南大學教育科。在學業(yè)上,陳啟天同樣也是十分突出,他在讀書期間相當勤奮,并開始撰寫論文,“我此時的文字,尚不十分成熟。不過從他人看來,多把我當做一個特殊的學生看待。我藉寫文字,一面促進研究的興趣,一面補助個人的用費”,[4]88以致患上“咳血與腦痛”,對這他日后回憶:“吾以病軀而猶能力學者,一則以予向學之志甚堅,不成不休,一則賴有諸師友之鼓勵獎進而。”[4]20此外,陳啟天在學校學生活動中擔任的一些要職與參加一些政治與學術運動,下文有詳細論述,這都可能引起師長的關注,并同他們形成親密的關系,為日后的約稿也提供了便利。
基于的協(xié)整常系數(shù)檢驗發(fā)現(xiàn),現(xiàn)貨與各期貨合約之間在各分位數(shù)下的協(xié)整系數(shù)并不相同。因此,下一步需要使用分位數(shù)Wald檢驗來檢驗各分位數(shù)下β=1的原假設是否成立,結果檢驗見表5。
而東南大學教育科中教師在當時教育上的影響,也成為陳啟天樂于征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教育科教師隊伍中,如陶行知、汪懋祖、鄭宗海、程湘帆、朱君毅、程稚秋(其保)、廖世承、陳鶴琴、俞子夷等人,他們大多留學國外,在教育領域都學有所長。如俞子夷是當時中國著名的小學教育專家,一直從事教學方法的改革試驗。陶行知組織發(fā)起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直關注著平民教育的教育與實驗;陳鶴琴作為中國幼兒教育的開拓者,開展形式各樣的幼兒教育研究;廖世承、朱君毅二人積極從事智力測驗及教育實驗活動,廖世承在擔任東南大學附中主任期間,使得“東大附中幾執(zhí)全國中等學校的牛耳,投考人數(shù),為全國稱首”。[5]187如此眾多的教育專家匯集在南京高師或東南大學教育科,在當時大學教育科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他們是中國教育科學化的試驗先驅人物,始終站在教育發(fā)展的最前沿,引領著當時教育的變革。
雖然東南大學教育科教師在《中華教育界》的刊文并不算多,僅有25篇,但這些論文的導向性與前瞻性相當強。這些撰稿人及他們的論文出現(xiàn)在《中華教育界》,一來擴大了該刊在當時教育界中的影響,增加銷售量。二來分享了教育中的最新問題與發(fā)展趨勢,推動著教育改革的深入。
2.同學:相互砥礪與共同奮進
東南大學教育科作為當時中國創(chuàng)辦最早、影響較大的教育學科之一,這不僅得力于一群留學美國的教師身先士卒,而且也同東南大學教育科畢業(yè)生在當時社會或教育改革中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這種影響主要來自東南大學教育科一套行之有效的培養(yǎng)模式。
在入學的資格上。東南大學教育科是在1918年成立的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在最初的招生簡章中,對招生人數(shù)及教育教學經驗的要求較嚴。如在學科及學額上,規(guī)定“現(xiàn)招教育、體育、農業(yè)、商業(yè)專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學資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師范或中學及同等程度之學校畢業(yè)、身體堅強、品行端正而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專修科生除上列資格外,須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經驗,應由服務之機關繕具說明書”,[6]706從招生簡章可以了解到,招生的人數(shù)較少,只有二十五人,利于小班教學。教育經驗作為是否錄取的重要參考依據(jù),符合教育學科自身發(fā)展特征。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們也是這樣遵守的,如吳俊升報考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之前在如皋師范附屬小學擔任一年級國文一年,[7]11古楳報考之前曾在梅縣第七區(qū)立高等小學校擔任教師,[8]25施仁夫則為江蘇省第一師范附屬小學教師,[9]162-163因為有了從事中小學教育經驗,加上他們心中的一些改變教育現(xiàn)狀的理想,使他們研習教育更有針對性,對問題的把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在培養(yǎng)模式上。東南大學教育科的教師大多以留美為主,他們耳濡目染美國新教育運動,并根據(jù)國內教育學發(fā)展現(xiàn)狀,十分重視教育科學的科學化與專業(yè)化運動。在課程的培養(yǎng)上,生物學、遺傳學、測量學、心理學等最新研究成果加入其中。1919年入學的教育專修科學生章柳泉對他的學習課程有這樣的回憶:“我入學的第一學期,就有一門介紹科學常識的課,陶老師(陶行知)在這門課中給我們講遺傳學,從達爾文到德弗里斯,特別市孟得爾的雜交試驗。第二年我們就學‘科學的發(fā)展史’。生物學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課程。心理學是教育學的重要科學基礎,我們學得很不少,有‘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實驗心理學’是重點,共學兩年,做過很多實驗,還開設‘心理學史’課程。此外還有教育統(tǒng)計學,‘測驗之編制與應用’。”[10]332東南大學教育科這種培養(yǎng)模式,在當時教育科學發(fā)展程度不高時代,對于提升教育科學的學科品質,系統(tǒng)培養(yǎng)教育科學人才,使學生掌握教育、心理專業(yè)知識與以后開展教育實驗活動都是大有裨益的。
正是由于東南大學教育科這種培養(yǎng)模式,使得其學生大多具有較強的專業(yè)理論知識與科學開展教育實驗的能力,這些使得他們成為陳啟天時期《中華教育界》撰稿人的必要條件,而他們與陳啟天的親密關系,使得他們成為《中華教育界》撰稿人。
陳啟天是東南大學教育科一個活躍分子,他積極參加各種教育研究與社團活動,由此練就他較強的組織與領導能力,并同其他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記載他的東南大學的生活:“關于課外活動,我曾參加教育科甲子級會、教育研究會、學生自治會及鄂籍學友會等。甲子級會是同班同學增進友誼,砥礪德行,并處理級務的一種組織。我承同學的厚愛,被推為會長,連任三年,始終彼此都很相得,沒有惡感,因此我領悟同學的友情非常純誠,實不下于兄弟。教育科研究會,我只做了一個會員,參加開會,并偶爾為教育季刊寫稿。”[4]88-89
陳啟天時期的《中華教育界》撰稿人中,東南大學教育科的畢業(yè)生或在校學生占較大的比例,刊發(fā)的文章也較多。這些人,要么作為陳啟天的學長,如曹芻、夏承楓、顧克彬、周邦道、胡叔異、唐瑴、施仁夫、錢希乃、楊效春、葛承訓等人,[11]要么是他的同班同學,如吳俊升、凌純聲、古楳、徐益棠、祝其樂 潘子庚、程宗潮、邰爽秋等人。[4]20還有就是他的學弟,如羅廷光、沈子善、李清悚、張宗麟、胡家健、王倘、甘豫源、衛(wèi)士生等人,這些人是我國較早培養(yǎng)的一批教育學專業(yè)人才,在東南大學教育科這個大家庭中,他們不僅接受著嚴格的專業(yè)訓練,而且在此過程中形成了真摯的友誼,使得他們能在陳啟天主編的《中華教育界》上集結。
3.同道:思想的吸引與呼應
陳啟天1919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該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為宗旨,堅持“奮斗、實踐、堅韌、簡樸”為信約,以《少年中國》為其機關刊物,會員主要來自于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學校的青年學生。對于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間的理想與共同追求,黃鐘蘇曾做過這樣的描述:“少年中國學會初非一種綱紀嚴整、規(guī)律詳密、服從某一領袖、遵守某一主義之集團,而是一種追求光明的運動。會員莫不反對封建主義,崇尚進取,重視新知識,于各種新制度極感興趣,思想自由,不受約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13]3由此可知,初期的少中會員雖然學習與研究的領域不同,但他們?yōu)榱烁脑炫f社會,建設新時代的共同目標團結起來。對于會友間的友誼,左舜生后來回憶道:“在最初幾年‘少中’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后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鉤心斗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13]455可見,早期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間的關系是十分融洽的,他們之間只有同志間的友誼,加上學術上的相互關照,儼然是一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陳啟天也開始接觸各種不同領域的人,“我于民國八年由王光祈在武昌介紹入少中。民國十年我到南京以后,發(fā)現(xiàn)少中會友多純潔可愛,有志上進。因與常相往還,使我得到精神上的鼓勵不少。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即少中給我們尚友天下之士的機會,使我們的知交,不僅限于同鄉(xiāng)與同學,至于我后來參加中國青年黨活動,除時事關系外,也與少中有關系。”[4]85因為早期少中會這種兄弟加戰(zhàn)友的親密關系,陳啟天認識了王光祈、周太玄、常乃德、李璜、穆濟波、王崇植、常道直、舒新城等少中會人,并由此結下深厚的友誼,在陳啟天擔任《中華教育界》主編之時,他們多數(shù)人成為《中華教育界》重要撰稿人。
隨著少年中國學會分裂之后,國家主義派核心人物王光祈、周太玄此時留學國外,陳啟天此時逐漸成長為國家主義派的領袖人物,思想也開始趨向于國家主義學說,“民國十三年夏畢業(yè)于國立東南大學后,即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教育界》月刊兩年半,幾乎每期都有我的教育文字發(fā)表。我在未主編《中華教育界》以前的教育文字,多半依據(jù)民主主義的原則,討論各種教育問題。……但在主編《中華教育界》的時候,又多半是依據(jù)國家主義的原則,討論各種教育問題”。[4]97為了擴大國家主義教育學說的影響,將分散的力量集合起來,陳啟天擔任主編之后就對《中華教育界》進行改革,并提出了兩點希望:“第一新希望是以教育的言論促進教育的改革而形成中華民國立國的國魂。……第二新希望是以教育的言論提醒目前中國混亂而無宗旨的教育不足救亡建國,而反對國人借重外人在華文化事業(yè)的趨勢以免于無形中速亡覆國。”[14]在確定辦刊方向后,陳啟天立即向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征稿。
由于國家主義教育提倡的“教育建國論”與先前的“教育救國論”不謀而合,其思想在當時教育界與知識界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原來少中會中思想傾向國家主義的會員與擁護國家主義教育學說的人士積極撰文投稿,《中華教育界》很快組織好了這次專號,并以兩個專號的形式刊載了這次征文活動。這些文章既包括理論上的建構,也包括國際比較研究,還包括國家主義思想在教育領域的運用,他們從不同角度對國家主義教育進行了訴說,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極大的反響。對此,《中華教育界》還陸續(xù)刊發(fā)了留學問題號、師范教育號、小學愛國教材號、公民教育號等專號,掀起了宣傳與推廣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熱潮。在此基礎上,陳啟天以倡導國家主義教育思想者為重要發(fā)起人,成立了國家教育協(xié)會。該會以“國家主義的精神以謀教育的改進”為宗旨,成立之初發(fā)起人有39人。如余家菊、李璜、陳啟天、曹芻、李儒勉、范壽康、舒新城、常道直、羅廷光、周邦道、唐瑴、穆濟波、楊廉、邰爽秋、周調陽、李琯卿、祝其樂、古楳等。在他們的影響下,《中華教育界》團結了一大批教育界人士,他們有的作為陳啟天的同學,有的作為陳啟天的老師,有的作為陳啟天的同事,也有的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師或教育管理人員,他們?yōu)榱斯餐叛觥逃脑靽遥驹诓煌牧雠c不同的角度發(fā)表著他們救國救民的愿望。
4.同鄉(xiāng)與同事:相忍相諒與鼎力支持
在撰稿人中,陳啟天與余家菊、任啟珊三人同為湖北黃陂人。其中,陳啟天與余家菊的人生發(fā)展軌跡極其相似,不論是他們所受的教育、學術研究方向,還是他們服務單位,都存在交集。陳啟天1906年進入黃陂縣道明高等小學堂學習,余家菊也于1909年考入該校,陳啟天對此這樣回憶道:余家菊“比我的年齡小四、五歲,與我不在同班,在校時期自少個別往來的機會,不過每周仍在操場上共同運動兩三次”,但“出校以后與我的關系很多”。[4]71-72高等小學堂畢業(yè)后,余家菊于1912年考入中華大學預科,并于1916年就讀于該校中國哲學門。陳啟天則于1912年考入中華大學政治經濟別科,1915年畢業(yè)。對于此時二人的關系,陳啟天說:“同學各省人皆有,而鄉(xiāng)人獨多。與予往來較密者,為任啟珊、陳伯康、熊國英、阮子印、吳中行、余家菊、惲代英、梁紹文諸人”。[4]15陳啟天畢業(yè)后應任啟珊之約,在漢口民新學校任教,而仍在校學習的余家菊也同在該校兼課,后二人同在中華大學中學部教書。1919年,經王光祈的介紹,陳啟天與余家菊同時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秋王光祈自北京來鄂,介紹惲代英、余家菊、梁紹文與予四人入少年中國學會”。[4]19翌年,陳啟天考入南京高師教育專修科,研習教育,余家菊則入北京高師教育研究科就讀,也研習教育。期間,他們“同赴長沙就職第一師范”,之后經過學習之后,又同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后來成為中國青年黨重要人物。
從上文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陳啟天與余家菊人生有數(shù)次的交匯點,同鄉(xiāng)、小學與大學校友、同校教員、研習學科相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等。這些相同的經歷,我們如不從人物內心的角度去審視,可以斷定他們是親密無間的朋友。而實際上,對于二人的關系,陳啟天與余家菊在回憶錄中記載都很少,相比于陳啟天,余家菊則僅有一段話的介紹:“修平(陳啟天,字修平,筆者注)長予五歲,而與共甘苦最久,而氣質思想皆不相近,始終相忍相諒,實為難能”。[15]204余家菊所說的“氣質思想皆不相近”,這從他倆對待中青黨的態(tài)度上可以略知一二,余家菊認為自己加入中國青年黨,“第一是是因為朋友們的面子關系,第二是因為要合力宣揚國家主義,在實際上我的思想與青年黨主要人物的思想都不相同,周旋其間很是苦惱。我支持青年黨三四十年只基于義務的感情而并不是基于自發(fā)的興趣。”[15]35而陳啟天對于中青黨有這樣的記載:“我與初建的中青卻有兩點因緣:一是中青海外建黨時期的五個中央委員,有三個委員(曾琦、李璜、何魯之)與我同為少中會友,自然容易接近。二是我在中青建黨以前,已在國內提出國家主義的主張,自然更容易接近。所以中青由海外建黨時期進到國內建黨時期以后,我便始而參加中青的宣傳,繼而參加中青的組織了。”[4]143從他們二人對于加入中青黨的態(tài)度,以及后來他們的整個政治活動,我們可以了解到,陳啟天熱衷于政治,善于利用一切關系來發(fā)展自己,余家菊則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自由主義者。但這種態(tài)度并沒有影響二人的感情,他們“共甘苦最久”,又“終相忍相諒”,是二人關系的最真實寫照。余家菊此時作為《中華教育界》重要的撰稿人,發(fā)表了14篇文章,大多是關于國家主義教育思想,這是他們同鄉(xiāng)惺惺相惜的最好注腳。
陳啟天在1924年7月至1926年11月?lián)巍吨腥A教育界》主編期間,以“教育改造國家”為其辦刊宗旨,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網(wǎng)絡,匯聚一大批教育界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五四”運動之后在中國教育史上又一重要的教育思潮——國家主義教育思潮,其對民國時期收回教育權運動與留學教育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中,《中華教育界》主編陳啟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發(fā)揮的影響可謂是厥功甚偉。近代教育期刊主編中類似陳啟天還有很多,我們只有深入地進行挖掘,還原近代教育期刊編輯生活的原生態(tài),探討他們獨特的辦刊風格與辦刊思想,這些對我們處在一個期刊泛濫的當代中國,如何有效地發(fā)揮期刊的參入教育、服務教育的功能不失有很好的歷史借鑒意義。
[1] 佚名.本社啟事[J]. 中華教育界, 1920(1).
[2] 佚名.本志的新希望[J]. 中華教育界,1924(1).
[3] 李廉方.京山新志(序)[Z].武漢:湖北通志館, 1949.
[4]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5] 廖世承.我的少年時代[A],良友人物(1926-1945)[C].上海: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6] 潘懋元,劉海峰.近代教育資料匯編(高等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7]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M].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
[8] 古楳.卅五年的回憶[M].無錫:民生印書館,1935.
[9] 施毓湘.化雨春風啟后學 老年碩德仰前賢——回憶老教育家施仁夫[A].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C].1984.
[10] 章柳泉.憶行知師在南京高師時的幾件事[A].紀念陶行知[C].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1] 佚名.本屆畢業(yè)生狀況[N].申報(教育與人生周刊),1923-10-22.
[12] 沈云龍.王光祈先生紀念冊[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13] 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14] 佚名.本志的新希望[J].中華教育界,1924(1).
[15] 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憶錄[M].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