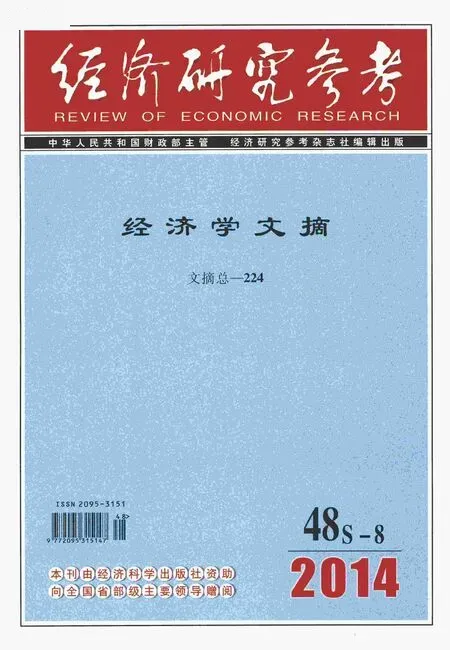中國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
趙春曉 付敏杰
中國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
趙春曉 付敏杰
羅森《財政學》開場白的第一句話是:“人們對于政府應該如何從事其資金運作的看法,深受其政治哲學的影響。”政治哲學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人們對于政府經濟活動適當范圍的看法,從而也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活動的范圍和程度,從而也就有了財政學中所謂的要素稟賦、效用主義和平均主義公平觀之間的區別及其各種可加總情況下的復雜混合方式。由不同公平觀及其混合方式所決定的社會再分配偏好和再分配效率直接決定了“餡餅”的大小。在動態環境中,理性預期的納稅人可以直接將再分配效率內生于偏好之中,所以再分配偏好就成為影響各國宏觀稅負,當然也是中國宏觀稅負的首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認為,居民的公平觀和再分配偏好受到信仰、收入、職業等個人特征的影響,但是從總體來講,偏好、職業和收入的差別在宏觀層面上要遠遠小于微觀層面,甚至還可以出現中和。對于居民偏好產生系統性沖擊的各種社會思潮的出現,社會哲學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都會深刻影響個人對公共部門、政府作用方式和政治決策進程的看法。20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居民再分配偏好的擴張是受到了社會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最明顯的自然歷史實驗就是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德國經歷的國家分裂再到國家融合的過程,從而為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所強調的控制實驗研究提供了極好的歷史背景。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的實證研究發現,具有社會主義傳統的東德更加偏好國家干預和再分配,而東西德國之間由于45年(1945~1990)面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居民再分配偏好差距需要20~40年(1~2代人)才能彌合成完全一致。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已經達到60余年,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收入分配差距小而缺少激勵: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和不干一個樣。長期的社會主義傳統,會導致中國居民對于社會公平和再分配的偏好會更加顯著的高于其他國家,導致財政政策用于收入分配功能的比重會更高,理應意味著更高的宏觀稅負。
影響中國宏觀稅負的第二個因素是計劃經濟傳統所造就的政府具有很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給宏觀稅負的上升提供了巨大空間。國家能力的核心是政府資源動員能力,而中國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以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社會體制為基礎。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典型特征是以市場價格為基本競爭平臺的政府強干預,分稅制框架下的政府競爭通過一系列的價格和非價格補貼措施,競相壓低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利率)成本而實現了以供給面擴張為基本特征的低價格工業化和對全面市場的迅速占領,由此帶來了中國奇跡。政府作為一個資源配置主體而具有了拓展市場的企業家職能,是中國生產型政府的典型特征,也是造成中國諸多結構問題的根源。中國政府的強資源動員能力,在市場經濟的競爭平臺上,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土地等公有制資源轉化為政府各種形式的稅收或租金收入,其作為資源實際控制者的角色使得可以通過扭曲資源價格來增加相應的政府收入,從而會對應更高的宏觀稅負水平,這無疑與眾多發展中國家脆弱的國家能力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三個因素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財政政策理應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間。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擴大相伴而生,而控制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財政的主要功能。前面的分析中已經明確,現代政府支出的絕大部分是轉移性支出,用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由于中國沒有公開的家庭調查數據,根據各種已有數據估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已經迫近了0.5的警戒線。由于缺乏財產稅等直接稅種來減少私人財富的累積速度,建立在私人財富起點上不平等逐步加劇。結合前面我們對于國民分配偏好的分析,社會主義傳統會使得中國國民更加注重平等,這樣就必須要求高稅率的財產稅和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以減少私人部門的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認為由于中國居民具有更強的再分配偏好和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從而意味著相對而言更高的宏觀稅負,而中國政府極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又為宏觀稅負的攀升提供了現實基礎,所以在同等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水平下,由財政功能所決定的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會明顯高于一般國家。
(成林摘自《地方財政研究》2014年第7期《國際宏觀稅負演進趨勢與中國的合理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