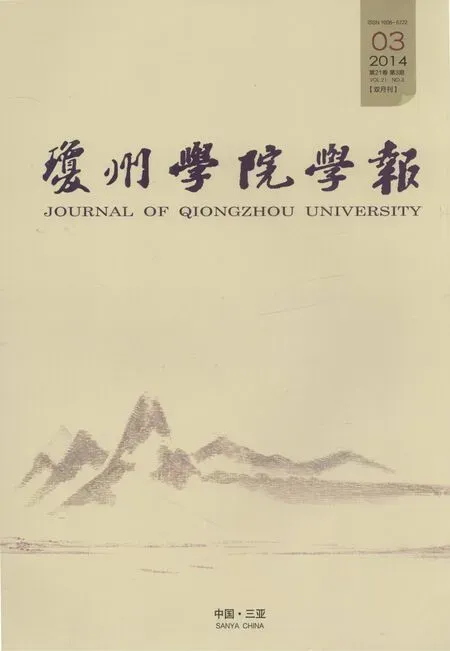宇文所安五言詩研究值得關注
木 齋
帶著滿身傷痕,拖著疲憊之心,我于今年四月應美國普渡大學之邀,進行為期一年的學術訪問,來到這個與中國幾乎是最遠距離的國度,潛意識里有著某種隱逸規避的解脫,也朦朧有著告別學術,潛心反思,重新開始一段人生的希冀。但現代化的通訊設施,使隱逸與規避都成為了空想,《瓊州學院學報》的相關專欄,依然故我而不能止。主編約稿應期而至,我不得不在我美國的西拉法耶特普度大學的陋室中,眼望窗外雨后燦爛的陽光和迥然而異的草坪野花,思考著在這一期的主持人語中寫寫什么。
這一期的兩篇大作,不約而同地將研究的目光轉向了美國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先生,特別是對宇文所安先生的漢魏五言詩研究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是讓我感到由衷高興的。其中李明華、胡良萍的《宇文所安五言詩論》一文,可以視為《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大作問世之后,對其中五言詩問題研究的首次系統梳理。作者之所以選擇對宇文先生的一部著作中的一個問題進行專門研究,正在于它是學術史歷程中值得研究的學者和值得研究的問題。當下學風日趨細微,對一些所謂學術史無人問津的末流作家或是瑣細問題趨之若騖,卻不知道學術史之路是由一條條獨辟之蹊徑所構成,是由一座座奠定了新理論體系的豐碑所標識,是由一尊尊顛覆了前人公式而建樹了新公式的偉大學者所建構。沒有新的理論體系,只在前人的窠臼中生存,僅僅是一種數量的重復。而宇文所安先生,“他的新思想特別多,他會開拓一個新的方向”(顧彬語),也正如他自身所說:“一個傳統要繼續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讀、新的闡釋注入新的活力,否則這個傳統就死了。”(宇文所安語)正因為如此,他所反復強調的,是文學史研究與解讀的“不可確定性”。在漢魏五言詩問題的研究中,宇文所安也同樣發出了與中國主流學者“不一樣的聲音”:“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紀的猜測之外——表明無名‘古詩’的年代早于建安的確鑿證據。”①參見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6頁。這與我近十年來相關漢魏五言詩的研究可謂是不謀而合的。
由廈門大學著名學者,對曹植研究建樹頗深的胡旭教授與其女弟子劉美惠合作撰寫的《論古詩十九首中的異文與模件化套語》,雖然并非對宇文先生的專門研究,但其內容、寫作風格等,卻無不在在顯示著所受前者的影響的痕跡。其中除了受到宇文所安先生的影響之外,在具體的細節上,譬如在手抄本的影響方面,胡旭先生對于漢魏五言詩的研究,特別是對曹植甄后的研究,或許比我本人更早,對于兩者之間的戀情關系的肯定,比我更為激進。也許我對于兩者的關系,在潛意識上受到世俗偏見的壓力,此前常常試圖將這種戀情關系局限于精神上的層面(雖然在內心深處,也深知這種局限于神經層面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愛戀之不可能,特別是在曹魏通脫時代的不可能),而胡旭先生則明確指明,兩者之間的戀情不僅僅在于精神的愛戀,更存在于肉體關系,曹丕對曹植的殘酷打擊,正是“對曹植奪妻之恨的強烈發泄”胡旭先生《文選·洛神賦題注發微》,一文,更是從魏晉六朝乃至唐代的歷史文獻中旁搜遠紹,鉤玄爬梳,證明了曹植甄后之間的戀情的真實性,并明確指出,兩者之間的私情“不一定在甄氏歸曹丕之初,而極可能在建安后期,特別是曹丕隨曹操出征、曹植留守鄴城的那些時期。曹丕不僅處死甄氏,而且侮辱她的尸體,這源于甄氏背叛自己而產生的刻骨怨毒”①以上均見胡旭《文選·洛神賦題注發微》,載于《中國韻文學刊》2013年第2期,第63頁。,可謂振聾發聵、錚錚有聲。通過本文,可以看出劉美惠扎實的文獻功底和敏銳的學術感受和表達能力,15歲而能參與寫出如此老到之論文,評之為天才學術少女,當不為過,其學術前景,無可限量。
胡、劉師生合作的這一篇大作,視角新穎,為古詩十九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畛域。僅舉一例:
有些異文則可能將詩歌導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東城高且長》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馳情整巾帶”有“中帶”的異文。由于《東城高且長》中兩段并不融洽的內容,對這一首詩究竟本為一首還是兩首偶然湊成則成為歷代論者討論的焦點,對后半段主人公的判定也難有定論。但“巾帶”和“中帶”有著相當不同的性別指向。與“巾”相關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男性,而“中帶”則無比明確地指向女子的內衣帶。②見《儀禮·既夕禮》:“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裈衫。”
“巾帶”與“中帶”,看似一字之別,但卻有著天壤之別,巾帶,是男人服飾,中帶,則是女性之褻衣。有些事情其實并不需要繁瑣的考證,需要的僅僅是基本的常識,需要簡單的情理以及作為學者的基本素質和良心。我們如果知道了十九首中大量出現的這些女性用品,性的饑渴(“空床難獨守”之類),以及男性在美色面前的猶豫徘徊(“馳情整中帶”之類),以及兩者之間愛而不能同居(“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之類)的對話,我們就不會再相信這是所謂比興君臣、友朋之作的無恥讕言。我注意到近一個時期開始有一些學者和我的商榷,這原本是我所衷心期待的事情,遺憾的是,其中罕見有提出新的材料,新的論證,新的邏輯關系,有的僅僅是將我所顛覆和拆碎的謊言,重新給予復合。十九首等漢魏古詩,原本由梁啟超提出為東漢之作,就僅僅憑著“直覺”而并無任何實在證據,當下中外學者提出的如此之多新的證據和論證,學術界理應在新的起點開始新的研究歷程。我的研究是一個縱橫交錯的理論體系,我一直期待著有學者能同樣建樹一個詳備的體系來闡明十九首等何以為東漢而非建安曹魏,何以為無名氏文人而非曹植甄后。然而,迄今為止的商榷文章卻是破碎的,陳舊的,只言片語的,基本上大多還屬于尚未讀懂的狀態。這使我感到了某種深重的悲哀:“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卻不接受光。”③參見“HOLY BIBLE`JOHN”,“He himself was not the light;he came only as a witness to the light.”“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but the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 it.”第 160 頁。
近日有學者從國內發來孫明君先生的論文,該文就《青青陵上柏》這一首詩的作者和作年問題,與我進行了商榷。此文可謂是近年來相關商榷文章之最為優秀者,在兩宮問題上,似乎提出了新的材料,作出了新的思考(雖然還不足以支撐東漢說)。同時,在學術界有關漢魏五言詩的總體研究態勢方面,對宇文所安先生和我的研究給予了這樣的評論: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早期詩歌是一個復制的系統,找不到“古詩”早于建安時期的確鑿證據,木齋提出《古詩十九首》及建安詩歌的重要組成大部分詩作為曹植之作,掀起了文學界的波瀾,推進了古詩研究的學術歷程。④孫明君《<青青陵上柏>作者與作年辨》,載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很多時候,在所謂的直接材料歷史的缺席的背景之下,情理的吻合極為重要。梁啟超用“直覺”作出結論,讓后來人相信了將近一個世紀,我們不能再相信直覺,而要進一步在材料的基礎之上,做出邏輯的鏈條,最后,再用“情理”來加以檢驗,如果微觀上每句每字都能合于情理,宏觀上吻合于中國文化史、語言演變史、文學思想史、社會風俗史、中國文學在斯時前后的演變史,特別是吻合于該詩作其所屬性的文學體裁、題材、風格等的演變史,我們就可以在直接材料歷史缺席的情況之下,給予一個接近歷史真相的階段性定位,并延續這一定位,給予不間斷的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