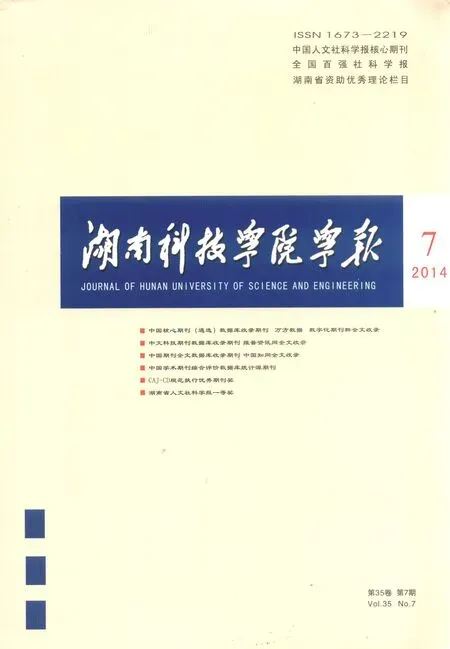未來時空中的“寓言”書寫——王小波小說解讀
尹 琴
(貴州師范大學 求是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7)
王小波的小說中有一部分作品故事發生在虛擬的未來時空,如《白銀時代》、《未來世界》、《2010》和《2015》等。雖然故事設置的時間是在未來,但王小波筆下的未來常常只具有一種“寓言”式的象征性意義,并不是他對現實生活的預敘。王小波在《未來世界》的自序中說道:“有一些小說家喜歡讓故事發生在過去或者未來,但這些故事既非對未來的展望,也非對歷史的回顧,比之展望和回顧,他們更加關注故事本身……我在寫作時,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1]53
他筆下的未來世界既不是關于歷史的思索,也不是對未來時代的想象,王小波關注的是人類的,主要是知識分子在權力之下的困境。權力對知識分子的控制與束縛成,知識分子在權力之下的生活是王小波這一類小說的核心。雖然時間設置在未來,但是這些小說中更像是“寓言”,其意所展現的是人在權力之中的困境;這種困境卻是可以穿越時空;即存在于過去,也可能繼續存在于未來。
一 “寓言”式敘述
這類小說在時間的設置上都選擇了21世紀,如2010年,2015年等等;《白銀時代》這個文本里,王小波設置的時間是2020年,對題目“白銀時代”,文本中有過解釋;
“希臘神話里說,白銀時代的人蒙神的恩寵,終生不會衰老,也不會為生計所困。他們沒有痛苦,沒有憂慮,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兒童。死掉以后,他們的幽靈還會在塵世上游蕩。……如你所知,我一直像個白銀時代的人。”[1]P40
然而整個文本對未來時代的敘述卻并不是要構建一個理想世界,反之是要否定、顛覆這種敘述;我們可以從文本里“我”與寫作公司,小說與生活這兩組關系中看出王小波在這個文本中的這一傾向,同時在這兩組關系中王小波還對文學與生活、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未來時代中的狀況作了探討。
“我”受雇與寫作公司,身處中間階層,既受制于人沒有完全的寫作自由,又控制著另一部分人的寫作自由;可以隨意“槍斃掉”別人的稿子。而生活與小說之間的關系是寫作公司里對作品評價的原則。“‘克’或者別的上司會把它挑出來,用紅筆一圈,批上一句‘脫離生活’”。“假如我寫了,上面就要槍斃有關段落,還要批上一句:脫離生活”。顯然這其中的評價遵循的還是“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加工”等創作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任何以虛構、變形、夸張等方式寫作的作品都得不到承認,得不到出版發行,文學只能淪為記錄生活的工具;文學獨特的藝術價值是被否定的。“如你所說,我們所寫的一切都必須有‘生活’作為依據”。生活在未來的“白銀時代”里的作家們的創作只能依據唯一的一個原則;社會的發展狀態并不符合現代性理念預設的結果,未來時代中“人在公司里只有兩件事可做:槍斃別人的稿子或者寫出自己的稿子供別人槍斃”。作家喪失了自由創作的權利,藝術創作也毫無生氣、活力,只是在重復寫作同一主題的小說。“寫作公司”在文本里并不僅僅只是一個機構,而是具有濃厚的象征性意義,寫作公司里明顯存在界限分明的等級、權力。個人的生存發展狀態并沒有隨時間的推進而改善,個體與社會、個體與國家的關系也沒有達到和諧,現代性觀念下的進步、發展的樂觀前景沒有出現。王小波所建構的這些關于未來世界的故事,是一種“反面烏托邦”敘述的寓言。未來的社會生活在他的筆下沒有朝著光明美好的方向發展,個體的自由狀況更是堪憂;對此王小波在《〈代價論〉、烏托邦與圣賢》里說:
“‘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烏托邦,還有反面烏托邦。這后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2]P199
王小波對反面烏托邦特征的表述在他的小說里獲得了形象的展示。《未來世界》的“舅舅”是一個作家,但寫東西不準出格,結果他的才華被浪費掉,生前一部作品也沒發表過,在一次電梯事故中死于非命;“我”是歷史學家,因為寫舅舅的傳記而犯“直露錯誤”和“影射錯誤”的思想錯誤,交給公司(全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安置,被剝奪了身份證、信用卡、住房、汽車、兩張學術執照以及兩個博士學位。公司重新給了“我”一個名字M,安置了住處407和一個“妻子”F,還安排了一份建筑工的職業。為了好好改造思想,按照公司規定每月月底領工資同時挨保安員一頓鞭打。被公司安置的基本是知識分子,同樣的都被剝奪了以前的一切而由公司重新安置,而且相互之間不能聯系。“通過這種支配技術,一種新的客體對象正在形成……這種新的客體對象是自然的肉體,力的載體,時間的載體。這種肉體可以接納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的、步驟、內在條件和結構因素的操作。在成為新的權力機制的目標時,肉體也被呈獻給新的知識形式。這是一種操練的肉體,而不是理論物理學的肉體,是一種被權威操縱的肉體”。[3]P175這個文本里“公司”正是權力的象征,被它安置的人失去了自主性,公司的各個部門分別掌控了人的各個方面;人變成了服從公司規定制度的機器,連姓名都不再需要,只用一個符號代替。
《2015》里的“小舅”是個畫家,常因無照賣畫蹲派出所,后來被送進習藝所。他的錯誤在于畫來沒人懂,犯了“叵測”罪,最后雖然平反了,卻再也畫不出“叵測”的畫了。習藝所里有各種各樣的新潮藝術家;習藝所用一臺電刑機給學員“測智商”,因為教員們認為“假如讓他們的智商太高,不利于他們的思想改造”。這正是一次又一次所開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的根本旨意所在,因為他們的智商太高,就需要依靠一次次的批判運動來壓制。權力的影響無處不在,滲透到生存的各個方面;“在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權力比例通常是極不平等的,那些擁有相對較多的權力機會的人或集團往往把他們的權力機會發揮到極限,為了自己的目的他們常常窮兇極惡、肆無忌憚。”[4]P111在《2010》里患了數盲癥的人可以走上領導崗位,而在沒患這種病的人來看,他們就是傻子,也就是說,進入了非理性的世界,這種生活里有種種特權。北戴河技術部的王二是資格最老的工程師,卻因開Party闖了禍,被判鞭刑。受刑的地點是在廣場上用木板搭的臺上,而且受刑過程將向全國轉播;甚至在等待受刑時呆在玻璃棚子里的畫面也被轉播。將受罰公開化,其目的正可以極好地詮釋權力的含義,展示權力的威力。
以上幾個文本中敘述了各種機構、組織對知識分子的規訓與懲戒,其發生的場所諸如寫作公司、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習藝所等無不具有象征性意義,它們的內涵可以擴充、放大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層面;它們與其中的知識分子的關系就可以個體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表征;而權力關系就是其中的核心。這些設置在未來時空中的故事,不能說是王小波對未來時代的展望;將這些故事看作是一則則的“寓言”應該更為恰當,而知識分子在權力之下的生存狀態則是王小波思索的重點。“肉體是馴服的,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這種著名的自動機器不僅僅是對一種有機體的比喻,他們也是政治玩偶,是權力所擺布的微縮模型。”[3]P154由于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軟弱,權力更成了一張無邊無際,無所不能的網,它籠罩著任何一個角落,權力的觸角直接貫穿到個人,他們的軀體、姿態和日常行為。在這種權力之網中人成為機器,對自由的追求成了夢幻。
二 被權力穿透的肉體與精神
如果說王小波筆下生活在“文革”時期的人物的行動還多少折射出對“革命時期”各種規范的抗拒與嘲弄的話,那這些處于未來時代的人物面對權力的淫威,選擇屈服是他們共有的特性。
《白銀時代》里作家們在寫作公司里只有兩件事可做:槍斃別人的稿子或者寫出自己的稿子供別人槍斃。“我”受雇與寫作公司,身處中間階層,既受制于人沒有完全的寫作自由,又控制著另一部分人的寫作自由;可以隨意“槍斃掉”別人的稿子,一篇叫《師生戀》的小說卻不得不根據“頭頭”的意見重寫了十幾遍。作家的創作需要選材、構思、主題設置的自由;沒有這一切作為基本條件是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現。但是寫作公司里的作家卻拋棄了這些基本因素,甘愿稱為寫作機器,聽命于“頭頭”的指使。讓作家們如此的正是權力,寫作公司所蘊藏的力量源于權力 ;而又是作家們對權力的屈服使得寫作公司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我們習慣于把權力想象為一種來自外部的壓迫主體的東西,是使主體屈從、下置并降級為一種較低等的東西……權力將自己強加于我們,并且,因被它的壓力所弱化,我們最終將內化或接受它的條款。”[5]P2生活于“白銀時代”的作家們被外界的權力所弱化,喪失了獨立自主性,肉體與精神屈服于權力之中。
《未來世界》里“我”因為寫舅舅的傳記而犯“直露錯誤”和“影射錯誤”的思想錯誤就被公司剝奪了一切,包括姓名;重新安置了一個字母F做名字;雖然擁有兩個博士學位卻只能接受公司安排的建筑工的工作。不但胸前要佩戴大大的紅色字母D,去公司“聽訓”,還要接受鞭打;因為“我是為公司而生,公司是為我而設”。公司的權力已經內化為人物精神之中可以接受的因子,“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對應于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服從成了對待一切權力的方式:
“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么。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沒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 作廢了”。[1]P137
個體已經將權力的威嚴視為正常化并接受,更缺乏對權力加以抵御的行動;權力已經穿透了人物的肉體與精神,剩下的只是屈服。《2015》中習藝所里有各種各樣的新潮藝術家能夠接受電刑機給自己“測智商”,而這臺機器上的電極“假如安得位置偏低,就會把陰毛燒掉;安高了則把頭頂的毛燒掉”,“食堂里遇到毛沒有煺盡得豬頭豬肘子,也會送來測測智商,測得的結果是豬頭的智商比藝術家高,豬肘的智商比他們低些”。有的學員在自認為犯錯時,甚至不用教員問,竟可以“主動伸出頭來要挨一棒”。權力不但對肉體進行了規訓與懲戒,精神同樣屈服在它之下。所謂規訓,就是那些使“肉體運作的微妙控制成為可能,使肉體的種種力量永久服從的,并施于這些力量一種溫順而有用關系的方法”。[3]P155《2010》里“數盲癥患者”們規整了一個秩序森嚴的社會,僵硬、虛偽、壓抑,人在一個日復一日沒有變化的龐大機器里機械地生活,這種機械甚至延伸到了性愛,人的活生生的欲望變成了不帶任何情感的性交。他們的工作主要就是聽報告、做報告和用一整套非人道的制度去束縛、控制非數盲,維護森嚴的等級制度,一旦有違者即遭到殘酷的鞭笞之刑。王二因開Party被判鞭刑,行刑時只挨了八鞭就暈過去,吸氧打強心劑醒來后“有人要把我解下來送醫院——余下的下回再打。我堅決不同意,并且抱著柱子不撒手,說自己沒問題”;“作為一個受刑人,我認為它對我有好處。當然,它對身體有點損害,但是皮肉之苦可以陶冶情操”。受鞭刑在個體精神上已經被轉化為具有好處并可以接受下來的東西,精神已經屈服于權力。受鞭刑的過程全國轉播,公開的懲罰強化權力的力量;肉體所受的懲罰變成一種儀式,一次權力無所不能的表演。王二堅持受完鞭刑的行為進一步強化了權力對個體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規訓。
雖然王小波敘述的這些“反面烏托邦”寓言設置的時間是在未來,但是這些“未來故事”的產生與王小波對歷史、現實的認知、理解有關,同時也與他的現實關懷精神相聯系。
“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歷過烏托邦鼓舞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2] P199
在王小波看來剛過去不久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實現烏托邦是不可能的,是愚蠢的;這樣的歷史不應該讓它再次出現。而虛構一個個反面烏托邦就具有了現實意義,它可以讓人們對實現烏托邦的可行性與可能性有清醒的認識;可以說王小波的創作最終指向的都是對現實的關注。文本里的人物在權力面前幾乎沒有做出什么抗爭,肉體和精神在權力之下已經被弱化;施加于肉體的規訓進而將精神也馴服,這些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無所作為,權力完成了對他們的肉體與精神的穿透。“未來時代”里的人物如此孱弱,他們受困于權力之網,既無力掙脫也無意掙脫。
三 對知識分子的拷問
王小波的小說里,人物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是一個較普遍的因素;許多文本里都有相關的敘述。《紅拂夜奔》中李靖當了唐朝的開國功臣之后還是想著如何建立一座長安城,設計了風力長安、水力長安和人力長安三個方案;在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之下剩下的生活就是裝瘋賣傻。紅拂在楊素家做歌妓是,也是百無聊賴之中留三丈長的頭發,一尺多長的指甲;與李靖出奔后成了衛公夫人,屬二等貴婦。依然“妖艷”的紅拂不得不在上班之前“精心打扮”:在臉上畫魚尾紋、戴假肚子、假臀部、灑上從發酵的黃豆、淘米水、油煙里提煉出來的香水。因為這樣才符合朝廷規定的二等貴婦的形象。最后連“殉夫”都必須經過申請,層層審批。《尋找無雙》中宣陽坊里的坊吏王安老爹只用鐵尺在王仙客肩上拍一下,正在宣陽坊吵鬧的王仙客登時變老實了,老老實實拿出博山府開的路引,鞠著躬雙手呈上,并交代自己的姓氏籍貫。魚玄機在監獄里甘愿承受各種侮辱,行刑前還被要求做一個“模范犯人”。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說同樣存在權利對人的規訓,《黃金時代》里王二和陳清揚被批斗、禁閉、寫交代材料;《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二必須接受無聊的“幫教”,參加各種受教育的會議。
在敘述“未來世界”的幾個文本里,權力對人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規訓更成了王小波關注、表述的重點;而且這一部分作品里的人物多為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的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也就是知識分子選擇服從或者選擇逃避的時代。王小波認為中外知識分子都在做一件事——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否則就不能叫知識分子;他自己就是如此。王小波的小說創作以一個個充滿想象力的虛構故事傳達出對社會、人性的思索和關注。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時刻,給朋友劉曉陽的郵件里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他生前以一種“獨立特行”的姿態進行創作,“在中國文化的精神譜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種異數:不僅其文學風格無法歸類,而且這個人也難以理喻。從年齡來說,王小波屬于紅衛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紅衛兵的狂熱激情,反過來倒多了一份英國式的清明理性;從思想脈絡來說,他似乎是半個世紀以前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傳人,但又不似胡適、陳源那樣帶有自命清高的紳士氣”。[6]P254而要做到“自由派”就不可能在權力之下屈服,更不用說由肉體的被規訓到精神的弱化。但是王小波筆下的這群生活在“未來世界”中的知識分子卻屈服于權力,精神也被馴服,甘愿聽命于權力。
《未來世界》里“我”因思想錯誤就被公司剝奪了一切,包括姓名;重新安置了一個字母F做名字,雖然擁有兩個博士學位卻只能接受公司安排的建筑工的工作。不但胸前要佩戴大大的紅色字母D,去公司“聽訓”,還要接受鞭打;因為“我是為公司而生,公司是為我而設”。《白銀時代》里作家們在寫作公司里只有兩件事可做:槍斃別人的稿子或者寫出自己的稿子供別人槍斃。“我”受雇與寫作公司,身處中間階層,既受制于人沒有完全的寫作自由,又控制著另一部分人的寫作自由;一篇叫《師生戀》的小說卻不得不根據“頭頭”的意見重寫了十幾遍。《2010》里王二受鞭刑時只挨了八鞭就暈過去,吸氧打強心劑醒來后“有人要把我解下來送醫院——余下的下回再打。我堅決不同意,并且抱著柱子不撒手,說自己沒問題”;“作為一個受刑人,我認為它對我有好處。當然,它對身體有點損害,但是皮肉之苦可以陶冶情操”。
在這樣的敘述中,除了展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之外,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也顯現無疑。對權力的屈從乃至依附、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是王小波筆下的未來時代中知識分子的特性。他們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不再承擔“啟蒙者”的角色;軟弱、毫無擔當的這群人物在王小波的筆下成了被拷問的對象。本應該具備的對現行秩序的疏離與獨立意識、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對權力的抵抗、對不合理的揭示在他們身上并不存在;而“未來時空”中整個社會被權力所籠罩,掌控著權力的種種“公司”“機構”將之揮向了每一個個體。這樣從內外兩方面生產了這群無所作為的知識分子。
王小波立志做一個自由派,但筆下的這些人物卻完全相反;其中的緣由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關于權力滲透社會和個人各個方面的思索與敘述。作家的人生體驗與閱歷與創作有密切的關系,王小波親歷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權力對個體的規訓極為嚴厲,權力深入個體的精神與肉體中;言論、行動、思想統統要符合既定的規范,否則就必須接受懲戒,以便將肉體和精神重新納入規范之內。雖然《白銀時代》、《未來世界》、《2010》和《2015》中故事時間是在未來,但是人所承受的權力困境卻沒有消失;權力是一個不死的幽靈,穿越古今。正是出于人對權力的束縛不可擺脫的生存境遇的關注,王小波將原本可以為之憧憬的未來世界也至于權力的控制之下;在那樣的時代,權力依然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另一方面則是對出于權力之下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注視。薩義德認為知識分子“在公開場合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是以代表藝術為業的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數學或上電視。而那個行業之重要在于那是大眾認可的,而且涉及奉獻與冒險,勇敢與易遭攻擊”[7]P18。但是這幾個文本里的知識分子們卻沒有承擔起應該擔負的責任,在權力面前毫無作為,一味屈服于權力。王小波認為“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知識分子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敢于承受因之而來的后果。他在自己的小說里創作了一群無所作為的知識分子,在對這樣的人群作出拷問的背后有隱含了對勇于擔當、敢于對權力做出抗拒的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的呼喚。王小波在文本里展示受困權力的生存狀態,正是為了期望能夠擺脫這樣的人生境遇。
[1]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七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一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3]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第3版)[M].北京:三聯書店,2007.
[4]諾貝特·埃利亞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朱迪斯·巴特勒.權力的精神生活:服從的理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6]許紀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A].不再沉默——人文學者論王小波[C].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7]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