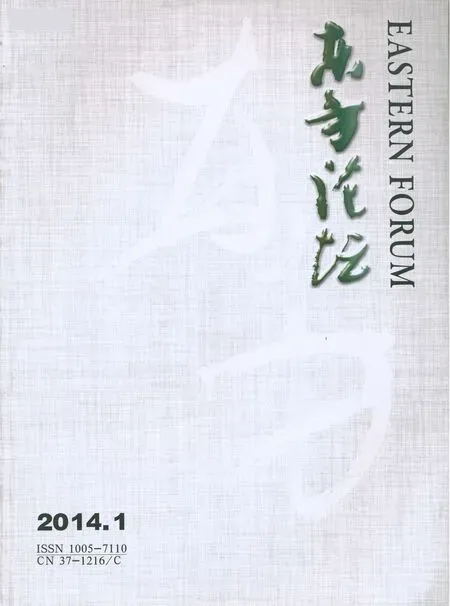漢學“再現”視域下的儒家詩歌功能觀
徐 寶 鋒
(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3)
漢學“再現”視域下的儒家詩歌功能觀
徐 寶 鋒
(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3)
漢學家對儒家詩歌功能觀的理解是和“再現”理論關聯在一起的。不管是劉若愚對于西方“再現”理論的接受和轉化,還是歐陽楨等漢學家對于中西文論背后的哲學差異的理會,都十分明確地展露了他們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理解。其在分析中國詩歌的反映和表現問題時,都或明或隱地參互進了對于“再現”這一源自西方詩學的理論范疇的體認。
漢學;再現;儒家;詩歌功能觀
在漢學視域下,“再現”理論與儒家的詩歌功能觀是關聯在一起的。儒家視“德”為天法倫理﹑社會規范,將“德”理解為表現心性以及倫理觀念的規范性行為,而檢驗“德”的標尺恰是儒家反復強調的“禮”。當儒家把“陰陽”“天地”“乾坤”“天道”“地道”“人道”“天文”“地文” “人文”等等看作了可以在詩歌中進行情感分析和再現的對象時,儒家實際上針對的分別是因道而生的自然的法則或社會的法則,指向的是詩歌顯現倫理觀念和道德心性的功能與作用。對此,蘇熙源(Haun Saussy)認為,中國古代批評文本傾向于“采用道德的立場,這種立場是為由古代的禮儀主義所激發的所有美學理論所共有的”,“從詩歌到對政府的回聲之間的路徑是雙向的。”[1](P90-910)法國漢學家侯思孟(Donald Holdzman) 也認為 “文學理論(或稱文學批評)在中國古代未能發展是因為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在談論文學時根本不把文學看作是一種與道德﹑禮儀﹑政治平行的獨立存在,不把文學看作是一種應該獨立考慮的東西。”[2](P47)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則更為明確地點明:“《詩大序》有關詩歌教化功能的表述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基石。”[3](P42)以上這些論點十分明顯地彰顯了大多數漢學家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體認姿態。不管是以劉若愚為代表的早期漢學家對于西方“再現”理論的接受和轉化,還是歐陽楨等后期漢學家對于中西文論背后的哲學差異的理會,都十分明確地展露了他們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理解。
一
劉若愚在其《中國文學理論》一書中,劉若愚依據劉勰“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的觀點,明確指出在中國古代的詩學傳統中,不管是“道沿圣以垂文”還是“圣因文而明道”都呈現出了一種十分明顯的“再現”關系。劉若愚引述鄭玄《詩譜序》和清初批評家汪琬的觀點認為,無論是《左傳》所載季札對《詩經》所表現的道德性格和政治情操的討論,還是《樂記》對于“音樂反映一國政治情況”的概括①實際上都在說明“文學是當代政治和社會情況不自覺之顯示”。[4](P97)到了唐代,中國的詩人們已經“漸趨重視文學的功利作用而非形上性質,因此在他們的理論中,形上要素與實用要素合并在一起”。[4](P39)劉若愚以唐代初期的李百藥﹑魏征﹑王勃以及白居易為例,認為:“唐代以及后期的作者繼續提及天文與人文的類比,可是他們通常是用以作為實用理論的宇宙哲學基礎,而不是像劉勰和蕭氏兄弟那樣,借以證明文學的崇高地位。隨著從文學形上概念到實用概念的這種轉移,‘道’的形上概念也轉移為道德概念。”[4](P39)
通過對艾布拉姆斯文學四要素的全面改造,劉若愚分別從“決定理論”“表現理論”“實用理論”和“形上理論”四個角度對文學的功能加以了闡述,并以此為出發點,從“再現”的理論視域出發展開了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討論。在討論“實用理論”和“形上理論”關系時,劉若愚認為“以文學為宇宙之原理的顯示為基礎的形上理論”對于“道”的強調,在儒家這里實際上被強調為“在人與人的關系中,遵循古圣先賢依據自然之道所立下的倫理之道”[4](P20-21),在討論“決定理論”和“實用理論”的關系時,劉若愚認為:“決定概念時常與實用概念結合在一起,因為在文學不可避免地反映產生它的社會這一前提之下,很容易產生的結論是:文學可以作為歷史的‘鏡子’,從中可以學到實際的教訓;也很容易從決定論的立場 ——認為不管是否自愿,作家顯示出當代社會和政治現實,轉移到實用的立場——認為他‘應該’自覺地這樣做。”[4](P98)
在劉若愚關于文學的這四種關系理論中,最能對應其對于儒家的詩歌功能觀理解的是其“實用理論”。劉若愚在他《中國文學理論》第六章開篇即指出,“實用理論,主要著重于藝術過程的第四階段,是基于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手段的這種概念。由于得到儒家的贊許,它在中國傳統批評中是最有影響力的。”[4](P164)劉若愚認為孔子談詩的見解“思無邪”“顯然表示對詩的道德內容和影響力在實用方面的關切”,《論語》中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整句話顯然是在描述自我修養的程序,而所關切的是詩的實際效果。”[4](P164)劉若愚接下來討論了孔子“興”“觀”“群”“怨”等具有道德和社會功用效果的文學概念,并認為:《詩經》之后,“有些人強調文學的政治功用,或從統治者的觀點,認為文學有助于統治,或從臣民的觀點,認為文學是批評和抗議的手段;另一些人則強調文學對個人道德的影響。”[4](P168)因此,《詩大序》中“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從統治者的觀點出發,規定出詩的政治功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腳以戒,故曰風”是從臣民的觀點描述詩的政治功用。劉若愚認為《詩大序》的推論本身是不合理的,因為其“對于個人感情的自然表現如何以及為何一定反映政治情況,或者如何以及為何這種表現能達到道德﹑社會和政治目的,并沒有給予邏輯的解釋。”因此《詩大序》的思想應該是基于如下的假定:“除了政治情況所產生的感情之外,沒有別種人類的感情,而所有如此產生的感情,必然是道德的﹑有助于改善政治情況的。”[4](P180)從自己所建構的關于中國文學理論的體系出發,劉若愚認為《詩大序》中這些不合邏輯的地方,終其全篇都沒有獲得解決。“將詩的表現概念和實用概念互相調和的這種意圖并沒有成功。首先,在國史‘吟詠情性’與‘發乎情,民之性也’的陳述之間,有著顯然的不符之處;即使我們接受孔穎達的解釋,認為作者的意思不是說國史在詩中表現其本身的情性,而是說他們采集了人民情感的詩歌,可是我們仍然懷疑,人民情感的表現,是否一定‘止乎禮義’。”[4](P181)
劉若愚指出,雖然到了劉勰那里,“道德的‘道’以宇宙之‘道’為基礎,而且由于文學顯示出前者,他能夠適合道德目的”;但是,“自韓愈始(他對‘道’這個字的道學定義,我們已經知道),理學家通常認為文學是宣揚‘道’的手段,而‘道’被理解為道德原理而非宇宙原理的要素。”[4](P172-184)他認為,儒家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詩歌功能觀使后世學者的理論呈現出了一種理論上的矛盾之處,就連強調“詩在表現上不必受到約束,以及詩不必與社會和道德有關”的袁枚在論及情詩時,依然把道德品格以及是否違背道德看作了評判詩歌的一個必須前提。劉若愚指出,袁枚的論調似乎是要魚與熊掌兼得:“一方面,你無法從詩中看出一個人的道德品格,而寫‘不道德’情詩的某人,可能事實上具有毫無瑕疵的道德品格;而另一方面,你可以從詩中看出一個人對愛情的真誠,而性愛并沒有什么不道德的。”[4](P207)袁枚的這種妥協的姿態反映的恰是儒家的詩歌功能觀相形于西方“再現”詩學的復雜性。
二
對于劉若愚所涉及的這個問題,余寶琳(Pauline Yu)認為,“在中國,文學與社會政治秩序的關系長期以來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這個世界中,宇宙模式(文)及過程與人類文化模式及過程之間存在著某種基本的一致性。因而《詩大序》得以斷言,內在的東西(情)可以自然地發現某些外在相應的形式或行為,詩可以反映﹑影響并達到政治和宇宙秩序。鑒于這種個人與世界天衣無縫的一致性,詩歌得以立即揭示情感,提供某種政治穩定性的尺度,并且還可以作為某種實用的說教工具。”[5]而且,“主客體之間或客體之間的聯系,這些西方大體歸于詩人創作獨創性的東西,在中國則被視為是先前業已建立的東西;詩人最基本的成就往往在于超越他自己的個性以及與世界各種因素中的不同之處,而非是對這種個性和差異加以斷言。”[6](P32-33)詩對于政治和宇宙秩序及其現實實存的反映從理論上講就是一種“再現”,而與之相關的情感之揭示則為“再現”的一個層次和維度。很顯然,余寶琳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討論也是從“再現”理論入手加以闡發的。
余寶琳從《小序》﹑鄭玄以及朱熹對《詩經·唐風·綢繆》的注疏出發,認為這些中國傳統的注釋的例子說明:“一首詩通常被當成實際歷史狀況的文字評論而加以閱讀的,而評論者的任務則在于重構詩歌的語境,即解釋出是哪一類特別的促進因素產生了那種反映。相比之下,有一些學者并不那么贊同將《詩經》中的詩歌視為是對當時國家初始狀況的實際編年記事,然而即使這樣,他們的解釋也從未擺脫對歷史真實性(Historicity)的信念。人們無疑相信《詩經》中的詩歌被采集起來是為了測定人民的情感以及確立選集的經典地位。這一信念指導了儒家評論家產生出了如此倫理化﹑有關時事的隱喻式的解讀,然而他們的遺產也形成了‘現世的’詩學傳統。”[5]余寶琳借助史密斯(Barbara Smith)“自然表達”(Natural Utterance)的觀點認為,意義的生成在于:其語境“為何發生:產生它的環境﹑動機﹑條件﹑‘外部’和‘內部’的,物質和心理的這些因素,引發表達者以當時適當的形式表達。”[5]大陸學者高玉對余寶琳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認為余寶琳在通過《詩大序》中的文字闡述儒家的詩歌功能觀時,“其實是用西方文論的方式來談論中國古代文論,其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都是西方的。中國古代文論在這樣一種新的談論和言說中其內涵其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內在’‘外在’‘形式’‘反映’‘政治’‘宇宙’‘個人’‘情感’‘主體’‘客體’這些西方的術語﹑概念和范疇不能完全涵納‘風’‘天下’‘鄉人’‘邦國’‘教化’‘志’‘心’‘情’‘形’等這些中國古代的術語﹑概念和范疇。同時,西方‘影響’等概念和范疇其意義又溢出了中國古代的‘教’等概念和范疇的意義。”[7]高玉認為余寶琳的問題在于把“內部”“外部”這些西方詞語的背后更為深層的理性﹑科學﹑邏輯等精神,與“風”“教化”等中國古代詞語的背后更為深層的道﹑氣﹑禮﹑仁等精神混同看待了。“余寶琳把中國古代文論納入了西方文論體系,從而使中國古代文論成為被認為是具有‘普適性’的西方文論的注腳。余寶琳所解說的《詩大序》的思想只是名義上的中國古代文論,而實質上是西方文論。”[7]事實上,余寶琳意識到了她的做法可能會“被那些處于不同規范的批評家當作‘膚淺’”,她本人對高玉所說的現象十分警惕并曾予以了尖銳的批評。前文曾經言及,余寶琳堅決反對援用西方文論研究中國文學的問題時,削足適履地生搬硬套相異的方法和標準;她深知,漢學研究在將各種西方文學理論運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之上時,務必要先了解歐美文學術語在其文化脈絡中的哲學意涵,然后才能有效地植西入中。在余寶琳看來,“一種植根于儒家宇宙觀的概念支配著評論:政治就是顯而易見的倫理觀,而且任何個人都難于在涉及本人時不去涉及更為廣泛的語境。這些整體論的臆斷逐步以某種形式構成對非經典文本的解讀,事實上亦成為后來詩學理論的基礎。”[5]
三
漢學家們在討論儒家的詩歌功能觀時,孔子“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段話被漢學家廣泛援引。范佐倫(Steven Van Zoeren)在《詩與人格:中國傳統經解與闡釋學》(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一書中認為,這段有關孔子提倡學習的句子包含了《詩經》“興﹑觀﹑群﹑怨”這四項功能,不僅說明孔子已經意識到了“文學的作家認定,在自然與社會﹑文化世界的內外存在著某種復雜﹑持續以及類似網狀物的緊密聯系”。[8]而且,如何適時地引用《詩經》作為道德教育的素材以激起一種道德感,從文學批評本身來講已經涉及了詩歌和社會的復雜關系問題。英國漢學家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呼應了范佐倫的觀點,他認為:《詩經》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些本是用以比喻年輕情人優美容顏的句子往往會因出于教育目的(educational purposes),而被儒家給以更富有道德性的闡釋,用來喻指如何培育道德修養;《論語》對《詩經》進行了有意的誤讀并使之成為道德的標簽,使《詩經》語義徹底發生了改變;孔子對《詩經》的誤讀性闡釋明確表明孔子視《詩經》為道德培訓(moral training)的教科書。[9](P23)道森認為在以上這段孔子討論《詩經》的話中,孔子關注的“并非是其審美趣味(aesthetic appeal),而是實用目的(practical purpose)。”[9](P22)孔子說所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表明其對于《詩經》行政和外交等實際功能的強調。對于范佐倫和雷蒙德·道森所提及的道德教育和實用功能問題,美國學者海倫娜(Helena Wan)在《孔子的教育思想》(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Confucius)一文中從情感教育的角度加以了深化性理解,她認為:上述《論語》的這段話實際上說明孔子在賦予詩歌以重要教育功能的同時,并不單單把詩歌視作彼此交流的工具,而是同時強調其表達情感的渠道作用;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句話說明孔子在詩歌的所有功用中,最為重視的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功能,孔子實際上認為“詩歌可以使人的感受(sentiments)與情感(emotions)得以適當地宣泄,使之趨于緩和并向合乎規范的方向發展”。[10](P190)因此相較于“不學詩,無以言”這句孔子敦促兒子伯魚在道德﹑智力等層面上獲得提升的話而言,“思無邪”(have no twisty thoughts)主要是指《詩經》具有助于凈化(purify)與喚起(arouse)情感的道德教化功能。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馬丁(Martin Kern)在《新出土文獻與中國早期詩學》(Early Chinese Poetic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nuscripts)一文中,辨析了從西漢晚期以來的經學儒生的道德和政治維度,主張“從出土的文獻,如《孔子詩論》來討論早期詩歌的不同接受與解讀,借此可以再斟酌我們對這些早期詩作的構成﹑流傳﹑解讀和社會文化地位的基本假設”。[11](P72)加拿大漢學家格雷厄姆·桑德斯(Graham Sanders)從“詩歌能力”(poetic competence)和“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兩個角度對孔子的詩學觀念加以了分析。在桑德斯看來,“詩歌能力”指的是某人為達到某種預期目的(desired end)而以詩歌話語(poetic discourse)為手段來影響另一個人的態度與行為的能力。“文化能力”指的是對于傳統的掌控能力。[12](P16)儒家試圖在面對適當的場合﹑適當的對象時,選擇適當的《詩經》中的詩句加以發揮,通過應用過去的知識于當下的情境,調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進而強有力地影響(sway)其聽眾。桑德斯認為,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以及“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是為了激勵弟子學習《詩經》并懂得如何適時地加以運用,“孔子非常鼓勵弟子們通過刻苦努力來獲取知識并應用于實踐。”[12](P26)宇文所安認為:“一切內在的東西都要走向外在顯現,內與外是完全相符的。這是中國文學思想的一個信條,中國文學思想的主流就是這個原則上發展起來的”;[13](P217)“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最深層動力往往不在于孔子對文學自身所表達的見解,而在于《論語》所蘊涵的儒家思想對更廣泛問題的關注”;[13](P17)《論語·為政》中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這句話已經說明儒家認為通過一個人的行為狀態(所以)﹑行為動機(所由)和行為者的心理(所安),可以察知他的道德品行和性格特征。
費維廉對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政治及社會功用觀也較為關注。作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他在為《印第安那中國古代文學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專門撰寫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論文中,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看法:
公元前1世紀上半期的《詩經》中包含了最早的有關運用詩歌的論點。其中大部分抒情詩、歌謠、風、雅、頌都為不知名的口頭傳統作品。但其中有一些作者聲稱,其意圖是表達某種悲傷,意愿,對美與善的贊美,對統治者的批評,以及對早期圣人的緬懷。從3世紀起,這種創作文學自我意識的抒情詩持續下來,只是后來增加了一種觀點,即詩歌是在精神上自我完善的手段。在《詩經》之后的世紀中發展了有關詩歌的政教觀,這些觀念在儒家經典和其他古文獻中都有大量的記載。例如,《禮記》中記載說,封建王室每五年就要求宦官們引誦民謠,以此測定政治氣候。《漢書》中的傳記文中也指出,古代君主要任命采詩官來檢測其政策的有效性。《尚書》中“詩言志”的表述成為后來經常引用的權威論點,即詩歌是政治性和群體性的,而非是情感和個人的表述。至于詩歌的用途,在諸如《左傳》和《國語》的歷史材料中均清晰地說明,君子應當熟諳《詩經》,因為這是其高雅社會身份的象征。在復雜的辯論中,抽取有關的詩篇以及公認的闡釋進行引用成為這種論辯的組成部分。[14]
費維廉以《左傳》《國語》和《論語》等歷史文獻為參照,較清晰地言明了《詩經》經世致用思想對早期詩學社會功用觀所形成的巨大影響。
總體說來,漢學家們對于儒家詩歌功能觀的認識大都滲透著其對于中西文化和哲學的差異性理解,在分析中國詩歌的反映和表現問題時都或明或隱地參互進了對于“再現”這一源自西方詩學的理論范疇的體認。漢學家們在“再現”與“儒家詩歌功能觀”的話語闡述和意義表達方面的深層學理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1] Haun Saussy.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 宋柏年.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3] James Robert Hightower.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 [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4] 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5] 余寶琳.間離效果: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研究[J],1997.(2).
[6] Pauling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7] 高玉.論中西比較詩學的“超越”意識[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7).
[8] Steven Van Zoeren.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Pre-Modern Theories of Poetry.1994.
[9] Raymond Dawson.Confucius.New York:Hill and Wang,a division of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1.
[10] Helena Wan.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Confucius. PhD Dissertation,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Ann Arbor,Mich:UMI,1980.
[11] Martin Kern.Early Chinese Poetic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nuscripts,Recarving the Dragon:Understanding Poetics.Prahue:The Karolinum Press,2003.
[12] Graham Sanders.Words Well Put:Vision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4] Craig Fisk.Literary Criticism[A].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M].William H.Nienhauser,Jr.Editor and compil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責任編輯:潘文竹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Poetic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XU Bao-fe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The sinolog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poetic func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theory. Both the acceptance and adaptation of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on"theory by James Liu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by sinologists like Eugene Ouyang display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poetic function. While analyzing the refl ections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poetry, they overtly or covertly embody an idea of the "representation"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poetics.
Sinology; representation; Confucius; poetic function
I207
A
1005-7110(2014)01-0075-05
2013-10-07
本文為北京語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為13YBG34)的階段性成果。
徐寶鋒(1974-),男,河北承德人,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漢學、中國文化與詩學。
①在這里,劉若愚引述了《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忍,其民困”,并將之與《詩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加以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