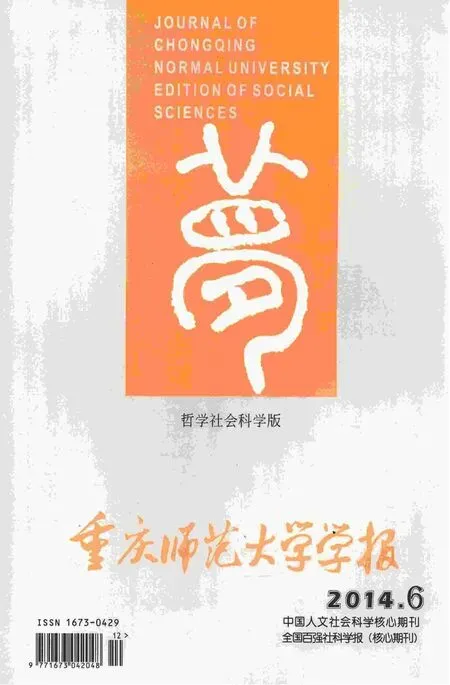戰國秦漢即墨形勢的海洋地理學分析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北京100872)
即墨與臨淄、平陸曾經并稱“三齊”,史籍可見“臨淄”“即墨”并說,“瑯邪”“即墨”并說情形,也顯示出即墨在齊區域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戰國秦漢人言齊地資源與經濟實力,有“東有瑯邪、即墨之饒”的說法。就此有“二地近海,財用之所出”的解釋。即墨“實表東海”,是依托海洋條件取得“三齊”形勝的地位的。即墨的優越地位和特殊形勢,體現出齊人海洋開發的成就。
一、“三齊”說與即墨的地位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記載項羽滅秦后分封十八諸侯事,對于齊地的控制,采取如下措施: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史記·項羽本紀》)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句下,裴骃《集解》:“徐廣曰:‘都即墨。’”可知即墨有與臨菑相近的地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項羽本紀》又記載: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殺擊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史記·田儋列傳》)
田榮隨即據“三齊”實力發起變亂,沖擊項羽主宰天下的地位。“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余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余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愿大王資余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余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余迎故趙王歇于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余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征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在這一形勢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項羽不得不“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回救。(《史記·項羽本紀》)
“三齊”地方的實力,曾經可以與項羽抗衡。注意“三齊”的說法,可以理解“即墨”的重要地位。
關于“三齊”,裴骃《集解》:“《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對于所謂“三齊”,又有其他的理解,如張守節《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元〕于欽《齊乘》卷一《沿革》)清人朱鶴齡《禹貢長箋》卷三寫道:“愚按古稱‘三齊’者,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取張守節《正義》說。雖然對“三齊”的解說或有不同,“即墨”往往位列其首。
二、“臨菑”“即墨”并說的意義
《戰國策·齊策一》記載張儀對齊王施行恐嚇的言辭,其中說到了齊地都市“臨淄、即墨”: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熟計之。
前引《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司馬貞《索隱》:“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張守節《正義》:“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也。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后太公封,方五百里。’”
清人曹學詩《擬蠲免錢糧謝表》有“問風俗于臨淄、即墨,有魚鹽表海之雄”[1]句,應是體會到了“臨淄、即墨”“有魚鹽表海之雄”的特殊的經濟實力。清人徐震《樂田演義》也寫道:“齊乃大國,臨淄、即墨,兵甲眾多,不易剪滅。”[2]則強調了其政治軍事地位的重要。
“臨淄、即墨”并說,后來成為語言習慣,亦反映兩地形成鮮明文化共性的情形,如所謂“海以東多逋逃,渠耽耽臨淄、即墨之饒而狡焉思逞者爲憂”[3]言其地之“饒”,又如所謂“夫臨淄、即墨,諸槍手、礦人多奸俠亡命伍也”[4],則言地方治安隱患。
三、“瑯邪、即墨”并說的意義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均“瑯邪、即墨”并說。亦見《前漢紀》卷三《高祖三》、《宋書》卷三六《州郡志二·青州》、《資治通鑒》卷一一“漢高祖六年”等。
唐人柳宗元《賀中書門下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遂使瑯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柳河東集》卷二九)同樣并列“瑯邪”和“即墨”。
“瑯邪、即墨”的表述方式,體現“即墨”和“瑯邪”曾經具有相近的地理形勢和經濟水準。《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顏師古注:“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指出“瑯邪、即墨”作為相互鄰近地方,形成了能夠以“近海”地緣關系為國家提供“財用”條件的經濟優越地位。
越王勾踐曾經徙治瑯邪。[5]“瑯邪”作為“四時祠所”所在,秦漢時期曾經是“東海”大港,也是東洋與南洋交通線上的名都。秦始皇東巡海上,在“瑯邪”有特殊的表現。“瑯邪”被看作“東海”重要的出航起點。[6]關注“瑯邪、即墨”并說的情形,有益于理解“即墨”的地位。
四、關于“瑯邪、即墨之饒”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云夢,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又為劉邦分析形勢: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田肯的意見得到劉邦贊同。“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瑯邪、即墨之饒”,顏師古注:“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資治通鑒》卷一一“漢高祖六年”:“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胡三省注也采用此說:“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可見,歷代史家多以為“瑯邪”和“即墨”的富足,經濟基礎在于“近海”的地理優勢,便利了海洋資源的開發。宋代學者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卷一〇《七國形勢考下·齊》也贊同這一意見:
田肯謂“瑯邪、即墨之饒”,顏氏云:“二縣近海,財用所出。”蘇秦說趙曰:“齊必致魚鹽之海。”
則更明確的指出“瑯邪、即墨”地方經濟的先進條件,主要是開發利用了海產“魚鹽”。
所謂“蘇秦說趙曰:‘齊必致魚鹽之海’”,應出自《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愿也。”
“蘇秦說趙”之辭所謂“齊必致魚鹽之海”,《戰國策·趙策二》的記載文字略異,寫作:
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
又《戰國策·齊策二》蘇秦說趙王語,也可見“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戰國策·趙策二》又有張儀策動連橫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太平御覽》卷九六六引《史記》,則蘇秦所說對象不同:“《史記》曰:蘇秦說燕文侯曰:‘君誠能聽臣,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關于齊的“魚鹽之地”,又可見《戰國策·齊策一》:“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托于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也。”齊王獻地,是屈從于張儀的恐嚇。前段文字敘說了緣由,其中說到“即墨”:“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熟計之。”
五、田單據即墨抗燕的海洋地理學理解
田單抗擊燕軍進犯,據即墨一城,最終扭轉戰局,成功復國。《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于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史記》卷八〇《樂毅列傳》:“齊田單后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于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史記》卷八二《田單列傳》:“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田單用火牛陣破敵,“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余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于莒,入臨菑而聽政。”
田單以即墨持久抗戰取勝,應有多種條件。如果從海洋地理學思路理解,或可從三個方面總結:
(1)即墨應有多年“魚鹽之利”經營而積累的充足的軍需物資和生活物資儲備。
(2)即墨面對燕軍的強攻,以背水的形勢持久守備,應利用了自身海上運輸和海上轉戰能力方面的優勢。
(3)即墨很可能有外島武裝策應以助支撐。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記錄了楚頃襄王時代一則有關楚擴張的政治寓言:“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余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昔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這位“好射”者與楚頃襄王談到對齊地的進取:“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此言“長城”,應是指齊長城。張守節《正義》:“《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余里,至瑯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筑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余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邪臺入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同時說到的“東莒”和“即墨”,正是燕軍伐齊,所謂“城之不拔者二耳”(《史記田單列傳》),“唯獨莒、即墨未服”(《史記樂毅列傳》)之最后兩處得以成功堅守的軍事據點。田單復國即因即墨,《史記》卷八〇《樂毅列傳》:“齊田單后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于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也寫道:“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清代學者陳景云《通鑒胡注舉正》寫道:“《史記》:田橫入海居島中。張守節《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杜佑《通典》云:海州東海縣田橫所保郁洲,亦曰郁洲,漢贛榆縣是。唐人皆以橫所居海島在海州。胡氏注既引《史記正義》之文,又曰《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得名,且并以愔亦嘗匿此地矣。按《北齊書》及《北史》皆云愔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齊神武令光州刺史搜訪以禮,發遣光州。隋改東萊郡。《隋志》云,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是愔匿即墨海島。史文明甚。至海州之地,此時方南屬蕭梁,愔不得越境至此。合《齊書》、《北史》及《隋志》考之,則田橫所居海島,自當以三《史》為是。”“田橫島”在即墨,可能正是由于有田單救亡復國史跡以為前鑒,劉邦對田橫居海島形式的武裝獨立,不得不心存疑懼。
六、膠東王都即墨
《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記載漢景帝三年(前154)“吳楚七國之亂”爆發,導致西漢王朝面臨嚴重政治危局: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關于齊地四國,“膠西王卬”,張守節《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十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濟南王辟光”,張守節《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扐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川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張守節《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膠東王雄渠”,張守節《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
宋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卷一〇《七國形勢考下·齊》“即墨”條寫道:“《郡縣志》: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本漢舊縣。田單守即墨,破燕軍,盡復齊地。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此。漢屬膠東,北齊并入膠水,隋復置,屬萊州。城臨墨水,故曰‘即墨’。”
漢武帝被立為太子之前,封膠東王。《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七年)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裴骃《集解》:“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少年劉徹為膠東王時,應當未曾就國。
七、即墨“實表東海”“流光千載”
元人于欽《齊乘》卷一《沿革》“大小二勞山”條寫道:“即墨東南六十里岸海名山也。又名勞盛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云: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即墨勞山是東海海濱顯著的地標。這座在航海者看來也許在某種意義上超過泰山的山峰,也象征著即墨在海洋開發史中的崇高地位。
乾隆《山東通志》卷二三《風俗志》:“即墨縣樵蘇為業,魚鹽為利,澹泊自足,不尚文飾,士好經術,人務耕織,禮義之風,有足稱者。”“魚鹽為利”是其經濟生活的主要特點。
元人秦裕伯《即墨先賢祠記》寫道:“即墨古城,實表東海。有美多賢,流光千載。”(《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藝文志十九·記上》)“表”有瀕臨的字義,也有徽識、標記的意思。
古代文獻中所見稱“實表東海”的還有其他地方,如:
廩丘。《水經注》卷二四《瓠子河》引王隱《晉書·地道記》
鄆。《王荊公詩注》卷二五《律詩》《送鄆州知府宋諫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營丘。明黃洪憲《碧山學士集》別集卷四《山東青州府莒州知州王紀時》(明萬歷刻本)
即墨以其在戰國秦漢時期的重要地位,與這些地方相比,絲毫也不遜色。
即墨確實“實表東海”。其“三齊”形勝的地位的取得,依托海洋地理條件和海洋資源優勢,也借助歷史悠久的海洋開發的成就。
即墨以“實表東海”的形勢,成為戰國秦漢時代齊人海洋開發的紀念性標志,在中國古代海洋探索史和海洋開發史上,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位置。
[1]〔清〕曹學詩.香雪文鈔[O].清乾隆刻本.
[2]〔清〕徐震.樂田演義(卷一)[O].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3]〔明〕劉理順.樂陵令張公榮薦序[G]//劉文烈公全集(卷八).清順治刻康熙印本.
[4]〔明〕王世貞.答虛齋王中丞書[G]//弇州四部稿(卷一二六)《文部》.明萬歷刻本.
[5]辛德勇.越王句踐徙都瑯邪事析義[J].文史,2010年1輯.
[6]王子今.東海的“瑯邪”和南海的“瑯邪”[J].文史哲,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