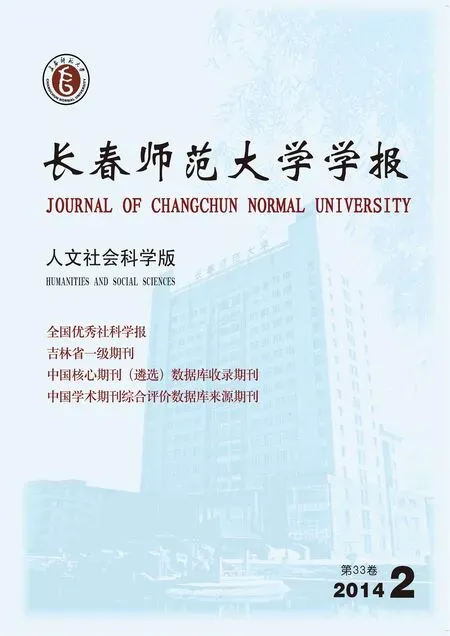從圖式理論角度論《葬花吟》英譯
潘華菊
(嘉興學院 外國語學院,浙江 嘉興 314001)
從圖式理論角度論《葬花吟》英譯
潘華菊
(嘉興學院 外國語學院,浙江 嘉興 314001)
本文對《葬花吟》三種英譯進行了比較,分析這些翻譯策略和手段在激活源語和目的語圖式方面的效果,從而得出結論,即譯者翻譯中國詩歌時刻應注意相關圖式的激活和建立,以實現譯者傳播文化的橋梁作用。
圖式;葬花吟;翻譯策略;原文;譯文
《葬花吟》是《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十分重要的一筆,其文辭優美,手法嫻熟,音韻鏗鏘,承載著深厚文化意蘊的典故。其通行英譯本有三種,即楊憲益、戴乃迭合譯版,大衛·霍克斯譯版和許淵沖譯版(以下簡稱楊譯、霍譯和許譯)。
圖式理論最早由德國哲學家 Kant 在 1781 年提出。英國心理學家F. C. Barlett 成為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對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釋取決于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圖式。一般說來圖式可分為以下三類:(1)結構圖式或體裁圖式,指的是文章的體裁特點,如詩歌、散文、議論文、說明文等;(2)語言圖式,通俗地講就是平常所說的詞匯與語法;(3)內容圖式,是以文本的內容以外的語言、背景知識為主要內容建立起來的知識記憶。可以說每種圖式都參與到翻譯實踐活動中。本文分別從圖式的三種分類在翻譯中的運用為出發點,對《葬花吟》風格各異的三種英譯進行比較分析。
一、結構圖式
《葬花吟》共有52句,前面8個詩節的押韻方式為aaba,第9節為abcc, 第10節為abbb,第11節為abab,第12節為aabc,第13節為abcb。這些押韻方式是譯語讀者所不熟悉、卻與源語相關的認知圖式。霍譯和許譯基本上都采用譯語讀者耳熟能詳的“英雄(偶句詩)體”(即aabb)的押韻方式,因此都有利于激活譯語讀者已有的關于目的語的相關結構圖式,并讓讀者體會到原詩的形音之美。而楊譯運用的是隔行押韻abcb,雖沒有采用原作的押韻方式,卻重現了原詩的音樂美感,從而通過激活譯語讀者的已有的結構圖式幫助讀者感受原詩的音美。
二、語言圖式
在許淵沖看來,“‘中國詩詞往往意在言外,英詩卻是言盡意窮’,并說過‘中詩的特點是朦朧,詩句往往沒有主語,讀者可以想象……’”這在《葬花吟》中得以充分體現。《葬花吟》上半部分有很多無主句,這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理解。如“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楊、許均把“來復去”的主語理解為“閨中女兒”本人,而霍處理為隱含的人。楊譯為“Hoe in hand she steps through her portal/Loath to tread on the blossom as she comes and goes”;許譯為“I step out of my portal with a hoe/On fallen petals could I come and go?”霍譯為“Has rake in hand into the garden gone/Before the fallen flowers are trampled on”。原詩黛玉是惜花、傷花、葬花之人。霍忽視了“英語主語突顯”這一特點,理解上也不正確,得出誤譯;楊、許在對原詩正確解碼的基礎上,根據英語主語突顯的特點,在譯詩中加上了適當的主語,使譯文讀者正確理解原詩。所以說,譯者須具備中、英詩兩套語言圖式,才能對原詩進行正確的理解,并根據目的語讀者習慣的語言圖式把原文的信息表達出來;否則很容易誤解原文,產生誤譯,進而誤導讀者曲解原詩。
三、內容圖式
錘煉字詞是中國詩歌的古老傳統。原詩的“紅消香斷有誰憐”一句中的“斷”字可謂點睛之筆。要譯好此句的關鍵在于傳神地譯出這一字眼。楊譯“that has been”和霍譯“hues bereft and bare”只是傳達了原句的大意,至于“斷”字所擁有的意境卻沒能傳達,不如許譯“die”到位傳神。“die”讓譯語讀者深深地感受到原詩賦予“香”以生命和黛玉的多愁善感,令讀者自然而然地體味到原詩所要傳達的凄美的意境。因此,許通過字詞的錘煉來激活讀者的已有認知圖式或即時建立新的內容圖式,從而讓讀者對原詩有最貼近的理解。
再看一例:“青燈照壁人初睡”(楊譯為“A green lamp lights the wall as sleep enfolds her”;霍譯為“And lays her down between the lamplit walls”;許譯為“A bed in dim-lit room when night is still”)中,“青燈”是指那種昏暗陰冷且蒼白無力的燈光,以此來襯托黛玉內心的蕭索與落寞。楊譯的“green lamp”有誤譯之嫌,與原詩有很大出入;霍譯直接省略了“青”字未譯,筆者以為這是明顯的欠譯(undertranslation);而許譯的“dim-lit”中“dim”一詞的添加準確地傳達了漢語“青燈”之“青”之意,讓讀者領略原詩的凄美并在腦海中構建相關圖式以備日后激活理解原文,堪稱佳譯。
《葬花吟》一詩借用了兩個典故:一是“灑上空枝見血痕”(楊譯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譯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許譯為“Like drops of blood turn bare branches red”),相傳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號“瀟湘妃子”;二是“杜鵑無語正黃昏”(楊譯為“Dusk fall and the cuckoo is silent”;霍譯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ngs no more”;許譯為“As twilight falls, the woeful cuckoos sing no more”),其中“杜鵑”即杜鵑啼血的典故:傳說蜀帝魂化杜鵑鳥,啼血染花枝,花即杜鵑花。看到這兩個典故,中國讀者腦海中的的文化圖式會立即被激活,幫助他們理解“血痕”與“杜鵑”所隱含的典故深意,而外國讀者由于相關文化圖式的缺失,往往會覺得不知所云。楊譯、霍譯既沒有文外加注,也沒有文內作解。雖然保證了譯詩的可讀性與流暢性,卻未能傳達原詩悲切凄美的意境,剝奪了譯語讀者學習、體味源語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的機會與權利,不能幫助讀者新建相關的文化圖式。而許在“灑上空枝見血痕”譯文中添加了“turn…red”暗示黛玉淚灑花枝,把花兒染紅,正是對典故的解釋說明;在“杜鵑無語正黃昏”譯文中增添了“woeful”來修飾“cuckoos”,表達了黛玉孑然一身,悲嘆自己孤苦無助的處境。這種增詞翻譯填補了原文中文化缺省形成的意義空位,為譯語讀者建立新的認知圖式,使其正確理解原文。
四、結語
《葬花吟》三種英譯風格各異,相比之下:楊譯注重內容的忠實,追求形式,用詞準確;霍譯更注重音形的追求,有時不免會因音形害意,但總體上并不脫離原作,讀起來朗朗上口;許譯則注重音美、形美,可謂傳神之作。總之,各有千秋,均堪稱佳作。
翻譯是語言轉換,更確切地說是文化轉換。文化的共性使轉換成為可能,文化的個性決定轉換不可能完美。文化的個性形成文化差異的鴻溝,譯者的使命就是架設跨越鴻溝的橋梁。而認知圖式正是支撐該橋梁的支點。譯者的譯文應有益于激活讀者的已有圖式,并且為讀者建立相關的認知圖式,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學習源語的文化知識。
[1]Bartlett, f.c. Remember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2]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Group Ltd, 1980.
[3]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4]曹雪芹,紅樓夢 [M]. 長沙:岳麓書社,1987.
[5]張智中,許淵沖與翻譯藝術[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013-12-07
潘華菊(1980- ),女,江西鷹潭人,嘉興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碩士,從事翻譯實踐與教學研究。
H315
A
2095-7602(2014)02-00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