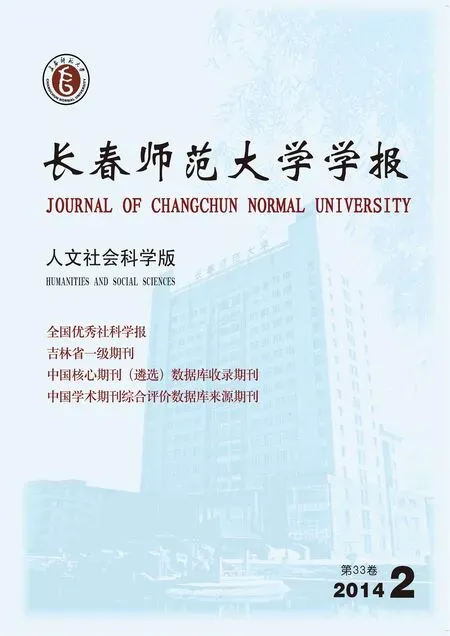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字”、“詞”關系芻議
——“字本位”理論的優勢與不足
崔金濤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字”、“詞”關系芻議
——“字本位”理論的優勢與不足
崔金濤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字”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核心,但隨著西方語言學的傳入,“字”及其研究日益被邊緣化。徐通鏘先生的“字本位”理論有助于徹底扭轉這種局面。“字本位”在成功避免了切分“語素”或“詞”的窘境的同時,也過于輕率地否定了“詞”在漢語中的客觀存在。作為漢語的基礎性結構單位,單音節的“字”可以通過語音、語義兩種途徑來構造雙音節或多音節的“詞”。
“字”本位;“字”;“詞”;語音構詞和語義構詞
“字”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中心問題。對“字”的研究通常稱為“小學”,具體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個部分。自西方語言學傳入以來,“字”從語言研究的中心退到了邊緣,僅被作為純粹的文字形體來看待。①隨著“字”喪失了作為一級語言單位的資格,傳統“小學”,除了“音韻學”仍然被看作是語言學之外,“文字學”和“訓詁學”均被冠以“語文學”或者“文獻學”之類的名目,從而基本上被排除在了語言學的研究之外。這種情形一直到已故著名語言學家徐通鏘先生正式提出“字本位”的語言理論之后才有所改變。徐先生還“字”以語言學的資格,我們深表贊同,因為這樣有利于中華本有語言學傳統的繼承,有利于更好地解決目前漢語學界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諸多困難。但首創者難為功,作為一種新生的理論,“字本位”本身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不足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字本位”包羅甚廣②,這里只選取“語言單位”一個角度,對這一理論的優勢、不足及其解決之道進行分析,以求解剖麻雀,以見全體之效。以下就從這三個方面展開相應的討論。
一
“字本位”理論在“語言單位”方面的最大優勢在于:它較好地避免了“語素”與“詞” 切分的窘境。按照目前最通行的說法,“語素”指“最小的音義結合體”,“詞”指“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的音義結合體”。僅從定義上看,二者作為語言單位的特征非常明顯,但事實上,不論是“語素”還是“詞”,在漢語中都不是一望而知的,因而需要一些嚴密的操作方法來“發現”,諸如所謂“替代法”、“插入法”(或稱“擴展法”)、“剩余法”者即是。從可操作性的角度來衡量,目前學界對“語素”和“詞”的界定就顯得不夠明確,也不甚經濟。在形態較為發達的印歐系語言里,“語素”的發現通常是比較容易的,只要將某一詞匯的原形(如book)與其相應的語法形態(如books)進行比較,就可以較為簡單地把一些不成音節的“語素”(如-s)離析出來。至于“詞”,那就更容易尋找,比如在英語中,只要一組相連的音素具備一個明確的主重音,就可以判定它是一個“詞”。但是反觀漢語,確定一個“語素”或“詞”卻并非這樣容易。例如,普通話中常見的“兒化”現象,其中的“兒”并不代表實際的音節或音素,而僅僅是一個卷舌的標記。盡管我們知道,“面”絕不是“面兒”、“粉”也不是“粉兒”,但在“面兒”和“粉兒”中卻找不到一個相當于了“兒”的音素。至于“詞”的切分,更是要比“語素”復雜得多。首先,我們在運用某一標準切分“詞”時,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例外。比如在“鴨子”這個結構中的“鴨”不能單用,“子”也不能單用,所以“鴨子”是“詞”,但又存在著諸如“鴨蛋”、“鴨肉”、“鴨血”、“鴨舌”、“鴨掌”、“鴨胗”這樣一系列的形式,但似乎沒有哪位學者認為這些含有“鴨”的組合形式是“詞”,似乎也沒有那一本權威詞典收錄過這樣的“詞”。其次,就是某一結構符合此一標準,卻不合彼一標準,這樣便出現了不少兩難的情況,比如“道歉”,其中的“道”和“歉”都沒法單用,所以根據自由與否的標準,“道歉”應該是詞,但是“道歉”中間又可以插入諸如“一次”、“兩次”這樣的數量結構,而按照是否可以插入成分的標準(即所謂是否可以“插入”或“擴展”的標準),“道歉”又絕不是“詞”,于是便發明了“離合詞”的概念來彌合這種矛盾。
相對于“語素”和“詞”切分面臨的這種窘境,“字”是絕對清晰可辨的,根據徐通鏘的定義,“字”的最基本特點是“1個字·1個概念·1個音節的一一對應”③。由于漢語的音節結構非常簡單,再加上貫穿整個音節的聲調的作用,這種三“1”對應的格局使“字”在漢語非常容易切分、辨認,基本不存在模糊不清的現象。如果我們拿一段話給一個沒有受過語言學訓練的漢族人,問他其中有多少個字,恐怕沒有誰會回答不出來。但是如果我們問他其中有幾個“語素”或“詞”,答案十有八九是不知道或者言人人殊。因為,這樣的問題,恐怕連大學中文專業的學生也未必答得上來。只要我們聯想自己學習或升學的經歷,都會記起這樣一種頗為尷尬遭遇:我們經常拿不準一句話里究竟有幾個“詞”或“語素”。可見,對于以漢語為母語的漢族人來說,“字”是一個遠要比“語素”和“詞”來得現實得多、也確定得多的“語言單位”,當然選擇“字”作為漢語描寫和解釋的起點,也會比用“語素”或“詞”來得可靠得多。
母語者的語感是否能夠作為檢驗語言學理論合理性的標準?起初,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Bloomfield)在論及類推現象時曾經指出:“一個正常的說話人,并不是一個語言學家,不會去描寫他的言語習慣,而且如果我們愚蠢得竟然去追問他,他也決不可能說出正確的條理來的……我們隨時得記住,說話人缺乏高度專門化的訓練,是不會描寫他們的言語習慣的。”[1]布氏這種否定母語者語感在語言描寫中的地位、強調專門化技術作用的觀點,發展到了后期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家那里,就產生了對描寫技術的過度依賴,以至于出現了像布洛克(Bloch)那樣變亂日語“五十音圖”的極端事例[2]。這種所謂“全新”的“發現”,雖然在描寫主義語言學家那里獲得了熱烈的歡呼,但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于單純依賴語言描寫技術的深刻懷疑:究竟是某一語言的母語者的語感正確?還是某種僅僅依賴描寫技術而得到的“科學結論”更正確?隨著喬姆斯基(Chomsky)學派的興起,這些重要問題已經有了比較確定的答案,在生成語言學家那里,母語者的語感再一次成了檢驗某一語言學理論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尺,而語言學的中心任務也從利用技術程序去“發現”某種陌生語言的結構系統,轉到了如何更好地說明和解釋母語者的語感上。
二
“字本位”理論在“語言單位”方面最顯著的不足是,在強調“字”的基礎性地位的同時,簡單取消了“詞”這一級語言單位。應該說,徐先生這樣的處理缺乏必要的事實依據。
葉斯柏森(Jesperson)把語言中的形式分成慣用語和自由用語兩大類。對于“慣用語”的特點,葉氏指出,“語言中有些東西……具有慣用法的性質”,“慣用語……是怎么樣構成的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慣用語在語言的實感上必須永遠是一個不能作進一步的分解的,即不能像自由用語那樣可以分解的單位。”[3]根據葉氏的這段論述,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漢語中,不論古今,都存在同樣性質的單位,而雙音節或多音節的“詞”正好與之相當④。一般認為,古代漢語是單音節的“字”占絕對優勢的語言,但不容否認,其中也存在一部分雙音節甚至多音節的詞匯單位。《說文·玉部》:“玫,火齊,玫瑰也。”“玫”下緊跟“瑰”字,云:“瑰,玫瑰。”按,這是《說文》非常重要的一條體例,即如果是雙音節詞,則在組成該詞的前一個字下列出全詞,并注出全詞的意思,而后一字則僅把該詞寫出,不再做任何解釋。由此可知,對于許慎來說,“玫瑰”實在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雙音節詞,并不是“玫”、“瑰”可以拆開來理解的“字組”。《說文》是漢語文字學最重要的典籍,既然許慎設立了這樣一條條例,并貫穿全書,足見上古漢語中存在雙音節詞是不爭的事實。至于中古以后,漢語的詞匯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雙音化過程,其詞匯主體由單音節“字”變為雙音節“詞”,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更為重要的是,在現代漢語中,單音節的“字”在雙音節的“詞”(即葉斯柏森所說的“慣用語”的一種)中的組合能力與它在由“字”組成的“詞組”(即葉斯柏森說的“自由用語”的一種)中的相應表現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雙音節“詞”中,單音節的“字”具有非常強的組合能力,基本上只要意義允許,就可以和其他單音節的“字”組成具體某一個“詞”。例如“金”既可以在前組成“金光”、“金身”、“金色”,也可以在后組成“泥金、燙金、赤金”,而與之組合的“光”、“身”、“色”或“泥”、“燙”、“赤”,或為事物,或為動作,或涉及人類,或涉及非人的自然,實在無法從中找出某種規律,用以描述它們與“金”的相互選擇。但在句法層面,“金”一般不具有獨立活動的能力,我們通常使用“金子”或者“黃金”的說法。比如,我們可以說“樂羊子在路上撿到了一塊金子”,卻不能說“樂羊子在路上撿到了一塊金”。另外,在雙音節的“詞”和“詞組”中,單音節“字”的意義的組合方式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比如“打印”,盡管它含有“打”和“印”兩個“字”,而且二者都具備造句能力(如“打人”或“印卷子”),但“打印”的意思絕對不等于“打”加上“印”,這里“打”僅是“印”的一種方式或手段。又如“司機”,“司”的意思是管理或負責,“機”是機器、機械,但“司機”并不是管理機器之類的意思,而是指駕駛車輛的人。
綜上所述,漢語中多音節的“詞”和單音節的“字”都是客觀存在的單位,絕對不能由于強調“字”的基礎性地位,而主觀上無視“詞”的客觀存在。誠如周薦先生所說:“漢語的‘詞’誠然不同于西語的word,漢語中的‘合成詞’(或復合詞)固然迥異于西語中的compound,但是漢語中詞這一級單位及其下位單位的存在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宣布漢語中的‘詞’就是漢語中的‘詞’,不是西方語言的word;漢語中的‘詞’的所指就是漢語詞匯層次中的這一個。”[4]其實,即使是徐通鏘先生本人,在處理與雙音節或多音節的“詞”相關的語言現象時,也并沒有真正做到“去詞化”。在“字本位”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字組”(或“辭”)這樣的概念,而“字組”中又有“固定字組”一類。徐先生所說的“固定字組”正好相當于葉斯柏森所說的“慣用語”,也就是一般所說雙音節或多音節的“詞”。
三
如果既承認單音節的“字”在漢語結構系統中的基礎性地位,又堅持“詞”作為比“字”更高一級的多音節固定單位的合法性,那么就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由“字”到“詞”,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組合規律?
綜合前輩時賢的諸多相關探索,由“字”到“詞”的組合規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為語音途徑,一為語義途徑,可以姑且稱之為“語音構詞”和“語義構詞”。“字”作為一級語言單位,具有自己獨立的語音和語義,在構造上一級語言單位時,自然也就可以通過語音和語義兩種途徑來進行。
先看語音構詞。在討論語音構詞現象時,必須首先排除像“布爾什維克”、“咖啡”這樣的情況。眾所周知,這些看上去每個“字”都只有音節作用而無實在意義的所謂“單純詞”,實際上僅僅是假借漢字進行記音的產物,其根本性質屬于多音節的非漢語,根本不能作為討論漢語結構系統本質特征的依據。除去類似的音譯外來詞的情況,漢語的語音構詞可以再細分為分音和疊音兩個小類。所謂“分音”,指的是本來是“1個概念·1個音節對應”的1個“字”,由于漢語音韻結構的變遷,為了適應演變后的音節結構而分化成了雙音節的“詞”。例如“尋”,本“徐林切”,平聲侵韻,以m收尾,義為“尋覓”,如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以前)所志,遂迷,不復得路”。隨著咸、深二攝并入山、臻二攝,閉口韻在漢語普通話中已經不復存在,所以為了適應新的音節結構,“尋”字分音而為“踅摸”(音xué ·mo,義為“尋找”),原本作為韻尾的m獨立成為一個音節mo。又如“沓”,本“徒合切”,入聲合韻,以p收尾,義為“多言”,如《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孟子》所引之《詩》,出自《大雅·板》。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由此可知,孟子所說“沓沓”亦為“多言”之義。隨著入聲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消失,為了適應新的音節結構,“沓”字分音而為“嘚啵”(音dē ·bo,義為“絮叨、嘮叨”),原本作為韻尾的p獨立成為一個音節bo⑤。所謂“重疊”可以有完全重疊、部分重疊兩種。完全重疊者自古有之,如《詩經·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其中“關關”二字即模擬雎鳩鳥雌雄和鳴之聲,故朱熹《詩集傳》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又《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集傳》云:“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可見“丁丁”、“嚶嚶”都是擬聲詞。部分重疊者亦自古有之,如《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集傳》:“窈窕,幽閑之意。”可見“窈窕”是摹狀的疊韻聯綿詞。又《邶風·谷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陸德明《釋文》:“黽勉,猶勉勉也。”孔穎達《正義》:“言己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陸德明說“猶勉勉”、孔穎達說“黽勉然”,可見“黽勉”是表示勉力而為之情狀的雙聲聯綿詞。
有關語義構詞,漢語學界一般都在“構詞法”的名目下進行討論。因為較為常見,不做過多分析,這里只是指出“構詞法”研究的一些主要問題,以供學界同仁參考。首先,根據“構詞法”對漢語的復合詞進行分析,一般并不能順利地預知其真實意義,上文所述的“打印”、“司機”就屬于這種現象。現代漢語中有“溫床”一詞,義為“對某種事物產生和發展有利的環境或重要條件”。這一意義并不是“溫”、“床”意義的簡單相加,而是中間經過了若干次隱喻之后才最終形成的。又如“墨綠”,義為“深綠色”。“墨”作為一個名詞性的成分充當“綠”的修飾成分,但是這種普通名詞作狀語的結構,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具有句法上的能產性,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無法直接說“墨綠”就等于“墨”加上“綠”。其次,單音節的“字”在構造雙音節或多音節的“詞”時,未必采用其常用義項。如“馬”,作為一種動物,廣為人知,而它的另一個義項“大”卻很少有人注意,但恰恰是這個義項構成了兩個相對較為常見的雙音詞:“馬蜂”和“馬勺”。《爾雅·釋蟲》:“蝒,馬蜩。”郭璞注云:“蜩中最大者為馬蜩。”足見“馬”之有“大”義,其來有自⑥。又如“國”和“家”作為“國家”和“家庭”的意義,非常常用,但作為“諸侯國”和“卿大夫的采邑”,卻非常生僻,所以本來是聯合式的“國家”也就經常被理解成了只有“國”而沒有“家”的偏義復詞。
以上所論,僅是個人管窺蠡測的一得之見,之所以不揣固陋拿出來討論,正是想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以激起學界有關“字”本位語言理論的興趣,從而使這一可貴的語言學探索不會隨著徐通鏘先生的過早去世而衰歇,它豐富的理論意義與潛在的實踐價值理應得到充分的顯露與發揮。
[注 釋]
①其實當我們追問,漢字作為一種純粹的形體符號何以也具有語音、語義時,答案恐怕只有一個,就是它記錄的漢語中的那一級語言單位帶給它的。因此,即便把“字”局限在文字形體這樣一個狹窄的領域內,也根本無法否認在漢語中存在一級“字”所記錄的語言單位。事實上,自甲骨文以來,漢字作為一種文字系統的性質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一直沒有改變。
②在徐先生提出“字本位”理論之后,漢語學界和理論語言學界都提出了不少質疑和批評。平心而論,在這些質疑和批評當中,有不少帶有想當然的色彩,比如說徐先生分不清語言單位和書寫單位的基本界限,顯然就并不符合徐先生本人的原意。另外,作為一種全面研究漢語所有現象的語言學理論,“字本位”涉及了從書寫系統到語音、語義、語法,乃至修辭、語言心理等諸多層面的語言事實。因此,僅從漢語的某一現象(比如語法上的“自由”與否)入手,是根本無法徹底否定這一理論的合理性的。
③有關“字”的定義,徐先生自己有過不同的提法,這里采用的是《說“字”——附論語言基本結構單位的鑒別標準、基本特征和它與語言理論建設的關系》(《語文研究》1998年第5期)中的觀點。
④按照目前通行的說法,“詞”既可以是單音節的,又可以是多音節的。由于我們承認單音節“字”的基礎性地位,那“詞”理應指非單音節(也就是雙音節或多音節)的那些固定單位。
⑤有關“沓”與“嘚啵”的關系,俞敏先生亦有簡說。詳細情形請參看《俞敏語言學論文二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第53頁的相關分析。
⑥《爾雅》所謂“蜩”,即后世所說的“蟬”,所謂“馬蜩”就是個體較大的蟬。今北京周邊稱較大的蟬為“馬嘎”(音),當為古語詞之孑遺。
[1]布龍菲爾德.語言論[M].袁家驊,趙世開,甘世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501-502.
[2]王洪君.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8-30.
[3]葉斯柏森.語法哲學[M].何勇,夏寧生,司輝,張兆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5-22.
[4]周薦.論詞的構成、結構和地位[J].中國語文,2003(2): 148-155.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WORD: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ZI-based Theory
CUI Jin-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ZI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but ZI and its research ar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Mr. Xu Tongqiang's ZI-based theory helps to completely reverse this situation. ZI-based theory manages to avoid the segmentation dilemma of MORPHEME or WORD, but simply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WORD in Chinese. As the basic structure unit of Chinese, ZI(one syllable expresses one meaning) can construct WORD(two syllables or more syllables express one meaning) by two ways of phonetics and semantics.
ZI-based theory; ZI; WORD; phonetic word-formation and semantic word-formation
2013-12-21
2010年新世紀廣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一般項目(2010JGA094)。
崔金濤(1977- ),男,河北香河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從事訓詁學、經學和對外漢語教學研究。
H14
A
2095-7602(2014)02-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