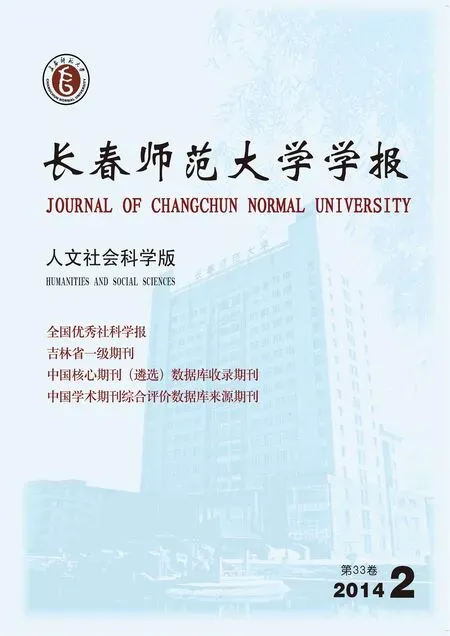論張曉風散文語言的動感藝術
詹秀華
(電子科技大學 中山學院,廣東 中山 528400)
論張曉風散文語言的動感藝術
詹秀華
(電子科技大學 中山學院,廣東 中山 528400)
作為臺灣著名的散文大家,張曉風是一位“以動寫靜,化美為媚的能手”,其散文語言不僅富有古典美、色彩美、音樂美,而且充滿強烈鮮明的動感,形成一種撲面而來、讓人印象至深的動態美。她特別講究動詞的運用,其動詞不僅用得精、巧,并且動量足、氣勢豐沛。此外,她大量運用擬喻,并配合通感、夸張等多種修辭手法,展示的不僅是自然景觀的靜態的外在之形,更令自然之物充滿張揚飽滿的生命精神,散發出獨特的動感魅力。
動感;擬人;通感
張曉風是臺灣著名的散文大家,她的散文不僅有著獨特的詩性感悟[1]、極高的文化藝術素養,在語言的運用上也富有創造性。其散文語言不僅富有古典美、色彩美、音樂美,而且充滿強烈鮮明的動感,形成一種撲面而來、讓人印象至深的動態美。其散文中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無不充滿豐沛的生命活力。正如學者樓肇明所說,“她是一位以動寫靜,化美為媚的能手,她筆下的自然美,幾乎無不具有一種氣勢逼人眼目,感知‘入侵人的肌體’的‘挑釁性’和‘侵略性’”[2]。她散文中的寫景狀物,非表面空泛的形容,非靜態的臨摹,非平凡客觀的寫實,而是深入傳神的刻畫,是靈動新奇、動態十足的表現,凸現了自然景物張揚飽滿的生命精神,散發出獨特的動感魅力。
為表現事物的動態美,張曉風靈活調動了多種語言表現手段。其化靜為動、以動寫靜的語言藝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妙用動詞,化靜為動
要表現事物的動態,最關鍵的莫過于動詞的運用,正如余光中所說,“景有靜有動,即使描寫靜景,也要把它寫動,才算高手……只會用形容詞的人,其實不懂寫景。形容詞是化妝師,動詞才是演員。”[3]張曉風在描寫自然山水時,總是把焦點放在動詞身上,通過動詞的妙用來營造景物的動態感覺。曉風妙用動詞的藝術手法主要有:
首先,發揮中國古典文學以動寫靜的藝術精髓,化敘為摹,化靜態的描寫為動態的敘事。這不僅可使靜景動化,且往往有“點石成金”之效,使一般動詞在表現上藝術化、陌生化。
(1)我轉身離去,落日在我身后畫著紅艷的圓。(《畫晴》)
(2)爬藤花看起來漫不經心,等開完了整個季節之后回頭一看,倒也沒有一篇是沒有其章法的——無論是開在疏籬間的,潑撒在花架上的,嘩嘩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調皮刁鉆爬上老樹,把枯木開得復活了似的……(《花之筆記》)
(3)小草莓包括多少神跡啊!如何棕黑色的泥土竟長了灰褐色的枝子,如何灰褐色的枝子會溢出深綠色的葉子,如何深綠色的葉間會沁出珠白的花朵,又如何珠白的花朵已錘煉為一塊碧澀的祖母綠,而那顆祖母綠又如何終于兌換成渾圓甜蜜的紅寶石。(《詠物篇》)
例(1)中,個“畫”字把落日寫動了,普通的一個字讓整個句子活了起來;例(2)中一連用了“開”、“潑撒”、“流下”、“淌”、“爬上”等動詞,爬藤花開的各種姿態寫得活潑靈動、生機勃勃;例(3)在頂真的句式里,連續變換運用“長”、“溢出”、“沁出”、“錘煉”、“兌換”等動詞,將枝而葉、由葉而花、由花而果的整個成長過程以及其間不同顏色的更迭寫得精確入微。
其次,大量選用幅度大、氣勢猛、量能十足的動詞,有意識地從速度、力度、氣勢等方面加大動量。這不僅強化了動態事物的動作感,也使張的散文在秀媚之中透出剛健猛勁,正如余光中所贊,“張曉風不愧是臺灣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挾風雷的淋漓健筆。”
(4)春柳的柔條上暗藏著無數叫做“青眼”的葉蕾,那些眼隨興一張,便噴出幾脈綠葉。(《詠物篇》)
通過一個“噴”字,本是緩慢而不顯眼的植物成長過程被強化為具體可見、速度飛快的動作,動感效果格外顯著。
(5)滿山的牽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沖擊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勢。(《秋天 秋天》)
(6)疾勁的山風推著我,我被浮在稀薄的青煙里。(《歸去》)
“沖擊”一詞不僅化靜為動,并且使本是柔美的花兒具有了如海浪一樣的強大力度。“推”寫出了山風的力度之強,“浮”則從反面襯托了勁風疾吹的效果。
(7)可是,等車不來,等到的卻是疏籬上的金黃色的絲瓜花,花香成陣,直向人身上撲來。(《情懷》)
(8)梅葉已凋盡,梅花尚未剪裁,我只能佇立細賞梅樹清奇磊落的骨格。不可想象的是,這樣寂然不動的巖石里,怎能迸出花來呢?(《常常,我想起那道山》)
“撲”強調了花香之濃郁和傳遞速度之快捷,“迸”字突出了梅花盛開的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強。動詞的精心選用使上述二例氣勢磅礴,動感十足。
二、且擬且喻,生發動感
張曉風的語言運用技巧超乎常人,在她的散文中幾乎所有常用的漢語修辭手法都有所涉及,但她最偏愛的手法莫過于比擬。她文中比擬之繁密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以致有學者命名為“藝術仿生學”[4]。它們或單用,或擬喻合用;或賦予自然生物以人的喜怒哀樂,或為無生命現象注入生機。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說:“詩人的聲音不是發自自然,而是給自然以呼吸,讓自然表達他的思想”,曉風正是這樣一位給自然以呼吸、與自然同呼吸的深情“詩人”。以詩為文是她散文最大的特點,在她看來,“煙嵐是山的呼吸”,“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揚起來的一聲歡呼”,“土地一定是有生命的”,“顏色也是有欲望,有性格甚至有語言有歡呼的”,她所夢想的花是“那種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聲喊醒的梔子,或是走過郊野時鬧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節逼得雨中行人連魂夢都走投無路的杏花,那些各式各流的日本花道納不進去的,市價標不出來的,不肯許身就范于園藝雜志的那一種未經世故的花”。整個天地自然在她筆下被飽注了精、氣、神,萬物在悠然自得地輕舞飛揚,充滿了勃勃的生命律動感。
(9)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云,一陣杜鵑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鵑花……(《春之懷古》)
(10)那時候,是五月,桐花在一夜之間,攻占了所有的山頭。(《花朝手記》)
雷可以惹哭云,花與鳥爭斗不休,桐花的盛開是對山頭的攻占……在曉風的筆下,觸目所及皆是生命的活潑與張揚,比擬的運用讓其文字充滿了強烈的動感。
除了單用擬人之外,曉風更多的是喻擬合用,二者的結合更增添了文字的威力。經濟簡短的文字迅猛出擊,“把對象徹里徹外地寫透寫足”乃至“寫到十二分”,讓人在感受其想象的奇特之外更感悟其強烈鮮活的動感。
(11)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萬戶的屋梁受盡風欺雪壓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春之懷古》)
(12)荒旱的沙磧上,因為一陣偶雨,遍地野花猛然爭放,錯覺里幾乎能聽到轟然一響,所有顏色便一剎間竄上地面,像什么壕溝里埋伏著的萬千勇士奇襲而至。(《矛盾篇之三》)
在這里,春天如被企盼多時的王師,所向披靡,趕走了肆虐多時的風雪,而桃花正是它的先頭部隊;沙磧野花的爭放有如伏兵瞬間奇襲而來,本是風花雪月的景致在曉風的筆下硬是寫出了“刀光劍影”,顯得“殺氣騰騰”。
三、巧寫幻覺,動化感覺
1.運用通感
人的心理感覺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當人們感知某一客觀事物時,不僅引發相應的感覺,大腦中原先貯存的來自其他感官的感知信息、經驗、記憶,經過想象和聯想,會自動對此感覺進行補充,并把一些沒有直接感知到的東西賦予它。這種基于經驗和習慣而產生的不同感官之間在心理上的相互勾通即為通感[5]。它不同于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往往呈現為一種心理上的幻覺,但這種幻覺有助于更真實生動地表達人們對客體的直覺和體驗。曉風在寫作中常利用通感,將視覺感受轉化為聽覺、味覺、嗅覺、壓力等多種感受,將個人的感覺經驗動態化,增強了寫景的動感效果。
(13)殘霞仍在燃燒著,那樣生動,叫人覺得好像差不多可以聽到火星子的劈拍聲了。(《歸去》)
(14)對了,就是這燦白,閉著眼睛也能感到的。在云里,在蘆葦上,在滿山的翠竹上,在滿谷的長風里,這樣亂撲撲地壓了下來。(《秋天.秋天》)
(15)陽光的酒調得很淡,卻很醇,淺淺地斟在每一個杯形的小野花里。(《魔季》)
例(13)中用“燃燒”把視覺感受轉化為觸覺體驗,并幻化成聽覺感受;例(14)中的“壓”字,讓本是視覺感受的燦白仿佛有了沉甸甸的壓力感;例(15)中的陽光如酒一樣淡卻醇香,將視覺形象幻變為味覺和嗅覺。多種感覺的并現帶來了表達上的生動鮮活。
2.變換視點,倒置主客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本是動態的審美主體,山水是靜態的被審美的客體。但曉風在寫景時,有意變換視點,倒置主客關系,寫出了一種奇妙的幻覺——自然幻化成主體,成了動作的主動發出者,人則退居成被動的客體,轉為靜態的動作的承受者,由此巧妙地將靜態的景物動態化了。
(16)而方才幻燈片上的山水忽然之間都遙遠了,那些絹,那些畫紙的顏色都暗淡如一盒久置的香,只有眼前的景致那樣真切地逼來,真把我逼到一棵開滿小白花的樹前。(《詠物篇》)
(17)船在長江上走,兩岸風景逼人而來簡直是一場美的夾殺。(《同色》)
(18)山從四面疊過來,一重一重的,簡直是綠色的花瓣……(《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例(16)中本是人走近花樹,卻變成景致把人逼向樹前;例(17)中,兩岸風景不僅逼人而來,且可以對人形成“一場美的夾殺”,兩個“逼”字具有同等的動感催化作用;例(18)中本是船動人動山不動,但用“疊”字卻寫出了人不動而山動如花盛放的美妙幻覺。
四、對比夸張,強化動感
對比和夸張乃是不同的修辭手法,對比涉及對照和比較的兩個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夸張只關涉被夸大的單一事物,但二者在表達效果上具有相似之處,即它們都對事物進行了強調和突出,通過加大其某一特性的程度使事物更加鮮明。曉風在寫景時,常對事物進行對比或夸張,有意加大動感的強度,予讀者更深刻的印象。如:
(19)有些美,如山間月色,不知為什么美得那樣無情,那樣冷絕白絕,觸手成冰。無月之夜的那種渾厚溫暖的黑色此刻已扯開。(《春俎》)
(20)兩側的山又黑又堅實,有如一錠古老的徽墨,而徵墨最渾凝的上方卻被一點灼然的光突破。(《春俎》)
(21)漫天的雨紛然而又漠然,廣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這樣一株紅蓮!像一堆即將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傾潑的顏色!(《雨之調》)
同樣是寫黑夜中的光亮,例(19)中在通感的基礎上進行了對比,“觸手成冰”“冷絕白絕”的月光硬生生地把溫暖的黑色“扯開”,生動地展示了月光進入夜色的力度和冷暖的對碰;例(20)中則比喻、對比兼用。夜幕下,如古老黑墨的山被“一點灼然的光突破”,在展現山色的厚重無邊與亮光的凝練耀眼的同時,強調了亮光切割夜色的艱難;例(21)中用“廣不可及”的灰來烘托一株蓮花的紅,用雨的“漠然”的來反襯紅蓮如“即將燃起的火”一般的熱烈,蓮花的卓爾不群躍然紙上。
(22)少年游獅頭山,站在庵前看晚霞落日,只覺如萬艷爭流競渡,一片西天華美到幾乎受傷的地步。(《花朝手記》)
(23)那年春天,波斯菊開得特別放浪,我站在花園中間,四望皆花,真怕自己會被那些美所擊昏。(《初綻的詩篇》)
(24)真的,山月如雨,隔著長窗,隔著紗簾,一樣淋得人兜頭兜臉,眉發滴水,連寒衾也淋濕了,一間屋子竟無一處可著腳,整棟別墅都漂浮起來,晃漾起來,讓人有一種絕望的驚惶。(《春俎》)
落日晚霞可以美到讓人“受傷”,花兒的美可以把人“擊昏”,山月如雨,可以把人連同屋子里的一切徹夜“淋濕”,以至讓人產生“絕望的驚惶”。如此極致的自然之美在敏感熱烈的曉風心里引起的強烈震撼,非夸張難以盡言。
五、活用詞性,表現動感
曉風不僅深諳動詞增動之效,精通中國古典文學的她還曉知詞性活用之妙。她曾經舉例分析過余光中散文中詞性代換的驚人之筆,對于余光中散文語言中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詞性的變化與互用,給予極力贊賞。在寫景中,她自己亦擅長詞性的活用,利用特定的語境將形容詞活用為動詞,藉此手法來表現事物的動感。如:
(25)那一樹桅子花復瓣的白和復瓣的香都留在不知名的籬落間,徑自白著香著。(《詠物篇》)
(26)典型的臺灣鄉間的景色,秧針綠在水田里,鷺鴛白在田埂上,小小的四合院隱在山阿里,青苔覆瓦,杜鵑躑躅在在山邊水湄。(《中庭蘭桂》)
例(25)中,“白”、“香”活用為動詞,并與名詞化的白與香相搭配,使得花兒的色與香濃郁襲人;例(26)中,“綠”、“白”活用為動詞,與下文的“隱”、“覆”、“躑躅”等動詞相呼應,一串漂亮的排比句讓臺灣鄉間景致躍然紙上。
(27)我一時為之驚愕駐足,那樣似開不開,欲語不語,將紅未紅,待香未香的一珠紅蓮!(《雨之調》)
(28)有時,一夜之間,花拆了,有時,半個上午,花胖了。(《詠物篇》)
例(27)中的形容詞“紅”與“香”活用為動詞,用“將紅未紅”、“待香未香”寫出了一種美在揭曉之前令人向往的神秘和奪目;例(28)中,一個“胖”字,形容詞用為動詞,幽默感十足地濃縮并動化了花開的過程。
綜上所述,強烈的動感是張曉風散文的突出特點,其散文以用好、用精動詞為核心,并調動起多種修辭手法,展示的不僅是自然景觀的靜態的外在之形,更發掘出自然之物內在的生命精神,充滿生命的動感。她的文字不是純客觀的外在景觀的描述,還是作者主體精神的觀照和外在投射。不僅用眼睛觀察、發現自然,更以心靈的直覺和想象去重組和再造自然,是曉風“以眼觀物”到“以心觀物”的自然結果,這使得曉風筆下之景,已非如實呈現的自然之景和一般的經驗感受,而是帶著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的對自然之景的變形,充分體現了文學語言的變異美。
[1]徐光萍.生命的箋注—張曉風詩性解釋散文解讀[J].江蘇大學學報,2003(12):79-82.
[2]樓肇明.張曉風散文論[J].文學評論,1994(1):106-117.
[3]李軍.語用修辭探索[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248.
[4]樓肇明.星約·情象·詩課[M]∥張曉風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371-397.
[5]李榮啟.文學語言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7.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Zhang Xiao-feng Essay’s Language
ZHAN Xiu-hua
(Zhongshan College UEST of China,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02, China)
As a famous essay writer from Taiwan, Zhang Xiao-feng is an expert at converting static state into dynamic state. Her essay’s language not only embodies classical beauty,polychrome beauty and musical quality, but also is full of impressive emotions. She express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verb, and utilizes plenty of rhetoric skills such as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synaesthesia and exaggeration. Her essay’s language not only shows the static state of nature, but also infuses new life and energy into natural things, so it is full of especially dynamic enchantment.
dynamic; personification; synaesthesia
2013-10-17
詹秀華(1969- ),女,江西婺源人,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講師,碩士,從事語言學研究。
I207.6
A
2095-7602(2014)02-0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