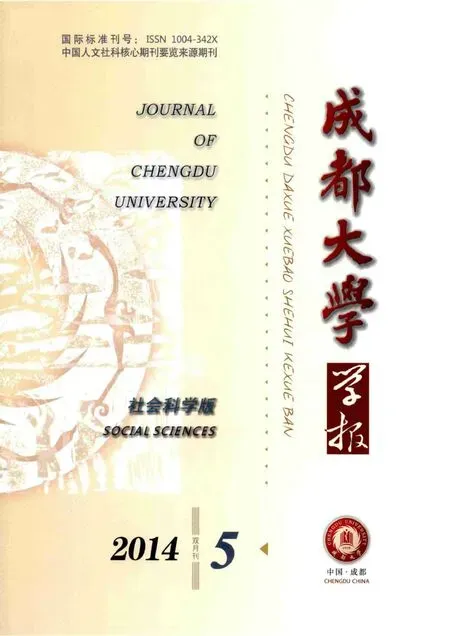文學翻譯系統中制約因素的圖式架構*
——基于對譯作生產與接受過程的描述
徐修鴻 鄧笛
(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鹽城224051)
文學翻譯系統中制約因素的圖式架構*
——基于對譯作生產與接受過程的描述
徐修鴻 鄧笛
(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鹽城224051)
翻譯是一項極為復雜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必然會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的來源、范圍與制約力不盡相同,卻通過作用于譯者,參與并影響著翻譯選擇的全過程。先前學界針對翻譯制約因素的研究往往存在視角選擇不夠科學、研究范圍不夠全面、理論框架不夠合理、核心概念不夠清晰等問題,嚴重地制約了翻譯研究的發(fā)展。選擇合適的研究視角,對譯作的生產與接受過程作出系統的描述,考察翻譯各階段存在的制約因素,厘清相關核心概念,并嘗試建立制約因素的圖式架構,為描述性翻譯研究提供更為綜合全面的視角。
文學翻譯;翻譯系統;制約因素
前言
翻譯是一項極為復雜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必然會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目前,國內外針對文學翻譯中制約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其一是基于以色列翻譯理論家基迪恩·圖里(Gideon Toury)的翻譯規(guī)范論對翻譯活動中那些被稱為“規(guī)范”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制約展開的研究;其二則是運用美國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改寫理論中的“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三大因素來討論翻譯活動中譯作對于原作的背離。上述兩種西方理論對于我們認識翻譯中的制約因素有著一定的幫助。然而,這些理論也存在自身缺陷,比如翻譯規(guī)范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規(guī)范”至今都沒有得到清晰、合理的闡釋,很容易誤導論者將翻譯中制約譯者行為的因素都看作“規(guī)范”;無獨有偶,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由于理論框架“仍然太粗略”,“不夠一致”,“只能指出著重文學的社會語境這個大方向,而無法指導深入的研究”[1]139-142。翻譯過程中的制約因素林林總總,豈是這三條就能概括?因而其三大改寫因素在闡釋翻譯現象的時候常常顯得捉襟見肘,缺乏應有的說服力,從而削弱了其理論的嚴謹性和適用性。
筆者認為,只有對譯作的整個生產過程進行描述性研究,依次考察翻譯的籌備階段、實際翻譯過程、翻譯完成前后的修改、譯作面市后的接受以及讀者和學術界對譯作的評判等過程中涉及到的制約,我們才有可能系統全面地研究翻譯活動中的制約因素。由于對譯作生產過程的描述是一項較為龐大的系統工程,就目前而言,據筆者所知,國內外尚沒有論者對此過程作出描述性研究。因而,筆者試圖通過客觀描述譯作生產和接受的全過程,厘清翻譯過程中不同階段存在的種種制約,從而嘗試性地架設制約因素的圖式框架,為描述性翻譯研究提供更為科學的視角。
一 翻譯研究視角的選擇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一古詩句反映了視角不同,對事物的認識就可能產生差異,由此可見研究視角的選擇對于事物本質的認識極為重要。一般說來,當前學界的翻譯研究視角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宏觀研究范圍的無限擴大化。研究者站在距離研究對象越來越遠的位置統觀全局,宏觀研究范圍無限擴大。但由于觀察距離太遠,許多相關因素無法得到細致的認識。比如說,當前的翻譯研究涉及越來越多的學科,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翻譯研究現在已經意味著研究和翻譯有任何關系的任何東西”[2]1,翻譯研究范圍越來越廣,但由于距離太遠,翻譯過程中的許多細節(jié)無法得到細致的研究。
其二則是微觀研究對象的無限細化。研究者的視角距離研究對象很近,猶如手持“放大鏡”,近距離觀察翻譯行為,微觀研究對象無限細化,片面夸大某種因素的支配作用。當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翻譯研究中出現的泛意識形態(tài)化傾向,由于勒菲弗爾把原本屬于文化范疇的內容一股腦地納入了對意識形態(tài)的討論,以致產生了意識形態(tài)無處不在的結果。[3]68在其理論的指引下,不少論者將意識形態(tài)的分類無限細化,其指涉范圍無限擴大,結果翻譯中任何行為都成了意識形態(tài)支配下的產物,使得翻譯研究出現一邊倒的趨勢,非常不利于翻譯研究的后續(xù)發(fā)展。
筆者認為以上兩種研究視角都不利于翻譯研究的發(fā)展。科學的翻譯研究應該是長短視距的有效結合,首先選擇合理的研究范圍,然后再對范圍內的研究對象展開細致的分析,這樣才能對翻譯活動獲得系統、深刻的認識。由于制約因素或蟄伏或活躍于譯作的生產與接受過程之中,因而,將研究視角架設在此過程之上,必然有利于增強我們對翻譯活動的認識。
一般說來,一部文學作品經由翻譯進入目標語語境,大多需要經歷翻譯準備階段、實際翻譯階段、修改階段和完成階段。譯作每經歷一個不同的階段,都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約,最終發(fā)生偏離原作的現象。文學翻譯的基本過程和參與對象可以參考下面的流程圖。

圖S1:文學翻譯流程圖
二 系統內容與范圍的界定
在研究視角確定之后,下一步需要確立的就是研究內容與范圍。筆者認為翻譯中的制約因素分別來自于三個涵蓋范圍和優(yōu)先等級不同的系統之中,根據其所涵蓋內容和范圍的大小,筆者依次將他們稱為微系統、中系統和大系統,其基本構成可以參照下方的示意圖。

圖S2:文學翻譯系統的內容與范圍
從該模型可以看出,文學翻譯系統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處于模型最內部的是由原作、譯者和譯作構成的微系統。在這個相對封閉的微系統模型中,譯者構成了聯系原作和譯作的唯一媒介,原作與譯作跟譯者之間保持著單向線性關系。在此系統中,影響著翻譯選擇的因素主要局限在譯者和原作方面。在微系統的外圍是中系統,包含個人、群體、機構等直接或間接象征權力和標準的因素,中系統將微系統緊密包圍,并且通過作用于譯者施加其影響力,從而間接地影響著譯作最終的風格和面貌。處于模型最外側的是大系統,包含來自文化、社會甚至整個世界的因素。由于大系統包含了我們物理世界中所能認知的一切因素,因此可以認為它是翻譯研究的最大載體和最后歸宿。從譯作的生產過程來看,由于微系統中直接包含生產者(譯者)、生產原料(原作)以及生產產品(譯作),要素之間聯系緊密,相互影響頻繁,因此可以視為翻譯系統中的內部系統。微系統外部的中系統和大系統,由于其涵蓋范圍巨大,且距離譯者相對較遠,對于譯者的影響也變得相對間接,因此可以視為翻譯系統中的外部系統。以此為依據,筆者將在之后的論述中將來自微系統的制約視為內部制約,而將來自中系統和大系統的制約看作外部制約。
三 文學翻譯系統中的制約因素
譯者的翻譯活動從來都不是在真空狀態(tài)下進行,必然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制約。這些制約既有來自微系統的內部制約,也有來自中系統與大系統的外部制約。內部制約主要來自譯者和原作,其中來自譯者的制約主要集中在闡釋能力、價值體系、文學修養(yǎng)和美學偏好方面;而來自原作的制約則主要體現在詞匯、句法、語義和修辭等方面。外部制約則分別來自于群體、組織和社會,源自群體的制約主要來自讀者群和研究界,來自組織的制約則體現在委托方、出版方和第三方權威方面,而來自社會的制約則涉及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多重因素。以下是文學翻譯中制約因素構成的拓撲圖。

圖S3:文學翻譯中的制約因素
(一)內部制約:來自譯者
1.闡釋能力
根據德國闡釋學派代表人物伽達默爾(Gadamer)觀點:“一切翻譯已經是闡釋,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4]62譯者的闡釋能力體現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其一是譯者的認知能力,其二是譯者的表達能力。前者決定了譯者認識原作的能力,后者則決定其反映原作內容的能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需要對原作信息進行解讀,倘若譯者語言或文化認知能力不足,便極有可能出現讀不懂原作語言或者無法理解原作文化的情況,更不用說準確表達原作的內容和意義了。譯者的闡釋能力建立在自身儲存的語言文化信息以及先前積累的經驗之上,這些信息隨時接受譯者的調用,經過譯者的組織和整理,最終反映在譯作的文字和意義之中;與此同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會積累新的知識,并將其存儲在大腦的“信息庫”中。從某種意義上講,譯者儲備信息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闡釋能力的高低,而譯者闡釋能力的高低則直接關系到其是否能夠準確傳達原作意圖,是制約其反映原作容貌的關鍵因素。

圖S4:譯者的闡釋過程
2.價值體系
譯者的價值體系屬于意識形態(tài)范疇。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的價值形態(tài)猶如一股涌動的暗流,時刻會參與對原作的價值判斷。符合譯者和目標語讀者價值觀的地方,蘊含在譯者潛意識中的價值體系可能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之,則有可能與之進行抵觸,減損甚至抵消原作價值體系給目標語文化可能帶來的沖擊。譯者作為相對獨立的個體,都有著各自的價值體系,并應用其對原作作出價值判斷。當然,譯者的價值體系并非不受約束,除了受到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取向的影響之外,還受到當時翻譯界普遍接受的翻譯倫理的制約。芬蘭學者切斯特曼(Chesterman)認為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需要恪守翻譯倫理,保證差異雙方完成最大程度的跨文化交際[5]41。譯者的價值體系在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下會對譯作產生不同的影響。當譯者群體中翻譯倫理意識較強,翻譯環(huán)境較為嚴苛時,單個譯者的價值體系極有可能受到嚴格約束,其價值觀對譯作的影響極有可能趨于柔和,譯者便淪為“帶著枷鎖的舞者”,“隱身人”和“傳話筒”。反之,當譯者群體中翻譯倫理意識薄弱,翻譯環(huán)境較為寬松和包容時,若缺乏足夠的自律和來自譯界的監(jiān)督,譯者的價值體系極有可能如脫韁野馬般任意馳騁,此時的譯者便似乎擁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成為賦予原作“第二次生命”的叛逆者。在此過程中,翻譯界普遍信奉的翻譯倫理便成了約束譯者價值體系的關鍵因素。

圖S5:譯者的價值判斷
3.文學修養(yǎng)與美學偏好
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經由不同譯者翻譯的同一部文學作品,其譯作往往呈現出迥異的語言風格。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譯者不同的文學修養(yǎng)和美學偏好造成的。由于不同譯者文學修養(yǎng)不同,他們在語言的運用能力和表達效果上就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會滲透在譯作的字里行間,最終影響著整部譯作的語言表達效果與風格。因此可以認為譯者文學修養(yǎng)的高低也是制約譯者翻譯能力的一大內部因素。
此外,譯者的美學偏好也制約著其反映原作風貌。為了流芳百世,代代相傳,任何作家在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時候,都少不了對文采的追求。對于譯者而言,為了賦予譯作“第二次生命”,他們會孜孜不倦地嘗試著將原作的美感傳遞給目標讀者,某些譯者甚至嘗試超越原作,在翻譯的過程中添加個人的美學偏好。然而,不同的譯者審美能力不盡相同,他們在閱讀同一部原作時的理解和感受必然存在差異,再經過譯者的藝術加工之后,譯作必然會不同程度地偏離原作。理論上來講,和原作作者審美偏好比較接近的譯者更可能較為忠實地傳達原作的意圖和風格。不過,由于原作作者和譯者之間存在或大或小的時空距離,這種審美差異往往會被放大,“忠實傳遞”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越來越多“不忠”的譯文被引用在翻譯研究者的論文之中,經歷著從褒揚到貶損之間的一切可能。
(二)內部制約:來自原作
1.詞匯與句法
詞匯是構成語言意義的基本單位,其意義的準確傳達是重現原作風貌的前提條件。索緒爾(Saussure)時代曾經穩(wěn)固、確定的語言意義在德里達(Derrida)時代慘遭解構,變得模糊、飄渺。事實上,受限于當時的語言學研究,特別是詞典編撰的相對落后,構成語言的基本單位——詞匯的意義曾經顯得相對難以捉摸。然而,隨著語言學研究和詞典編撰方面的進展,詞匯意義的內涵和外延相對確定了,因而語言的意義也相對確定了下來,這就為翻譯的可行性提供了現實基礎。
不過,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的確會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詞匯和用法,這一方面可能由于詞匯的意義具有多樣性,另一方面則可能由于該詞匯承載了來自異域的陌生文化信息。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詞匯都會對譯者構成最為基本也是最為直接的制約。如何恰如其分地將這些詞匯的意義表達出來便成為了譯者的首要目標。
除了最基本的詞匯以外,原作的句法也會給譯者帶來一定的麻煩。由于原作的語言和譯作的語言可能分屬不同的語系,有著不同的句法規(guī)則,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一般說來,所屬語系的地理位置相隔越遠,則語言之間句式的差異越大,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需要對原作句式進行的改動就會越多。傳統對比語言學指引下的翻譯研究往往非常注重原作和譯作語言層面的對比研究,然而,在翻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語言層面的研究卻被認為是封閉的、保守的、甚至過時的研究手段而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擯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誤區(qū)。
2.語義與修辭
文學翻譯的過程中,除了詞匯、句法層面的表層制約以外,還存在語義及修辭層面的深層制約。和日常翻譯以及科技文本不同,文學文本出現的語言大多不僅僅具備表層意義,還具有深層次的聯想意義。特別是文學作品中會出現一定數量的形象性詞語、成語、諺語、典故、俚俗語等。它們受到源語文化的制約或為該文化所特有,譯者很難將其中包含的所有成分,從表層意義到深層內涵,全部地保留在譯文中。就這點而言,文學語言的語義比非文學語言更難把握,因此,譯者在面對文學語言的翻譯時,無疑會面對更多的挑戰(zhàn)和制約。
修辭是一種運用語言的學問,以準確、生動和修飾為目的[6]265。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者會大量運用修辭來增強文學作品的美感。而修辭則具有強烈的民族色彩,雖然有些具體的修辭手段是許多文化通用的,但也有很多修辭沒辦法從一種語言移植到另一種語言。在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會遇到諸如比擬、夸張、諧音雙關、幽默、回文、韻律等修辭方式。就目前而言,翻譯研究界普遍認為對于比擬、夸張這類修辭尚容易處理一些,然而對于諧音雙關、幽默、回文、韻律這一類只有源語語言才能構成的修辭,學界普遍認為是不可譯的。即便嘗試翻譯,譯者一般也只能在字形、字音、詞性、詞的結構、縮減、詞義更換等方面做些文章,幾乎無法做到重現原修辭所反映的形式與面貌。可以說,修辭是文學翻譯過程中來自語言層面對譯者影響最大的制約因素。
(三)外部制約:來自群體
1.期待視野
根據德國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姚斯(Jauss)的觀點,期待視野是指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yǎng)、理想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7]13。從譯作的接受過程來看,讀者是譯作最終需要面對的群體,也是出版方的利潤來源或者政治勢力拉攏的對象。讀者數量越多,則譯作的銷量越大,影響力也越大,出版集團可以借此收獲更高的經濟利益,政治集團則可以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與此同時,譯者也收獲更高人氣,抬高自身的身價。讀者的期待視野在接受主體自身的心理圖式的同化和順應過程中不斷變化和調整,因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讀者往往對譯作有著不同的閱讀期待,涉及譯作的題材、主旨和語言風格等因素。譯作的內容和風格如果能投合讀者的閱讀需求,則為譯作的成功奠定了群眾基礎。因而,譯者在選材和翻譯的時候都會充分考慮甚至主動投合讀者的期待視野,努力尋找自我與讀者之間的連接點,以便獲得讀者的認同與贊賞。不過,由于不同的讀者的期待視野不盡相同,即便是同一讀者,其期待視野總是隨著接受主體的認知過程而不斷變化和發(fā)展。因而,對于譯者而言,想成功把握住讀者的期待視野是一件“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事情。通常說來,譯者能夠顧及的只是當時在讀者群中占據主流地位的審美情趣,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適合所有讀者各種閱讀期待的譯作是無法存在的。當前的研究中有這樣一種論點:只要成功地關照讀者的期待視野,譯作便可以獲得成功。依筆者看來,作為讀者群中率先接觸原作的一份子,譯者能成功把握主流讀者的閱讀期待已實屬不易。加之翻譯過程中制約因素紛繁復雜,道路交叉曲折,譯者咬文嚼字、斟詞酌句,其難度與艱辛超乎常人想象。那種認為只要關照了讀者的期待視野,譯作便能獲得成功的觀點無疑顯得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了。
2.翻譯標準
譯作出版后除了面向普通讀者以外,還有可能面向一類特定的讀者。他們會對原作和譯作展開描述分析,研究譯者的翻譯策略,評價譯作的質量,并且參與制定一套旨在指導譯者的行業(yè)規(guī)范。這類特定的讀者就是翻譯研究學者,他們制定的行業(yè)規(guī)范就是翻譯標準,其目的是為了使翻譯活動成為一種有章可循的規(guī)范性活動。翻譯標準體現了一定時期翻譯界對翻譯活動的本質性認識,是一定時期大多數從事翻譯活動的專業(yè)人員所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
當然,不是所有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都有資格參與翻譯標準的制定,只有那些在翻譯研究界享有一定的聲望,并且掌握翻譯研究核心內容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參與翻譯標準的制定。古今中外,參與翻譯研究的論者不計其數,但能夠提出并制定了翻譯標準的論者卻寥寥無幾。而且,“翻譯標準并非是某個翻譯家隨心所欲地規(guī)定出來的,而是譯者、讀者間長期以來的某種默契的結果,翻譯家往往是發(fā)現了一些標準可以滿足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特殊要求,而不是純粹主觀地發(fā)明了這些標準,從而強加在讀者身上。”[8]12-14
一定時期占據主流位置的翻譯標準對譯者的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制約力,因為它不僅可以用來作為一定時期一定群體的譯者從事翻譯活動的規(guī)則和指南,還可以用來描述翻譯現象、評價翻譯文本質量。一般說來,翻譯標準對于初涉譯壇的譯者制約力極強,違背翻譯標準意味著譯者可能招致批評,甚至影響到譯者的后續(xù)發(fā)展。而對于在譯壇享有聲望的譯者而言,翻譯標準僅僅是一種參考,并非畫地為牢,即便違背翻譯標準,其違規(guī)行為往往被視為個人風格被容忍,很少受到追究。比如清代的嚴復,其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而他的諸多譯作,連最根本的“信”都沒能做到,不過,此舉對于嚴復在中國近代翻譯界的地位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從這層意義上來講,翻譯標準對于地位和影響力不同的譯者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制約力。由于來自翻譯標準的制約因人而異,且無法量化,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因而,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翻譯標準的制約力大小都將是一個高度模糊的概念,但翻譯標準的確可以對翻譯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制約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四)外部制約:來自組織
1.委托方
本文所涉及的委托方指的是任何委托譯者翻譯的組織或個人,它和勒菲弗爾提出的“贊助人”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亦有所區(qū)別。在勒菲弗爾的論述中,贊助人可以是諸如宗教集團、階級、政府部門、出版社、大眾傳媒機構,也可以是個人勢力。[9]17是“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學作品的產生和傳播,同時又可能妨礙、禁制、毀滅文學作品的力量”[10]176。筆者認為,勒菲弗爾的“贊助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過于寬泛,這必然導致研究中出現模糊性,結果就是翻譯過程中幾乎所有對譯者具備支配作用的人或組織都被視為“贊助人”。正是由于其理論核心概念的模糊性和發(fā)散性,當前翻譯研究界在使用其理論研究翻譯制約因素的時候,得出翻譯中的改寫行為“是贊助人和意識形態(tài)合力作用下的結果”以后,翻譯研究便戛然而止,很難獲得更深層次的突破。
筆者認為,在譯作的出版前后存在兩股不可忽略的力量,一方是選擇并資助譯者的委托方,另一方則是審查并出版譯作的出版方。委托方相當于勒菲弗爾筆下的“贊助人”,雖然有些出版方也會直接委托譯者翻譯,充當“贊助人”的角色。但在許多情況下,出版方是獨立于委托方之外的實體,出于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筆者建議將兩者視為相對獨立的力量,分別加以研究。
委托方委托譯者翻譯意味著一定的經濟付出,自然有著其特定的經濟或政治目的。無論為了實現何種翻譯目的,委托方都會和譯者簽訂書面或口頭的協議,對翻譯作品提出一定的要求,但這樣的要求一般都是提綱挈領式的,是對譯作的整體要求,相當于社會學概念中的“產品規(guī)范”(product norms)。而委托方往往自身不懂翻譯(自譯除外),因而翻譯過程中那些具體化的“過程規(guī)范”(process norms)則是先由譯者自行把握,最后由權威人士審核。通常來說,委托方對于名氣較大的譯者相對“信任”,提出的要求相對寬泛;而對于名氣不大的譯者則相對“懷疑”,提出的要求相對嚴苛。無論如何,委托方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必然盡可能選擇與知名譯者合作,從這一點來看,委托方的要求對于他們“信任”的譯者雖有制約,但這種制約是外部的、婉轉的、有限的。
2.出版方與第三方
出版方對翻譯活動的影響相對委托方而言顯得更為直接和具體。一般而言,出版方會安排編輯負責對譯者初稿內容進行審查。由于編輯是出版工作的直接代理人,他同時負責多部作品的出版與發(fā)行工作,再加上文學譯作篇幅較長,很難親自閱讀整部譯作。此時編輯會委托至少一名第三方權威對譯作初稿進行審閱。這種審閱一般涵蓋語言層面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語言層面涉及用詞是否準確?表達是否得當?譯作的美學標準能否提高?意識形態(tài)方面則涉及政治、宗教和價值觀等一系列因素。權威專家會通讀譯作,必要時,還需要譯者提供原作。審閱后,第三方權威會將自己對譯作的意見向編輯反饋或直接與譯者溝通,這一階段會酌情對譯稿提出修改、補充或刪減等意見,譯者通常會予以配合。一般說來,能有資格接受委托的譯者大多學識淵博、經驗豐富且態(tài)度認真,其譯稿幾經修改,送達專家權威的時候大多問題較少。這一階段,譯作雖然會歷經變化,但這種變化是柔和的、漸進的,并不會導致譯作面目全非。

圖S6:組織對翻譯過程的監(jiān)督
(五)外部制約:來自社會
1.經濟利益
翻譯是一種目的性行為。一般來說,在和平時期,委托方希望通過引入外國文學作品來斬獲經濟利益。譯作賣得越好,出版冊數越多,走紅時間越長,委托方自然斬獲更多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譯作的成功也提高了譯者的聲望和身價,為下一輪與經紀人的利益分成談判增加籌碼,這實質上是一種雙贏的關系。
為了確保經濟利益的實現,委托方會精心物色譯者。一般說來,那些在翻譯界久負盛名的譯者憑借其豐富的知識、經驗以及影響力,相比名不見經傳的譯者更有可能翻譯出成功的譯作。因此,聘請知名譯者從事翻譯工作雖然意味著更高的勞動報酬,但對于委托方而言,這意味著“省心”和“放心”。另一方面,出于對翻譯倫理和自身形象的考慮,譯者的翻譯宗旨基本圍繞翻譯出優(yōu)質的譯本,他們會非常慎重地對待譯本,盡可能地還原原作的文學價值,并且憑借自身的文學修養(yǎng),在遣詞造句方面反復斟酌,既要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又要確保譯作的整體語言水準高于普通讀者的審美預期。在權衡的過程之中,譯者一般不會對原作的意義進行太大的歪曲或改變,必要時只是換用說法,改變原作的句式結構或表達順序,并對譯作適當潤飾,確保譯作應有的感染力。
經濟利益的驅使固然可能導致譯作與原作之間出現背離,但這種背離是有限的并且可控的。任何具備健康的翻譯倫理觀念的譯者都很難忍心粗暴、恣意地對待原作,很難接受貪圖一時的蠅頭小利之后,譯作被翻譯研究者從塵封的書柜中翻出,橫加指責,最終身敗名裂這樣的慘淡前景。因此,經濟利益對于翻譯活動的制約雖然客觀存在,但這樣的影響同樣是外部的、間接的,也是有限的。
2.政治利益
在某個國家或地區(qū)出現政治運動或者意識形態(tài)轉型的時候,外國文學作品因為比純粹的政治作品委婉許多,其中蘊含的某些迎合國內政治勢力的思想往往更容易披上合理化的外衣,通過翻譯進入目標語語境。這時候的委托方一般是某種形式的政府或者其他政治勢力,他們最關心的既不是原作的文學功能,也不是翻譯之后可能帶來的經濟收益,而是外國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政治思想或文化特征,寄希望于通過引入陌生的政治思想、生活方式、價值體系來改良本國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在這種翻譯宗旨的指引下,翻譯發(fā)起人會默許甚至直接要求譯者刪改原作,保留甚至大肆渲染其希望介紹的內容,而對于那些他們不關心的內容,則擔心它們喧賓奪主,大多要求譯者刪減。因而,當政治利益和文學價值被硬生生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原作的文學價值便成了掩護政治思想的“特洛伊木馬”。政治利益驅使下的譯作一般背離原作較多,中國清末民初時期出現的大量譯自國外的“政治小說”便是很好的例證。
3.文化環(huán)境
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對文化所作的定義中說,“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種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整體”[11]1。不同的國家由于在地緣、歷史等方面存在差異,沉淀下來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思想意識也不盡相同,這些差異最終也會滲透在文學作品的字里行間,制約著譯者的翻譯抉擇。
當前的翻譯研究界對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探討得較為深入,但也存在一些認識上的誤區(qū)。比如有不少論者夸大文化的制約作用,秉持卡撒格蘭德(Casgrand)觀點“譯者事實上不是在翻譯語言,而是在翻譯文化”[12]338的譯者大有人在。這樣的論點有失偏頗。筆者認為:多數作者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并不能預見作品可能會被譯成其他文字,作品中涉及文化因素的描寫大多是為了讓作品更為飽滿,更加貼近生活,而非刻意描繪以傳播本國文化,渲染文化強勢,推行文化殖民。因而,在文學翻譯中,來自文化方面的制約大多呈現零星狀、無規(guī)律地分布在譯文中,并不會抱團出現,很難對翻譯過程產生全局性、決定性的影響。而且,隨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以及人們對異域文化接受程度的逐漸提高,文化空白和文化差異構成的陰影區(qū)域日益受到擠壓,文化對翻譯的制約作用也因此顯得越來越微弱,這也或多或少地解釋了共時背景下的文學翻譯要比歷時背景下的文學翻譯顯得相對容易的原因。
結語
文學翻譯是一種受諸多因素制約的復雜活動,來自翻譯系統不同層面、不同距離、不同方向的制約因素將譯者層層包裹,通過對譯者施加壓力,參與翻譯選擇的過程,并最終影響著譯作的風貌。相對而言,在搭建的翻譯系統模型中,距離譯者距離越近的因素(包括譯者本身)對于翻譯活動的制約作用越明顯;反之,距離譯者距離越遠的因素對翻譯的制約作用越趨于緩和。換句話說,來自看似封閉的微系統中的因素對于翻譯活動的制約作用最為直接和明顯,中系統的制約次之,來自大系統的制約相對最弱。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翻譯研究全盤“文化轉向”或者“社會轉向”的片面性。文學翻譯研究本來就應該是綜合全面的研究,其特殊性決定了它需要涉及來自語言、文學、美學、文化、社會等領域的眾多因素,需要得到系統、綜合、全面的研究。研究中考察的因素越多,研究得越全面,無疑可以深化學界對文學翻譯活動的認識。可喜的是,歷經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和社會轉向等歷次轉向之后,翻譯研究領域最終走向了最大化,為全面研究文學翻譯中的制約因素提供了可能。
[1]Hermans Theo.Translation between Poetics and Ideology[J].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1994(3).
[2]Lefevere&Bassnett Constructing Culture: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Cleven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
[3]孫藝風.視角闡釋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4]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5]Chesterman 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2001(2).
[6]陳淑英.英語修辭與翻譯[M].北京:北京郵電學院出版社,1990.
[7]朱立元.接受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辜正坤.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J].中國翻譯,2005 (1).
[9]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10]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C].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
[11]泰勒E.B.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12]Casgrand J.R.The Ends of Transl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1954(4).
I0-05
A
1004-342(2014)05-64-08
2014-04-18
本文為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中的制約因素研究”(批準號:13BWW009)和2012年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制約因素研究”(批準號:12WWD0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徐修鴻(1979-),男,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鄧笛(1964-),男,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