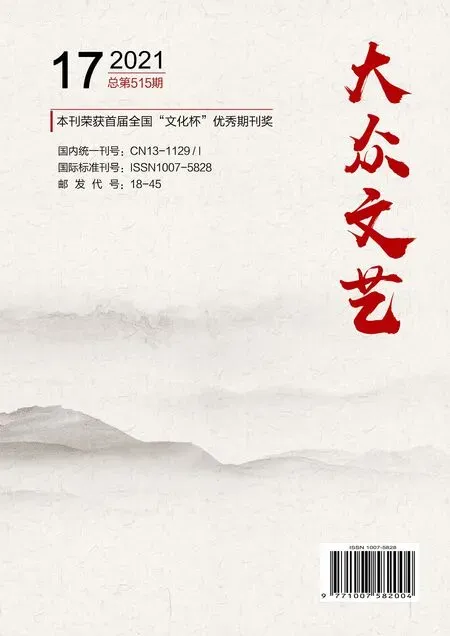瑪琳·杜馬斯作品初探
(華中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430079)
一、瑪琳?杜馬斯簡介
1953年,瑪琳?杜馬斯生于南非開普敦,成長于城鄉結合部Kuils River地區的家族葡萄園里。作為70年代早期開普敦大學麥克里斯藝術學院的一名學生,起初,杜馬斯用10年時間專注于概念論與藝術理論。然而是攝影,特別是戴安?阿勃斯的攝影作品本來將在這一時期對這位年輕藝術家產生最大的影響,將她引入“影像的負擔”以及表現人類形式的復雜性。由于接受了荷蘭藝術家經營的藝術工作機構提供的獎學金,杜馬斯于1976年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繼續生活并創作。在這形成自我風格的幾年間,杜馬斯用剪切過的圖片、章節,以及姿勢性繪畫運動的方式,探索了影像與拼貼畫文字之間的關系。
二、杜馬斯的作品特征
杜馬斯的畫風趨向于強烈的表現主義精神,常被稱為“睿智的表現派藝術家”。她通常使用粗重的線條、簡潔的筆法、幾近原色的紅、橙、藍,以及對比強烈的黑與白描繪人物的面孔和厚重的人體姿態,而且畫得很薄、極少修飾,打破所有觀念的禁忌,模糊了再現與抽象、油畫與素描之間的界線。她用對比和模糊的方式表現人物心理和精神狀態的不平衡,質疑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視覺和心理的定式,挑戰普遍性的價值體系。
《朱莉》是一個無形的肖像畫,在極端的特寫下, 只有模特的眼睛和嘴唇都完全呈現誘惑和性的屬性。作品的其余部分是由肥胖的肉質粉紅,暗示罪惡,暴力和普世女性氣質的抹殺。表現和抽象之間的對比拉大了心理差距,其中的道德,一般女性特征和社會習俗受到了質疑。“我不具備多大的寫實功力,我從來沒有關心過任何解剖學的概念。在這方面,我喜歡與孩子們做的一樣。什么是體驗?最重要的被認為是真實的,而不是論實際意象。對我來說,特寫是擺脫不相關的背景信息的方法,并通過使面部元素那么大的部分,增加了關于相框的抽象感。”(瑪琳·杜馬斯,1992)
杜馬斯經常發現靈感,報紙和雜志的圖片都是她的巨大的視覺檔案。她認為,每一天,我們都受到攝影圖像層出不窮的影響,我們到底如何看待對方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是她作品的重要議題。杜馬斯通過揭示這些圖像的心理,從社會和政治方面解決了這個視覺猛攻。她的素描和油畫產生巨大的直接和表現力,在她的視覺作品中,杜馬斯反映了當代水墨書畫界的新領域,新趨向。
個人與歷史的碰撞在杜馬斯的畫像《瑪麗蓮之死》(2008年)中得到體現,杜馬斯反映著臭名昭著的形象瑪麗蓮?夢露,揭示了一段超越其原始來源的視覺體驗,作品采用尸檢照片的意義層所做。白色,藍色,綠色,灰色突出顯示拍攝對象的臉部斑點涂的筆觸。畫作的小尺寸和細膩的渲染使得它成為不朽的肖像畫。名人,追求轟動效應,而女演員的個人敘事的神秘的概念卻受到質疑。在《朝圣者》(2006年)中,杜馬斯在轉移拉登的惡名,她的圖像拉登,其相對和平的眼睛,溫和的笑容與媒體的典型寫照產生了極大反差。杜馬斯筆下的公眾形象和歷史意義的主題,留給我們的是重新對政治和身份的批判與審視。她說,她的作品其實可以被更好地理解。在我們觀看影像原件時,鏡像有時太令人震驚,而她能抓住這些影像的核心之處。
杜馬斯也是一個狂熱的教育家,她認為:“教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我教[學生]東西,而且還因為我們有一個對話,你看你真正想要的。你發現的東西出來。我仍然相信在蘇格拉底的對話。藝術是真實的,你從被周圍的人身上可以學習東西。”
2005年2月,倫敦佳士得拍賣行,她的作品《教師》橫向組畫像,從她自己的童年變成胖婦人的畫作,出售334萬美元,這使她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貴的女藝術家。她的狀態保持了一年,直到路易斯?布爾喬亞出售400萬美元雕塑,抓獲女畫家世界冠軍。
三、杜馬斯作品中的表現與影響
馬蒂斯認為:“我首先所企圖(繪畫)達到的就是表現……尋找忠實臨寫以外的表現”。表現主義不但是一種藝術特征,也探詢了藝術的本質,它否認技巧,反對客觀再現。杜馬斯符合表現主義的特征,但也不局限與此。她在作品中更加注重了畫面主人公精神層面的刻畫,在她的作品中我們或可看到柴姆?蘇丁的油畫影響,而這種源流可以追溯到荷蘭的凡?高,那些充滿充滿神經質表情的自畫像可以看作是一種精神表現的最初起源。
瑪琳?杜馬斯的作品強調人體的物理現實和心理價值,杜馬斯傾向于描繪她的人民處在生命的周期的極端邊緣時的狀態,從出生到死亡,與不斷強調代表性的西方藝術中的經典模式,如裸體或陪葬的畫像有別。她遵從內心的作品,也逾越這些傳統的歷史先例,杜馬斯使用的人物形象,以批判種族,性別,社會身份等議題,成為展現當代思想的一種手段。其實杜馬斯并不在乎主題的表達,注重的是人物情緒的流露. 她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在從不同的角度凝視著我們, 畫面中人物對觀眾堅定的凝視暗示著他們的生存狀態挑戰了我們的道德觀和社會意識形態, 映射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脆弱和壓抑。
縱觀杜瑪斯的繪畫藝術,一方面是積極地利用影像的各種因素;一方面卻表現出對影像的深切懷疑。兩種態度并存于同一畫面反映出藝術家對攝影圖像既依賴又反抗的復雜情感。畫家借用攝影的觀看方式來建構繪畫與當下現實的關系,又用繪畫的表述方式來質疑攝影所復制的現實。這種對攝影圖像的復雜情感和關系當然可以理解為圖像時代的邏輯必然,但在這被動接受攝影圖像的影響與主動利用攝影圖像之間,在藝術觀念上是有著天壤之別,前者意味著屈從,后者預示著超越。
參考文獻:
[1]魏尚河著.《我的美術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
[2]林曰惠著.《憂慮與希望—解讀畫家瑪琳?杜馬斯及其作品》.原載于《美術觀察》2005(5).
[3]《來自內心:瑪琳?杜馬斯》 載于《當代藝術家》總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