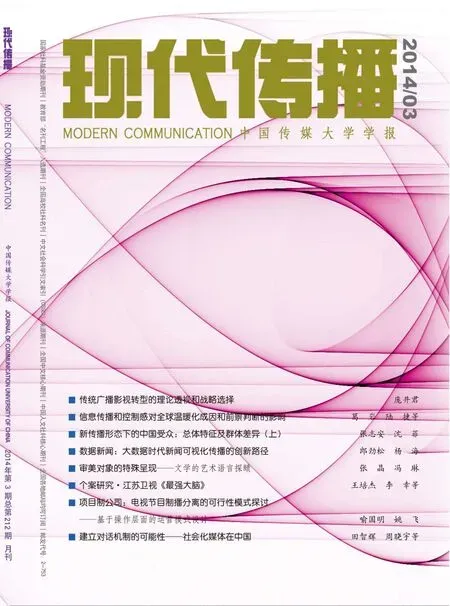2034年的傳媒大學(下)
■ 朱光烈
2034年的傳媒大學(下)
■ 朱光烈
(續前期)
專業主義教育批判
1.愛因斯坦說,專業主義教育訓練出來的是一條很有用的狗
生活在20世紀上半葉的大思想家愛因斯坦在《目標》一文中研究了科學與宗教的關系,認為猶太教和基督教為我們的志向和價值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和目標。科學所能告訴我們的不過是各種事實之間是怎樣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是認識客觀世界“是什么”的問題,但并不能打開通向“應當是什么”的大門,不能導出我們人類所向往的目標。只是憑著思考我們還領會不到那些終極的和基本的目的。弄清這些基本目的和基本價值,并且使它們在個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建立起來,這正是宗教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所必須履行的最重要的職能。“如果人們從它的宗教形式中把這個目標抽了出來,而只看它純粹屬于人性的一面,那么,也許可以把它敘述為:個人的自由而有責任心的發展,使它得以在為全人類的服務中自由地、愉快地貢獻他的力量”。“個人的崇高的天命是服務”。“應當幫助青年人在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中成長,使他感到這些基本原則對他來說就好像他所呼吸的空氣一樣。”①
在《倫理教育的需要》一文里,愛因斯坦則說:“我確實相信:在我們的教育中,往往只是為著使用和實際的目的,過分強調單純智育的態度,已經直接導致對倫理價值的損害。我想得比較多的還不是技術進步使人類所直接面臨的危險,而是“務實”的思想習慣所造成的人類相互體諒的窒息,這種思想習慣好像致命的嚴霜一樣壓在人類的關系之上。”②在《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一文里,愛因斯坦極其反對專業教育,他寫道:
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許良英、劉明注:這里的價值即社會倫理準則)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為了獲得對別人和集體的適當關系,他必須學習去了解人們的動機、他們的幻想和他們的疾苦。
正是實用的專業主義阻斷了人文主義的發展鏈條,那么人文主義應當如何去培育呢?愛因斯坦繼續寫道:
這些寶貴的東西,是通過同教育者親身接觸,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過教科書傳給年輕的一代的。……當我把“人文科學”作為重要的東西推薦給大家的時候,我心里想的就是這個,而不是歷史和哲學領域里十分枯燥的專門知識。
過分強調競爭制度,以及依據直接用途而過早專門化,這就會扼殺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據的那種精神。③
愛因斯坦這里的論述,恰恰與上述社會建構主義學習范型以及行為教育的主張相一致。其實,這類經驗與教育思想并不是源于愛因斯坦的,而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工業社會發展起來的專業主義教育把它阻斷了而已。而這個時代的愛因斯坦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尖銳地批評專業主義培養出來的只是一只訓練有素的狗或者好使的機器,他使這些思想更為深刻。但是目前引用出這樣的話來,一定會使許多專業主義教育的奉行者感到是發了瘋了。
2.專業主義扼殺創造性
所謂專業主義就是指那些眼光只落在專業之內的狹隘經驗學習理念。在自然科學經驗學習領域中,專業主義就是科學主義,它有一套扎實的基礎理論和嚴密的邏輯,但是它走不出科學的領域,把科學當成唯一的、排它的真理標準,拒絕與人文主義的整合,也不承認文化素養的意義。愛因斯坦把專業主義教育訓練出來的人比做狗,實際上是工業社會對于人的異化結果,這一點也不奇怪。另一方面愛因斯坦也說過,“我想的比較多的還不是技術進步使人類所直接面臨的危險,而是‘務實'的思想習慣所造成的人類相互體諒的窒息,這種思想習慣好像致命的嚴霜一樣壓在人類的關系之上。”他還曾經表示過,過多的知識傳授只能使學習者處于淺薄狀態。愛因斯坦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專業教育,他反對的主要是由于務實的思想所帶來的對于文化素養的遺棄。
現行的大量高等教育中的專業教育以在社會上尋找職業為目標,那里不重視基礎知識和學科邏輯建設,所看重的只是專業技能的訓練、專業直接有用的知識和技術以及狹隘的、可以直接用于操作的聯系實際的理論,所有這些都成為不證自明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那些專業主義者看來,當下無法即刻使用的一切學問、知識和理論,都是該死的牢什子,都是瞎胡鬧。他們更是不知文化素養為何物。
專業主義教育和學習,特別是狹隘的專業訓練和學習,所帶來的是封閉的心靈,心被封閉在專業牢籠里,如同黑暗的牢房一樣,沒有一點活氣。莊子說:“哀莫大于心死”,不過,許多人對此習以為常,并不能察覺這種悲哀,死而不知其死,這是悲哀中的悲哀。這里當然不會有創造之花的開放,事事急功近利,很難避免“上手快而后勁不足”的命運。
現代社會的學科越來越多、越來越窄,這種發展趨勢使現代人容易忘記且難以把握基本的理論和廣博的知識。林語堂在《老子的智慧》一書中寫道:遠古的學者追求的是道之根本,而后來的諸子百家“各走極端,執迷不悟”,“所以圣人明王的大道,幽暗而不能彰明,閉塞而不能光大,天下人都自以為自己所偏好的見解就是大道。”17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在他的《思想錄》一書里曾經說過:“凡事略知一二,勝于全知一事”。帕斯卡爾在《思想錄》里還極其推崇“有教養的人”,這種人“不是數學家,不是傳教士,也不是雄辯家,而是有教養的人,我唯一喜歡這種全面性”。生活在20世紀的法國學者路易·多洛說:“20世紀的科學革命與當前的文化聯系起來,正提出如下的基本問題:關鍵不是考慮自己要認識什么,而是不能對什么全然無知,否則就不能自認為是一個有文化素養的人了”。④對于一件事物來說,“略知一二”難于與“全面性”有緣,但是對于認識整個世界來說,在不同領域的“凡事略知一二”大致說來能夠從不同側面和層次去觀察世界,具有相對意義的全面性,以求達到破除“全知一事”的片面性局限。人的能力有限,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
人的精神、人的心靈是極容易被什么東西蒙蔽和禁錮的。這種蒙蔽和禁錮頭腦的東西被稱為“所知障”,即你所知道的東西對于你進一步認識事物所形成的障礙,你難于跨越這個障礙,創造難于實現。當我們對什么東西比較熟悉、比較習慣的時候,譬如做學問接受某種理論或觀點的時候,特別是形成了某種體系的時候,或者業務形成若干經驗的時候,不可忘記要隨時跳出這些東西給你的心靈設下的“所知障”,跳在圈子外面反觀它,懷疑它,批判它。專業主義者充滿著專業的所知障,以為除了專業知識其他的都是沒有用的勞什子。創造力的絕對要求是必須破除各種所知障。中國有兩句話值得我們注意:一句是“隔行如隔山”,我們必須熟悉專業知識和技巧,不然就無法從事專業工作;另一句話是“當局者迷”,所以要進行反觀、懷疑、批判,使頭腦隨時隨地處在與外部世界相適應的不斷發展變化的最佳狀態之中,強調把任何事物、任何知識、任何經驗都看成是一種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更需要我們不斷地完善它,盡量不使它成為“所知障”。只有隨時隨地破除“所知障”,才能為智慧和創造力的發揮開辟道路,而破除“所知障”的唯一途徑是提高文化素養。提高文化素養的第一步就是走向專業的邊緣,廣泛涉獵不同學科知識以及獲取不同領域的經驗,“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幅對聯充分表現了中國的智慧,它把創造的立足點擴展到整個世界和整個人生,強調的正是提高文化素養的決定意義。
我的“烏托邦”?
1.讓教育回歸本位
生活在19世紀的英國宗教家和教育家約翰·亨利曾經在當時英國的天主教大學發表過演說,在演說里他把大學分成兩類,一類是不督察學習的,修滿若干課程并考試及格的任何人都授予學位;另一類則既無教授亦無考試,只是把一定數量的年輕人組織起來集體學習。青年人心胸開闊,富于同情心、善于觀察,來到一起自由密切交往,即使沒有人教育他們,他們也必定互相學習;所有人的談話,對每個人來說,就是一系列講座課,講述他們自己逐日習得新概念和新觀點、新的思想以及判斷事物和決定行動的各種不同原則。亨利表示,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一類大學,它是一種真正的教育。
約翰·亨利的演說發表于近一百六十前,但是,它并不是奇談怪論,以學生相互學習和自由學習為主本來就是遠古時代的學校學習模式,當時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的本初模式,體現出教育的根本特征——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稍晚一些的教育,譬如中國古代的孔子和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開辦的教育,也是以學生相互討論為主的。工業社會的到來,由于社會實際工作和學科的分化越來越細,越來越多,以及知識總量增多的速度越來越快,教育越來越走向以教師講課為主和應試教育以及專業主義教育的階段。世紀之交的先進教育理論和學校教育已經出現了復歸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約翰·亨利理想的趨勢。現在看來,我們還不能在所有的專業領域實行這種教育模式,但是,像新聞專業這樣的專業,由于它不具有很難習得的操作技巧,而相應的實際工作又需要與社會廣泛的接觸,采用這種文化主義的教育(學習)改革,我相信是合適的。
據筆者所知,有些西方國家沒有師范教育,任何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都可以當教師,但是需要經過相應的一段時間的專門訓練。我的設想實際上很像是這種培養教師的路數。這樣做的好處之一是利用了其他專業的優勢,尤其是基礎比較厚實的專業的優勢,以克服長期以來用人單位反映的新聞類專業教育后勁不足的痼疾。
筆者也不主張學生靠漫無邊際的討論了事,在現實生活中,我曾經遇到過有的青年人思想極為極端,而且很難改變,因此教師的引導很重要,不過這樣的教師一定是高水平的。
筆者并不主張一切專業訓練都應當下馬,專業性訓練依然應當辦下去。但是,我建議把教育與專業訓練分開來。教育的目標只是培育文化素養,培育人;專業訓練的內容只是實際工作所需要的操作技能。未來的學校,特別是未來的大學所從事的只是教育,而不再負責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原則上由各個用人機構自己負責,或由社區統一負責。
終身教育的出現是20世紀的一件大事,它宣告青少年時代學習然后終生享用學習成果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隨著知識爆炸時代的到來,終身教育時代也接踵而至。終身教育實際上是終身學習。我們現在或許還沒有意識到終身學習出現的重大意義。在傳統教育事業中,學前教育是從小學到大學教育全過程的準備。終身學習的出現將要改寫這種格局,重要的不再是學前教育作為教育全過程的準備,而是學校教育(包括從傳統的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到大學教育)都是終身學習的基礎準備。在這個階段,需要打好知識的基礎,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素養的培育、人的培育,養成創造性和獲得創新能力。學校教育必須以學習為中心。教育必須開倒車,教育至此終結,即以應試和專業技能為上的現代教育的終結。這種終結是對于教育的提純和回歸。這種新的教育實際上就是學習,一切外在的教育(外部灌輸的教育)都必須服務于內在的學習,學習是永遠的。這種轉折的根基深深地扎在當前正在興起的信息社會之中,扎在電腦網絡所構成的虛擬世界之中。這個虛擬世界不僅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學習機會,而且其全世界的交流機會、瞬息萬變的信息刺激正在沖垮舊的教育模式。
教育的本質是人心的培養,是人的塑造。隨著物質主義文明的發展,特別是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到來之后,教育被改造成就業的前期準備,成為為它者服務的工具,被嚴重物化。在當今大學里,專業設置多如牛毛,在專業主義教育里面,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成為不二的霸主。專業主義教育美其名曰為社會建設服務、為學生就業服務。教育的這種異化如果不能迅速扭轉,使其回歸教育的本質,人類文明毫無希望。因此必須把教育與職業培訓區別開來,一切強加在教育身上的東西都必須要被扔到九霄云外。職業培訓當然仍然需要,但是要在教育之外另起爐灶,讓教育回歸本身。“教育為什么什么服務”這樣的信條都是教育異化的堂皇的說辭,教育只為一個目標服務,那就是人心的培養,人自由而全面發展,達到物我統一的、審美的人生境界。這個目標達到了,整個教育的社會目標也就達到了。
2.思想家搖籃:未來大學的神圣身份
人總是生活在各種壓力之下,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人而不再是動物,是因為人能夠自覺地應對這些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人不斷地思考,從而形成了人獨有的思想。迄今為止的文明經驗告訴我們,面對著這些壓力,人類所思考的主要問題除了富裕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希望過上自由、平等、公正的生活。來自于自然和社會的壓力是永遠存在的,因此自由、平等、公正作為一種理念大概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它只是一個不斷展開的歷史進程,是沒有盡期的,于是思想探索和發展也就沒有了盡期。正是因為這種特質思想賦予了人類真正的生存意義,蘇格拉底說過:“沒有思考過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早在1970年人類社會剛剛進入信息社會的時候,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學著作《未來的沖擊》一書里的《引言》寫道,信息社會正經歷有史以來最為瞬息萬變的境遇,來勢之猛實已到了足以潰決廟堂、否定價值、毀拔根基的地步。時代發展之巨、之快使人們普遍感到迷茫,風靡一時的后現代主義中的極端相對主義大概就是這種狀況的反應,在那里,整個世界都陷入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不可知的矛盾之中。但是急劇而重大的變革又特別需要新的思想及思想家的出現。在我們剛剛進入這個世紀之交的時候,西方的一些機構評出了千年最有影響的十大思想家,包括托馬斯·阿奎那、笛卡爾、牛頓、康德、馬克思、麥克斯韋、達爾文和愛因斯坦等,被廣泛報道。那個時候筆者沒有看到別的千年大家的評選的報道,譬如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和發明家等,這種把思想家高高地凸顯了出來的現象,表明人類目前是多么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思想家。
氣候變暖以及各種環境的威脅已經引起世界范圍內的有識之士的廣泛憂慮,人類還能不能在地球上持續生存下去早以已經成為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霍金曾一再說過,人類在地球上活不過21世紀末。當前人類最大的危險是物質主義的瘋狂肆虐,人類的生存危機非但沒有減弱,反而不斷日趨嚴重。最近一些年來,發達國家的許多研究機構利用各種方法對人類未來進行了許多研究,發現人類文明極大的、根本的革命很快就會到來,世界在“今后20年將發生‘巨大變化'”,“我們將在2030年遭遇一場‘全面風暴'”,“激進”“巨變”即將來臨。“今后40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段時間”。最近的重大研究成果要算是2012年12月10日美國情報機構委員會組織發表的報告,報告稱,在今后18年里將爆發劇烈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關鍵的節點上,這可能會通往‘截然不同的未來'”。如果這些預測大致是正確的,則文明大革命爆發的時間離我們很近了,早則十七八年,晚則二十七八年。
根據筆者的研究,這個“截然不同的未來”應當是文化主義文明。人類以往的文明是以物質力量為主導的,信息社會正在把文明推向以文化力量為主導的發展階段。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一次大革命(這些問題這里不能展開討論)。在新的文明里,必將涌現出新的發展模式和新的觀念,需要很多新的偉大的思想家。
托夫勒曾經說過,信息社會是以大學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大學一沒有政府的施政權力,二沒有企業的物質力量,那以什么力量來組織社會?沒有別的可能性,大學只能通過新的思想探索從而引導社會的發展來組織社會。于是筆者相信,在信息社會以及未來的文明里,思想的探索便成為了大學的真正任務,思想家搖籃便成為大學的真正身份。
3.2034年的我的母校
這里已不再是人山人海的,為數不多的人圍坐在一起,或相約散步,討論著學術和思想問題,爭論激烈,這里是2034年的定福莊傳媒大學校區;這里是人山人海,數不清的有志之士聚攏在這里,同樣討論著學術和思想問題,爭論激烈,這是2034年網上的虛擬的傳媒大學。隨著整個世界和整個中國一起起舞,從2014年到2034年間,傳媒大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
從廣播學院到傳媒大學,長期辦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在2034年之前它選擇了優勢學科并根據時代的巨變對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主攻思想家的培養。
文科的專業教育并沒有扔掉,但是堅決地把它與思想家培養分離開來,課堂教學為主改變成實習教學為主,目標只是學習專業技能解決就業問題,大多數教師來自于媒介實際工作崗位,自己的教師主要進行組織工作和輔導教學。在20世紀60年代這所學校的新聞系推出過社會知識課和政策講座課,就是這樣實施教學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的是后來這些課程都沒有繼續開下去。這種專業教育大大壓縮了時間,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只有少數教室還是老樣子,大量的座椅和一個講臺;大多數的教室被隔成了許多小房間,里面有點像今天飯館里的包間,或者小小的會議室,宿舍大多數也改造成這個樣子。在這些小房間里總是有許多人討論著學術和思想問題。
到這里來的學生是虛擬世界里的傳媒大學學生中的佼佼者,酷愛思想的探討。在虛擬大學里的討論雖然已經有面對面的感覺,但還總是感到有些隔膜,一些同學久而久之就萌生了到定福莊這個實體的大學里會會老師和同學的想法。
這里的老師很少,他們在社會上都有許多兼職,有些在社會的思想庫里兼職,其實學校里也是個思想庫,思想庫都是自發形成的。教師們的興趣很廣泛,愛好頗多。他們很少登上講臺講課,而是先給同學提出問題,開列書目,請同學們閱讀,然后再與大家一起討論。討論的結尾一般都是開放性的,沒有唯一的結論。
校園里可以經常看到這樣兩條語錄:
人是會思想的蘆葦。——卡西爾
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世界范圍內的最大量的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馬克思
信息社會是由大學為中心組織起來的。——托夫勒
這些語錄在虛擬的傳媒大學里也能看到。
在虛擬的校園里,你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曾經的廣播學院和傳媒大學,那座灰色的五層樓房,那所人流如海的和誰也說不清楚有多少專業和研究機構的五光十色的曾經的傳媒大學,2034年的師生們并不難理解那座灰樓,但是他們很難理解曾經的傳媒大學。在2034年的建校80周年之際,也許有幾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在校園里一邊艱難地走著,一邊搖著頭說:
“連課都不上,都在侃大山,還算是大學嗎?”
“我的老學兄,時代變了。”
4.烏托邦?
巨大的規模,金字塔式的科層制結構是工業社會的典型結構。信息社會正在向著小型化迅速離散。我們正處于急劇的空前的文明大變革的時代,未來的文明將根本不同于以往文明,人們必須而且完全可能從物質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不斷地探討和創造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精神創造之上將成為每一個人的必需。思想庫將在社會里普遍建立,而大學將是最重要的思想庫基地。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到2020年中國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決定性的成果。這次會議展現出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這樣的可能性:在2030年這個人類文明大革命的“歷史關鍵的節點”到來的時候,使我們這個目前還相對落后的國家以最大的可能接近于世界發展的先進潮流。任務非常艱巨,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領導人非凡的勇氣和智慧、能力,我們不知道他們可能遭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挫折,但是考慮到整個世界即將爆發空前的大革命,此時此刻筆者懷有偉大的希望。
于是我便想象到了2034年的傳媒大學的如上,景象2034年是我的母校建校80周年,美國情報機構所指出的“截然不同的未來”的“歷史關鍵的節點”定在2030年,80周年是在這個“歷史關鍵的節點”之后的第4年。如果以上這個預測以及其他類似的預測能夠基本實現的話,本文所描述的未來母校發展目標當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的烏托邦,而是一個有理想的有一定根據的烏托邦。未來全球的大變革將成為中國超高速發展的極為有力的推動力。這種烏托邦被有的學者稱之為積極的烏托邦,按照美國左派學者華勒斯坦的說法,是一種“有托之鄉”。我想讀者會恥笑我在癡人說夢,這就算是我的“中國夢”吧。
以上的那些關于未來二三十年世界將發生大變局的研究結論大多來自于學界,雖然這些研究是依靠電腦模擬做出的,或許可能仍被認為是烏托邦,但美國情報機構委員會的研究應當是非常講究實際的。
我們面臨的文明空前復雜和瞬息萬變,并即將爆發空前的、疾風暴雨式的大變革。我們已有的經驗來自于以往社會緩慢運行的階段,僅憑我們的經驗來觀察現實和想象未來未必可行,而大型電腦模擬研究被證明可以比較全面地把握這種時代的巨變,對于那種“截然不同的未來”即將到來的預測不可以僅僅當成科幻作品作為飯后茶余的談資了之。
剛剛進入新世紀的時候,傳媒大學提出了要將自身打造成為世界上知名的傳媒大學的發展目標,既如此,就應當超越以往的專業主義追求、操作層面的追求,更必須跳出華而不實“發展”的巢穴,而進入思想探索的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傳媒大學長期以來所處的系統環境、專業特點都使得超越自己特別困難,首先是人們的觀念很難改變。也許2034年的傳媒大學根本就不是這里所說的樣子,甚至完全化為烏有。當然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實現這個烏托邦的任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是一重大創新的過程,如同一切重大創新一樣,必須拿出大勇氣、大智慧來,必然會遭受到種種諷刺、打擊和莫名的磨難,但是只有在這樣的征途上才會有壯麗的風景可以欣賞。
烏托邦,有托之鄉,應然,或然,對于本文可以做出各種不同的解讀。學術寫作無論如何不能完全擺脫內心冥冥中的精神指向,謹以此文祝福母校的未來。(2004—2013.11.20)
(續完)
注釋:
①②③ 愛因斯坦:《目標》,載許良英、劉明編:《愛因斯坦文錄》(中譯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45-46;60頁。
④⑤ [法]路易·多洛:《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頁。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高級編輯)
【責任編輯:張國濤】